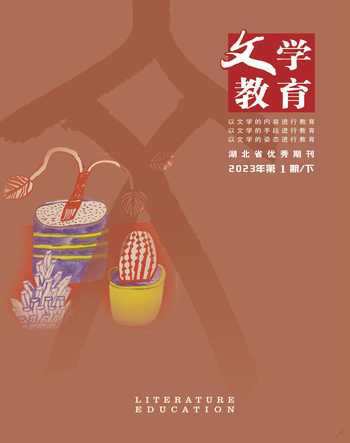苔菲与阿赫玛托娃笔下的同情
王文欣
内容摘要:俄罗斯白银时代的特殊背景,使女性作家群体得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其中极具代表性的有“俄国幽默‘王后”苔菲,以及“俄国诗歌的‘月亮”阿赫玛托娃。似乎这两者之间看不到任何共通之处:苔菲自称契诃夫学派的学生,阿赫玛托娃则高擎“反契诃夫”的大旗;苔菲以笑抗恶,书写刺贪刺虐的幽默小说,而阿赫玛托娃这位“哀泣的缪斯”用泪水铺成抒情诗歌。但也正是在这样极端的对立中,发现了与“同情”理论中“心理距离”“物我合一”之争相互阐释的可能。
关键词:苔菲 阿赫玛托娃 同情 心理距离 物我合一
俄罗斯白银时代可以说是“最坏的时代”,也可以被认为是“最好的时代”。正是在这个动乱的时代,一片废墟的俄罗斯土地上诞生了一大批思想家,作家,诗人,例如舍斯托夫,别尔嘉耶夫,索洛古勃等等。甚至俄罗斯女性作家大量登上文坛,从俄国传统男性创作笔下的“塔季扬娜”一跃成为文学界的“缪斯”。也正是这个时代孕育出了“俄国幽默‘王后”苔菲,以及“俄国诗歌的‘月亮”阿赫玛托娃。俄罗斯学界及中国学界鲜有人对这两者进行对照分析,因为苔菲与阿赫玛托娃看起来似乎是终极的两端:苔菲被迫逃亡海外,从侨民作家视角出发,甚至在20世纪40年代,斯大林盛情邀请苔菲回国时仍选择远离故土,坚持做一个“旁观者”,而阿赫玛托娃始终坚定“与人民站在一起”,尽管她不断被打击,被友人劝说离开俄罗斯,这位俄国诗歌的“月亮”还是选择留下来,选择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虽在如此极端的不同中,两者用不同的方式却都传达了对俄罗斯人民的“同情”,理解两位作家的作品与“心理距离”、“物我合一”的“同情”理论相互阐发的可能。
一.“心理距离”与“物我合一”之爭
同情这一概念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有无数的理论家对它进行解读,这些阐释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心理距离”说与“物我合一”说。
同情这一概念来源已久,最早可以推到亚里士多德《诗学》里对悲剧的作用阐释。之后的18世纪,医学心理学兴起,把弦的振动类比于人的神经活动的说法影响了莱辛的对“同情”的看法:“莱辛用类似于两个字符串的方式说明了外部(或用虚构表示的)情感与怜悯的情感之间的关系,类似于两个字符串,第一个字符串是“弹拨(gezupft)”,第二个字符串是“不弹拨”,加入振动(mitbeben)。”[1]莱辛把人看成“振动的身体”,强调了人在观看悲剧的时候,会“进入他人的身体”,也就剥夺了自己的思想,甚至是存在,完全把自己交给表演者,也就是“物我合一”。
我国著名学者朱光潜就在其著作《文艺心理学》里对审美同情中的“物我合一”做出了深入阐述,朱光潜先生认为美感产生的关键就在于“凝神的境界”。凝神之时,欣赏者不但会忘记观赏对象之外的世界,更会忘记自己的存在,这也就是莱辛认为的放弃身体达到“振动”。在纯粹的直觉中我们无法自觉地区分开物与我(莱辛理论中的“演员”与“观众”),也正是对这种区分的忘却才能真正的“凝神”。
在提出审美同情中“物我合一”之后,朱光潜先生笔锋一转开始论述“心理距离”的重要性。而朱光潜先生在他的《文艺心理学》中强调:“艺术家之所以为艺术家,不仅在能感受情绪,而尤在能把所感受的情绪表现出来;他能够表现情绪,就由于能把切身的情绪摆在某种‘距离以外去观照”[2],重视在鉴赏中借助于“心理距离”去除功利性因素而获得的美感体验。
综上所述,同情理论中始终存在着“物我合一”与“心理距离”的争论,批评家们看到了物我两忘达到凝神境界的可能性,又认为在同情过程中理智和反思对成为“旁观者”的重要作用。研究同情理论,实践中这截然相反的极端的确无法统一应用于一者,但或许这种矛盾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绕道而行,变换视角,用这两种“同情”去阐发文学中的一些看似截然相反的现象,而这种“截然相反”又可以反过来印证这二律背反的“同情”理论。
二.“王后”之距离感下的同情——苔菲
二十世纪初,白银时代的俄罗斯许多学者开始重新审视“契诃夫学”,“反契诃夫”之说甚嚣尘上,“高贵”的反对者们集结起来,不断驳斥“过于冷酷”的契诃夫,阿赫玛托娃甚至认为“指责他的世界里没有英雄及受难者,没有深度,没有黑暗,更没有精神高度”[3]。似乎契诃夫冷静的“对灰暗生活表面下‘潜流的深入挖掘”[4]引不起俄国现代主义者的兴趣。但在那个学者纷纷驳斥契诃夫的时代,也有一些“契诃夫学派”忠实的学生逆“潮流”而上,在自己的作品里实践着契诃夫式冷静旁观的魅力。其中就包括俄国幽默小说的“王后”——苔菲。
苔菲的“故事是低调、克制的,叙述者通常说服读者静下心并平缓情绪。”[5]在苔菲的笔下多是因嫉妒破坏朋友姻缘的年轻少女,熟知“暧昧心理学”的情场妇女等等。如此写出女性“阴暗心理”的苔菲,为何会被俄罗斯的妇女们高呼“我们的亲人”?在如此讽刺的小说里,在如此扭曲黑暗的人物形象上,批评家们为何不约而同地看到了“同情”?
这正是苔菲利用的“心理距离”表达出的同情魅力,她看似冷静以至于冷酷的作品中始终传达着一种温情,“笔下的苦痛并不是撕心裂肺、鲜血淋漓的,希望之光依然照耀人间。”[6]苔菲对人性脓包的揭露,是自己站在一定的“心理距离”之外,带着自己的理智与反思,对俄罗斯妇女痛苦的公正旁观下的同情。苔菲的旁观是对于民族劣根性的直击,是作品中的始终在场,是敢于刺破脓包,引发理智的思考,为更好地医治创口。苔菲的代表作《生活和衣领》,讲述了一个“拜物”的故事。奥列奇卡·罗扎娃先前生活简朴,不爱出风头。但生活脱轨往往起于一件小事。罗扎娃在手工场店里看到了一条漂亮的女式衣领,并被它吸引买了下来,之后生活便开始不受控制了,或者说是罗扎娃被衣领控制了,奥列奇卡开始过“衣领的生活”,最后一步步走向破灭。
这一被“物品”控制的主题内容在生活中其实十分普遍,而苔菲也是将其生活中所见记录下来。苔菲的生活就是她创作的源泉,她强调“这些事件几乎每次都是我原原本本从生活中撷取出来的。”[7]而应当指出的是这种对生活的体验和感悟并不是停留在生活的表面,而是对生活的超越,这也就是为什么契诃夫和苔菲的作品书写生活的表面的同时,却能极大地触动读者的心灵。苔菲在专注俄罗斯妇女生活的时候,始终以一个“公正的旁观者”的视角挖掘深度,她拒绝和那些妇女一起“振动”,相反始终带着自己一贯的理智和自我反思去触到生活深海下最隐秘的存在。在《生活与衣领》中,苔菲在叙述过程中冷静地描写了奥列奇卡刚开始被物支配时的痛苦不堪,她甚至向自己的丈夫寻求过帮助,却还是失败了。如此“冒犯”的内容是阿赫玛托娃不会、也无法写出来的,恰恰因为苔菲离得足够远,她才能知道问题的根源在于何处。
在小说的开端,苔菲就利用冷静的“克雷洛夫寓言式”语言起笔,表明了自己似乎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接着苔菲在文中充分利用作者插话和自由的间接引语带来的“距离感”,“对于神经质的人和意志力薄弱的人而言,有一些痛苦,尽管十分之痛,却是不可或缺的”[8],敏锐地抓住了妇女的心理弱点。苔菲的作者插话利用作者插话与自由间接引语造成“距离感”,利用冷静的叙述语言,造成读者的“情感距离”的同时,更注重引导读者自我思考与反省。在小说的结局苔菲放弃了全知全能的视角,放弃了对人物进行而是通过设问,把读者从想象的世界里拉了出来,要求理性的回归:
“‘那衣领哪儿去了?您会问。
‘那我又如何得知呢?我会这样回答,‘它被送到洗衣女工那里了,你去问她吧。
唉!生活!”[9]
短短三句话,苔菲就把自己从上帝的位置上拽了下来,进入了文本本身,她似乎就置身于事件之中,这里就构成了苔菲-叙述者-作品人物-想象读者-真实读者的结构。不同于萨克雷在《名利场》中一如既往的笃定冷静语气,苔菲在最后利用想象读者提出问题,将真实读者的理智拉回现实,如此又通过最后一句“唉!生活!”让人疑惑,是谁在哀叹?那么哀叹的又是什么?换句话说,同情的是什么?同情的只是奥列奇卡,还是同情那些被拽下上帝位置的有着同样经历的读者?可以说苔菲从不将自己的思想强加给读者,而是让读者自己在作品中去渐渐体会,在反思中渐渐升起对小说主人公的同情。作家冒犯式的讽刺能够被公众们接受,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作家通过其叙述手法使读者对其笔下的人物有“心理距离”。苔菲的《生活与衣领》就利用了“心理距离”达到了“善意的冒犯”的效果,而在这背后便是对生活暗流下的妇女们的深切同情。
三.追求物我合一的同情——阿赫玛托娃
与冷静旁观的“王后”不同,阿赫玛托娃同情俄罗斯妇女,是血与泪的同情,是把自己变成“振动的身体”的同情。阿赫玛托娃相信痛苦的可传达性,她用她的作品反驳了苏珊·桑塔格的旁观痛苦理论,她强调的是在同情他人痛苦时消解自己的存在。阿赫瑪托娃拒绝冷静的旁观态度,追求的是与受难的人民的感同身受,她尝试放弃自己的存在,进入俄罗斯妇女的身体,成为他者之“我”。《安魂曲》是阿赫玛托娃的书写“同情”代表作之一,就如帕夫洛夫斯基所写的那样:“她的主要成就就是她的叙事长诗《安魂曲》的创作,它直接地反映了‘大清洗的年代——描写了深受迫害的人民的苦难。”[10]
与苔菲不同,阿赫玛托娃在强调对人民的同情时,并没有选择保留她的理智,更多的是把自己的心扉打开,与受苦难者在一起,完全融入受苦者。她始终超越自我的界限,将诗章赋予了千千万万的母亲们,赋予了整个受难中的人民大众,使得诗歌代表了最大多数人的心声。阿赫玛托娃始终把自己放置在人民之中,她完全放弃了自己的存在。
通篇读来,我们可以发现在大量的段落里,读者甚至无法确知叙述者究竟是谁,似乎在安娜·阿赫玛托娃语音的背后有着俄罗斯妇女的声音,不同于苔菲小说的苔菲-叙述者-作品人物-想象读者-真实读者的分裂力量,这诗篇里追求的是统一与团结,诗人的声音与千万受苦的妇女声音相混合,有时甚至这些受苦难的母亲们推开了阿赫玛托娃,走到了台前。这在苏珊·兰瑟的女性主义叙述理论中,就是一种集体型叙述中的“单言”(singular)形式的力量,即叙述者代某群体发言。阿赫玛托娃开篇代序中就这样写道:
“当时,一个站在我身后的女人,嘴唇发青,从来没听说过我的名字,她从我们都已习惯了的那种麻木状态中苏醒过来,凑近我的耳朵问道:
‘喂,您能描写这里的场景吗?
我就说:‘能”[11]
在苏珊·兰瑟看来一共可以分为个人型叙述,作者型叙述,以及集体型叙述。其中,集体型叙述是这样一种叙述行为:“叙述过程中某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群体被赋予叙述权威;这种叙述权威通过多方位、交互赋权的叙述声音,也通过某个获得群体明显授权的个人的声音在文本中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12]《安魂曲》里的阿赫玛托娃明显是代表在“大清洗”中作为边缘群体的女性发出的集体控诉,这位俄罗斯诗歌的“月亮”在集体中放弃了自己的身体,甚至存在,把所有受苦难的俄罗斯妇女都挤进自己的声音里。
而当我们对《安魂曲》的情与景因素分析的时候,我们又能发现阿赫玛托娃直接组合景物、事件和感情的方式,给予了读者更丰富的联想。如诗歌的第二段,第一第二句,诗人吟诵着静静的顿河,和澄黄的月亮,之后笔锋一转,描写了一个病怏怏、孤苦伶仃的女人默默地做着祷告。美国诗人斯坦利·库尼茨就曾说过:“是的,她(阿赫玛托娃)能够紧紧抓住一个场景。她具有亨利·詹姆斯所说的‘场景想象力(a scenic imagination)。”[13]顿河的流淌与月亮光下的人影似乎只是为了引出哀伤的女人的登场,亚当·斯密就曾强调:“同情如其说是因为看到对方的激情而产生的,不如说是因为看到激发这种激情的境况而产生的。”[14]反复吟诵,就会发现,阿赫玛托娃借助于这看似毫不相关的景物描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想象场景,让我们在场景中更深入地感受到那位妇女的悲哀。
读者在阅读诗篇的时候,始终沉浸在阿赫玛托娃用格律和韵节构筑起来的悲伤情景中,不自觉地被忘记了自己的存在,全身心地进入到受苦者之中。“同情”似乎在阿赫玛托娃这里宣扬了“物我合一”的力量,不仅诗人通过身体的共振深切的传达“同情”,俄罗斯诗歌的月亮更是营造了“月光”下清辉的受苦场景,将读者带入想象的场景中,剥夺读者的存在,使读者与诗人,以及受苦者达到合一。
阅读“同情”理论,我们或许一直困惑于如何将“物我合一”与“心理距离”结合起来,但如果我们避开寻找这两者的统一,而放大这两者的差异,也许会打开文本阐释的另一个视角。重视冷静客观的“心理距离”的苔菲,和强调“与人民站在一起”的“物我合一”的阿赫玛托娃在各自的作品中都表达着自己的对受苦者同情,试图通过自己的作品来引起读者的同情,但很少有学者将这两者并置起来阐释。也正是同情理论中的这一对“二律背反”帮助我们发现了重新阐释俄国幽默小说“王后”与诗歌“月亮”的作品的可能性,加深了我们对这两者的理解,反过来说,也正是对这两位作品关于“同情”因素的分析又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同情理论。
注 释
[1]赫尔穆特·施耐德:移情、想象和戏剧——18世纪理论中的一种社会手段,移情认知问题与跨学科概念的文化历史视角,伦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17年版,第211页。
[2]朱光潜:文艺心理学,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年版,第20页。
[3]库尔特·罗素:未来来客,文学评论,1989年第6期,第77页。
[4]徐乐:白银时代俄国的“反契诃夫学”,外国文学研究,2017年第39(03)期,第63页。
[5]伊迪丝·海伯:女巫苔菲:俄罗斯精神的神话,苔菲的创作与20世纪上半叶的俄罗斯文学过程,莫斯科:纳斯列基耶出版社,1999年版,第84页。
[6]蓝菲:永留心间的微笑——俄国的“幽默王后”苔菲,世界文化,2016年第12期,第35页。
[7]苔菲著,张冰译:生活与题材,世界文学,2004年第01期,第53页。
[8]苔菲著:胸针,黄玫,杨晓迪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8页。
[9]苔菲著:胸针,黄玫,杨晓迪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0页。
[10]帕夫洛夫斯基:安·阿赫玛托娃传,守魁、辛冰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1页。
[11]阿赫玛托娃:安魂曲,高莽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8年版,第17页。
[12]苏珊·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黄必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13]王加兴:阿赫玛托娃艺术风格探幽,当代外国文学,1995年第01期,第153页。
[14]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