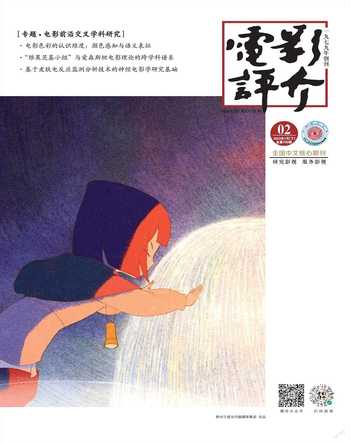抽象中的真实:电影音乐的文化认同功能研究
20世纪20年代晚期,随着技术的不断革新,图像和包括音乐在内的所有相关声音终于得以保存在统一的材质上,电影迎来了有声时代,音乐真正成为电影的内在元素,成为了现代意义上的电影音乐。电影成为了视听综合艺术。电影中的画面、光影、人物、情节等,与电影中的背景音轨、对白以及音乐等一系列元素一起进行组合表达,从视觉和听觉的维度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意义系统。随着电影叙事功能的逐步完善,音乐与电影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了,作为“电影音乐”的音乐,不再只是为了弥补听觉体验或是配合电影画面的附属品了,而是具有了更为丰富、深刻的作用,“它或为电影体验的一部分,或为构成电影文化背景的一部分。”[1]
最初的电影只是以视觉为导向的娱乐行业中的一员,凭借其短小且奇特的呈現方式,这种“视觉传奇剧”成为了传奇剧场和杂耍场中引人注目的卖点。尽管对于电影诞生初期,音乐是否就从未缺席的事实还存有争议,但电影史学家们一致认为,在1895年以后,音乐伴奏已是电影放映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电影不断突破其传统架构,并最终发展为一种独立的娱乐形式后,独立的电影院也随之诞生。而电影院的发展,也为音乐形式的不断丰富和壮大提供了场所。1910年后,电影院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音乐成为了竞争以及提高影院的声望的重要营销噱头,一些很重要的影院甚至成立了专属的大型管弦乐团。默片时代(即无声电影),对于音乐在电影中的作用已经引起了电影爱好者、影院经营者、音乐评论家等人士的重视,比如剧院的指挥如何用音乐来阐释电影、音乐伴奏是否适用于该电影等讨论成为了重要话题。尽管,音乐与电影的关系看似密不可分,仍有学者认为,此时的音乐还不能算是电影音乐,只是电影之外的附加物,是整个电影放映活动的一部分而已。
一、音乐的意识形态功能
音乐是否具有意识形态功能?“意识形态”(ideology)一词,最初由法国哲学家德斯蒂·德·特拉西于1796年提出,用以描述一门由他提出的新兴学科。[2]在特拉西的构想中,该学科通过对观念和感知的产生、结果与后果进行系统分析,进而为一般科学知识提供坚实的基础,并得出更为实际的推理,更重要的是能够促进社会自然调节。“通过对观念和感知的谨慎分析,意识形态使人性可被认识,从而使社会与政治秩序可以根据人类的需要与愿望重新加以安排。”[3]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关乎我们如何认知事物的原本属性以及如何对其做出判断,是一整套能够影响甚至决定我们思考和行动的观念体系。艾伦·帕·梅里亚姆在其著作《音乐人类学》中提出:“每种音乐体系都是由一系列观念预示构成的,它们使音乐融入全体社会活动……这些观念决定着音乐的实践和表演,以及乐音的产生……这些观念共同构成了一个框架,音乐在社会中的位置,以及人们对于音乐是什么、音乐应该是什么的看法都建立在这个框架之上……”[4]梅里亚姆将音乐放置到“人类整体行为”中来理解,按照不同的观念来定义音乐的意义,延展了音乐的内涵。比如非洲地区的一些民族认为鸟鸣声是音乐,但对欧洲人来说就不是,这种差别,完全是观念不同所致,既然音乐可以作为一种观念体系,它就能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事实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将音乐作为“术”传递和重塑观念的传统延续了数千年:《尚书·舜典》记载了乐师夔将“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毋虐,简而毋傲”的道德观念以乐舞的方式传授给贵族子弟,“于是正六律,和五声,以通八风,而天下大服”[5];《史记·周本纪》中记载了周公“制礼作乐”,大司乐“以乐德教国子,中和、袛庸、孝友”[6],将“德音”与“和”的观念通过音乐教育的方式来重塑个体的行为,于是“民和睦,颂声兴”。音乐使用者正是利用了音乐抽象性,通过对音乐内涵的预设,向聆听者塑造了一个具有想象性的语境,并使听众确信这种表达的合理性。通过对音乐内涵的重塑,使得音乐内容与听众产生某种映射关系,这一过程建构了听众与音乐之间的想象性关系。也就是说,听众对音乐的听赏是带着自己的情感投射和审美想象的,听众之所以会有感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听众相信音乐所传达的意义,进而也就认同了作品中所隐含的价值观。
二、电影音乐如何发挥意识形态功能?
电影音乐,无论是原创音乐或是音乐选段,在电影中都具有多重功能。电影音乐既是电影的,也是音乐的。
从音乐的视角来看,电影音乐具有强大的文化暗示功能。音乐普遍存在于人类文化中,是一种无国界的文化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音乐并非世界通用语言,不同文化赋予了音乐不同的含义,这使得音乐的表达能力以及对音乐的解读能力会因人们所处的文化语境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文化意识通过音乐来彰显自身。不同的音乐可能指涉特定的历史时期:比如编钟音乐能够唤起国人对春秋战国时期的联想;也可以指涉特定的国家:比如由尺八音乐联想到日本,由风笛音乐联想到苏格兰等;甚至可以指涉特定的社会环境:比如由布鲁斯音乐联想到酒吧,由古典音乐联想到音乐厅,这些音乐因产生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中,与特定的含义联系在一起,于是就能够在特定场景中传达特定的含义,从而形成一种蕴含文化意识的音乐惯例。音乐惯例在文化中根深蒂固,以音乐的集体无意识发挥作用,无论听众是否意识到这种惯例,都会受到影响。比如:詹姆斯·霍纳为《勇敢的心》作的配乐中,大量运用了风笛和爱尔兰哨笛,高亢的风笛与明亮的哨笛声瞬间将人带入了广袤的苏格兰高地,与影片所呈现的故事背景相得益彰,能够使观众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自行融入这个来自他乡的遥远的故事,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个体之所以能够“理解”这些音乐所带来的情绪体验或者审美体验,是因为在听赏这些音乐之前,个体已经具备了相关的文化背景和足够的知识储备,这决定了个体能在音乐中听到什么。
在约翰·威廉姆斯为《星球大战》所作的配乐中,和弦的运用、打击乐的节奏推进方式、弦乐通过颤音所产生的紧迫感等,都大量借鉴了古斯塔夫·霍尔斯特于1914年—1916年期间所创作的《行星组曲》中《火星》篇章的创作手法(这一乐章完成于一战前,被认为是预示了战争爆发的寓言之作,作品运用了大量的打击乐,配合弦乐用弓子敲击所产生的独特音效,制造了大战在即的紧迫感),为影片中由于银河系共和国解体,帝国崛起,而导致反抗军与黑暗势力抗争的故事背景定下了基调,对音乐表现手法的认知,比如鼓之于行军的隐喻、不和谐的音程之于紧张感等,能够在不知不觉中引导观众进入故事的叙事节奏当中,感受到战争一触即发的紧张感。有趣的是,威廉姆斯所创作的“星球大战”的主题曲则是直接运用了与在埃里希·科恩戈尔德为于1942年为影片《金石盟》(Kings Row)所创作的电影配乐中非常相近的音行来致敬这位作曲家,这当中很难排除作曲家受到自身音乐知识积累的影响。作曲家们在为影片配乐时,如何选取创作所需的音乐素材抑或通过风格、音色等特定形式结构以实现音乐自身的可理解性,从而配合影片的发展,取决于作曲家所受的音乐训练和文化意识,也就是前文提到的音乐惯例。电影作曲家们会依赖音乐惯例来引导和控制观众的反应,随着电影情节的推进,引导观众的情绪和心理。基于音乐惯例,音乐能够在观众与银幕之间创造情感共鸣,令观众产生情感回应,这样一来,电影音乐使观众忽略了电影的虚拟性,具有强大的意识形态控制功能,使观众进一步融入影片,甚至失去判断能力,全盘接受电影中传递的文化价值。正如皮埃尔所说:“影视音乐并不只是影视画面的陪衬。音乐本身及其内涵都在一定程度上传递了观众的价值取向和时代观念。”[7]
从电影的视角来看,电影音乐能够让意义在不同层面具象化。“电影音乐中音乐并非纯粹的音乐,而是一个更大的意义系统中的一部分。”[8]电影是一种视听艺术,也是一种叙事媒介,电影中的音乐作为这个叙事系统中的组成部分,必须在这样一个大的设定下来进行。音乐作为一种时间的艺术,能以一定的形式特征,使人联想起叙事文本的结构,使其能以叙事范畴来表述音乐体验。
电影音乐规定了观众感知叙事的视角,影像赋予其指称性而使音乐更加明晰,将音乐的普通表现力特殊化。比如:欧洲传统宗教音乐中,常使用管风琴演奏(其演奏场所只限于教堂),为人们制造一种“神圣且浩瀚”的声音,但这种概念是抽象且模糊的,当汉斯·季默将代表了人们对超越世俗生活、超越已知世界、渴望探索未知的管风琴音乐运用到影片《星际穿越》中,观影者看着浩瀚的宇宙时,管风琴音乐实现了与视觉的匹配,对音乐内容的联想有了具体的投射,音乐支持和构造了电影叙事,而影像则为音乐提供了具体的想象对象;电影音乐可以对影像进行特殊化处理,能够在众多意义中强化某一种,比如:马斯卡尼创作的独幕歌剧《乡村骑士》中的《乡村骑士间奏曲》分别被运用到《教父3》《阳光灿烂的日子》《立春》《导盲犬小Q》等多部影片中,成为众多影片中的经典配乐。这部歌剧描写了一个悲剧的故事,该间奏曲出现在歌剧的第八幕与第九幕之间,预示着危机重重的故事走向以及男女主人公即将到来的悲剧结局,乐曲本身包含了诸多复杂的情绪。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将乐段运用在马小军对米兰迷恋与向往的场景中时,音乐本身所蕴含的对结局未卜的迷茫感便恰如其分地烘托了主人公青春的迷惘;《教父3》中,教父在歌剧院门口遭遇枪袭导致最爱的女儿当场死去,这时《乡村骑士间奏曲》悄然滑入,音乐作为一条纽带,呈现了他与女儿跳华尔兹、与妻子在婚礼上拥舞的回忆场景,回忆过后,白发苍苍的教父坐在夕阳下,一人一狗,迎接生命的终点,乐曲本身所蕴含的对美好过往的追忆、对男主角决斗失败被杀、对故事结局的哀叹也恰好映射了教父最美好的回忆、最痛彻心扉的失去以及人生的落幕,为电影中表现的情感提供了声音定义,令观众产生情感共鸣。
三、电影音乐的文化认同价值
电影音乐具备强大的意识形态功能,这就提示我们在观影时,不能简单地去理解音乐附着在电影中所传达的表层含义,而是应该关注为什么会采用这样的模式来为电影配乐。比如:在描写宏大的场面的时,通常会采用恢宏的交响乐来配合画面,在某个宁静的时刻,舒缓的钢琴声就会响起;大调式能唤起明亮的愉悦感和正义感,而小调式则会唤起暗淡的忧伤与哀愁;和谐的音乐烘托秩序与平和,不和谐的音乐则暗示失衡与疯狂,这种音乐体系主要是建立在西方音乐对十二平均律的广泛使用以及和声概念之上的,但世界上还有很多音乐体系,比如中国传统音乐艺术是以线性形态、单音体系和五声、七声结构为主的(中国的音阶体系十分丰富,但明代朱载堉确立的十二平均律,最终却落得“宣付史官,已备稽考,未及施行”的结局,十二平均律在17世纪传入欧洲,才得以发展壮大);印度音乐和中东地区的音乐是依靠即兴创作来发展的。作曲家在创作时,会采用某种模式来进行创作,事实上已经默认了某种“本该如此”的模式,甚至一些作曲家只按照音乐惯例来配乐,好像只要是影片到了某一高光时刻,就要使用大编制的乐队音乐,明示“泪点”的到来,这样的刻意为之反倒令观众出戏,影响了其观影体验。电影建构的并不是某个虚无缥缈的世界,而是用以表达自己和了解他人的象征形式,它部分地构成了社会“真实”的一面,电影通过影像传递价值观,潜移默化地影响观众的价值观,影响创作者的价值观,而很有可能创作者在创作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某种价值观,电影音乐贯穿于其中,同样如此。电影音乐的影响力甚至比影片更加深远,当观众走出电影院后,不一定会反复观看影片,但配乐却可能出现在任何一个不可预见的地方,可能是咖啡店、西餐店,甚至路边的某个广告中,时刻暗示个体,只有你认同某种价值观,你才会获得某种身份或立场。
正因如此,音乐文化同样可以通过电影获得一定程度的重塑。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唢呐主奏的乐曲《小刀会序曲》。《小刀会序曲》是商易先生为中国民族舞剧《小刀会》所创作的作品,作品描写了1853年8月上海地区爆发的为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王朝的双重压迫而爆发的小刀会起义,这段音乐在周星驰主演的《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中被用来作为至尊宝登场的音乐,以烘托英雄人物的形象,同样的一段旋律被徐克用到《龙门飞甲》的片头,为影片反抗暴政的英雄行为奠定了基调,通过这些影片为观影者建立了一种心理暗示:当有(正面的)重要人物或者事件(尤其是具有反抗性的事件)出现时,唢呐音乐便成为一种恰当的选择。唢呐音乐不再仅限于人们通常认知中婚丧嫁娶等民俗中所使用的野腔滥调,是成为一种有震撼力的、正面的音乐形象,通过电影这种更为隐蔽而广泛的方式,使唢呐音乐文化实现了重建,重获认同,并得以传播和推广。(历史上,出自波斯、阿拉伯的唢呐从金、元时期传入中原之后,一直用于军队的鼓吹乐中,为军中之乐,直到明代末期,唢呐才从官府和军队的专属乐器逐渐走入民间。)近年来,这样的尝试比比皆是:电影《英雄》的配乐中,作曲家使用了古琴,古琴作为中华文化的象征,历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件乐器从上古时期作为与神沟通的法器,到成为士大夫修身理性的重要载体,正是由于其包含的特殊的非器乐性与非观赏审美性,使得古琴音乐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非常神秘,通过电影片段,使古琴音乐有机会“走下神坛”,展示在大众面前;在电影《卧虎藏龙》的配乐《离》与《丝绸之路》中,使用了二胡来与大提琴的配合,优美的旋律充分展现了二胡柔美而深沉的音色特点,也让这件在很长一段时间背负着“恶名”的乐器获得了崭新的面貌。电影音乐向内可侧重文化的根植,向外可关注听众的意识,因此,它应当被视为音乐文化在文化领域中的延伸,要将电影作为一种载体或媒介,来传播中国音乐文化。
結语
费孝通先生定义“文化自觉”为:“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趋势,不带任何‘文化复归的意思,不是要重复,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9]但有自知之明显然是不够的,好比我们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来龙去脉如数家珍,却备而不用,甚至束之高阁一样。活态的传承一定是建立在认同之上的,这事关我们从事文化活动的初心和诉求以及对自身文化感知方式的选择。电影音乐作为现代社会一种重要的音乐文化感知方式、表达形式和表征媒介,有力量去影响认同的建构、延续和转变,通过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实现文化自主性,从而提升文化自信。
【作者简介】 罗章菡,女,贵州贵阳人,贵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讲师。
参考文献:
[1][挪威]彼得·拉森.电影音乐[M].聂新兰,王文斌,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7
[2][3][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高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30,31-32.
[4][美]艾伦·帕·梅里亚姆.音乐人类学[M].穆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65.
[5]吉联抗.吕氏春秋中的音乐史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54.
[6]徐正英,常佩雨译注.周礼·春官·大司乐[M].北京:中华书局,2014(02):477.
[7][法]皮埃尔·贝托米厄,著,杨围春,马琳译,电影音乐赏析[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03):1.
[8][美]凯瑟琳·卡利纳克.电影音乐[M].徐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1:16.
[9]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6(07):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