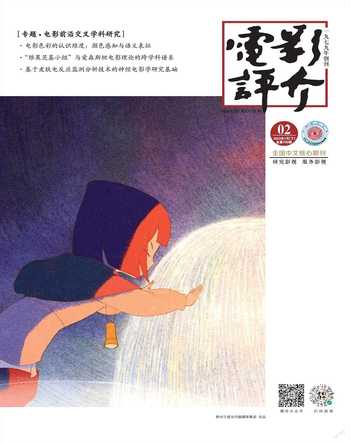故事形态学与电影文本分析结合的价值与困难:形式主义与普洛普叙事学的电影应用
李杨

在托多洛夫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主流结构主义叙事学遭遇危机时,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盛行于俄國文学批评界的形式主义方法被重新挖掘而出。[1]其中,民间文学研究者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普洛普与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雅各布逊等名字被重新提出,这些被组织在结构主义理论阵营中的研究者比托多洛夫的理论早了40余年。普洛普的叙事理论研究从对民间故事叙事模式的把握出发,以全局性的眼光和具体的民间故事为分析文本,发掘出超越具体民间故事文本的基本结构,并力图将其应用到一切广义上的叙事作品中。
其中,同样具有叙事性功能的电影艺术便在故事的形态学方面具有相当的应用前景。从电影的叙事功能角度出发,电影与民间文学作品一样都是当代文化不可或缺的叙事文本种类,而电影叙事学也是叙事学科在当下的重要分支。本文将从形式主义和文本研究方法出发,对早期的故事形态学理论与电影文本结合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以及二者结合的实践价值与困难之处作具体分析。
一、俄国形式主义与形式主义电影理论的结合
在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法国保加利亚籍文学理论家茨维坦·托多洛夫正式提出“叙事学”这一概念,指的是“关于叙事结构的理论”。[2]托多洛夫借用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中的“单元”“序列”“文本”等关键术语,对故事的创作编写与批评系统进行了综合性的梳理;进行之后的叙事学以结构主义叙事学为主流,它标志着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文论的直接成果。[3]然而,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包括结构主义在内的诸多宏大理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此时,在40年前发源于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的另一种“叙事学”——故事形态学,重新作为重要的叙事文本分析理论资源进入了研究者视野。与法国结构主义注意以符号能指与所指为方法不同,形式主义对文学研究对象的关注超过了对研究方法的关注,将研究领域从对具体研究方法开发的评判扩大到了对研究对象的本质定义。[4]形式主义认为,一般言语的主要功能是通过语言让说话者的内心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进而将信息或消息传递给听者;另一方面,形式主义又将文学语言确定为这一表述的中心,任何关于“传达”与“表达”的话语本质上都是以话语自身为中心的、在被使用的过程中表达自身的表达。[5]因此,语言或文学的主要作用不是与外部事物发生联系,而是引人注意它的形式特征,也就是语言符号本身的内在联系。“我们都可发现艺术的特征,即它是专为使感受摆脱机械性而创造的,艺术中的视象是创造者有意为之的,它的‘艺术的创造,目的就是为了使感受在其身上延长,以尽可能地达到高度的力量和长度,同时一部作品不是在其空间性上,而是在其连续性被感受的。”[6]无论在何种艺术中,艺术家都从不摹仿,而是通过创造全新的形式重塑对客体的“视象”。这样的观念可谓是和电影理论阵营当中的形式主义电影理论不谋而合。
形式主义电影理论与写实主义电影理论共同构成了经典电影理论的一体两面,这种分类法分别来自梅里爱和卢米埃尔两位电影先驱。[7]其中,形式主义电影理论在二三十年代构成电影理论史上的第一个高峰,雨果·明斯特伯格、鲁道夫·爱因汉姆、谢尔盖·爱森斯坦、贝拉·巴拉兹等名字将彼时尚在襁褓阶段的电影理论引入正轨。在法国诗意电影理论与德国表现主义运动的配合下,以形式主义方法来表现生活的电影观念逐渐形成。尽管这一时期尚未出现成熟的电影理论,也没有理论家为这一观点进行辩护,但电影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几乎成为所有有识之士的共识。这一迄今为止已经普遍获得大多数人认可的观念,仍然需要归功于从20世纪早期到30年代间形式主义理论家们提出的各种真知灼见。世界上第一本真正从理论角度把握电影本质的著作《电影诗学》即是俄国形式主义的主要成员在1927年出版的。[8]电影艺术毫无疑问建立在光学的物理基础上,电影拍摄是一种普通的摄影术,但它又保留着自身的节奏与创造新世界的能力。“诗歌使我们关注词语而不是信息,绘画使我们关注线条、色彩、构图和其他形式特征而非内容。同样,作为艺术的电影应当使我们关注这种媒介的表达基础,而非它所摄录的事物。”[9]电影以现实中的客观存在为影像素材,通过全新的形式组合创造出另一个世界。简而言之,传统的形式主义电影理论与写实主义电影理论分别强调素材与创造新世界的方法。
在人才辈出的形式主义电影理论中,“形式”的创造特性成为理论家们关照的重点:明斯特伯格以电影美学与心理学论述人类体验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以及电影作用于人类心智的原理[10];爱因汉姆以“电影为艺术形式”的问题为理论探索的前提,以电影这一媒介“不完全写实的几个方面”倒推,得出这一媒介具有的创造性在于如何组织和引导观众去感知事物的结论[11];苏联蒙太奇学派的先驱爱森斯坦则打破了单纯的机械认知论,将电影视为复杂的有机体、有力的说词工具与了解宇宙的神秘方法[12]。以“新形式主义”为研究对象的美国学者克里斯汀·汤普森认为,现实主义既不再是自然的,也不是艺术作品的一个不可避免的保守特征,它是一种形成于具体历史语境中的风格。克里斯汀·汤普森以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偷自行车的人》(维托里奥·德西卡,1948)为例,提出影片之所以可以在不采取一个确定的社会思想立场的情况下完成结局,部分原因是故事的政治意味在最后被父子之间的戏剧性冲突所淹没。这部著名影片讲述的是在二战时普遍失业的意大利街头,一个城市工人里奇终于得到一份贴海报的工作,却在上班的第一天误将自行车遗失,里奇带着儿子满城寻找,最终也没能找到他赖以活命的自行车。眼见无指望的日子又要降临,里奇牙咬牙走上偷自行车的道路,可是他的运气却没有别的小偷好,被逮个正着。车主被孩子扯着父亲衣服哭泣的一幕感动,决定不再追究的故事。影片中的主要矛盾——能否找到自行车已不仅仅是生计问题,更是一个父亲在孩子眼中的尊严与形象。而当这份尊严在无情的生活面前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之时,他的沮丧直接演化为焦躁,无辜的儿子小布鲁诺成为压倒里奇的最后稻草与绝境中的唯一希望。在最后一幕中,落魄父亲里奇带着天真孩子——布鲁诺的叙事在场具有多种功能,其中之一就是为了创造一种同情的基调,以平衡抵消影片对于政治的客观处理。这种同情以及里奇和布鲁诺之间的情感关系很可能是《偷自行车的人》成为迄今最受欢迎的新现实主义影片之一的一个主要理由。[13]综上所述,电影对形式的强调与俄国形式主义在根源上具有极强的关联性。
二、普洛普叙事学与电影叙事学的结合
1928年,俄国文艺学家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維奇·普洛普撰写了《故事形态学》一书。按照普洛普的说法,这项研究的目的在于对俄国民间故事领域里的诸多形式进行考察,并确定其结构的规律性。[14]在书中,作者对许多俄国民间广为流传的“神奇故事”进行了非常详尽的形态比较分析。这里的“神奇故事”指“建立在上述各类功能项有序交替之上的叙述,对每个叙述而言会缺失其中几项,也会有其他项的重复”[15]。普洛普引入了功能项的概念作为其中的基本单位,并从行动过程角度定义了角色行为。普洛普发现俄国神奇故事的全部内容用简单的三言两语就可以完全概括,这些故事之间也存在着相当的类同性。例如主人公被下禁令(父母要到森林里去,禁止孩子出门),主人公打破禁令(父母久久未归,孩子走出家门),主人公遭遇机会或危险(在去往森林的路上遭遇动物精怪,精怪偷走了孩子所带的物品),主人公得到帮助后解决问题(善良的女巫借给孩子魔法道具让他从洞穴中取回被偷走的物品,或打败敌人)等,诸如此类。尽管这一时期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叙事学尚未出现,普洛普也是在“形态学”这一借鉴自植物学教程与哥德文学研究的概念下进行故事功能讨论的,但这一术语仍然在对贯穿整个自然的规律性的判定中揭示出这项研究具有的叙事学前景。普洛普对打破了以往俄国民间故事研究中按照单一主题、人物等单一标准划分的做法,他认为这种分析方式只停留在表面,对故事的整体性叙述较少。相反,他着力从文本出发研究神奇故事在叙事中的共性,力图以全局性的眼光把握民间故事的叙事模式。[16]在普洛普叙事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其应用的对象已经远远超越了最早的“神奇故事”即民间文学领域。
只要可以从行动构成意义角度对角色行为进行定义,那么普洛普这种从形式主义出发,用角色和功能研究民间故事的叙事学研究就依然卓有成效。根据普洛普的故事形态理论,人物和情节只是故事的组成部分,渗透在故事组成部分中的功能才是故事最基本的单位,它们组成了故事的基本结构。从功能单位看透体现在每一具体的故事中、同时又超越每一具体文本的基本结构就显得十分重要。[17]所有的叙事功能都可以归纳为6个基本叙事阶段:准备阶段、深入阶段、遣派阶段、搏斗阶段、返回阶段、承认阶段。将这一结构性划分的方法应用在电影《新神榜:杨戬》(赵霁,2022)的叙事分析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各个阶段的性质和功能。这部影片从二郎神杨戬将自己的妹妹杨婵压在华山之下开始,以沉香劈山救母告终。主人公杨戬本来师从金霞洞府的玉鼎真人,身负天官威名与过人法术,却因为在镇压玄鸟时失败而陷入低谷——这是准备阶段的铺垫。接下来几个阶段与故事剧情的对应如下:深入阶段,坏人伤害了家庭中的某个成员——华山中玄鸟的力量渐渐强大,杨婵兄妹二人以杨婵的自由和杨戬的一只眼睛(以及斧头)为代价将玄鸟封印在华山之下;遣派阶段中总会出现灾难或贫穷等种种问题,主人公得到请求或命令,被送到、派到或带到灾难的发生地解决问题——杨戬在潜入蓬莱靠近目标后却发现引诱他前来调查的对象是与杨婵颇有渊源的神女婉罗。一方面,杨戬被神女婉罗的美貌所打动,不忍心伤害她;另一方面,杨戬也了解到玉鼎真人所做的一切。在搏斗阶段,寻找者(通常是主人公)同意或决定反抗——杨戬带着神女婉罗一起进入玉鼎真人的“天书”绘卷中。在幻象的蛊惑与激烈的战斗中,在与玄鸟大战后一直未能恢复的杨戬身负重伤。但在沉香的激励下,命悬一线的杨戬重整旗鼓,与玉鼎真人在华山展开了生死决战。相比之下,《新神榜:杨戬》的返回阶段与承认阶段较为简单。在普洛普的功能模块中,这一模块的主要叙事目标是假冒主人公,或对头被揭露,或主人公改头换面,敌人受到惩罚,主人公获得荣誉或爱情等。在影片中,这一阶段中的杨戬借助玄鸟的力量睁开了“天眼”,获得了自己的完整形态——对应着“改头换面”的功能项;并最终在玄鸟的帮助下让玉鼎真人这个邪恶的修道者得到了惩罚,不仅为被镇压在华山下的玄鸟一族解除了危机,而且将天下的民众和神女婉罗、外甥沉香从邪恶的势力中拯救了出来。在揭露玉鼎真人的阴谋并消灭敌人后,曾一度被人视为丧家之犬的杨戬也获得了名誉的恢复与地位的提升。在普洛普对神奇故事规律的总结中,功能项在故事中的作用与性质是稳定的,其不根据具体人物、情节的变化而变化[18];而且功能项的排列顺序是固定的。最后,故事中的功能项在详尽或简略的程度上可能存在变化,也有不具备所有功能项的故事,但是缺少的功能项不影响其他所具备的顺序排列。从《新神榜:杨戬》这些故事情节中可以看出,这部影片故事的起承转合与普洛普的31项“功能单位”几乎不谋而合。尽管人物角色的身份可能发生变化,但角色在故事中发挥的基本功能是故事里固定不变的成分,功能的顺序也并不受身份影响的限制。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肖尔斯在《结构主义与文学》中所说:“就结构而论,所有的神话都属同一种类型。”[19]
三、符号学方法在电影文本分析中的前景展望
无论是俄国形式主义建立在语言学基础上的形式特征,还是普洛普以俄国民间故事为研究文本探求叙事功能与形态的规律,都在方法上具有相似的符号学方法基础。早在俄国形式主义主要成员在《电影诗学》中将形式主义的方法运用到电影中,探讨电影的原理、本性、风格与摄影等问题,寻求“诗学研究的方法与电影语言形式的内在联系”,从而“建构起形式本体论的电影艺术观”[20]以来。符号学方法就一直是电影理论推进的重要思想资源。例如在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的研究迫于社会压力暂停之后,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又以神话为文本进行了类似的语言结构研究,并发现了世界各国古老神话中普遍存在的永恒结构。总而言之,尽管电影叙事学无法被视为完全意义上的符号学方法或结构主义文论,但叙事学在近半个世纪中的发展却与符号学方法的关系极为密切,符号学方法在电影乃至其他艺术门类的叙事理论研究上用力较重,对当代叙事学的建设和完善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
在最近的二十多年里,叙事学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转折,使其走出了经典形态,而进入当代形态的“后经典叙事学”。宏大叙事逐渐失落之后,后经典叙事学使叙事学得以从西方开始复兴。伴随着更加复杂的故事构造,重新在符号学中寻求分析系统与具体方法的学者逐渐增多,“后经典叙事学”也作为叙事学分析的重要发展方向备受瞩目。这项门类与方法繁复的学科被美国叙事学学者杰恩认为采用了“叙事学+X”的研究模式,即叙事学是结合了其他研究方向形成的“后学科”之一,其特点是“从发现到创造,从一致性到复杂性,从诗学到政治学”[21]。如此兼容并包的后叙事学能够解决的问题和分析的文本也更加趋于多样化。以在叙事上的复杂性都远远超过民间故事模式的影片《瞬息全宇宙》(关家永、丹尼尔·施纳特,2022)为例,该片采用了复杂的“多重宇宙观”进行叙事,女主人公伊芙琳穿梭在她每次选择造成的分叉事实之前。在每种可能性都能创造出一个平行宇宙的世界观中,伊芙琳从中发现了多重宇宙的秘密,并借助穿梭于不同宇宙之间的方法拯救着自己的家庭与幸福。
《瞬息全宇宙》的创新之处在于将诸多基本角色功能重合,从而创造出了女主人公“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多重宇宙。影片中的女主人公伊芙琳爱上了魏蒙德。为了逃离反对这桩婚事的父亲,她选择与魏蒙德私奔到美国,并生下女儿朱宝,几十年如一日的经营着一家洗衣店。她发现如果自己不选择与魏蒙德结婚,就会以功夫女星的身份大红大紫——在无数个平行宇宙中,她都有着不同的生活与社会位置。在一次由某个宇宙中的少女朱宝引起的灾难中,主宇宙的伊芙琳偶然具有了穿越不同平行宇宙并获得特殊技能的能力。于是,影片中的伊芙琳具有了同时承担普洛普31项功能单位与7种行动范围的“特殊功能”。她可以是主人公、反面角色、帮助者、被寻找者及其家人、派主人公外出历险者、主人公、假主人公等任何角色,也有可能通过一些低概率举动(将左右鞋子反穿,想象自己在储物间按下耳机,吃唇膏等)卷入更多种类的“行动范围”之中;其他角色也是一样,身处不同宇宙中的角色可能具备不同的功能,例如伊芙琳的女儿朱宝在片中最初作为平庸的女高中生出现,希望母亲可以体会自己的痛苦;但她在故事中很快被转化为最大的反面角色;随着故事的推进,她在后半部分又转化为“被拯救者”与“帮助者”,时而告诉母亲这个世界还有值得她去爱的东西,时而带领着伊芙琳领略多重宇宙之广阔,帮她找到存在的意义。
近代以来,市民文学的兴起影响了以普通人承担英雄或主人公角色的叙事模式;而过于英雄化的主人公形象又影响了日常叙事的复归。在不同功能与特性的反复纠缠中,诞生了《瞬息全宇宙》这种主人公既是普通人又是英雄,并同时承担多重身份功能的影片。在无拘无束的想象力中,伊芙琳一家穿越到了武侠宇宙、人偶宇宙、卡通宇宙、没有生命的石头宇宙等许多新奇多样的叙事空间内,但影片传递的内核依然简单而朴素。在故事内部的单一宇宙中,伊芙琳同时开着洗衣店,与顾客争执、与窝囊的丈夫及喋喋不休的公公说话、安抚被忽略而不满的女儿,忙碌的脚步始终不曾停歇;在故事的多重宇宙中,伊芙琳也要一边学习在多重宇宙中穿梭的能力,一边与各种敌人战斗,要从其他宇宙的自己身上汲取力量,在自己酿成的危机中拯救自己,还要顾及到家庭成员的安全与感受;在叙事学的维度上,伊芙琳则身兼许多叙事角色的功能,真正成为了瞬息之间成就整个故事的“超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样的伊芙琳已经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故事角色或故事人物,而是后结构叙事下身负多重真相与事实的赛博格。[22]在“事实”“证据”“现实”“结构”等曾经确定无疑的因素之间,伊芙琳以“超人”的行动力打破了既有叙事方法的稳定性和叙事规约的有效性,又以一种集多重要素于一身的混合身份重新确立了基于叙事方式的故事身份。或许在电影叙事学的未来,这种可以克服自身局限性的角色设置与行动模式,才是拓展叙事学研究范畴的全新视角。
结语
符号学方法赋予了叙事学研究以新的视野,让研究者们的目光从作品本身转到对叙事功能与读者阐释的过程上,并由文学叙事与符合文学规约的现象转向不同媒介、题材中的叙事作品。在这一过程中,形式、结构与功能等源自结构主义的术语被纳入经典叙事学的模式与概念中,用于对具体叙事性文本加以修正和补充,有效地将叙事学的研究范畴扩展到电影等其他艺术领域之中,形成成熟多元的电影叙事学。在结构主义进入后结构主义之后,建立在后结构批评理论基础上的后叙事学依然具有符号学的基本方法。它被视为一种新叙事学,是对叙事学的更新。
【作者简介】 李 杨,女,广西桂林人,广西艺术学院影视与传媒学院影视编导系副主任,副教授,主要从事电影导演、影视剪辑艺术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2021年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實践项目“融合地方汽车制造业的设计学新文科建设与创新实践”(编号:2021160050)、广西高校高层次人才引育工程及高水平创新团队“‘艺术+科技设计创新研究团队”(编号:RC2100000062-C)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5]杨燕.俄国形式主义的叙事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12,24.
[2][3][4]谭君强.叙事学导论 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45,57,78.
[7][8][10][11][12][美]达德利·安德鲁.经典电影理论导论[M].李伟峰,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7:35,37,51,78-79,88,100-103.
[6][俄]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等.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M].方珊,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107.
[13][9]张进.文化研究关键词(修订版)[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129,91.
[14][15][16][17][18][俄]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普洛普.故事形态学[M].贾放,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18,22,55,69,25.
[19][美]克里斯汀·汤普森.打破玻璃盔甲:新形式主义电影分析[M].张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31.
[20]宋杰,徐锦.被遗忘的俄国形式主义:电影语言研究的重要力量[ J ].当代电影,2022(04):115-122.
[21]张美晴.“人类”何以想象未来[D].山西大学,2021:16.
[22]怀宇.普洛普及其以后的叙事结构研究[ J ].当代电影,1990(01):7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