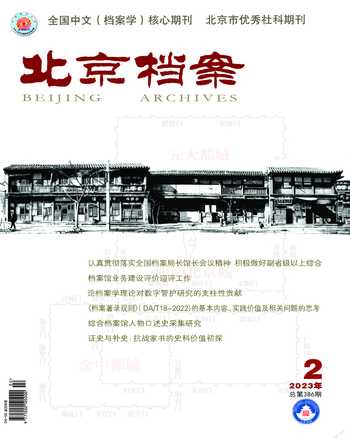证史与补史:抗战家书的史料价值初探
宋谌
摘要:抗战家书是指写于1931-1945年的、内容与抗战有关的私人书信,具有私密性、真实性、广泛性、双遗产性、唯一性和实物载体多样性等特点。抗战家书的史料价值体现在证史和补史两个维度:作为历史的载体,抗战家书能够生动再现时局图景,表露战时社会思想;因其书写者具有多元性,可以从多角度诠释抗战史,在补充史传缺失方面拥有独特价值。抗战家书作为一种档案史料,可极大丰富并扩展抗日战争历史研究的视野,值得学术界进一步关注并加以利用。
关键词:抗战家书 史料价值 档案史料 证史补史
Abstract: Family letters in the War of Re? 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refer to the personal letters written from 1931 to 1945, which are related to the War of Resis? 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They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ivacy, authentici? ty, universality, dual heritage, uniqueness and diversity of physical carriers. The histori? cal value of the family letters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s reflected in two dimensions: proving history and supplementing history. As the carrier of history, the family letters in the War of Resis? 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can vivid? ly reproduc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reveal the social thoughts in the war time; Because of the diversity of its writers, it can interpret the history of the War of Re? 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from multiple angles and has unique value in supplementing history. As a kind of archival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 family let? ters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 gression can greatly enrich and expand the vision of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which is worthy of further at? tention and use b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Key words: family letters in the War of Resis? 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historical value; archival historical materials; prove the history; supple? ment to the history
引言
近年來,家书作为一种史料引发学术界的关注,从家书入手研究历史逐渐成为一个新视角。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步平先生在为《抗战家书:我们先辈的抗战记忆》一书做的序中提出:“家书在史学研究上的功用似应得到更多的关注,因为与一般的资料相比,家书的特点在于具有生命,其魅力在于真实……许多家书的作者都是那个时代重大事件的见证者、亲历者,他们的视角往往是一般的史书中所看不到的。”在谈到抗战家书的作用和意义时,步平先生指出:“《抗战家书》从一个侧面真实记录了抗战时期的社会状况、市井民情,为后人深入而全面地认识、研究那个时代,提供了新的史料和新的视角。”[1]目前,抗战史研究大多依据官方档案、地方史志和当事人回忆,这就在客观上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第一,依据这些材料还原的历史多以大场面和基本数据为主,历史细节较少,难以给人留下鲜活的印象;第二,当事人的回忆多在事件结束后,甚至时隔多年,可能与实际情况有所偏差;第三,能够被官方档案和地方史志相对完整记录下来的人本身具有一定级别和知名度,但是那些数量庞大的普通军民的个人经历和心理活动却并不为人所知。而作为史料的抗战家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三方面的不足。家书的作者都是抗日战争的亲身经历者并且大多于战时写就,这就使得家书不同于那些依托事后回忆形成的材料,更具有真实性。同时,我们既能透过家书的字里行间感受当时战场形势和社会状况,获取更多的历史细节,也能深入了解那些普通士兵和百姓们的英勇事迹和心路历程。总而言之,抗战家书作为一种史料,可极大丰富并扩展抗战史研究的视野和角度,值得学术界进一步关注并加以利用。
关于抗战家书的史料价值,虽然专门撰文进行研究的成果不多,缺乏完整深入的论述,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种史料的家书在抗战史实际研究中已经得到了使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其史料价值。笔者通过广泛收集和实地考察散落在各地的抗战家书,力图全面占有史料,进一步挖掘抗战家书的史料价值。
一、抗战家书的定义及特点
(一)家书与抗战家书
家书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家书是指家人(含亲戚)之间的通信,包括父母与子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祖孙之间、叔伯姑侄之间的通信,以及与外祖父母、舅父姨母、表兄弟妹之间的通信;广义的家书泛指所有私人通信[2]。“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能够保留下来的书信难能可贵,所以本文研究的抗战家书归在广义家书范畴内,收寄家书主体范围较广,限制较小。
对于抗战家书的定义,张丁从写作时间和内容两方面对其进行界定,提出“凡是1931年至1945年抗战时期所写的、内容与抗战有关的私人书信,都可称为抗战家书。”[3]笔者认为,除这两个要素外,在收寄主体方面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抗战家书既然是写于抗战时期(1931-1945)的家书,那么其收寄主体就不仅包括身为抗战亲历者的中国军民和海外华人华侨,还应包括作为侵略者的日本人和亲身经历中国抗战的第三国人士。作为史料的抗战家书,其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能够如实记录战时情况,相较于中国军民,侵华日军和亲身经历中国抗战的第三国人士观察战争的视角不同,战时所处地理位置和心理位置不同,家书受到的邮寄限制和邮路状况不同,可以为抗战史研究补充更多的细节。
对于抗战家书的分类,张丁认为抗战家书包含两个大类,一类是已经公开出版的重要历史人物的家书,比如毛泽东、朱德、左权、彭雪枫、傅斯年等人写于抗战期间的家书,多为大家所熟知,另一类是民间家书[4]。笔者认为,从历史学科对各种文献档案材料的实际利用情况来看,对抗战家书的分类应进一步细化。“被各级各类博物馆、档案馆收藏的家书”与散落在民间的家书相比,它有被档案使用者查阅并加以利用的可能,而在个人手中的家书我们无从知晓数量、甚至是否存在。所以,从研究者获取史料的难易程度来看,“被各级各类博物馆、档案馆收藏的家书”应该介于“民间家书”和“公开出版的重要历史人物家书”之间,独立成为第三类,需要研究者多下功夫、多方寻找、广泛查阅、深入发掘才能真正掌握。
对于抗战家书的性质,前文我们将其笼统称为“史料”,那么抗战家书属于哪种类型的史料呢?张丁认为,“档案是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产生的原始历史记录,而家书是家人和亲友之间沟通联系所留下的原始记录,完全符合档案的定义。”[5]因家书在寄出后就几乎失去了再被改动的可能性,所以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真实性。但是,要注意民间家书和重要历史人物家书有所不同。任继愈先生在谈到民间家书时曾说,“(民间)家书写的时候不是为了发表的,也不是为了给别人看的,所以讲真话的多”,肯定了民间家书作为史料的真实性,同时也提到“有一些家书是做给别人看的”[6]。所以,抗战家书应该被看作是档案的一种,但在使用中要注意对书写者写作时的出发点和内容的真实性进行甄别,并和其他类型史料互证。同时,被书写在以纸张为主要载体的抗战家书,也应属于实物史料。它的存在本身和在战争的硝烟中完成从寄信人到收信人投递的过程,就足以成为历史的见证。
(二)抗战家书的特点
前文提到广义家书泛指所有的私人通信,私人通信首先具有私密性[7],所以抗战家书自然也具有这一特点。在私密性的基础上,抗战家书的内容具有真实性和广泛性。在主要依赖书信交流的年代,写信是亲人、朋友、战友之间互通有无最重要的方式,其目的是要让远方的亲朋知晓自己的近况。这种私密性带来的结果便是寄信人写作顾虑较少,更容易在家书中记录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真实经历,表露真实的想法和情感,那么抗戰家书作为史料的可信度就更强,呈现的历史细节就更丰富,研究者也可以从中获取更多的信息。
其次,抗战家书具有双遗产性,是集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于一身的特殊文化遗产。家书实物作为手稿,属于物质遗产;而家书作为一种通信方式,其中蕴含的情感表达和文化礼俗传承,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8]。对于抗战家书来说,无论是实物还是内容,都是重要的历史遗存。[9]
再次,抗战家书具有唯一性。建川博物馆馆长、著名收藏家樊建川先生收藏了近百万封家书,其中不乏抗战家书。他认为,书信是最重要的文物类别之一,包括书信在内的手写品每一件都是孤品。相比报刊、书籍、传单之类的印刷品来说,手写品具有唯一性。印刷品的文字通常会经过提炼、取舍、修饰,属于挑选性的呈现。而书信的内容往往更随心率性,有原始的情感流露,能够补白历史细节,属于真实的呈现。[10]每一封抗战家书都是独一无二的,无论是寄信人不同,还是寄信人相同、收信人不同,还是同一寄信人写于不同时期的家书,其传递的信息、表达的情感、反映的社会历史都是不同的,这种唯一性更突显其珍贵。
最后,家书还具有实物载体多样性的特点。在笔者收集到的众多资料中,抗战家书不局限于写在纸上,还以其他各种形式被保留下来。比如《符梅轩致符镇宝》家书,就是用毛笔小楷写在一块白色丝绸上的;川军将领、第七战区长官部参谋长傅常将军写给妻子的家书,被妻子刻在灯柜上,得以在战火中保存下来。
总的来看,抗战家书具有私密性、真实性、广泛性、双遗产性、唯一性和实物载体多样性的特点。厘清抗战家书的特点,就是论证了选用家书作为史料投入到学术研究中的合理性,为学术界进一步利用和开展深入研究打下基础。
二、证史与补史:抗战家书的价值与运用
目前,可以获取抗战家书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公开出版物,包括以抗战为主题的家书汇编和综合性书信集。以抗战为主题的家书汇编包括《抗战家书》《抗战家书选编》《重读抗战家书》等。综合性书信集包括个人家书集和普通书信集,个人家书集多为名人家书结集出版,比如《毛泽东书信选集》《周恩来书信选集》《左权家书》等,这类书信集以个人生活、成长、工作经历为线索,所收录家书不一定都与抗战相关,需要筛选;普通书信集如《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图说红色家书》《一百位共产党员的红色家书》等,收录书信内容多元,时间跨度较长,需要筛选出和抗战有关的书信;第二种是分散藏于各级各类博物馆、档案馆中的抗战家书,如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就将抗战家书作为一种收藏门类,广东、福建等侨乡是侨批收藏重镇,四川省建川博物馆收藏侵华日军家书2000余封,2018年由国家图书馆出版八卷本《建川博物馆藏侵华日军家书》;第三种是已经被公开但并没有结集出版,散见于报刊、网络之中,需要研究者进行搜集整理;第四种是通过走访抗战老兵等战争亲历者及其后人,对仍藏于民间的抗战家书进行广泛寻找和深入挖掘。
(一)证史:抗战家书是历史的载体之一
不同类别的抗战家书在证史这一维度上发挥不同的作用。具有一定级别的重要历史人物家书本身既属于档案,又属于文物,原件入藏包括中央档案馆、国家博物馆在内的各级档案馆和博物馆。这类家书中记录了大量历史事实,可作为原始文献加以利用。数量众多且散落在各地的民间家书,当年仅作为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真实记录和互通消息的媒介,若干年后的今天便成为那个时代的见证和缩影。无论是重要历史人物家书还是民间家书,能够对当时情形如实记录并得以在战火中保存下来,都可以成为历史的证明。
1.抗战家书生动再现时局图景
家书是当时情况的如实反映,是彼时个人经历和社会环境的真实记录。所以,基于真实性的特点,抗战家书生动叙述了战时各地区的战事进程及各群体的生活状态等细节。
“七七事变”之后,高等学府为了躲避战乱一路南迁,时任清华大学教授闻一多在给亲人的多封家书中记录了这一过程。1938年1月3日,闻一多在写给父母亲的信中说:“临大全校现又有迁云南昆明之议,并拟自购汽车十辆以供运输之用。”[11]1938年1月30日,在写给妻子高孝贞的信中说:“学生将由公路步行入滇,教职员均取道香港、海防去。”[12]1938年2月11日,在写给父母亲的信中提到学校安排进入云南的三条路线和自己的选择。[13] 1938年2月26日,在写给父亲的信中提到他们从长沙到昆明各段路程里数和交通方式等。[14]
通过这几封家书,我们可以看出清华大学南迁的部分轨迹和校方在行进过程中的种种思虑。无独有偶,清华大学教授陈铨在家书中也记录了学校搬迁一事,可与闻一多家书互作补充和印证。陈铨在1938年1月27日家书中提到:“学校昨已正式宣布搬往昆明,但今日闻又有波折……但无论如何,搬家势在必行,数日后当见分晓也。”[15]与1月30日闻一多家书互为补充,三天后校方即决定迁往云南。教员和学生陆续到达云南后,生命安全仍随时受到威胁。1940年11月,林徽因在致费慰梅、费正清的信中写道:“早晨在城里有课,常常要在早上五点半从这个村子出发,而还没来得及上课,空袭就开始了。”[16]这几封抗战家书是中国高等教育在战时艰难存活的证明,寄信人在随信向亲人朋友汇报位置行踪的同时,也表达自己对时局的认识和对国家形势与未来前途的思虑,这些都通过家书这一载体如实记录下来。
2.抗战家书流露战时社会思想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人民生活条件极端困苦,生命随时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形下,许多人通过家书抒发自己的感受,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国人对战争的真实情绪。
林徽因在战时频繁与友人通信告知生活近况与研究进展,全面抗战伊始,她在日渐糟糕的形势下尽力保持乐观的心态,并且劝慰友人以积极态度面对现状。1937年12月9日,林徽因在致沈从文的信中写道:“我们根据事实时有时很难乐观,但是往大处看,抓紧信心,我相信我们大家根本还是乐观的……”[17]经过几年颠沛流离的生活,林徽因染上疾病,1941年8月11日,她在致费慰梅、费正清的信中写道:“这二十七架从我们头顶轰然飞过的飞机仍然使我毛骨悚然——有一种随时都会被炸中的异样的恐惧……眼下,在中国的任何角落也没有人能远离战争。”[18]我们在家书中可以看到林徽因的挣扎与无奈,正如她自己所说,所有人都受到了战争的波及。此时距离局部抗战开始已整整10年,她的乐观要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被消耗殆尽了。很多抗日志士不愿做亡国奴,在家书中流露出爱国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比如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与日军决战前夕,国民革命军陆军某排长褚定侯在致哥哥的信中写道,“然吾军各师官兵均抱视死如归之决心,决不让敌渡浏阳河南岸来”[19],表达了誓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
一封封抗战家书直接体现了战时的社会思想,无论是积极还是悲观,抑或是在二者之间摇摆,都还原了那个时代的民众情绪。这种细微的战时记忆是抗战家书独特的价值,它捕捉到人性中最真实的一面,这是书写宏大场面的史书所不具备的,为抗战史研究补充了最生动鲜活的细节。
(二)补史:抗战家书多方补充史传所缺
相較于宏大的战争场面和总揽全局的战术谋略,民间抗战家书记录下普通军民积极投身抗战事业,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巨大牺牲的壮举。他们数量庞大却默默无闻,抗战家书成为后人认识他们的窗口,也成为他们被历史记住的契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书写者,抗战家书就是亲历者书写的历史,对抗战家书的关注也体现了历史眼光的下移。谢春涛在谈到民间家书的价值时曾说:一部整个历史,既包括上层认识的活动,更包括人民大众的观点。家书对于拓展历史研究的领域,对于更多更真实地反映老百姓活动的历史,从而更真实更全面地体现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历史,具有非常大的价值。[20]
1.抗战家书主体具有多元性
在广泛收集抗战家书后,笔者将家书作者进行归类整理,将其分成中国共产党各级别党政军人物、中国国民党各级别党政军人物、文化界人士、普通士兵、不同职业和身份的百姓、海外华人华侨、援华友人与第三国人士、侵华日军共8类。
虽然笔者收集的家书数量有限,但从现存的文本中可以看出从属不同党派、从事不同职业、拥有不同身份的抗日义士的身影,可以进一步对家书作者身份进行定性分析。某种程度上,一封家书可以代表一个群体,对我们了解各行各业各地区在战时的生活情况做了有益的补充,突显“全民族抗战”的内核。例如,海外华人华侨抗战家书,集中展示了身处侨居国的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和抗战举动,即使生意不景气,生活捉襟见肘,也要积极认捐,为抗战贡献力量;刘宗歆医生在1941年写给妻子的信成为中国医生抵抗日军在浙江实施细菌战的有力证明[21];出版人黄洛峰致刘大明的信为我们补充了战时出版行业艰难存活的实例,全文看似聊家常实则谈论各地书店情况的语言特点,也是特殊时局的产物[22]。
另外,在各级各类博物馆中藏有大量侵华日军家书和反映日军侵华的明信片。侵华日军在家书中真实记录了自己的“生活起居、作战经历和心理感受”[23],反映了日军在中国的残暴行径。明信片的图画内容或炫耀战功,或掩盖罪行粉饰太平,或描绘在中国的生活和中国的风景。这些明信片之所以能成为历史的证明和补充,是因为它们的印刷和发行时间为战争期间,且由日本方面发行,成为日军侵华的罪证之一。其中部分明信片为战时实寄明信片,即在明信片上书写内容并寄出,属于抗战家书的一种,虽然文字内容不具有私密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记录历史的作用,具有反映一定时期社会现实的功能。
2.抗战家书多角度诠释抗战史
因为抗战家书主体的多元性,以致其内容覆盖面广、细节丰富,可为全面诠释抗战史提供多角度的史料。抗战家书中既有对前线战争场面的描述,也有对抗战大背景下社会环境的记录。比如,通过抗战侨批,可以对滇缅公路邮路和“驼峰航线”邮路进行研究[24]。战时邮路的作用不仅在于寄送信件,更重要的是成为一条运送武器、药品等重要物资的“生命线”。信件在邮寄过程中,每到转运之处便会加盖邮戳,因而成为研究邮路的重要史料。一般来说,经过实寄的抗战家书在信封上可留下邮路痕迹,表里兼具史料价值,这也正是抗战家书不同于其他史料的珍贵性和特殊性所在。比如,王南陔在致王华林的信中记录了薪水、津贴和物价情况[25],反映出战时物价上涨,生活艰难;又如,何亮采在致妻子的家书中提到如何防空袭并抄寄了一份民众疏散避难方法[26],这是战时空袭数量频繁,民众防空意识增强的体现。
在长达14年的对日持久作战中,动员百姓参军和及时补充兵源是维系军队有生力量的重要保障,在抗战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前方战士对后方家人参军的鼓励与鞭策。方惟善在致父母亲的信中将侄子未来的选择分为上中下三等,提出“慷慨应征,为国效力”[27]才是最好的选择。王孝慈在致弟弟的信中写道:“你应立即奔上抗日的战场,在战斗的环境中创造你的人生,开辟你的前途!”[28]国难当头,家即是国,國即为家,个人命运、家庭幸福和国家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抗战家书中的谆谆教诲和自然流露的情感为从多角度进行抗战史研究补充了史料,应将其运用在学术研究中彰显价值。
余论
在将抗战家书应用到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其中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多年来,与抗战家书有关的研究成果数量有限,一是受到的关注度不够,二是与在实际利用中的困难有关。
首先,除侨批外,抗战家书存世量有限。在战争年代,形势瞬息万变,邮路风雨飘摇,性命朝不保夕,能够写一封家书并成功寄送至收信人并不是容易的事。收信人收到家书后,是否有将信件保存下来的意识是影响其存世量的又一因素。抗日战争距今已经八九十年,即使收信人有留存书信的意识,而实际中是否有条件将之妥善保存又是另外一回事。将以上三种情况叠加,带来的结果便是我们无从知晓抗战家书究竟还有多大的挖掘空间。也正因为如此,目前已经公开的抗战家书较为细碎零散,诸如同一人写的集中连贯的家书或针对同一个历史事件的不同人写的家书这种对学术研究较为有利的史料可遇不可求。
其次,已公开的部分家书残缺不全或字迹不清,这就在内容辨识方面带来一定困难。抗战家书本身就在战火硝烟中诞生,保存难度极大,且写作时间距今已经过去几十年,出现字迹褪色和污渍导致模糊不清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所以对原文进行准确识别就成为将其在学术研究中加以利用的首要挑战。
再次,在使用抗战家书时应考虑隐私权和著作权问题。家书的内容具有私密性,如果作者或者其后人不同意公开,那么学者在利用上就受到限制,研究成果可能面临不能发表的问题,所以在使用前要首先征得家书作者或者其后人的同意。公开后的家书作为史料被使用时,有关著作权的问题也要和作者本人或其家属进行协商,双方达成共识之后才可以使用,避免出现不必要的麻烦和争议。
另外,对于某些抗战家书的引用率过高,容易得出同质化结论。对于部分比较典型或受到媒体追捧以至于影响力较大的家书,在各类文章中被反复引用,而在基本史实已经非常明确的情况下,很难从这些家书中挖掘到新观点和新内容,研究成果不免有“新瓶装旧酒”之嫌。
即使有局限性和困难,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已公开的抗战家书汇集到一起就是抗战史研究的一座宝库。在即时通讯并不发达的年代,写信成为亲戚朋友、同学战友间相互沟通并传递信息的重要又常见的手段。其中一部分家书从宏观视角出发,记录了家书写作者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战场形势、战略战术的看法和思考,为研究抗战时期某一历史事件或人物提供史料;另一部分家书则记录了更多细节,为研究抗战时期的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社会史、邮政史等侧面提供史料。家书写作具有即时性,写信人把自己的近况告知远方亲朋,个人经历和周围环境得以被记录下来,使得家书能够反映战时的民众生活和社会面貌。人民群众都是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者,他们对战事的记录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幅战争场景,那些不为人知的英勇抗争,那些不被承认的侵略行为,在抗战家书中得以窥见。此外,家书中有最诚挚的情感表达和最自然的真情流露,直接体现了战时的社会思想和民众情绪,这是在一般官方档案中难以见到的。2017年初,十四年抗战说取代八年抗战说写入中小学教科书,这是对1931年到1937年局部地区抗战历史的尊重。那些写于1931年至1937年间的抗战家书,其中包含的个体情感、社会风云、战场形势为抗战时间说法的改变提供了佐证。
未来抗战家书的征集、整理与研究工作任重道远,我们无法预知抗战家书的数量,也无从得知还有哪些人能够留下珍贵的家书,但是这也正是家书之奇妙所在,它拥有无穷的生机与活力,不断为抗战史研究带来新的惊喜与挑战。
注释及参考文献:
[1]步平.烽火家书抵万金(代序)[M]//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抗战家书:我们先辈的抗战记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2-3.
[2][7]张丁.民间家书的定位及分类探析[J].山西档案, 2012(02):64.
[3]张丁.《抗战家书》:了解抗战历史的新视角[N].中国纪检监察报,2015-8-28(7).
[4]公开出版的重要历史人物家书参见张丁《〈抗战家书〉:了解抗战历史的新视角》一文。在另一篇文章中,张丁对“民间家书”概念进行了详细阐释,认为其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其存世地点,是尚没有被各级各类博物馆、档案馆收藏的家书,即保存在个人手中的家人及亲友之间的通信。此类家书主要是普通人的家书,也包括一些由于各种原因散落民间的名人家书;二是指家书作者的身份不是社会精英人物,而是广大的普通民众,他们的家书就是普通人的家书,非名人家书。参见张丁《民间家书的定位及分类探析》,《山西档案》2012年第2期。
[5]张丁.社会记忆视角下民间家书的征集与利用[J].档案学研究,2018(01):66.
[6]任继愈在抢救民间家书项目启动仪式上的讲话[EB/OL].(2005-04-10)[2022-03-01].http://jiashu.ruc. edu.cn/jsyj/6d3a35ebd4024ce2bf308d23edd20afd.htm.
[8]张丁.民间家书的抢救性征集与编研实践[J].民间文化论坛,2011(02):23.
[9]如建川博物馆藏二战时期侵华日军家书已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10]丁宗皓.两地书军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7:127.
[11][12][13][14]聞一多.闻一多书信集[M].北京:群言出版社, 2014:114,116,118,121.
[15]孔刘辉.烽火岁月家国忧思——陈铨抗战家书(1938—1939)[J].新文学史料,2017(03):40.
[16][17][18]林徽因等.林徽因书信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6:112,39,117-118.
[19][21][22][25][26][27][28]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抗战家书:我们先辈的抗战记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92,182,241-243,219,110-111,48,55-56.
[20]谢春涛在抢救民间家书项目启动仪式上的讲话[EB/OL].(2005-04-10)[2022-03-01].http://jiashu.ruc. edu.cn/jsyj/6d3a35ebd4024ce2bf308d23edd20afd.htm.
[23]尹建英,潘殊闲.建川博物馆藏侵华日军家书[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8:2.
[24]李柏达.古巴华侨银信之国际邮路考[M]//李柏达.世界记忆遗产台山银信档案及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7:248-252.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