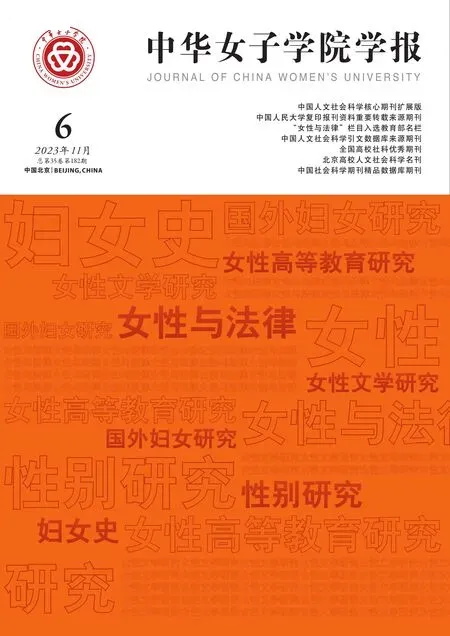乡土、学者与学术
——赵月枝访谈录
赵月枝 马 荟
被访谈人:赵月枝
访谈人和整理人:马 荟
缘起:在田野发现乡村,在乡村发现中国。2023 年7 月下旬,在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和河阳乡村研究院的支持下,“在乡村发现中国”调研团队先后在福建屏南、浙江缙云开启了跨学科、跨地域的游学交流活动。期间,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赵月枝受聘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的特聘专家和“乡村访问学者”。游学过程中,浙江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马荟对具有传播学学术背景且一头扎进乡村建设的赵月枝教授充满好奇,遂就其投身乡村建设的缘由、河阳乡村研究院的工作内容、对美好乡村的想象等话题进行了访谈。在本篇访谈中,赵月枝教授详细介绍了传播学与中国乡土社会的内在联系,以及其在浙江缙云的诸多乡村建设实践与学术交流活动,充分肯定了中国乡土社会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和美乡村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以待学术扎根乡土,乡土焕发新生。
问:您是传播学的学术背景,请问传播学与乡村振兴、乡村发展的联系是怎样的?尤其您是出于怎样的想法,投入到乡村建设事业中来的呢?
答:传播学科是一个相对新的学科,这个学科在美国起源时就有很强的倾向去关注传播技术在乡村发展中的作用,所以传播学学者关注乡村、关注技术,尤其是关注网络技术、新闻传播技术在乡村发展中的作用是其应有之义。此外,从广义的角度来看,传播学实际上关注的是人类共同体维系的问题,是关于网络、关于交流、关于意义的生产与分享的问题。既然要研究传播,就不可能不关注乡村问题,尤其对于中国而言,乡村是中华文明的基因所在,今天研究传播,就不能不关注乡村。当然了,中国的传播学从美国引入的部分有很强的西方中心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倾向,所以我回到中国乡村研究传播,一方面是回归传播学本身对乡村发展问题的关注,另一方面是希望能把这个学科重新植根于乡土中国,从乡土的视角来看传播问题。总之,我希望走出一条既有全球视野又有乡土中国立场的传播学研究路径。
为什么觉得回来特别重要?中国社会在过去40 多年经历了非常快速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现在我们又进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变期,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走向关乎整个世界的未来。中华民族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持续的农耕文明,这样的一个农耕文明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怎么样融合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中国与世界,一直是我们这一代人面对的挑战。
我是20 世纪80 年代上大学的一代人。那个时代刚好是中国进入快速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的开端。因此,就面对以上挑战而言,我们这一代人有着其他任何一代人都无可替代的使命。作为知识分子,我们更有责任和义务来思考这个问题,让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保持一些传统的智慧,与此同时又让乡村不是停留在过去,而是真正实现现代化,实现城乡融合、工农互补。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做这个工作,那么中国的城乡关系就真有断裂的危险。当年,我正是抱着这样的一种理想,或者说这样的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回到乡村来做研究的。
问:您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萌生这种非常强烈的要投身到乡村建设中来的想法的呢?您这种想法跟您的个人经历是不是也是密切结合着的?您认为您的道路跟自己作为一个女性学者有什么联系吗?
答:当然跟个人经历相关。一是出去读书的经历。1980 年,我15 岁的时候上的大学。虽然当时到城市去读书被认为是一个“跳农门”的过程,但是,根本没有时间和能力仔细去想,这一去,自己与家乡的关系意味着什么。虽然知道自己不可能回到农村工作,但起码在我的心目中,自己出去学的知识和从事的事业,对于以家乡为代表的广大农村应该是有帮助的。但是,读着读着,发现如果自己不特意回来的话,出去读书就真是一张“单程车票”,而且自己所在学科的知识也好像离乡村越来越远了。1986 年我出国留学后,虽然学术研究中有对“三农”的关切,也回来探亲和关注家乡,但乡村研究不是我的聚焦。
二是看到了乡村社会的变化。直到十几年前,我发现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城市化和现代化,好多农村都“空心”了。我也是目睹了家乡的变化,目睹很多青年人回到家乡也看不到希望,就觉得不能再等了,必须赶紧回来,以具体的行动参与到改变家乡现状的实际工作中来。
三是家庭变化的因素。原来父母在的时候,回来看看,觉得好像可以抚慰乡愁了。但是,父母都去世以后,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跟这个家乡的联系好像就断了。如果是别人的话,那可能就不再回来,但是我做了一个选择,决定把对家庭的小爱变成对家乡的大爱。所以,2014 年我回家乡办了河阳乡村研究院。
不过,回到前面的传播学科问题,对我来说,抚慰乡愁、建设家乡和发展传播学术,是三位一体的。也就是说,我的选择是有学术理性的。我认为,要发展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不只是传播学,其他所有的人文社科领域,都不可能脱离乡土中国。甘阳曾经说过,只有当我们积累了大量的关于乡土中国的知识,并能跟中国人文传统对话的时候,才是文化中国可以有所着落的时候。总之,中国要发展自主知识体系,就必须回到乡土中国,看乡土中国的变迁,在这个基础上提炼有乡土中国立场同时也具有全球视野的学术。我回到乡土中国,不只是乡愁的驱使,也不只是为了给家乡带来多少发展,而更多的是以自己熟悉又有一定代表性的家乡为田野,用学术的语言讲好中国故事。
多年前,我曾对《浙江日报》的一位记者说过,我对乡愁有三层理解。第一层次是感性的,是对家乡的一草一木的情感,对小吃、各种风物的一种感性的寄托。它使我在走遍天涯后,得到精神上的抚慰,找到心灵的安放地。第二层是知性的,就是对地方知识的兴趣。为什么我生长的这个县叫缙云?为什么这个村庄叫河阳?这个村庄的人是从哪儿来的?这个村庄什么时候建立的?对地方知识的探求,使我更加深化了对这片土地、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文明的认识。第三层次是理性的。如前所说,我们面临着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延续传统与融合城乡的挑战,这是人类从来没有过的挑战。西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走的是城市消灭乡村的道路,在北美,殖民主义者不仅建立了残酷的黑奴制度,而且灭掉了上千个原住民村庄,几乎把原住民赶尽杀绝。五千年的中华农耕文明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显然不能走这条路。所以,在理性层面,乡愁于我是一个经历了欧风美雨冲击后的中华文明对自己所求和所欲道路的探索和认知,而这必然是建立在理性思考,包括对世界历史和全球政治经济结构的思考基础上的。
这场调研,我们在福建屏南看到了文创赋能乡村振兴的前沿实践,看到了那里“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可能性,看到了只剩下18 个人的古村落是怎么被激活,成为城乡融合的新生产生活空间的。我很感慨,因为在那里,我看到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或者说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缙云,也有好多创新,包括我们这次调研的“两进两回”、生态价值转化以及强村公司等。这其中,作为新时代集体经济新形式出现的强村公司,让我感觉到是个前所未有的制度创新,非常值得我们关注。从这个意义上,作为一个学者,能见证与参与乡村建设,投入到实现共同富裕的事业中,我觉得是最幸福的事情,也是最有意义的事情。
说到性别层面,可以说有关系也没有关系吧。虽然中国社会里重男轻女的思想依然严重,但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不管是父母、学校和社会,并没有因为我是女性而歧视我。在国外的学术研究中,阶级、种族和性别被认为是三个关键身份因素。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我感觉在阶级社会里,在现有世界体系还是以民族国家为主要组织单位的语境下,国族和阶级可能比性别因素更重要。当然,如何分析,看具体的语境和分析层次。起码对我个人来说,感觉社会经济因素和族群身份在学术道路中影响更大。因此,尽管我曾开玩笑说,虽然文字中只有“游子怀乡”之说,殊不知,“游女也怀乡”,我总不能因为中国文化中只有“游子怀乡”之说,就不回乡搞乡村建设吧。总之,性别歧视客观存在,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理念根深蒂固,但自己的主体认知和身份定位非常重要。在这次的屏南研习营中,你也看到了其他许多投身乡村建设的女学者。我想我们的共同点应该是,在性别问题上不是没有关注和敏感,但是并不是只关注性别平等和以女性学者定位自己,而是把妇女解放当作社会解放的整体来理解和推进。
问:谢谢赵老师。想请问一下目前河阳乡村研究院主要在做哪些方面的工作?
答:河阳乡村研究院是一个网络式的草根民非机构,它是以项目和学术目标来开展工作的。河阳乡村研究院成立至今已经9 年了,我们做的主要事情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学术平台搭建和学术交流,主要是每年组织河阳论坛和“从全球到村庄”暑期班。河阳论坛是我们一个旗帜性的平台,其目标就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跨学科、跨界的学术活动,吸引更多人了解中国的乡村,并进入乡土。需要强调的是,这个活动的全称是“河阳论坛暨乡村、文化与传播学术周”。每年在论坛开始之前,我们都围绕论坛主题安排乡村调研和文化观摩,为学者提供理论联系实际的机会。这与一些学术会议往往先开会、后参观的套路不同。一方面,学者们带着已经有的论文来交流;另一方面,通过调研与文化观摩,也希望在缙云的所见所闻能跟学者的论文形成某种对话关系,从而使整个过程成为一个有机的思想碰撞和学术生产过程,而不是程式化的学术展演。“从全球到村庄”暑期班与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的硕博研习营类似,在设计中也贯穿了同样的理念,主要是给青年学者和硕博研究生提供东西方关系和城乡关系视野下的前沿理论与方法论,并在把他们带入乡村的过程中,使他们发展与深化自己的问题意识。
二是乡土中国的学术研究,主要是围绕与缙云有关的一些领域展开,比如缙云烧饼与乡土产业发展、乡村春晚与县域公共文化建设,等等。除了我自己团队的研究,也通过以上两个平台带动更多学者深入缙云,围绕这些议题做研究。总的来讲,就是围绕学科的前沿和这边的发展做乡土文化和乡村振兴方面的研究。此外还有研学。研学和暑期班相关,但不定期举办,主要为愿意进入乡村的高校师生提供进入缙云乡村的机会。今年清华大学也在缙云建立了社会实践基地,有两支共十几个人的硕士生团队,分别围绕乡村影视文化发展和乡贤回归这两个主题在缙云进行了调研。由于有我的指导和网络关系,学生们能以明确的问题意识、比较充分的背景知识准备以及精准的调研计划安排进入田野,从而达到调研效率的最大化。当然,我也非常清晰地认识到,我不是帮办,更不是让学生们跟着我的议程走,而是要充分发挥他们自己的积极性和主体性。比如,在行前做了充分的背景交代和必要的铺垫后,清华大学的这两支团队到缙云后,我就不仅不在场,而且几乎很少过问了。有时候,我感觉研究院像个研究中介一样,把愿意来这边研学的师生带进来,或者说他们来找我们,我们就帮助联系和落地,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三是关于国际传播和中国国际传播力建设方面的研究与实践。我知道,很少有人会把乡村与国际传播联系在一起。在我看来,这恰恰是问题所在,国际传播不能只是高高在上,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想着怎么做。尤其重要的是,我认为我们需要讲好乡村故事,通过讲好乡村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多年来,我们在请进来、走出去相结合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在把国外的学者请进来的同时,也曾让乡土文化人走出去,讲述中国乡村故事。我还在缙云仙都的独峰书院做了一个国际人文交流成果展,展示研究院多年来的国际人文交流工作。浙江工商大学的一位学者还对研究院所开展的工作进行了研究,写了一个一万多字的研究报告,甚至总结出了基于乡土文化自信的国际传播“缙云模式”。我不敢说自己创新了什么模式,但我的确提出了以乡村为聚焦讲好中国故事的路径,这就是,“从乡土文化认知中华文明,从乡村视角理解中国革命,从微观层面管窥恢宏气象,从日常体验感受中国发展”。今年八月中旬,我们就会以这样的思路为指导,以缙云为支点,开展一个近30 名中外学者跨文化交流的活动。我希望一边通过这样的活动来深化对国际传播的认识,一边也创新民间国际人文交流的形式,提高人文交流的水平。
第四,要讲好中国故事,就得先挖掘故事,所以对乡土文化的挖掘,尤其是乡村口述历史的采写,就成了研究院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的口述史是基于一些特殊群体来组织的,希望通过书写缙云各行各业中的人们的生命史,来自下而上地书写一个县域里普通人的历史,反映平凡中的不平凡。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展开多项口述史的工作。这个项目以一部河阳古民居中的村民口述史开头。当时的考量是,河阳古民居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对象的古建筑固然会说话,但这些建筑里的主人的故事同样值得挖掘和保留。以此为开端,我们把采写对象延伸到缙云各界,尤其是在缙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活中有代表性的一些群体。比如,缙云的婺剧非常有名,是全国民间戏曲之乡。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戏曲在这里能传承?如何通过婺剧的实践者来解码传统文化传承的密码?另如,缙云是全国麻鸭之乡,有过“四万鸭农闯天下”的传奇,估计全国人民都吃过缙云人提供的鸭蛋。这里有缙云鸭农筚路蓝缕的养鸭生计史,也有城乡关系的演变史,还有缺少土地的缙云在外养鸭人以及后来的养虾人如何在空心了自己的村庄的同时丰富了城市菜篮子的故事。再如,缙云壶镇是一个千年古镇,今天是缙云的工业重镇,这里当年出去“跑锯条”的农民是如何自发走上乡村工业化的道路,把一个以农耕为主的古镇发展成工业强镇的呢?也就是说,小小的壶镇是否诠释了“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总之,我们的每个口述项目既有地方特色,又有国家高度,或者说,这是我作为策划者和组织者希望达到的高度。当然,由于所有工作都是“业余”的,进展缓慢,但是我希望这一批口述史完成后,能对缙云整个工农业、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各个方面做一个全景式的描述。它不是那种县志式的概述,而是通过活生生的人,他们的生命史、他们的创业史来展现。这是一个不小的工程,所有项目都是在集腋成裘的过程中。可喜的是,今年春天,我们带着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团队做了一个相对“短平快”的项目,已经完成了一部关于缙云13 位优秀村书记的口述书稿。通过这些村书记,我们希望展现乡村中一些先富起来的个体是怎样先富带后富、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带头人作用的,从而把中国式现代化变为具体的实践。为了完成这些口述史,我几乎调动了一切能调动的力量。除了自己的学生,通过办暑期班吸引参加者,还赋能本地的文化人,为他们提供群体甚至一对一的培训,发动他们一起来参与。我认为,讲好乡村中国的故事,不仅是学者和媒体的事,还要发动更多的乡土文化人来参与。
最后,研究院也围绕乡村振兴和乡土文化复兴做一些公益性的智库工作。这无非是本着一腔热情,与感兴趣和对我们的思路有认同的各界交流,倾听他们的声音,分享我们的知识,提供我们的见解。
问:“新地球村”这个词在您的很多文章中反复出现,请问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个概念呢?
答: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在20 世纪60 年代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他的意思是由于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整个地球就像一个村庄一样,连接在一起了。这个概念很流行,非传播专业的人也可能听说过这个概念。这的确是一个很美好的概念,但是我对他的概念进行了一个否定之否定。因为麦克卢汉的概念里有技术浪漫主义的偏颇,缺少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不错,技术的发展,尤其传播技术的发展,是人类走向美好未来的基础,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了美国试图打压中国,看到了贸易战、科技战、舆论战,看到了各种脱钩断网。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在有些国家,互联网越发达,社会的撕裂越大,这不是技术能解决的问题。所以,麦克卢汉的“地球村”概念固然美好,但缺乏深刻的全球政治经济分析,他本人也并不真正关心村庄的发展,更不可能有中国乡建人或者中国意义上的乡村振兴理念。我关注全球秩序的演变,也关注具体乡村的发展,而且认为两者必须打通。我希望我们的村庄能从自在的村庄变成自为的村庄,也就是说从原来的那种自然状态的村庄,变成知道自己是谁、自己从哪儿来,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自信、自己的内生动力的村庄。现在有了网络,村庄真的能跟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能以自信的姿态真正地走向世界。还有一个就是,我希望整个世界能克服各种鸿沟,阶级也好,种族也好,身份认同也好,宗教也好。这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上来理解“新地球村”。这不是一种技术浪漫主义的想象,而是通过伟大的历史性斗争,克服现有的矛盾,走向美好的人类未来。这不是用一种文化统合另一种文化,让世界成为一个“麦当劳世界”,而是一个美美与共的世界。
正如我在一篇短文中所写的那样,在中国提出“新地球村”的想象,是有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我们有五千年持续农耕文明的智慧,有中国革命的洗礼,有乡村振兴战略、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等顶层设计,我们有不断增强的“四个自信”,有不断坚定的历史自信和历史主动性。几年前,在一个中国青年政治经济学者的年会上,我还说过,“一带一路”和“乡村振兴”犹如中华民族这只涅槃中的火凤凰的双翼,我们可以凭着它们来展开“新地球村”的想象。这次调研之后,我们会在缙云的一个小山村召开第九届河阳论坛。我们的主题是: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和性别平等。尽管西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在国际上占话语权的上风,尽管中国社会传统中的封建礼教还有一些负面的影响,中国的妇女解放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比起其他很多社会来,中国已经在包括妇女解放在内的社会解放方面取得了非常重要的进步,我们应该有充分的自信,展示这方面的成就。在一个正在蝶变中的小山村搞这样一个意在用中国经验与西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对话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的“新地球村”想象落地的一种努力呢!
问:作为一名乡建人,您能为我们描绘一下您理想中的乡村建设图景吗?
答:乡村建设的理想在官产学媒的表达中已经非常丰富了,而且正如村庄是多样的,我们不可能只有一个理想的乡村建设图景。在我看来,我们这次“在乡村发现中国”调研中考察的屏南和缙云的许多村庄,都是非常理想的乡村建设成果,而且许多发展是超出我自己的想象的。我对缙云的许多乡村建设成功典型非常熟悉,所以这次让我惊艳的是屏南艺术乡建的成功范例,这些村庄,尤其在“人人都可以是艺术家”这样的理念下激活的村庄的样态,让我几乎看到了艺术乡建的最高成就。
乡村是整体性的,它是生产、生活、生态、生命的有机统一。对于理想的乡村建设图景,我想没有比马克思所描绘的更美好的了:在那里,每个人的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上午捕鱼,下午打猎,黄昏从事畜牧业,晚上批判。所谓批判,就是我们中国传统耕读文化里的“读”,而前面的几项活动,就是广义上的“耕”。总之,理想的乡村在每个人心里都不一样,但是它一定是一个和美乡村,一定是大家安居乐业的、物质和精神都丰富的乡村。最重要的是,这必须是每个人的潜能都得到充分发挥的地方,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卷”,不像这样的每个人几乎都变成了单向度的人。
对于这样的乡建理想,我是充满希望的。十多年前,我回乡建立乡村研究院的时候,我自己圈里的好多人还沉浸在家乡衰败的悲情中。过去十多年来,尽管国际形势越来越严峻,悲观情绪也成了美西方媒体认知战或攻心术的一部分,但在缙云,在屏南,也包括我今年七月初在宁夏办“从全球到村庄”暑期班期间到宁夏以前有名的贫困地区西海固参观,我实实在在地看到了乡村振兴的成效,看到了这些地方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真实的,是很多人可以感受到的。那为什么能做到这样?我觉得就是因为有实干精神。这不是个人的行动,而是整个民族有组织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互动的结果。潘家恩老师不是经常说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机社会吗?我确实看到了这样的图景。今年春天,我与中国农业大学基层党建中心的一位领导一起在缙云调研,在听了我的口述史项目的一些内容后,他在给我的微信中写道:“中国改革开放激活了草根阶层,这些农民以冲天的干劲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这个国家。”在我看来,他们的付出和努力是我们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故事中不可或缺的。从这个意义上,对我这个小小乡村研究院的创办者来说,没有一句话比“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更令人振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