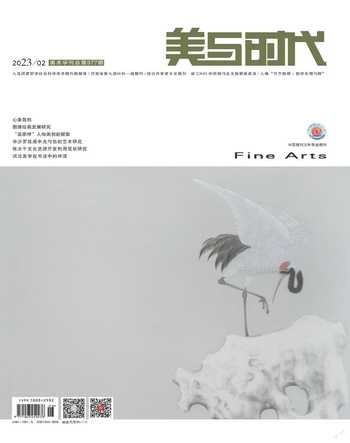“印迹·老街”系列油画作品赏析



摘 要:艺术创作通常源于某种感动。作为一位年轻的油画家,孩提时经常玩耍的故乡老街令人难以忘怀。为了留住这段美好,便用画笔通过油画创作的形式将自己的所感、所想以图像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系列作品取名为“印迹·老街”,以此缅怀那段难以忘怀的记忆。
关键词:“印迹·老街”;老街;油画;审美
对于曾经经历过的点滴,不同的人会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记录,如诗歌、绘画、音乐等。而笔者喜欢用画笔记录发生在身边的人和事,孩提时,曾在此居住和玩耍的老街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它见证了笔者的成长,陪伴了笔者的童年。为了留住那份美好,笔者决定用画笔追忆曾经居住过的老城,以引发人们对老城民俗和人文的共鸣。
一、与老街的情缘
生在江南,印象最深的是街道纵横交错,一条接着一条。邻里住得都很近,张家的院子对着李家的门,从王家的阳台能看到陈家的客厅。与小伙伴们整天满巷子里跑,或躲猫猫,或过家家,有时还会玩起警察抓坏蛋的游戏……总之,每天玩得不亦乐乎,街巷成了笔者童年时期的天堂、乐土,在那里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时光。与当下城市快节奏的生活相比,居住在老街的人们生活节奏都很慢,邻里关系也很好,他们闲来无事便会聊一上午,给人的感觉是那么平和、安详,确有一种“远亲不如近邻”之感。再回到久别的故乡时,原来的老街大都被拆,曾经具有乡土气息的热闹与喧嚣的街巷早已被林立的高楼取代。为了记录笔者孩提时的天堂——老城,让人们能够从作品中得到些许的精神慰籍,也为了使老城的民俗和文化得以延续,于是笔者创作了油画作品“印迹·老街”系列。
二、情感触发下的“印迹·老街”
著名的美术理论家王宏建说:“艺术来源于社会生活,是社会生活的反映。”[1]此语道出了社会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这从历朝历代国内外艺术家创作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如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安格尔的《大宫女》等,这些作品均是不同时代社会生活的反映。由此得知,只有贴近生活的艺术作品,才能具有动人心魄的力量,才能使观者(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更容易使人产生共鸣。秉着此创作理念,笔者在构思、选材中,专门选取具有生活气息的场景作为绘画的“质料”。许多带有斑驳痕迹的老墙和一些有历史痕迹的栅栏、斗拱、柱梁、方砖、铁丝网等元素成了笔者绘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康定斯基认为,“在画面上,一个‘点是基本元素,使空白的画面‘受孕结实;而画面上一条水平线是冷静的,像准备接受重荷的基地;一个三角形可以唤起活泼的激动”[2]。从他的话语中可知画面中元素之间搭配和谐的重要性。这些古旧墙体,以及庄重、典雅的明清木质结构的横梁、柱头、窗格、木门、方砖等,不仅蕴含着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更是一种文化的沉积,使观者生出追忆感,故笔者喜欢将它们纳入创作中。
例如在“印迹·老街”系列一(图1)中,选取了具有明清特色的院落的一角作为表现对象,房屋、门窗、廊柱等的造型均给人一种沧桑感,带有岁月的印痕。为了突出古院落的历史,运用了厚涂的肌理,同时在光线的运用上,以突出强烈的光影效果来表现。于黑白中又有色相的变化,影子的黑色和柱廊的红色相配合,黑红搭配在一起,给人以力量感。柱子的红色有微妙的色彩变化,主要地方用色较纯,次要地方用色较灰,隐于画面之中。这也是笔者对南齐谢赫六法中“随类赋彩”的体悟,即以物体本身所属的类别施以色彩。暗青色的屋顶结合了中国古建筑“绿瓦青砖”的特点,并用暗色降其色温,使之更好地融入整体画面的色调。为了不让屋顶的暗青色存在孤立感,在近景的地砖上也罩染了一层暗青色,使二者有所呼应。马蒂斯认为:“客观物象在进入画面时,需要经过翻译,油画家把他们翻译成线与色的纯平面效果,才具有绘画的价值。”[3]因此,在这幅作品中,画面每一处背光面的黑色都是有色彩倾向的,而不是会给人烦闷感的纯黑。天空和地面的受光面均是偏紫绿的冷色,以让画面冷暖平衡,中间远景的白房子是画面中最亮的部分,起着点亮画面的作用。艺术虽然源于生活,但必须高于生活,因为艺术创作不是对生活镜子式的再现,而是具有能动性的创造活动,是人主观能动的结果。只有如此,所创造出的作品才会更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画面色彩与线条如音乐的旋律般动人心弦,能引起人的情绪波动。
早在唐代,画家张璪针对艺术创作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即艺术家在创作时要以自然为师,但这种美的创作必须是经过心灵化的,是内在心灵的感悟,这对笔者启发很大。因此,在创作“印迹·老街”系列二(图2)时,在构图上便有意对房子进行了变形夸张处理,使近景的两栋楼房故意倾斜,把画面切割成一个梯形的框架。同时,又借鉴山水画中的截断法构图,在不完整中求完整,以求新立意。街景整體虽使用了焦点透视法,但某些建筑独立存在于另一个空间中,楼房上的窗户则运用了反透视的方法。画面中几乎全是直线,笔者想传递出某种力量感。光影的形也经过了仔细编排,使其在画面中起切割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近景左边房屋上的一个画面之外的房子的投影,给人意到笔不到之感。画面中的点都是些小物件,隐性的线是房屋的边,电线则是显性的。康定斯基曾说:“创作出一幅画,如同创造一个世界。”[4]的确,艺术创作确如创造一个独特的世界,需要艺术家对形、色的运筹把握,所以笔者在创作“印迹·老街”系列二《老城街景》时用色比较丰富,色彩用得较多,这增加了整体色调的把握难度,处理不好就会给人一种“花”的视觉效果,“如果色彩运用得好,并且调子和谐,色彩就能表现形体”[5]。为此,笔者看了一些画家的访谈,当看到艺术家高连保的访谈视频时,他说要想把诸多色系放在一张画面上做到既不冲突又协调,就得把每种颜色的纯度和明度都统一在一个度。因此,笔者把亮部的色彩统一在一个度,暗部的色彩又统一在一个度。画面全局中间黑,其余灰,天空亮。两侧是冷色为主,中间是暖色,但冷色中又有暖色的存在,反之亦然。这样做是为了让颜色与颜色之间相互区别而又有联系,形成统一体。这也是笔者对南朝宋画家宗炳提出的“以形写形,以色貌色”艺术主张的个人运用。在创作收尾阶段,笔者在画面的中景局部做了提亮处理,目的是使画面的点、线、面更加丰富,更能吸引观者的眼球。
艺术作品贵在独特、创新,在进行“印迹·老街”系列三(图3)的创作时,笔者描绘了一个红木色的门,视点是从半敞开的门中看到街景,视线从门中进去继而转折到街景一角(小巷)的远处,每个房屋都有各自内部的空间。近景的门是平面的,而门内中景是立体的,这样可以形成一种对比。整个构图中间密,其余疏,由此主次便拉开了。门的形象经过了一定的夸张变形处理,至于门框和门槛,将其朝不同方向做了倾斜处理,避免出现平行式的呆板感。之所以如此构图,笔者是想把整个画面从过于工整规矩的形式中解脱出来,给观者“有意味的形式”之感,以达到艺术高于生活的目的与境界。另外,门框的宽度与原有的宽度要有所不同,以便在整体中求变化。
在这幅作品的色彩处理上,笔者对内景与门的色彩做了对比处理,在地面处大量运用了冷色,以便与门的暖红形成对比。同时,在画面远景的部分配以强烈的光感,这也是画面中最亮、最突出的部分,受光部明度高且色彩暖。笔者欲通过强光的构成与光感,使画面实现具有装饰性的色彩呈现。由于红木色的门在起稿时用色太重,显得很闷不透气,于是,在反复提亮的过程中,最终通过在同类色中体现出变化。门后墙面的颜色开始处理得也不协调,感觉不入调性,后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变得和谐。受光的屋顶本来用的是深青色,但其和强光放在一起显得不太协调,于是,笔者专程逛了几趟古城,发现有暖色的屋顶,于是便进行了更改。总之,这幅作品在赋色过程中很纠结,因为绘画中表现情感的主要载体就是色彩,塞尚说过,“对于画家来说,只有色彩是真实的。一幅画首先是,也应该是表现颜色的”[6]。这一理念在后印象派代表画家凡·高的笔下首次得到充分诠释,凡·高的绘画非常强调主观感受和炽热情感的表达,他在《星月夜》中创造了旋风般的条状笔触,以表达自己不可遏制的激情与矛盾,从而把油画色彩的表现力提高到一个登峰造极的高度。这种用色彩表达情感的趋向也被野兽派画家马蒂斯发展得更为强烈,如他的代表作品《舞蹈》《音乐》充满律动感。到了后来的表现主义画家蒙克的笔下,绘画的目的只是在传达画家的内心感受,而在现代绘画中用色彩表达情感已非常普遍。笔者从大师们的身上充分认识到色彩表达情感的作用,这种认识被用于“印迹·老街”系列创作中。画老城,独特的感觉通过不同的形式组合以捕捉精神情感中的“真实”,这种旧时情怀更具深意。
三、“印迹·老街”系列作品的社会意义和内涵
“印迹·老街”系列作品是笔者多次穿梭于老城街头巷尾,置身于其中获得的新体会,也是“师法自然,成化于心”的表达。此系列作品容易把人们的思绪带回到过去,带回到人们曾世代栖居的地方,无论是斑驳的老墙,还是古旧的街道、纵横交错的电线、老式木门、别样的阁楼等,这些“印迹”不仅是岁月的记忆,还是民俗文化最深的积淀。笔者想通过绘画作品凸显老城旧有的“真实”,使人们能从作品中得到些许的精神慰藉。同时,“印迹·老街”系列也是对现代东西方美学吸收运用的结果,如凡·高、高更、马蒂斯的激情笔触、色彩的意蘊美和莫兰迪灰色系的忧郁美等。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建设节奏的加快,越来越多的老城区面临着拆迁改造,原有的城市文化遭到破坏,也许不久之后,曾经的老街文化将逐步淡出人们的视野,要想寻觅曾经老街的人文气息,恐怕只能通过绘画作品实现,这也是笔者选择创作“印迹·老街”系列的真正缘由。
参考文献:
[1]王宏健.艺术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30.
[2][3][4]戴士和.画布上的创造[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9,25.
[5]吕澎.现代绘画:新的形象语言[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28.
[6]朱伯.世界美术史[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90:631.
作者简介:
光昇,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