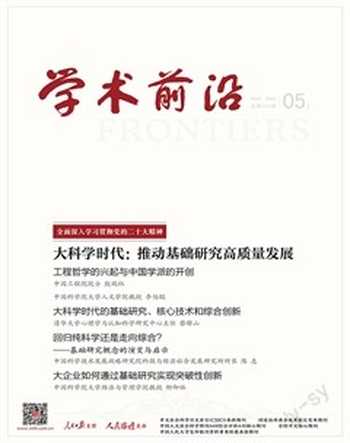工程哲学的兴起与中国学派的开创
殷瑞钰 李伯聪
【摘要】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都首先在西方开创,而工程哲学在21世纪初分别独立开创于中国和欧美,在四个关键方面,中国的开创步履甚至还早于欧美一年或数年。中国工程界和哲学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跨界合作创新,形成了工程哲学的中国学派,提出了工程哲学的“五论”框架。“五论”之中,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是开拓工程哲学的理论前提,工程本体论提出工程是现实的、直接的生产力,是“五论体系”的核心。工程方法论、工程知识论和工程演化论也都是工程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创新活动中,工程创新是创新领域的“主战场”。在工程哲学这个新学科在国内外兴起的过程中,工程哲学中国学派发挥了首创作用,发出了中国声音,体现了中国自信,作出了中国贡献。
【关键词】工程哲学 中国学派 工程本体论 工程方法论 工程知识论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08.020
人类社会中,科学、技术、工程是三种不同类型的活动,分别以三者作为哲学研究对象,可以形成三个哲学分支: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
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都是西方学者开创的,然后传播、输入到中国。而在开创工程哲学的过程中,以往那种学科发展史的“老故事”和“旧情节”没有再次重演。中国工程界和哲学界通过跨界合作互动,实现了原创性理论创新,率先独立地走上了开辟工程哲学的大道。虽然欧美同行也通过独立研究开创了工程哲学,但就几个关键步履的“各自第一步”而言,中国与西方相比还早了一年或数年。
工程哲学是工程和哲学的交集。而在世界工程史和哲学史上却长期存在“工程界不关心哲学,哲学界不关心工程”的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工程界和哲学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引下,逐步树立“工程界学习和研究哲学,提高工程界的哲学觉悟”和“哲学界学习和研究工程,提高哲学界的工程觉悟”的新风格,跨界合作,协同创新,取得了原创性理论成果,提出了由“五论”(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工程本体论、工程方法论、工程知识论、工程演化论)构成的工程哲学理论体系框架,经过20余年的努力,初步形成了工程哲学中国学派,对工程哲学这个新学科在国内外的兴起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发出了中国声音,体现了中国自信,作出了中国贡献。
21世纪之初工程哲学在中国和欧美同时兴起
根据科学社会学关于一门新学科形成标志的理论,可把21世纪之初工程哲学形成的步履简述如下。
工程哲学专门学术著作的出版。2002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今中国科学院大学)李伯聪出版《工程哲学引论——我造物故我在》,中国科学院时任院长路甬祥在为该书撰写的序言中提到,这本书“是现代哲学体系中具有开创性的崭新著作,属于马克思所说的关于改变世界的哲学”[1];2003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Louis L. Bucciarelli出版Engineering Philosophy(《工程的哲学》)[2]。2007年,中国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等出版《工程哲学》[3];同年,Steen Hyldgaard Christensen等出版Philosophy in Engineering(《工程中的哲学》)[4]。
专业学术会议的召开。2004年,中国工程院召开了“科学发展观与工程哲学”研讨会,同年还召开了中国首次工程哲学会议(至今已经召开了10次全国性学术会议)。在欧美,2006年,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召开了工程哲学研讨会;2006~2007年英国皇家工程院接连举办了7次工程哲学研讨会;2007年在荷兰召开了首次工程哲学国际会议(迄今已经召开了8次国际会议,其中第四次国际会议在北京召开)。
专门学术组织和研究机构的成立。2003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成立“工程与社会研究中心”,工程哲学是其基本研究任务之一;2004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工程哲学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成为中国推动工程哲学研究的专门学术组织和学术平台。2004年,工程研究国际网络(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Engineering Studies)在巴黎成立,工程哲学是其重要内容之一。2006年开始的WPE(Workshops on Philosophy and Engineering,工程与哲学工作坊)在2010年更名为fPET(The Forum on Philosophy, Engineering & Technology,哲学、工程和技术论坛),决定每两年举办一次国际会议。
有关学术期刊(辑刊)的出版。2004年,中国开始出版《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最初作为年刊出版,2009年,经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作为季刊出版,目前为双月刊)。2009年,Engineering Studies(《工程研究》季刊)在美国出版。这两个“同名期刊”在突出对工程的跨学科研究时,都明确地把工程哲学作为刊物的基本内容之一。2012年,Engineering Studies在创刊三年后就跻身SCI和SSCI期刊行列,这标志着包括工程哲学在内的跨学科工程研究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认可的一个新研究领域。
以上有关工程哲学开创步履的历史轨迹表明:工程哲学是21世紀之初由中国学者和欧美学者“分别独立开创”的新学科分支。在开创过程中,中国和欧美在出版学术著作、召开学术会议、成立学术组织、创立有关学术期刊四个方面都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不约而同”和“同步”现象,而中国在这四个方面的第一步都略早于欧美(早一年,有的甚至早数年)。
应该承认,在开创工程哲学的进程中,欧美学者走上开创之路的步伐虽然稍晚且不同于中国学者,但他们也是独立走上开拓工程哲学之路的。换言之,我们应该肯定“工程哲学是在中国和欧美分别同时开创的,而中国又稍稍在时间上先行”——这在学科开创史上实在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
虽然在学科开创初期,中国和欧美的学术交流较少,但随着工程哲学的逐步发展,双方的学术交流也在逐渐增强和逐步深入。
工程界和哲学界的跨界合作创新与工程哲学中国学派的形成
工程哲学是工程界和哲学界跨界合作创新的成果。如果没有工程界和哲学界的跨界合作创新,就很难形成工程哲学。回顾历史,石器时代已经有了“工程活动”,而哲学却只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欧洲和中国的哲学都诞生在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期”。
哲学诞生后,哲学与政治、科学、伦理、医学等领域都常有交集,可是,长期以来哲学和工程却罕见交集。孟子有云:“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在当时的社会条件和环境中,流行观念和主流意识形态都将工程活动视为“小人之事”,将政治、科学、伦理等领域视为“大人之事”。要在“不同类型的大人之事”之间形成交集比较容易,而“大人之事”和“小人之事”之间就很难了。正是这个“大人之事”和“小人之事”的鸿沟导致一方面在哲学界形成了忽视和贬低工程的哲学传统,另一方面在工程界形成了对哲学敬而远之和不问哲学的工程传统。这种哲学和工程相互疏远的传统虽然在近现代时期有了某些变化,但其影响在20世纪仍然相当强大。
与这个传统和状况互为表里,在中国和欧洲历史上都出现了许多“横跨科学与哲学”“横跨政治与哲学”“横跨医学与哲学”的“跨界学术成果”和“跨界人物”。然而,由于古代社会中直接从事工程活动的农民和工匠的社会地位和文化程度较低,限制了其跨界思考哲学的条件和可能性,而哲学家由于鄙视体力劳动而“理所当然”地认为工程活动中没有哲学问题。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原先的工匠阶层分化为“现代工人”和“现代工程师”,并且这两个阶层的人数和社会影响都愈来愈大。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主要由工匠阶层推动,那么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直接推动者就是现代工程师了。虽然某些具体人物可以身兼工程师和科学家两种角色,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肯定工程师和科学家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角色,二者有不同的本性和特征。
“现代科学家”是现代科学革命之后出现的社会角色与社会群体,而“现代工程师”则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出现的。前者形成较早,其角色特征相对单纯,角色自觉和角色社会定位进程都比较顺利。
由于最初的现代科学家都是“业余科学家”,这就使他们在定义科学家角色性质和特征时具有了很大的自主性和角色自觉性。他们把科学家角色“定义”为真理追求者,断定科学家没有一己私利,是全人类价值的代表者。在这种角色传统形成和固化之后,后来的“职业科学家”和社会舆论也沿袭性地接受了这一传统观点。
与现代科学家相比,现代工程师无论在角色社会定位方面还是角色思想自觉方面都遇到了更大的困难,其进程也滞后很多。
如果我们把国家科学院与国家工程院的成立分别视为科学界与工程界的“角色社会认可程度”与“角色自觉程度”的重要标志,那么可以看到,在英国,1660年就成立了皇家学会,它是世界上存在历史最长而又从未中断过的科学学会,在英国发挥着国家科学院的作用;而英国皇家工程院则于1976年才成立,比前者晚了三百余年。俄罗斯科学院成立于1724年,俄罗斯工程院成立于1990年,二者相差超过二百年。美国科学院成立于1863年,美国工程院成立于1964年,二者相差一百余年。
对于工程师的“角色社会功能认可程度”与“角色自觉”迟滞现象的形成,其深层原因就埋藏在工程师职业的内在复杂性和工程师的“角色功能张力困境”之中。
与“不直接参与”生产活动的基础学科的科学家不同,工程师的根本特征是“直接参与”生产活动,这就使工程师与工人一起成为了从事工程活动、发展生产力的最直接的社会角色。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工程师”大多是现代工厂(企业)的“雇员”,这就使工程师与工人有了共同的“雇员身份”和直接参与生产活动的“职业特征”。另一方面,工程师又是“管理”工人的生产技术管理者,这又使他们与“雇主”有了某些共同点,具有“直接参与管理活动”的“职业特征”。应该强调指出,工程活动和科学活动的本性是有很大区别的,前者主要考虑社会功利性,而后者主要考虑科学真理性,这就使工程师的角色性质和工作特征复杂起来。正如一些人所描述的那样,工程师是“边缘人”——“部分是作为劳动者,部分是作为管理者”“部分地是科学家,部分地是商人(businessmen)”[5];“工程师既是科学家又是商人”“科学和商业有时要把工程师拉向对立方向。”[6]
这种角色和职业“张力困境”使工程师的角色自觉道路不可避免地更加漫长,更加曲折。正如工人阶级在角色自觉的道路进程中经历过“卢德运动”一样,工程师在角色自觉的道路进程中也经历过所谓“工程师的反叛”[7]。“从时间上看,后者比前者晚了大约一百年;从斗争形式上看,前者采取了经济斗争和社会对抗的形式,后者采取了在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中进行‘制度内斗争的形式;但二者都成为了标志一个特定阶层在‘职业自觉方面的重要事件。”[8]虽然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工程师的反叛”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在20世纪下半叶,各个产业性工程师学会在章程中也都陆续明确肯定了“工程师的伦理准则和社会责任”,成为了标志工程师“职业和角色自觉”的关键事件。
上述状况与工程哲学在学科开创进程中的迟滞成为了互为因果的关系。
20世紀末期,情况发生了重要变化,不但“社会对工程的认识”有了新变化,而且“工程师的自我认识”也发生了改变。与这些变化互为因果,工程哲学也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了自身发展的酝酿期。在酝酿期之后,中国和欧美迅速地在21世纪之初进入了工程哲学的开创期。[9]
如果比较工程哲学在中国和欧美的开创进程,二者既有相同之处又存在差异。
1994年,中国工程院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工程界的一件大事。2000年,中国工程院又成立了工程管理学部。工程管理学部成立后,院士们一致认为在工程活动中存在着许多重大、深刻的理论问题,必须加强对工程管理和工程实践的基础理论问题和相关哲学问题的研究,这就形成了中国工程界“向哲学领域跨界合作”和提高“自身的哲学自觉意识”的新形势和新力量。
同时,中国哲学界也认识到必须提高“自身的工程意识和觉悟”,形成了向工程界跨界合作的新趋向和新动能。在这方面,作为中国哲学界重要组成部分的自然辩证法领域的专家发挥了关键作用。马克思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10]反思工程发展的历史并面对改革开放后中国作为工程大国崛起的现实,中国自然辩证法界的专家深刻认识到哲学界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对“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熟视无睹了,以往那种“忽视和贬低工程的哲学传统”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哲学专家必须“跨界”走向工程,研究工程中的哲学问题。
正是由于21世纪之初中国在工程界和哲学界同时出现了“跨界合作”和“相互呼应”的新形势,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于2004年6月召开了工程哲学高峰研讨会,七位院士和多位哲学专家参加研讨。中国工程院时任院长徐匡迪亲自到会并且发表了长达一个小时的重要讲话。徐匡迪指出:“工程哲学很重要,工程里充满了辩证法,值得我们思考和挖掘。我们应该把对工程的认识提高到哲学的高度,要提高工程师的哲学思维水平。”[11]
2004年12月,在中国工程院时任院长徐匡迪和理事长朱训的直接指导下,中国工程院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举办了“工程哲学与科学发展观”研讨会,紧接着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程哲学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工程哲学专业委员会,殷瑞钰任理事长,朱训任名誉理事长,傅志寰、汪应洛、李伯聪等任副理事长。
从2004年开始,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以系列课题研究的方式组织工程师和哲学专家合作研究工程哲学,通过20余年持续、艰辛的学术探索,先后出版了《工程哲学》(第1版和不断有新修订的第2、3、4版)[12]、《工程演化论》[13]、《工程方法论》[14]、《工程知识论》[15]。通过这些学术著作的出版,中国工程师和哲学专家提出和阐释了一个包括“五论”(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工程本体论、工程方法论、工程知识论、工程演化论)且以工程本体论为核心的、有原创性的工程哲学理论体系框架,使其成为了工程哲学中国学派形成的最重要的理论标志。
回顾工程哲学中国学派的形成过程,中国工程界和哲学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跨界合作、跨界联盟和跨界创新是一个关键因素。这个跨界联盟由两大支柱或者说是两股力量组成:一方面是以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为主力,还包括产业界和企业界的许多工程专家;另一方面是以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工程哲学专业委员会为主力,还包括高等院校和哲学研究机构的哲学专家。这个“联盟”中包括了工程专家、工程管理学家、战略工程师、哲学专家、人文学者等,他们分别供职于制造业、能源与矿业、交通运输、土木建筑、航空航天、水利、信息通讯、国防军工、医药卫生、金融、教育等不同领域。仅就参加“五论”撰写的成员而言,就有中国工程院院士20人,哲学界、教育界学者30余人,工程界、企业界人士30余人。
“五论”的理论框架是中国学派的原创性理论成果,以下对其进行简要论述。
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与工程本体论
中国学派工程哲学“五論框架”中首先提出的是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与工程本体论。
近现代以来,特别是在20世纪,中外许多学者都把技术和工程定义为“科学的应用”,这就成为了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的“科学一元论”。依据这种观点,许多学者和大众传媒都习惯性地把工程看作是“科学的应用”,把工程成就混同为或归结为科学成就,例如,美国、苏联、中国在“航天工程领域”的成就往往都被认为是“科学成就”,而未能认识其“本来面目”乃是“工程成就”。
在21世纪之初,针对“科学一元论”,我国学者提出了“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指出科学活动的核心是发现,技术活动的核心是发明,工程活动的核心是构建;科学活动的主要成果是科学概念和科学理论,技术活动的主要成果是发明专利和技术诀窍,工程活动的主要成果是直接的物质财富;从管理原则和制度规范看,科学活动、技术活动和工程活动也具有迥然不同的管理原则和制度规范。由于科学、技术、工程是三种不同的社会活动,如果分别以三者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就可以形成三个不同的哲学分支: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16]于是,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就成为了我国学者研究工程哲学的理论前提,成为了工程哲学学科进一步远航发展的“启程码头”。
“近代哲学巨擘”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作为基本的哲学箴言,而工程哲学提出了与其迥然不同的哲学箴言——“我造物故我在”,这就旗帜鲜明地宣示:工程哲学属于马克思所说的“改变世界的哲学”。
在中国工程界和哲学界合作研究工程哲学理论框架的进程中,工程本体论的提出是一个关键进展。
本体论在哲学中具有根本地位,但它同时又是意见纷纭的理论领域。中国工程师和哲学专家在研究工程本体论时,立足工程实践,明确提出,在人类社会中,“工程是直接的、现实的生产力”,强调其是与“工程派生论”迥然不同的“工程本体论”观点,强调必须立足这一工程本体论观点来分析和认识有关工程活动的各种问题。
工程本体论是立足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而提出的工程哲学理论。工程本体论认为,工程有自身独立存在的历史和现实根源、结构及其发展规律、目标指向及其价值追求,绝不能简单地把工程看成是科学或技术的衍生物、派生物。从本体论观点看工程,就是要确认工程的本根和本体地位,要依据现实直接生产力标准认识和处理工程活动中的诸多问题,由此而认识工程与科学、技术的相互关系。工程本体论肯定作为直接生产力的工程活动是最基础、最重要的人类活动,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工程活动不但塑造了社会的物质面貌,影响着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深刻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人类不仅从事工程活动,还从事科学、艺术、宗教等其他形式的活动。工程本体论不但要回答工程活动的最根本性质的问题,而且要从根本上——而不是从具体内容和细节上——回答工程活动和人类其他重要活动类型和方式的相互关系问题。
工程本体论由于突出了工程活动是发展生产力的活动而不同于某些哲学家主张的自然本体论或物质本体论,由于突出了工程活动是以人为本的活动而不同于神学本体论。工程本体论的内容深刻而丰富,需要不断发展,而不能对其进行教条化、简单化的理解。
作为独立方法类型的工程方法和工程方法论
虽然工程师、工人和工程管理者都很熟悉“具体的工程方法”,但是他们往往不太考虑“工程方法论”问题。
“具体的工程方法”不等于“工程方法论”。工程方法论是以工程方法为研究对象而进行哲学分析、哲学概括和哲学研究的过程和结果,是对工程方法的“二阶研究”和“二阶认识”。
虽然学术界有关“方法论”的论著数不胜数,并且也没有人否认工程方法是一大类具体方法,但学术界却鲜见有人研究工程方法论,这就使工程方法论成为了一个有待研究和开拓的新领域。
工程方法论之所以成为“方法论领域”中“被遗忘的角落”,原因有很多,就现代时期而言,其最重要的原因正是“科学一元论”的影响。
依据“科学一元论”——也就是“工程派生论”,“只需要有”并且“只可能有”科学方法论,而“不需要有”并且“不可能有”工程方法论,因为依据“工程派生论”观点,工程方法仅仅是科学方法的“派生方法”和“附属方法”,而不是一类“独立类型”的方法,这就“堵塞”了工程方法论的独立研究之路。
中国学者在研究工程哲学时,由于明确了工程本体论的基本观点,立“本”行“道”,也就顺理成章地在方法论领域得出了新认识和新结论:工程方法论并不是科学方法论的“派生理论”;必须肯定工程方法论是与科学方法论“并列”的方法论分支,必须把工程方法论作为一个独立的方法论分支进行新的开创性研究。
立足于这些认识,中国学派在2017年出版了《工程方法论》[17]。这本书首次对工程方法论的内容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18]。以下仅强调工程方法论的两个重要观点。
一是关于工程方法与科学方法的相互关系。一方面,需要承认这是两类不同的方法,二者存在根本区别,而工程方法论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要深入分析和研究工程方法与科学方法的不同之处;但另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否认二者存在密切联系。例如,科学方法和工程方法在结构上都是“硬件”(有关工具等)、“软件”(有关思想方法、程序等)、“斡件”(orgware,有关组织管理的原则和方法)的统一。可是,科学方法的“硬件”主要是科研仪器,而工程方法的“硬件”主要是工程设备。虽然科研仪器和工程设备也有某些重叠之处,但科学家和工程师都会承认科研仪器和工程设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类型,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在“斡件”方面,由于科研活动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科研活动的基本管理原则就是对科研活动的失败应该有很大的宽容度,甚至上千次的失败也“可以容忍”。而对于工程活动,由于它必须经过“事前的可行性论证”并且工程失败的后果极其严重,甚至导致灾难,人们无法容忍重大工程活动失败后再来第二次[19]。
二是科学活动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科学方法必须是“保证走向真理的方法”。表现在“科学问题的答案”上,科学方法必须是“保证取得唯一正确答案”的方法。一方面,在逻辑思维领域,科学方法论特别重视演绎法和归纳法的作用和意义。由于在真理面前不能讨价还价、没有妥协余地,这也成为了对科学方法的“硬约束”。另一方面,工程活动以发展直接生产力为目的,表现在“工程问题的答案”上,工程问题必然可以存在多种可能性答案,而不存在“唯一正确答案”。工程方法论特别重视启发法、集成法的作用和意义。工程活動中常常要运用“协调和权衡方法”进行“比较”“妥协”“选择”,这就深刻影响了工程方法论和科学方法论的性质和相互关系。虽然绝不能把科学活动的“自然科学真理标准”和工程活动的“生产力标准”对立起来,但对于科学活动和工程活动来说,如果忽视或混淆了“科学活动和科学方法论”与“工程活动和工程方法论”在基本性质和评价标准上的根本区别,那就必然会危害科学与工程的发展。
作为独立知识类型的工程知识和工程知识论
虽然在哲学传统特别是欧洲哲学传统中,知识论[20]一向受到重视,但由于多种原因,许多哲学家都仅仅关注对科学知识和伦理知识的哲学研究,而忽视了工程知识也是一个独立的知识类型。许多哲学家都忽视和贬低工程知识,孔子更在与樊迟的对话中,直接把工程知识排除在儒家教学知识体系之外[21],这就使工程知识论成为了知识论领域中、被遗忘的“处女地”。
21世纪以来,通过艰辛的探索和研究,中国学派出版了《工程知识论》[22],首次对工程知识论这个领域进行了初步而比较系统的论述。笔者在此仅简要讨论以下三个问题。
(1)两类物质世界和两类知识体系的划分是工程知识论的核心问题。
工程哲学认为需要承认有两类物质世界:一类是天然存在的“自然物”世界;另一类是人类出现以后才存在的“人工物”世界。二者成为了有本质区别的“两类物质世界”。
与“两类物质世界”相应,又有“两类知识”——关于自然物世界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关于人工物世界的“工程知识”。在探讨“两类物质世界”与“两种知识”的相互关系时有两个关键的认知前提。第一,在没有人类认识和人类知识的情况下天然物质世界已经存在了,它是“不依赖于人的认识而存在”的,是“无人类知识内蕴”的客观的自然物质世界。第二,如果没有相应的人类知识“在先”,就不可能出现人工物,所以它是“有知识内蕴其中”和“依赖于人类认识而存在”的物质世界。
许多古代哲学家在认识人类知识时都特别关注了人类的知识与外部自然界的关系和联系,这固然是正确的观点,可是他们却忽视了另外一类知识——有关“人工物”的“创造”和“使用”的知识。就对象范围看,“自然物世界”远远大于“人工物世界”,而就对人类的生活影响看,“人工物世界的影响”又远远大于“自然物世界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作为唯物主义者的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的交往才提供给他的”[23],这实在是一个很尖锐、很深刻的批判。
(2)从知识的内容和本性看,科学知识主要是对自然界和自然物的反映性知识,而工程知识主要是对人工世界和人工物的设计性、工程集成性、价值性知识。
从过程上看,“天然自然界”是“在先”的已存在的对象,科学活动是“在后”的认识过程,科学知识是科学认识的结果。而对于人工物的创造过程来说,却是要“先有”工程决策和工程设计,即工程知识“在先”。工程知识位于工程活动的“起点”,而人工物位于工程活动的“终点”。如果没有在先的工程决策和工程设计知识,就不可能有作为目的和结果的人工物存在。
从本性上看,科学知识是对天然自然界的“反映性”知识,而工程知识是关于人工物和人类行动的“设计—构建性”知识。如果使用哲学家常用的“实在”这个术语,可以说,科学知识是关于“已有的实在”的反映性知识,而工程知识是关于人类头脑中的“虚实在”及其“现实化”的“工程构建和集成”的价值性知识。
(3)在工程知识论领域,工程设计知识、工程集成知识、工程管理知识、工程评估知识、默会性工程知识、操作性工程知识均具有重要意义,而这些知识内容和形态都是以往的“知识论研究”所忽视的知识内容和形态。
由于人工物又被称为“器”,工程知识论也可被称为对“器”和“器理”的研究;而自然科学可被视为对“(自然)物”和“物理”的研究。由此角度认识工程知识论,可以看出工程知识论研究是整个知识论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意义十分重大。[24]
工程演化论与作为国家创新活动主战场的工程创新
工程是不断演化的,于是,工程演化论也成为了工程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工程演化研究和工程创新研究有着密切、内在的联系。
创新理论是熊彼特首先提出来的。作为经济学家,熊彼特主要是把“创新”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提出来的。熊彼特明确提出,发明不等于创新,技术和经济之间有可能出现不一致的情况。他尖锐指出:“经济上的最佳和技术上的完善二者不一定要背道而驰,然而却常常是背道而驰的。”[25]
目前,创新研究已经成为一个研究内容复杂、研究对象多样的领域,不但要研究各种各样的创新形式和类型(包括技术发明、知识创新、工程创新、制度创新等),又要研究多种多样的创新主体(包括企业、研究机构等)。在认识工程创新和知识创新的相互关系时,以下两点值得特别注意。
在创新动力方面,科学发现的直接动力往往来自科学自身理论逻辑的内在要求,而工程创新的直接动力主要来自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需求。与此密切相关,在心理活动方面,好奇心常常成为推动科学家新发现的关键心理要素。没有对科学奥妙的好奇心就难以发现科学问题和提出新的科学理论,科学就无法演进。而对于工程创新进程来说,推动工程师创新和推动工程演化的首要心理要素不是“好奇心”,而是工程师面对社会需求而产生的“社会责任心”。正是直接出于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强烈责任心,工程界人士才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工程创新之路。如果说在科学发现领域,科学家的“好奇心”往往是关键的心理要素,那么,在工程创新领域,工程师的“责任心”往往就成为了最关键的心理要素。
从工程演化论和工程哲学观点看创新,中国学派提出了一个新的重要观点:工程创新是创新活动的主战场。
工程活动是技术要素群和非技术要素群(诸多经济、社会要素)的集成和统一,必须从“全要素”和“全过程”的观点认识和把握工程活动。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以“可重复性”为基本特征,而作为直接生产力的工程活动以“唯一性”(例如,京沪高铁和青藏铁路都是具有唯一性的工程活动)和“当时当地”为基本特征,这就使创新必然成为工程活动的内在要求和特征。纵观历史,世界各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历程就是一个不断进行工程创新的过程。工程创新能力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是兴起或衰落。正如战争中既需要有“侦察兵”也必须有“主力军”一样,在“创新之战”中既要有相当于侦察兵的研发机构创新,也要有相当于主力军的企业创新。正如军事活动中侦察兵和主力军的相互作用、相互协同是军事胜利的关键一样,能否正确处理“研发领域的创新”和“工程主战场的创新”的相互关系也就成为了工程创新和产业竞争力发展的关键。人们绝不能忽视研发机构的侦察兵的作用,但也绝不能把侦察兵和主力军混为一谈。没有优秀的侦察兵,主力部队往往就没有正确的作战方向,但指挥员也不可能仅仅依靠侦察兵进行决战。工程创新是创新活动的主战场,人们必须强化在主战场上见勝负的概念和意识,不但必须重视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而且更要重视工程创新,必须深化对“工程创新是创新活动主战场”的认识[26]。
结语
就工程哲学作为一个分支学科和基本理论而言,它是全人类的学术公器,无所谓国家分野或族群分野。可是,就研究者的思想指导、理论创见、学术进路而言,不同国家的学者又会有自身特色,甚至形成不同的学派。从这方面看,工程哲学中国学派的形成,意义重大。在工程哲学这个新学科在国内外兴起的过程中,工程哲学的中国学派发出了中国声音,传递了中国话语,叙述了中国故事,作出了中国贡献,显示了中国自信。
工程哲学中国学派具有和表现出了以下几个重要特征。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以发展现实生产力、直接生产力为理论核心,以工程本体论为基本立场,努力正确认识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其他要素的辩证关系。
二是努力改变历史上工程界和哲学界相互疏离的现象,持续推进工程界和哲学界相互学习、相互渗透和跨界合作。
三是努力通过艰辛的理论探索获得了一批原创性理论成果,提出了以工程本体论为核心的工程哲学“五论”理论体系框架。
四是坚持工程哲学理论和工程实际密切联系的原则,深入工程实践调查研究,坚持理论研究和案例研究并重。
五是世界眼光和立足中国本土实际相结合,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中国学派、中国话语的建设结合起来。
目前,工程哲学仍处于学科发展的初创阶段,展望未来,工程哲学的中国学派应该努力作出更大贡献。
注释
[1][16]李伯聪:《工程哲学引论——我造物故我在》,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年,序言第1页、第10~12页。
[2]L. L. Bucciarelli, Engineering Philosophy, Netherlands: Delft University Press, 2003.
[3]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等:《工程哲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4]S. H. Christensen; M. Maganck and B. Delahousse (eds.), Philosophy in Engineering, Denmark: Academaca, 2007.
[5]S. Beder, The New Engineer, South Yarra: Macmillan Education Australia PTY Ltd, 1998, p. 25.
[6]E. T. Layton, The Revolt of the Engineer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886, p. 1.
[7]E. T. Layton, The Revolt of the Engineer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886.
[8]李伯聪:《关于工程师的几个问题——工程共同体研究之二》,《自然辩证法通讯》,2006年第2期。
[9]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等:《工程哲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6~44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7页。
[11]赵建军:《工程界与哲学界携手共同推动工程哲学发展》,杜澄、李伯聪主编:《工程研究》第1卷,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
[12]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等:《工程哲学》(第1、2、3、4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013、2018、2022年。
[13]殷瑞钰、李伯聪、汪应洛等:《工程演化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14][17]殷瑞钰、李伯聪、汪应洛等:《工程方法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
[15][22]殷瑞钰、李伯聪、栾恩杰等:《工程知识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
[18]对于《工程方法论》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国内外的“第一本工程方法论”著作,需要进行以下两点说明。一是此前已经有若干以“工程方法论”为书名的著作,但其具体内容都是关于“具体工程方法”的论述,而非对“工程方法论”的研究和论述。二是美国工程师科恩在2003年出版了《方法谈:工程师解决问题的进路》(Dicussion of Method: Conducting the Engineer's Approach to Problem Solving),必须承认这本书是具有“工程方法论特征”的著作,但其主要内容是着重论证“启发法”是特征性的工程方法,而不是对“工程方法论”理论体系的全面论述。如果可以认定科恩的著作是“第一本工程方法论”著作,则《工程方法论》就只能被认定为“第二本工程方法论著作”或“第一本论述工程方法体系的著作”。
[19]某些重大工程也可能以失敗告终,例如,美国塔科马大桥的坍塌。对于这类事件,需要从另外角度分析和研究。这类事件没有成为也不可能成为设计师“在设计时”就“准备”“工程失败”的理由。
[20]对于“认识论”(epistemology)和“知识论”(theory of knowledge)的关系,我国学者认识不一。有人认为存在区别,也有学者认为没有区别。
[21]在《论语·子路》“樊迟请学稼”章中,孔子明确地拒绝了樊迟要求学习农业知识(广义的工程知识包括农业知识在内)的要求。此章最后一句话是“焉用稼?”这就明确地在儒家教育体系中排除了学习农业和工程知识的要求。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页。
[24]李伯聪:《哲学视野中的“物”和“器”与“物理”和“器理”》,《哲学分析》,2021年第3期。
[25]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8页。
[26]李伯聪:《工程创新:聚焦创新活动的主战场》,《中国软科学》,2008年第10期。
责 编∕李思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