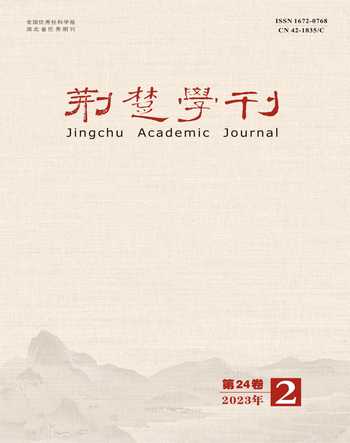南朝宫体赋中的美人书写及其审美意趣分析
摘要:宫体赋是南朝赋家、赋作题材向贵族宫廷化回归的典型,体现着南朝文人整体的创作心态与审美风尚。在美人书写上呈现出两条并行的路径:一即美人身份的不断下沉;二即美人描写的弱化与美感构筑的强化。赋家将美人作为宫体赋写作的主要对象,既满足了宫廷贵族日常生活消遣娱乐的需要,又迎合了以统治者为首倡导的重“篇什之美”的审美风尚。赋中对美人“氛围感”的精巧营构、对男女情爱的直言书写,或有“肤脆骨弱”之嫌,但从艺术创作角度来看,却是对一直以来以“扬诗守礼”为审美规范和道德标准的“写情”类题材赋作的新突破。
关键词:宫体赋;美人;南朝;审美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768(2023)02-0030-06
“宫体”题材涉及美人、美景、美物,但宫体诗赋无论是写景还是咏物,都是围绕“美人”来展开。同宫体赋相比,宫体诗中涉及的“美人”描写常因其语言的猗靡轻浮、内容的尚艳重色为人所诟病。而宫体赋虽同宫体诗有同样的创作主体,相似的创作内容,但受赋这一文体的影响,即使风格依然偏于阴柔、纤巧,但对欲望声色的书写却大大消减。前代赋中涉及美人的赋作或以“止欲归正”的讽谏为旨归,或以“神人相悦”“思妇独守”的哀情为旨归,像宫体赋这样对闺闱女性纯粹的体态形神、声貌情思的描写确为少见。过去学者对宫体赋已有较为清晰的界定,对宫体赋家笔下美人体态、心理的细致描绘也多有论及,但对赋作中美人的身份却少有分析。事实上,选取作为贵族宫廷生活点缀的美人作为赋家着意的对象,不仅在身份上同历代美人赋相比是一次明显的“下沉”,在美人的书写上亦是有别于前朝重工铺写而着意于“美感”营造的一次时代新变。
一、赋的宫廷化回归与贵族生活的点缀
赋自汉代大盛便被贵族化、宫廷化,此后却不断往文人化、生活化的方向发展,但在南朝,赋又重新回归到宫廷,成为宫廷贵族消遣娱乐奢侈生活的点缀,这不仅是南朝赋的创作主体由汉代围绕宫廷的“言语侍从”下沉到魏晋普通士族文人后,又重返宫廷贵族的一次“正统”回归,更是受时代、政治影响下,“玄虚放诞”、“逸乐苟生”的处世态度在赋家创作中的反映。宫体赋作为一种“宫闱内的、与姬妾们嬉戏的文艺,是一种令人快乐务必而又使人暗生羞耻的宫廷文艺。”[ 1 ] 110这与其创作背景和作赋主体是分不开的。
南朝混亂时代背景下文人逸乐放诞的心态是宫体赋孕育的温床。马端临《文献通考》中有言:“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今虽闾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盖亦因颜、谢、徐、庾之风焉。”[ 2 ]又有李曰刚所言:“自曹丕盗取汉室后,下讫陈后主之灭亡,其间三百六十九年(西元二二零——五八八年),为中国政治极紊乱,人性最觉醒之时代;篡夺继作,忧患频仍,党祸屠杀,人命危险。重以社会杌陧,民生困穷,儒术衰微,道佛兴起。于是人皆厌世,逸乐苟生。俗尚清谈,玄虚放诞。个人主义之浪漫思想,遂氾滥中国,得未曾有。”[ 3 ] 132日本学者冈崎文夫延续其师内藤湖南曾提出的“六朝贵族制”论,也认为“北魏异族统治背景下皇权复兴,从而使名门望族的政治权利处于‘被监视的境地。”[ 4 ]可见,混乱黑暗的政治、凋敝困穷的民生,鄙薄武事的时风使当时的文人不再拥有强烈的治世之心。朝廷在政治上偏安一隅,地域上固守江南,文人则在心态上游戏放诞,滋长了细腻柔软偏于阴柔的创作心理,体现在辞赋创作上更与“以精神之事,而托于游戏之笔”[ 5 ]的魏晋赋作不同,而是“志铭书札,亦多哀思之音,猗靡之词。”[ 6 ]同时,齐梁时期藩邸之盛也为文人集体创作提供了平台,《梁书·庚肩吾传》中讲:“初,太宗纲在藩,雅好文章之士,时肩吾与东海徐摛,吴郡陆杲,彭城刘遵,刘孝仪、仪弟孝威,同被赏接。及居东宫,又开文德省,置学士,肩吾子信,摛子陵,吴郡张长公,北地傅弘,东海鲍至等充其选。”[ 7 ] 690
所谓好恶取舍,随君上之所欲,南朝文人正是“时君爱尚文词旁求儒雅的风气”[ 8 ] 202下的追随者。宫体赋家几乎都与宫廷贵族发生过关系,且由于“皇室诸王爱文能赋者层出不穷”[ 8 ] 204,因此更滋生出一批围绕在君主、贵族身边娱乐游戏的文人。《南史·文学传序》有云:“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 9 ]1762又有《梁书·文学传》曰:“每所御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善者,赐以金帛,谒阙廷而献赋颂者,或引见焉。”[ 7 ] 685《隋书·经籍志》中载“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 10 ] 1090这样一种在统治者集结、倡导下的创作风气,形成了以萧纲、萧衍、萧绎为核心,庾肩吾、徐陵、庾信、萧子云、萧子显、刘遵、刘孝威等人为主的贵族精英创作集团。这些贵游子弟常常“熏衣剃面,傅粉施朱,架长檐车,跟高齿履,坐棋字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 11 ]纵情任性的生活状态、率性享乐的作赋心态,养成了宫体赋家偏于阴柔、迂诞浮华的创作风尚。冈村繁在《庙堂文学和宫闱文学》一文指出:“作为宫廷侍臣的文人重要的是在正经事上循规不逾,在感官享受方面则不妨率性由之。”[ 1 ] 111所以南朝赋家在接受政治“无能”后转而醉心于感官声色的享受与满足,而此时“美人”作为宫廷生活点缀的一部分,又是以贵族男性拥有物的身份存在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其姿容、丽饰、日常状态自然而然就成为贵族赋家赏玩的对象,同时或直接以美人为题或是选择与美人相关联的事物、动物、景物为题也正恰是迎合了宫体赋家纵情声色、颓废荒颓的审美趋向。因此宫体赋的发生多是围绕美人而展开的。
二、“美人”的下沉——从政治隐喻到情爱追逐
清人陈元龙编纂的《历代赋汇》中录有外集“美丽”二卷,共50篇,另有补遗2篇,共52篇。从这些赋作中描绘的女性身份来划分无外乎两支:一支是延续着“神性”身份,有着强烈政治隐喻意味以及个人理想色彩的赋作,如宋玉《神女赋》、曹植《洛神赋》、杨修《神女赋》、王粲《神女赋》等;另一支则是描写非神性女性的赋作,这其中又有分为以宫闱后妃为首的后宫思妇类赋作,如司马相如所作《长门赋》;以描写贵族侍婢为主的小赋,如蔡邕的《青衣赋》、张超《诮青衣赋》等;再者就是以围绕平民女性为描写对象的抒情小赋类,这些平民女性的身份大多是寡妇、思妇、弃妇,又或是“小女”,如潘岳《寡妇赋》、曹植《出妇赋》等。总之,在南朝以前,赋家笔下的女性身份就已经包含了社会各个层面——既有身份高贵的神女,如江淹的《水上神女赋等,又有如沈约《丽人赋》、江淹《丽色赋》、萧绎《采莲赋》这样描写普通女性容貌、生活的赋作。而宫体赋中的美人书写一个最主要的特点便是神性女性的缺失与人间女性的增加。这种转变既是美人身份由神化全面转入世俗化的改变,也是美人描写由虚到实再到虚的转换。
文人历来爱以男女情爱隐喻君臣政治,以此反映士人总归于位禄才得相背离的困窘。文人比君臣如男女的传统在中国文学中由来已久,女性也常被视为政治文化的象征符号。正如池万兴先生所言:“统治秩序的发生过程是以男女夫妇之道,经父子之亲而至于君臣之礼的。”[ 12 ] 252因此,无论是从《关雎》中的“后妃之德”到《离骚》“灵修美人以譬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 13 ]中的男女君臣之喻,还是从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中登徒子面对美色诱惑“心顾其义,扬诗守礼”[ 14 ] 27到《洛神赋》中明写对美色的向往,实则是“申礼防以自持”[ 14 ] 28、“长寄心于君王”[ 14 ] 29的表忠之辞等等,都是通过对男女情思欲念的或放纵或节制来影射对统治者的忠贞或是对礼义道德的坚守。可见,男性文人笔下的美色“均非某种客观生活的记载,而属于象征的范畴,或象征世俗的情欲,或象征至善至美的、带有终极意义的理想和‘大道。”[ 15 ]是以传统中国文化中,男性“溺情于房帷之中会被视为丧志的不肖子孙。于是士君子乃耻以闺房之情为念,开口闭口总要子曰诗云一番,方才显得庄重,即使咏及男女之事,也得以香草美人寓君臣大义。”[ 12 ] 127作为赋体文学勃兴的一个时代,汉魏赋家笔下的所塑造的神女一方面身份高贵,飘忽玄妙,另一方面却又物欲情浓,“愿荐枕席”;一方面代表庄重克己,礼义道德,另一方面却充斥着极度的欲望想象与声色铺排,极以美色诱惑之能事。这样的模式又常引发“人间女色的不可抗拒性与礼义大防的可坚守性之间的矛盾冲突,且以后者的胜利而结束”[ 16 ] 185的论述模式。但这种将对女性情思欲念的克制变成对赋家道德精神品格的褒扬与对统治者权力臣服的赋作在南朝宫体赋中却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对声色单纯的纵情享乐。
有别于在情爱肉欲中夹杂强权的政治求同类赋作,宫体赋则完全脱离了政治讽喻意味而浸润了情爱的色彩。其成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女性身份的下沉——由“主角”沦为“陪衬”。宋玉笔下的高唐神女是集情欲、神圣与美丽于一身的神祇,此后虽然还保留有描写神女的赋作,但绝大部分赋作中的女性身份不断下沉,赋家的关注点也由神界转移回人间,例如汉代枚乘《梁王菟园赋》中的平民“采桑妇”、班婕妤《捣素赋》中的“捣衣女”、王逸《机妇赋》中的“织妇”、张衡《二京赋》“舞女”,到了南朝又“下沉”为萧纲《筝赋》笔下的“女伎”、萧绎《采莲赋》中的“采莲女”、沈约《丽人赋》中的“銅街妓女”等。神女原型分身而为情欲的象征,是文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日益世俗化的必然产物,它标志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日渐低下,乃至最终沦为男性附庸和玩物[ 17 ]。但更要注意的是,南朝赋家笔下的女性即使是看似身份低微的女性,却也是贵族视野中的“底层”,赋中所展现的她们的生活也只是“贵族眼中的民间风俗画”[ 18 ] 225,与贵族生活相关联,而非现实社会中的普通底层平民百姓、底层生活。所谓沈约《丽人赋》中的“狭邪才女”、“铜街妓女”,萧纲《筝赋》中的女伎,又或是萧绎《采莲赋》中的采莲女都不过是贵族统治阶级的赏玩的对象,消遣娱乐的载体,赋中她们的生活状态、形容服饰都是“经过宫廷贵族的审美观点加工剪裁过的”[ 18 ] 224,从这一层面来看,宫廷贵族的游戏属性又与传统意义上“玩物”不同,开始上升到“玩人”(《南史·陈暄传》)。而作为贵族男性游戏笔墨的宫体赋,在赋中出现如“来脱薄妆,去留余腻”[ 19 ] 4271这样较为露骨的描写,也就十分正常了。因此,这种脱离政治化走向娱乐化、游戏化的赋作中自然而然也就没有了强烈的政治暗示意味。
三、情境统一下的“氛围感”营构
美人身份的下沉与创作技巧的衰退并无关联。南朝文人对于赋中女性的描写,非但没有局囿于汉赋家笔下一体化、总括性的集体铺绘,反而更加注重细节的刻画与情思的统一。赋家对美人的勾勒依靠的不仅是数个意象群的搭建,更强调一种情境统一下的“氛围感”。这种“氛围感”的营构无外乎两点:一即美人、美景的协调融合;二即美人的虚化与“美感”的强化。这种从对女性虚构的身份,如神女、仙等,进而落实到由具体的美人、美景所搭建的相对独立的情境世界,再到赋中不出现女性,仅以与女子相关的物件作为美人的指称,最后只留有一种“美感”而非“美人”的过程,正是南朝宫体赋以情景构筑“空灵”的意境与人物刻画的“留白”相配合下的美人书写。
南朝赋家在前人的基础上更加着意于对情境描写的点染与深化。“境非独谓景物也。”[ 20 ]但“境”的营造离不开“景”的搭建,刘师培在《论文杂记》所言:“盖南朝之诗,始则工言景物,继则惟以数典为工。”[ 21 ] 89南朝赋同南朝诗一样,都是“工言景物”的典型。周勋初在《梁代文论三派述要》中讲到:“趋新派的小赋,注意外形刻画,也注意心理活动,并且努力与情景的协调,内质和外形的统一。”[ 22 ]周说所谓梁代小赋三点在描写美人层面当是颠倒过来的。首先,宫体赋描写美人往往是侧重对“美感”的营造,这种营造所依靠的并不全是对美人外形的铺写,而在于情景的协调与统一。“氛围感”意境是在围绕美人所搭建的自然环境(风、月、云、影);场景选择(庭、楼、栏、窗);空间词语(深、闲、空、望);器物意象(烛、花、莲、扇)等的统一中得以实现的。以萧绎所作《对烛赋》为例:
“月似金波初映空,云如玉叶半从风。恨九重兮夕掩,怨三秋兮不同。尔乃传芳醁,扬清曲,长袖留宾待华烛。烛烬落,烛华明。花抽珠渐落,珠悬花更生。风来香转散,风度焰还轻。本知龙烛应无偶,复讶鱼灯有旧名。烛火灯光一只炷,讵照谁人两处情。”[ 19 ] 2445
赋虽以“烛”为题,但“烛”却只是赋家用来写人、抒情、造景的一个载体。“灯下美人”氛围的烘托,所依靠的正是外界的自然环境(月、夜、云、风)与内部虚设的场景(室内)外加指代时间流逝的词语(烛烬、烛明),以及以“烛”为中心的器物意象相统一之下构筑起的“氛围感”。同样是写“灯下美人”,与萧绎同题所作萧纲的《对烛赋》,也是在自然环境(“三更”“中夜”)、场景选择(“云母窗”“茱萸幔”)、时间词语(“渐觉”“蹉跎”)、器物意象(“明烛”“金屏”“丽盘”)四者的统一中得以实现的。南齐画家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曾提出画有六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因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摹写是也。”[ 23 ]赋家写人亦如作画,讲“气韵”,更讲“因物(即美人)象形”。讲“气韵”则如庾信《对烛赋》中写“莲帐寒檠窗拂曙,筠笼熏火香盈絮”[ 19 ] 2445,又如庾信《灯赋》中“蛾飘则碎花乱下,风起则流星细落”[ 19 ] 2442、“影来池里,花落衫中”[ 19 ] 292那般于周遭景物的烘托中写美人。这种美是赋家所追求的是一种在“空灵”意境下“虚化”的美人;因美人而“象形”则有沈约《丽人赋》与庾信《镜赋》:
“池翮荷而纳影,风动竹而吹衣。薄暮延伫,宵分乃至。出暗入光,含羞隐媚。垂罗曳锦,鸣瑶动翠。来脱薄妆,去留馀腻。沾妆委露,理鬓清渠。落花入领,微风动裾。”(沈约《丽人赋》)[ 19 ] 4271
“鬓齐故略,眉平犹剃。飞花塼子,次第须安。朱开锦蹹,黛蘸油檀。脂和甲煎,泽渍香兰。量髻鬓之长短,度安花之相去。悬媚子于搔头,拭钗梁于粉絮。梳头新罢照著衣,还从妆处取将归。暂看弦系,悬知缬缦。衫正身长,裙斜假襻。”(庾信《镜赋》)[ 19 ] 2398
《丽人赋》中的美人于光影交替中出场,出场前赋家就利用自然环境的动与静为其搭建了一种朦胧、宁静的“氛围感”,出场后美人的仪态、行容又使其看似未写“丽色”,实则确为美人的感觉。而庾信《镜赋》则是由写女子形容的鬓、眉;女子妆品颜色的朱、黛;女子发饰的钗、花以及女子的裙衫共同构成镜中的一幅“美人画”。
其次,情境描写的深化难免会带来人物描写的“留白”。对比前代赋家的重工描绘,宫体赋中“美人”书写也在不断地弱化、虚化,等到南北朝时期,单论赋家对美人形貌的书写,宫体赋明显不及前代。例如早期宋玉的《神女赋》从颜、眸、唇、眉描摹高唐神女的容颜,就连衣着配饰也都有细致的刻画,之后王粲《神女赋》中描写神女“唇譬含丹,目若澜波。美姿巧笑,靥辅奇牙。”[ 19 ] 4243更是细致到对唇、目、牙、耳的勾勒,此后更有著名的曹植《洛神赋》中对洛神的形容:“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瑰姿艳逸,仪静体闲。”[ 14 ] 28惊艳绝伦。这样再来看南朝宫体赋中对美人形貌的书写:
“芳逾散麝,色貌开莲。陆离羽佩,杂错花钿。响罗衣而不进,隐明灯而未前。……出阁入光,含羞隐媚。垂罗曳锦,鸣瑶动翠。”(沈约《丽人赋》)[ 19 ] 4271
“钗朵多而讶重,髻鬟高而畏风。眉将柳而争绿,面共桃而竞红。影来池里,花落衫中。”(庾信《春赋》)[ 19 ] 292
虽然从身份来看,这几位都非具有神性的神女,赋家描写女性容颜自然也不必用一大堆缥缈华丽的词汇,但就算是写普通女性,赋中真正直言女性容貌的句子所占比重也并不高。这是由于一方面宫体赋受制于篇幅的限制,很难同骋词大赋那般对女性形貌仪容作全方位,细致化的精工描绘,只能以女子的仪态与“鲜丽的物色和柔靡的情思”[ 24 ]相结合来描绘女性的“美感”。譬如以汉代张衡所作《西京赋》中的“女乐”描写同萧纲《筝赋》中乐妓描写对比为例,萧纲《筝赋》中写丽人抚筝动曲,对乐妓体态形神的描写精细入微,写神情有“黛眉如扫,曼睇成波”[ 19 ] 2632,绘体态又有“落横钗于袖下,敛垂衫于膝前。乍含猜而移柱,或斜倚而续弦。”[ 19 ] 2632而张衡光是对乐妓音色所引出的感觉描写就足有百余字,可见一斑。另一方面,这种选取人物的“一角”——或是衣饰、或是一件与女性相关的物件,如“熏香”“莲帐”“明镜”等来写人的方式更有助于这些宫体赋家表达他们“荡治情思的纵恣”[ 24 ]。
四、欲望声色的深化与时人开放心态的展现
南朝文人对欲望声色的深化是时人开放心态的体现。从赋中涉及美人的赋作来看,宫体赋不仅是文学摆脱政治教化意味的新的尝试,同时也反映了赋体文学创作中欲望情色的深化与题材内容的缺失与退化。
在宫体赋之前,赋家常以“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的写作模式来写情爱,所追求的也并非是纯粹地情欲声色的享乐而是强调用“定情”“止欲”的儒家道德标准来“以礼节情”。刘师培曾言:“宫体之名,虽始于梁,然侧艳之词,起源自昔。”[ 21 ] 90的确,赋中写女性之“丽色”“艳情”的传统自宋玉起便层出不穷。然而发展到汉代,一方面经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加深,另一方面赋文体本身又承担着讽喻劝诫的诗教理论,因此秦汉赋家即使歌颂、铺写女性的风姿,仪容,也多是借对女性形体,仪容的风华绝代来影射自己高洁不屈、只为效忠明君的政治求同心志。尽管赋中对美人的书写的比重远超宣扬讽谏道德,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常常是实际内容与作赋意旨相背离。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赋中写美人就形成了一种尽管“把美女写到极致, 只要没有行动, 最后‘讽谏几句, 就算是‘言论自由的范围,不犯法,也不违反道德”[ 25 ]的平衡。礼义大防的可坚守性同情欲美色的诱惑性之间像是在“微讽说而宣谕,色欢怿而我从”[ 19 ] 4244(杨修《神女赋》)中达到某种共存,而这种“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 19 ] 4278(陶渊明《闲情赋》)的评判标准在宫体诗赋创作的时代却被完全打破了。
马积高在《赋史》中有言,宫体诗赋的创作是对“以五经子史为标准来批评抒情言志的文学而提出的反驳。”[ 18 ] 22南朝赋家在通往丰缛丽彩、主情写爱的道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汉魏以来,儒家礼义道德教化观念深入人心,即使在南朝依然有一部分人坚守,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裴子野,他在《雕虫论》中讲:“淫文破典,斐尔为功,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 26 ]就是对“礼义大防”道德标准的重视。而萧纲的观点卻与这种儒家诗教观念相悖,他更重视为文的“篇什之美”。萧纲在《与湘东王书》中讲到:“既殊比兴,正背风骚,若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性情,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 9 ] 1247更有《金楼子·立言》中言:“至于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合,情灵摇荡。”[ 27 ]这种“声色大开”的创作理念虽从文学角度来看,是对政治教化功能的批判与开创,但也让后代学者认为南朝文学使“汉魏遗轨,荡然扫地矣。”是以有学者认为“南朝文学的全面独立与艺术上的新变,是以牺牲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为代价的。”[ 28 ]也出现如张溥在《梁简文帝集》题辞中那种“储极既正,宫体盛行,但务绮博,不避轻华,人挟曹丕之资,而风非黄初之日,亦时世使然乎”[ 29 ]的乱象。但不管怎么说,至此,赋家便不必“以礼义大防来克制对美色的企羡了”[ 16 ] 187,辞赋也“变为淫丽美文,以典雅丰缛为贵,不得再以诗目之矣。”[ 3 ] 11而“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采,词尚轻险,情多哀思。”[ 10 ] 1730更是形成了“君臣上下,惟以艳情为娱”的审美风尚。
时代思潮的觉醒,让文人更能观照自我情绪的抒发,进而感知他人。萧纲在《诫当阳公大心书》提出“文章且须放荡”[ 30 ],就是强调写文章要敢于打破内容、感情上的束缚,可以大胆、出格,体现在文学创作上则是追求“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以追新。”[ 31 ]南朝宫体赋家在抒写自我情志的同时,也将目光转向与他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人和事。譬如,在宫体赋中就有很大一部分是写这些宫廷贵族日常多接触到的人(乐妓、娼妓、宫女)以及这些与这些人息息相关的事物(与女子有关的器物、饰品)、景物(宫闱内或者是消遣娱乐场所)、事件(美人的娱人或自娱)等等。因此,宫体赋家对这些“身外之人”“身外之事”的感知与描绘不仅是基于对周遭事物情绪抒发下的切实体会,也是适应当时“文匿而采”“争驰新巧”的审美环境的“追新”之作。
扬雄《法言·吾子》中讲“辞人之赋丽以淫”[ 32 ],强调的是遣词用句的“丽饰”,而宫体诗文“对淫荡性生活的过度铺陈夸饰导致话语超载,诚可谓是另一种‘丽以淫了”[ 33 ]。过去,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宫体”类诗文被看做是“淫靡享乐性的软派文学”[ 1 ] 114,后来随着人们对南朝社会、文化认识的深化,开始重新审视宫体诗的文学性与文体性,但对宫体诗文为“宫阃深闺生活作轻艳的描写”[ 8 ] 208的认识却一直存在。宫廷文人“侮弄轻薄的生活态度与文章风格”[ 8 ] 207下创作出来的宫体赋作较于之前的美人描绘之所以被看作轻艳,一是因为脱离了儒学礼义教化目的,二是因为艺术形式技巧的突破。但实际上,按照赋中所描写的内容,实难称得上“轻靡”二字,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宫体诗,其所描写的内容也并全部“猗靡”。刘师培在《论文杂记》中讲:“齐、梁以降,虽多侈艳之作,然文词雅懿,文体清峻者,正自弗乏。”[ 21 ] 92又或者说,就写“艳情”而言,宫体赋受制于赋文体本身的“止欲归正”的特性,很难同宫体诗一样扣上一顶“轻靡”的帽子。宫体赋中写美人的“软艳”与同期追求情欲感官刺激以及直接描绘房中私密的宫体诗相比,明显更加含蓄隐晦。例如同样是写 “衽席之间”“闺闱之内”的“房中事”,宫体诗将“床底之言扬于大庭”(章太炎《国故论衡》),既有“簟文生玉腕,香汗浸红纱。”[ 34 ](萧纲《咏内人昼眠》),又有“愈忆凝脂暖,弥想横陈欢。”(刘孝威《鄀县遇见人织率尔寄妇》)的情欲描写。而宫体赋中的香艳描写,如“脂和甲煎,泽渍香兰”,力度就明显不如宫体诗。此外,尽管宫体赋中还有一部分以“倡妇”为题(如江淹《倡妇自悲赋》)或是描写空房难独守的倡妇类赋作,但不过是名为“倡”,实则是叙写夫妇离别的相思之苦,亦非艳情之词。或可以说,宫体赋无论是写作题材还是所抒情志都在前代有迹可循。
总之,宫体赋是南朝开放时风下特有的产物,宫体赋中对美人的书写既是迎合宫廷贵族消遣享乐生活下的游戏嬉笑之笔,符合了南朝贵族文人的创作心态与审美风尚,同时又对应着以统治者为首所倡导的重“篇什之美”的新趋向,以及在文体、声律等艺术技巧上的新探索。赋中对女性角色的精细化的描绘、对男女情爱的直言书写,或有“肤脆骨弱”“体羸气弱”之嫌,但确是对长期以来以“扬诗守礼”为审美规范和道德标准的“写情”类题材赋作的突破。尽管作为“宫廷游戏插科打诨者流”[ 8 ] 207,宫体赋无法同前代潇洒、旷达的魏晋赋相提并论,在赋史地位与成就上更无法如汉大赋那般有“熠熠焜焜”之貌,但宫体赋对“情”的大胆书写还是为之后作家在戏剧、小说等叙写男女情爱之事开拓了道路。
参考文献:
[1]冈村繁.文选之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2014:8655.
[3]李曰刚.辞赋流变史[M].台北:文津出版社,1989.
[4]冈崎文夫.南北朝的社会经济制度[M].东京:弘文堂,1935:131.
[5]冯小禄.汉赋书写策略与心态建构[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63.
[6]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M].香港:商务印书馆,1958:92.
[7]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3:690.
[8]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9]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3.
[10]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1]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6:208.
[12]池万兴.六朝抒情小赋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3]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2.
[14]于光华.评注昭明文选:卷4[M].上海:扫叶山房石印,1919.
[15]郭建勋.辞赋文体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205.
[16]胡大雷.中古赋学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17]郭建勋.先唐辞赋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60.
[18]马积高.赋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9]陈元龙.历代赋汇[M].许结,点校.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
[20]王国维.人间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8.
[21]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22]周勋初.钟山愚公拾金行踪[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207.
[23]谢赫.古画品录[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1.
[24]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170.
[25]曹旭,蒋碧薇.宫体诗与汉魏六朝赋的悖论[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51-60.
[26]李昉.文苑英华[M].北京:中华书局,1966:3873.
[27]萧绎.金楼子校笺[M].许逸民,笺证.北京:中华书局,2011:966.
[28]郭建勋.论南朝骚体文学艺术上的新变[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3):82-87.
[29]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60:212.
[30]严可均.全梁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13.
[31]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9.
[32]扬雄.宋本扬子法言[M].李轨,注.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54.
[33]李桂奎.论中国古典小说写人中的诗赋笔韵及其画境美[J].红楼梦学刊,2021(5):45-61.
[34]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1941.
[責任编辑:马好义]
收稿日期:2022-04-24
作者简介:王丹阳(1997-),女,山西太原人,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硕士,主要从事先秦汉魏六朝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