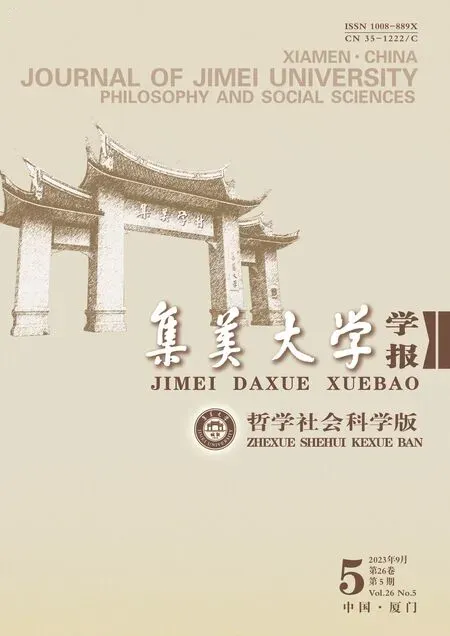美国越裔文学中的儒家文化探析
张英雪
(集美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一、引 言
中国儒家思想是越南文化的重要来源,越南民族性格的形成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虽然不同年代美国越裔作家对于越裔文学战争和身份主题的诠释各有不同(1)沿袭美国亚裔专家金惠经(Elaine Kim)对于美国亚裔文学的定义,并根据美国越裔学者阮清越(Viet Thanh Nguyen)和莫妮卡·张(Monique Truong)关于美国越裔文学内容和体裁的观点,美国越裔文学可以概括为美国越裔作家使用英语创作的,关于越裔在美生活经验、越南战争经历以及对母国集体回忆和个人想象的作品。依据内容,美国越裔文学可以分为战争主题和身份主题两大类型。关于美国越裔文学的概念起源及主题划分,参见张龙海、张英雪在《从边缘到主流:美国的越裔文学》(《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中对该问题的梳理。[1]80,但由于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保存了同母国文化的天然关联,因此不同阶段的越裔文学也都不自觉地融入了儒家思想。按照出生地及其接受越南文化程度的不同,可以将美国越裔作家划分为第1代、第1.5代和第2代:第1代出生在越南,到达美国之前就已经成年,他们接受过较为完整的越南式教育和越南文化,受儒家思想影响程度较高;第1.5代出生在越南,幼年随父母逃难或移民美国,虽未接受过完整的越南式教育和越南文化,但大多通晓越南语言,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儒家思想;同第1代和第1.5代不同,第2代出生在美国,从小接受美式教育和美国文化,多数不会讲越南语言,也很少有机会接受越南文化,受儒家思想的直接影响较小。尽管第2代受儒家思想影响并不明显,但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大多通过寻根越南历史建立自我身份,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儒家思想。
本研究以第1代越裔作家董宛梅(Duong Van Mai Elliott,1941— )的《神圣的柳树:一个越南家庭的四代史》(TheSacredWillow:FourGenerationsintheLifeofaVietnameseFamily)[2](以下简称《神圣的柳树》)、第1.5代越裔作家黎氏艳岁(Le Thi Diem Thuy,1972— )的《我们都在寻找的那个土匪》(TheGangsterWeAreAllLookingFor)[3]120以及第2代越裔作家黄丽丽(Lily Hoang,1981— )的《易》(Changing)[4]为例,分析不同阶段越裔作家作品的主要儒家思想。对于以上3部作品,国内相关论文和专著均有研究。如郭英剑主编的《美国越南裔文学作品选》中介绍了《神圣的柳树》和《我们都在寻找的那个土匪》两部作品[5]7-15;张龙海等的论文《从边缘到主流:美国的越裔文学》概述了3部作品的基本内容[1];张习涛和王永琴分别从民族主义和生态翻译视角对《我们都在寻找的那个土匪》展开分析[6-7]。目前尚未发现专门涉及以上3部作品有关儒家文化研究的文献。《神圣的柳树》再现了一段跨越2个世纪的四代家族史,从曾祖父到董宛梅,不同历史时期的个人选择体现了儒家文化中的“忠孝”伦理;《我们都在寻找的那个土匪》透过儿童视角审视越南战争后一个普通越南家庭的移民生活,尽管在美国的生活充满艰辛,但亲情和友情的温暖缓解了一家人内心的压力,表现了儒家文化的“仁爱”思想;《易》以追溯家庭故事为线索描述祖辈的难民经历,略带实验主义的写作风格展示了家族成员飘忽不定的命运,在反思战争的同时揭示了儒家文化“和而不同”的理念。本研究认为,受越南母国文化的影响,不同年代的越裔作家延续了儒家精神,其作品中的儒家文化展现了儒家思想在人类文明传承中持久的生命力。
二、《神圣的柳树》中的“忠孝”伦理
在第1代美国越裔作家当中,董宛梅占有重要地位,其回忆录《神圣的柳树》被提名普利策文学奖,是早期越裔文学中的优秀作品。董宛梅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越南一个传统的官宦之家,父亲曾在南越政府任职,官至海防省长。董氏家族历代深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入世思想的影响,历史上就有为官从政的家庭传统。除父亲之外,董宛梅的祖辈也不乏朝廷官员:祖父参加过科举考试,曾任南定省的教育行政长官;曾祖父是越南阮朝嗣德(Tu Duc)皇帝时期的内务官员,精通儒学。祖先的儒士品行有意无意地影响了董宛梅的思维方式,主要表现在其作品中的“忠孝”观念上。“忠孝”伦理是儒家最重要的伦理观念之一,儒家思想传入越南后,被越南本土文化极大吸收,影响塑造了越南民众的“忠孝”观。在《神圣的柳树》中,儒家的“忠孝”伦理在董宛梅家人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董宛梅的父辈继承了儒家“忠君”的观念,《神圣的柳树》前两章回忆了曾祖父董林和祖父董图潘“忠君报国”的经历,他们的言行举止和思想境界诠释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道德修养。1859年法国以保护传教士为名,逐步占领湄公河三角洲一带,几年内便控制了越南南部地区。1873年,法国军队轰炸并占领河内,这是法国征服南部后第一次对北方地区发起的攻击。法国军队一路北上,河内省长受伤被俘后绝食自杀,法国人随后占领了河内周边地区。在这种情况下,时任地方官员的董林积极招募并训练民兵保卫家园,在他的带领下,当地民兵终于抵抗住了来自法军的围攻。董林尽忠职守的英勇行为是儒家“忠君”思想在近代越南民族革命背景下的具体演变。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朱熹曾言:“尽己之谓忠。”儒家对于“忠”的提倡最早集中在政治性道德标准——“忠君”思想上。君王在古代是国家的象征,“忠君”思想实质上强调对国家要保持忠诚,近代便演变成为“爱国救亡”的民族思潮。儒家的“忠”在越南是一种重要的美德,“‘忠’是社会衡量一个人道德与尊严的量尺之一,儒家‘忠’的深邃内涵被越南人当作千古不变的教训来思考和追随”[8]90。作为一种伦理要求,儒家的“忠君”思想与近代越南被法国殖民的屈辱历史相结合,影响了像董林一样的儒士阶级,他们恪尽职守、英勇抗敌,将民族大义与个人命运紧密联系,在对国家尽忠的同时,也实现了自我价值。曾祖父“兼济天下”的儒士精神影响了祖父的人生轨迹。董图潘从小便以父亲为榜样,希望在事业上取得一番成就,他长大后积极参加科举考试,立志成为一名出色的汉学家。然而此时的法国殖民者却迫使儒士阶层学习法语以加强对越南的统治,面对这种形势,董图潘没有像其他官员那样对殖民者阿谀奉承转学法语,而是毅然继续学习中国古典文学[9]3-10。尽管祖父的一生并没有像他的父亲那样大展宏图,但他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寄情文字、著书立说,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儒家“独善其身”的高尚情怀。
到了董宛梅这一代,虽然信仰不同,但兄弟姐妹都参加了救国运动,尤其是三姐董宛唐,早年便追随丈夫加入了越南独立同盟会(简称越盟)(2)1941年5月,胡志明主持越共中央八次会议,决定发展游击战争并成立“越南独立同盟会”,目的是带领越南脱离法国的殖民统治,同时抵抗入侵日军。,在胡志明的带领下抵抗法国的殖民统治,延续了祖辈“尽忠爱国”的儒士精神。1947年,由于法国军队不断向三角洲地区入侵,董宛唐夫妇跟随越盟前往物质条件极其艰苦的越巴山根据地。在根据地他们一面与法军周旋作战,一面向当地山区人民宣传革命理念,为越盟招募新兵。《神圣的柳树》第八章详细讲述了董宛唐一家为了越南独立事业英勇抗争的过程。为了抵抗外族入侵,董宛唐甘愿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敌人阵地,这种舍生取义的品质与中国近代中华儿女为了民族解放事业前仆后继的斗争精神十分相似,都暗含了儒家广义上“忠君”的思想内涵,即将忠于国家利益与个人的信仰紧密结合在一起。“正是出于‘尽己之谓忠’”的儒士信条,儒家的“‘忠’就可以有非常广泛的诠释空间”[10]498。对于越南人民而言,早在陈朝时期儒家“忠君”思想就有所演变,它更加强调“人民的意愿”和“国家的权力”。例如,陈朝大儒黎文休就曾极力推崇“统一国土,稳定人心”[11]22的儒家理念,他认为国家统一是稳定人心的前提,这种将国土完整和民心安定统一起来的思想一直影响至近代越南的民族解放运动。19 世纪中叶,越南先后沦为法国、日本和美国的殖民地,经过将近一个多世纪的抗争,以胡志明为代表的越南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浪潮的鼓舞下,带领像董宛唐一样胸怀民族大义的越南儿女一起取得了国家的独立,建立了以维护国家统一和人民根本利益为宗旨的社会主义政权,这在根本上契合了越南儒士阶级历来推崇的“爱国济民”政治理想,是儒家忠义思想在近代越南独立运动中的完美体现。
儒家的“孝道”在越南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孝悌乃为仁之本”(《论语·学而》),儒家认为“孝”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最低要求,也是最根本的价值体现。受儒家孝文化的影响,越南社会始终将孝道作为社会道德规范,将其与家庭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使其成为评价个人品行的重要标准。孝文化在《神圣的柳树》中随处可见,如董宛梅重点回忆了曾祖父“守孝”的细节:在顺化任职期间,董林接到父亲病重消息后当即请求返乡探亲,但由于皇帝正值春游,探亲要求就被搁置下来。无法在父亲病床前尽孝让董林十分内疚,更为遗憾的是,在等待探亲许可期间父亲不幸病逝。为了弥补心中的愧疚,董林冒着损害仕途的风险,立即向上级提出守孝3年的请求。曾祖父的这一行为是儒家孝道在越南家庭发挥作用的典型缩影。历史上,虽然各个时期儒家学派为了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而有所不同,但孝道却一直为儒家所推崇提倡。越南在封建政权时期就将孝道列为法律条款,例如《黎朝刑律》第九十条以法律形式规定了子女对父母以及祖父母的义务:“作为子女必须孝敬父母,在(父母)老年时必须早晚奉养,不让父母衣食有所缺乏,亦不得强迫父母努力劳作才给他们提供衣食。葬礼和祭祀应注重仪式的基础地位,这才是子女的道德义务。”(3)越南封建法律将孝道的准则法律化,将孝道从道德范畴提升至法律范畴,并制定了一系列制裁违反孝道行为的措施,这在客观上起到了维护社会法纪的效果。有关越南孝道法律化的记载,参见阮胜和阮文财的专著《黎朝刑律》。[12]90需要指出的是,越南对孝道的接受在民俗传统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尤其是丧礼丧葬等习俗活动均以孝文化为指南。在《神圣的柳树》中,董宛梅提到每逢重大节日董氏家族都会组织扫墓、祭祖等祭奠先人的活动,甚至坦言自己重返越南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先人重建墓碑。从追忆祖辈对孝道准则的遵循到回顾自己对孝文化的延续,董宛梅以个人经历传递出儒家孝文化的深远影响,即使身居海外多年,深受越南文化的越裔儿女仍然不忘祖先关于孝文化的教导和训诫。
经过数千年的教化,儒家“忠孝”文化深刻塑造了越南民族性格,成为越南人民精神生活的信条和原则。对国家尽忠反映在私人领域就是对亲人尽孝,对亲人尽孝反映在公共领域就是对国家尽忠,两者相辅相成。“越南文化传统中的孝是与忠、义结合在一起的,它以爱国主义为主强调国家及社会利益的重要性”[8]92。对祖先的崇拜信仰是孝道的基础,而广义上的孝道则包含对国家的崇拜信仰,实际上,早在《论语·为政》中,孔子就将“孝”看作是为政的起点,认为君王的孝慈之治是百姓忠诚于上的原因。曾祖父董林就是将对国家的“忠”与对父亲的“孝”统一起来的典型例证。虽然董宛梅跟随父母逃难美国,但越南传统,尤其是祖辈的儒家忠孝精神仍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她的创作,并在她的回忆录《神圣的柳树》得到了有力的证明。
三、《我们都在寻找的那个土匪》中的“仁爱”思想
黎氏艳岁是第1.5代美国越裔当中成名较早的作家,处女作《我们都在寻找的那个土匪》于2003年出版,叙述了一个小女孩跟随父亲乘船逃亡到美国的故事。小说中没有暴力的场面和阴郁的气氛,透过儿童无辜的视角反思战争带给人的无奈和忧伤。虽然战争给女孩一家带来了痛苦和不幸,但依靠亲人和朋友的相互理解和救助,女孩一家最终在美国安定下来。黎氏艳岁以散文般优美的语言揭露了战后越裔群体生活的艰难,呈现出他们在异质文化中互相救助的心路历程。“仁者,爱人”,孔子从“爱人”的角度解释仁爱思想,尤其强调亲人间的血缘之爱;“仁爱”思想发展到现代主要倡导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相处。对于女孩一家而言,亲情和友情不仅帮助他们从战争中解脱出来,还支撑他们在美国开始新的生活。
仁爱的起点是对血缘至亲和家庭成员的爱。《我们都在寻找的那个土匪》继承了移民文学中家庭故事的书写传统,主要描述了女孩与父亲之间的父女关系。小说题目中的“土匪”指的是女孩的父亲,因年轻时吸食海洛因、贩卖黑烟、到处寻欢作乐等恶习,被外祖父冠上了“土匪”的名号。为了反对母亲与父亲交往,外祖父甚至不惜与母亲断绝父女关系。虽然父亲性情暴躁,但对女儿却宽厚仁慈——送她上学、陪她玩耍,就连女儿打破房东物品致使他们不得不搬家,父亲也没有半点责备。在儒家文化中,父亲角色在家庭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父亲与子女的关系对于子女的成长尤为关键,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调的是父亲在家庭和社会中的权威(4)儒家思想建立在完整的社会秩序之上并在具有完整秩序的群体中运行,群体内部形成了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权力结构,其运作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群体,自觉形成了一套规范的礼仪制度。在家庭关系中,父亲具有绝对的权威,父子/父女关系构成了“君臣”关系,对子女的成长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关于儒家文化下的中国家庭秩序,参见葛兆光的专著《中国思想史》。[13]93。在一起度过初到美国那段最艰难的日子之后,父亲与女儿建立了亲密的父女关系:女孩对父亲十分依赖,以至长大去外地后也经常梦到父亲,“在另一个梦里,我们坐在拥挤的咖啡馆角落的桌子上。通过我们坐着的样子——双腿微微分开,双手平放在膝盖上,躯干向前弯曲,和我们笑起来的样子——先是用眼睛,然后把头向后仰,我们周围的人都很清楚,我们已经成为了彼此”[3]120。父亲的慈爱为女孩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家庭氛围,女孩也因此并未像其他1.5代越裔难民那样被父辈的创伤记忆所影响,而是用一种“诗情画意”的眼光观察战后难民生活的艰辛。正如中国学者郝素玲所言,黎氏艳岁在描写越南难民生活时表现出了独具风格的才华,一般来说,多数描写越裔难民的小说会自然流露出难民生活的辛酸以及初到美国难以排遣的孤独感,但黎氏艳岁以隐晦的表达和细腻的语言让读者在阅读一个家庭辛酸往事时,并没有感觉到太多的悲伤,反而感受到了散文诗歌般语言带来的优美[14]99-100。在儒家传统哲学中,父亲角色是家庭人伦关系中的主宰,在家庭伦理中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小说中呈现出来的“父慈子孝”场景正是儒家理想家庭结构图景的展现,体现了父女关系的融洽对后代健康成长的重要作用。
除了家庭成员,儒家仁爱观还倡导对他人的互敬互爱。《我们都在寻找的那个土匪》不仅描写了父女之间的拳拳亲情,还讲述了朋友之间的深厚友谊。小说第一章叙述了父亲带着女孩和4个越南叔叔抵达美国暂居寄宿家庭、靠替房东修补房屋维持生计的故事。虽然他们来自同一个地方,没有血缘关系,但同样的命运将他们连在一起。“每逢周日下午他们就在附近散步,寻找其他越南人的踪迹。花了一段时间后,他们终于在一个游泳池大厅里找到了另外一些越南人”[3]15。通过叔叔们寻找同乡的经历可见,离散在异乡的越裔群体保持了越南传统的村落文化。历史上,越南人十分重视村落生活的共同性,每座村落都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化整体,村落里面既有城隍庙等专属的生活场地,又有民俗制度等日常的行为规范。美国越裔保持了这种村落文化,他们逃亡美国后在其聚居的地方,如加州的西斯敏斯特等地,逐渐形成了独具越南特色的生活社区——“小西贡”(Little Saigon)。社区是社会的基础,越裔群体在聚居地互帮互助、共渡难关,这种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对儒家乡邻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战国时期孟子有言:“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孟子·滕文公上》,倡导的就是同乡友人之间互相关心、互帮互助的友爱品质,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儒家“仁爱”思想对人际交往行为规范的具体表现。作为儒家思想的道德基础,“仁爱”是调节人际关系的重要手段,有利于推进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显然,越裔群体延续了儒家“仁爱”思想对同根同源异国同乡的友爱期待,在美国这个陌生的国度,越裔难民不仅在生活上互帮互助,还在精神上互相鼓舞。美国越裔学者阮富珍(Nguyen Phuong Tran)在《成为美国难民:“小西贡”的救援政治》(BecomingRefugeeAmerican:ThePoliticsofRescueinLittleSaigon)一书中描述了越南难民在美国同舟共济的场景,“这些难民在南加州找到了一个可以称之为家的空间,鲁南和其他人将情感结构融入越南音乐之中,这就产生了一种流亡的集体记忆,他们还发誓将不惜代价收回失去的精神家园”[15]48。重视人情关系是越南悠久的文化传统,也是越南传统文化与儒家文化的相同点。根据越南学者阮禄的观点,朋友道义是儒家道德术语在越南歌谣中出现次数最多的词汇,而越南的“义”和“仁”在意思上都很接近“情”[8]42,尤其是指朋友情谊,这在《我们都在寻找的那个土匪》中得到了充分印证,小说所传达的同乡之谊正是儒家仁爱思想在人际关系中的具体呈现。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也是儒家仁爱思想的外延。《我们都在寻找的那个土匪》中女孩救助被困蝴蝶、亲近自然的行为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当女孩看到一只金色蝴蝶卡在玻璃磁盘时,她的同情心不禁油然而生——她把磁盘转了又转,想尽办法要将它解救出来,甚至在晚上睡觉时,也一直担心受困蝴蝶的伤势。女孩对受困蝴蝶的怜爱和救助契合了儒家仁爱思想的博爱观。宋明理学的“万物一体”论将儒家“仁爱”内涵扩展到自然万物——“若夫至仁,则天地为一身,而天地之间,品物万形为四肢百体。夫人岂有四肢百体而不爱者哉”[16]174,这种将万物“同我”,视天地万物均为具有主观意识生命实体的观念也是儒家仁爱的最高境界。在小说中,黎氏艳岁以细腻的情感和诗意的语言描绘了女孩与自然的亲密关系,她不但怜惜受困的蝴蝶,将动物拟人化,还赋予物品以无限情感。“天空”“海滩”“月光”“鱼儿”“鸟儿”等意象反复出现,在女孩眼中,这些自然意象是家乡概念的具体化,代表着她内心挥之不去的浓浓乡情和对失去亲人的无限思念。作者将主人公的思乡之情与自然之景结合在一起,在艺术上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这与中国儒家所推崇的“天人合一”有异曲同工之处。在儒家哲学中,仁爱的核心精神是人类的同情心,这种同情心不仅适用于亲人、族人,还适用于自然界。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仁爱”思想最终可以指向“爱物”,即推己及物,突破狭义上亲情和友爱的界限,以一种博大的情怀和高尚的道德热爱自然。《我们都在寻找的那个土匪》中主人公与动物及自然意象和谐共处的场景既是其敬畏生命的外在表现,也是儒家“物我合一”精神追求在个体生命中的真实写照。
儒家“仁爱”思想包括“亲亲”“仁民”“爱物”3个层次(5)孟子对仁爱的3种境界有详细地论述,他认为:“君子之于万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仁爱始于“亲亲”,对至亲的爱是普遍仁爱的基础;“亲亲而仁民”,推己及人体现了仁爱的博爱;“仁爱而爱物”,万物之爱是儒家仁爱的终结。3个方面由内到外,由近及远,共同影响了儒家文化背景下人们的行为规范。作为第1.5代越裔作家,黎氏艳岁延续了儒家文化的仁爱思想,《我们都在寻找的那个土匪》展现了越裔难民在美国艰难环境下关爱亲人、友爱同族、亲近自然的艰辛历程,传递了儒家“亲亲”“仁民”“爱物”的仁爱力量。
四、《易》中的“和而不同”理念
作为一名学者型二代越裔作家,黄丽丽早在学生时代就开始了文学创作。小说《易》曾获2009年笔会开放图书奖(PEN Open Books Award),作品借用儒家经典著作《易经》中“卦”和“阴阳”的概念(6)《易经》包括《连山》《归藏》《周易》3部易书,现存的只有《周易》。《周易》将阴阳解释为:64卦首乾次坤,乾为纯阳,坤为纯阴,故谓之纯卦;后面62卦则阴阳杂陈,故谓之杂卦。这便给人以强烈的感受,即乾坤二纯卦之“和”产生了后面的62杂卦。参见杨庆中.多元文明和谐共存的哲学基础[J].学术前言,2013(18):81-85.[17]82。一方面呈现出越裔难民在失去身份后的惆怅和夹在两种文化中被撕裂的痛苦;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意义多重性和文化多样性社会的神圣憧憬。黄丽丽将“卦”理解为——要么是断开的(“阴”),要么是不间断的(“阳”)六边形,以变化各异的“卦”为形式载体,表达出对儒家“和而不同”理想王国的美好向往。
小说《易》以一种在随机事件中寻找秩序的方法为读者提供了认识越裔历史的新方式:内容上,种族歧视、性侵犯、父母疾病、朋友背叛等不幸遭遇通过杰克和吉尔回溯家庭历史的方式展现;形式上,64章节代表64卦,通过讲故事的形式将越裔难民的叙事线索联系起来。以两性关系为基础,小说追溯了女性在传统儒式家庭中地位的变化过程。在传统儒家文化中,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着辅佐丈夫、养育子女、照顾家人的责任。这一观点也深刻地影响了越南传统观念对于女性在家庭中的分工期待:越南社会是典型的“男权社会”,女性被鼓励安分守己地照顾家庭、生养子女,依照“从夫”之道服从丈夫。从母亲和女儿的处境可以窥探女性在越南传统家庭中的地位:在家里,母亲总是保持沉默,当父亲“争吵”“讲道理”“边生气边争吵时”时,母亲依然保持沉默,家里只有一种声音,那便是“父亲的声音”;在学校,女孩认识到“争论是不好的、冲突也是不好的”,甚至连受到骚扰也觉得“是可以接受”的。美国学者谢丽尔·格伦(Cheryl Glenn)将“沉默”界定为“有功能的缺席”,将沉默视为是一种实质性行为,可以独立传递信息。格伦尤其强调了性别化和种族化的沉默行为,提出边缘群体使用沉默策略具有很强的政治功效,沉默不是“简单的被动”,无论是支配性和压迫性的,还是“抵抗性和压迫性的”,它都可以用来达到与言行同样的目的[18]155。小说中母亲和女儿虽然成长环境不同,但都采用“沉默”策略应对家庭和社会对于女性自我身份的狭隘设定,无论是母亲的隐忍退让,还是女儿的主动抗拒都揭示了两代越裔女性自我身份的探寻过程。越裔女性的生存现状展示了女性与男性的地位差异,这既反映出作者对女性长久以来“第二性”地位的不满,同时也将尊重差异性变为一种政治诉求并以“阴阳”对立统一的形式表达出来。
随着越裔作家新生力量的不断兴起,越裔文学在承接传统儒家观念的基础上紧跟现实主义文学潮流,与此同时,第三次女性主义思潮的到来也极大地改变了越裔女性的思维方式,这就使美国越裔文学、尤其是越裔女性文学在主题思想上开始发生转变。黄丽丽从小便接受美式教育,她将东西方思维带入文学创作——在《易》中,黄丽丽从东西方两种文明审视女性的家庭和社会角色。她认为,一方面女性依然承担儒家传统家庭对女性生殖及养育子女的角色要求;另一方面,女性开始逐渐跳出父权制度下的二元对立思维,在认识两性生理差异和社会分工不同的基础上,追求更加均等的家庭地位和社会机会。建立在尊重差异基础上的两性关系符合了传统儒家思想和新儒学对于多元化社会与多样性文化的要求。作为儒家经典著作,《易经》阐释了天地间万象变化的规律,包括宇宙生成论和阴阳学说等朴素的辩证法则,它将宇宙阴阳的理念发展到“男女、夫妇、父子、君臣”等一系列具体“相克相生”的关系之中。男女两性关系是阴阳共生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序卦传》中曾记载:“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17]82从上述记载可见,《易经》不仅阐述了阴阳运行之道,阐释“男女、夫妇、父子、君臣”的权力关系是对阴阳秩序的维护,还将差异性视为调节不同权力关系的关键。小说以《易》为书名本身就是对儒家“和而不同”理念的宣扬。在后记中,作者再一次强调:“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这个故事没有什么新意,它不是我创造的。这仅仅是《易经》的一个新版本,尽管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去精确,你将会发现现实中仍然存在诸多差异,这些都是有待发现的客观事实。”[4]133小说以越裔女性为关注对象,探索女性在东方传统儒家文化和西方异质文化中的弱势地位,呼吁现代社会对女性生存境遇的关怀,符合儒家所强调的“因人而异”和“和而不同”的思维方式,是对处在不同权力关系中个体、尤其是弱势群体命运的深切关注。
此外,作者将儒家《易经》中“阴阳”有别的概念视为越裔家族叙事的内在隐喻,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对东方古老文明的侵袭。小说多次以父母亲视角回忆越南难民的流亡经历:由于语言不通,父亲由原来一位受人尊敬的画家沦为一名卑躬屈膝的清洁工,随之而来,母亲也从一位对生活充满热情的职业女性变为一名少言寡语的家庭妇女。以普通越裔家庭为参照对象,黄丽丽在创作中重新审视东西方文明,将越南战争看作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东方国家发起的殖民掠夺,从根本上体现了西方国家对待东方文明的傲慢与歧视。在儒家文化看来,“和而不同”不仅表现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方面,还表现在民族国家之间以及不同民族文化等多种层面上。儒家所提出的“天下一家”“亲仁善邻”等协调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理念,从根本上倡导不同文明要以平等的姿态和包容的精神进行交流和合作。对此,张岱年先生提出:“‘和而不同’这一命题所表达的基本意涵是要承认‘不同’,在‘不同’基础上形成的‘和谐’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17]81阴阳交互衍生出来的多元文明格局是“和而不同”理念的重要理论来源,只有和谐共存、共同发展才能促进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在小说中,黄丽丽以“和而不同”理念反观美国对越南事务的粗暴干涉,认为这种灾难如同阴阳失调之于身体病痛一样难以治愈,传达出只有在尊重多元和差异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真正人类文明的强烈夙愿。
天、地、人“和合共生”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命题。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国际上倡导的构建和谐世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就是提倡多元文明和谐共存。习近平总书记以“和”文化理念提出对待世界文明的四大原则,并强调:“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要理性处理本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差异,认识到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是独特的,坚持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不攻击、不贬损其他文明。”[19]儒家“和而不同”思想为解决当代世界难题提供了重要启发。在小说《易》中,黄丽丽将儒家《易经》阴阳相生概念引入越南战争难民叙事,一方面表达了对越裔女性及整个越裔难民群体命运的关注;另一方面也流露出对和谐人类世界的朴素向往,进一步体现了儒家思想在人类文明传承中的持久生命力。
五、 结 语
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儒家思想已经内化为越南民族精神的一部分,美国越裔作家与越南母国之间的天然关联使其不同程度吸收了越南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忠孝”“仁爱”“和而不同”等核心儒家思想在越南不断民族化和本土化,逐渐形成具有越南特色的儒家规范:“忠孝”伦理更为强调尽忠职守的爱国精神;“仁爱”思想着力推崇和谐友爱的人伦关怀;“和而不同”理念旨在探寻求同存异的生存准则。越南战争结束后,具有越南特色的儒家思想不仅未在美国越裔族群中消失,反而以多种形式出现在不同时期的越裔文学当中,这不仅体现了各个年代越裔作家对儒家文化的继承,也反映出儒家智慧的强大生命力及其对现实世界的指导价值。
——由刖者三逃季羔论儒家的仁与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