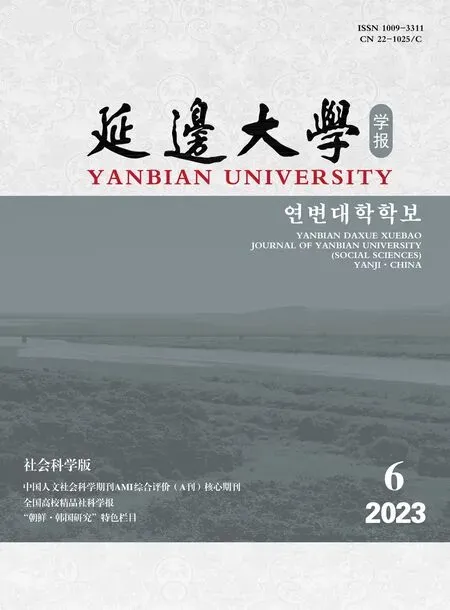韩国式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与韩国人口危机
李连波 汪根松
韩国在2020年首次出现了人口负增长,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发布的《2021年世界人口情况报告》,韩国的总和生育率连续两年排在198个国家中的倒数第一位。(1)《联合国人口基金会:韩国总和生育率连续两年全球垫底》,https://m.gmw.cn/baijia/2021-04/15/1302232990.html。韩国人口数量在2022年延续了下降趋势,根据韩国行政安全部公布的数据,截至2022年12月31日,韩国户籍登记人口同比下降0.39%,(2)《韩国人口连续两年减少》,http://world.people.com.cn/gb/n1/2023/0116/c1002-32607564.html。面临人口危机。韩国的人口危机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经济低迷、失业率攀升和房价高企等宏观经济因素外,以“三抛一代”(抛弃恋爱、抛弃结婚和抛弃生育)为代表的韩国年轻人价值观的变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女性的角度看,韩国长期存在的性别压迫使许多女性选择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实际上,当代韩国女性的地位与过去相比已有了根本改善,这与韩国女性长期的斗争分不开。韩国的女性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受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较大,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高潮。然而,随着女性主义理论的“后现代”转向,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在韩国占据了主流,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逐渐衰落。在韩国资本主义矛盾加剧和财阀垄断资本日益将女性作为榨取利润的对象的背景下,有必要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传统,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以揭示韩国人口危机背后的深层原因。
一、韩国性别压迫问题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韩国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儒家传统观念的影响下,韩国过去往往以家庭为单位从事所有生产活动,女性只有依靠家庭才能生存。(3)[韩]朴基南:《个人化时代女性运动方向探索——基于韩国女性民友会成员访谈的研究》,《女性主义研究》2012年第1期,第73-116页。在高丽时期及之前的朝代,韩国的男女地位相对比较平等,但是自朝鲜王朝全面接受程朱理学,采用了儒家严格的身份制度后,压迫女性的父权制得到了体制的保障。(4)[韩]韩国女性研究所:《新女性学讲义》,首尔: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62-65页。虽然现代韩国女性的地位与古代相比有了根本改善,独立和平等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女性的活动范围已从家庭走向社会,但儒家传统观念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并在家庭生活和职业发展的各个方面限制了女性的发展。例如,儒家性别意识对照料的代际交换产生了重要影响,按照韩国传统观念,儿子主要提供金钱支持,儿媳则有责任照料公婆。传统的性别角色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韩国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公婆和丈夫对职场妈妈照料父母的责任有较大的控制权。这种由女性承担照料工作的观念并未发生根本变化,韩国的职场妈妈不得不同时照顾老人和孩子。韩国政府虽然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改善抚育儿童和照料老人工作,但仍然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促进有偿和无偿劳动在男女之间平等分配,而这首先需要转变与性别角色相关的文化。(5)Sirin Sung,“Gender,Work and Care in Policy and Practice:Working Mothers’ Experience of Intergenerational Exchange of Care in South Korea”,Critical Social Policy,Vol.38,No.3(2018),pp.589-608.
对于韩国女性遭受压迫的另一个根源——资本主义制度,目前仍缺乏深入的分析。即使有的研究提到韩国资本主义制度对女性的压迫,也往往从“资本主义一般”的角度进行分析,未考虑到韩国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及其压迫韩国女性的特殊机制。
从“资本主义一般”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揭示了性别压迫的资本主义根源,并将消除性别压迫与反资本主义斗争联系在一起。虽然马克思并未系统分析女性问题,但他在《资本论》中多次谈到资本对女性的剥削和压迫。首先,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通过占有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增加资本剥削的人身材料”,(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82页。这些“廉价的”剥削材料无疑起到了扩大产业后备军、削弱男工反抗和增加资本利润的作用。其次,马克思指出,资本利用女性温顺的天性来加重对她们的剥削,“劳动资料作为资本——而且作为资本,自动机在资本家身上获得了意识和意志——就受这样一种欲望的激励,即力图把有反抗性但又有弹性的人的自然界限的反抗压到最低限度。而且,由于在机器上劳动看来很容易,由于妇女和儿童比较温顺驯服,这种反抗无疑减小了”。(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4页。最后,马克思用《工厂视察员报告》中的大量材料说明了过度劳动对女性身体的损害,以及矿山劳动等不适合女性从事的工作对女性精神、道德的伤害。马克思指出:“在矿井禁止使用妇女和儿童(10岁以下的)以前,资本认为,在煤矿和其他矿井使用裸体的妇女和少女,而且往往让她们同男子混在一起的做法,是完全符合它的道德规范的,尤其是它的总账的。”(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2页。
马克思的以上分析及其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资本积累理论和价值理论等,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性别等级和身份的结构特征,以及考察女性如何从属于特定的资本主义剥削方式。(9)Silvia Federici,“Notes on Gender in Marx’s Capital”,Continental Thought &Theory:A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Freedom,Vol.1,No.4(2017),pp.19-37.20世纪60年代,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提出了“家务劳动”的概念,指出正是家务劳动的无偿性造成了女性劳动的系统性低估及女性的从属地位,并提出了家务劳动社会化和家务劳动工资化等倡议。此外,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规训和压迫女性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莎朗·史密斯认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迫使男女双方坚守被严格限定的性别角色,包括将女性培养为从属于家庭中男性养家者的家庭主妇,而妇女照料家庭的角色使她们沦落为二等公民的地位,因为其首要责任和最大贡献被认为是满足家庭的需要。(10)[澳]莎朗·史密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妇女解放》,《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7期,第79-86页。从这个角度看,资产阶级的女性主义理论也起到了按照资本积累的要求规训和塑造女性的功能。
韩国作为资本主义国家,以上基于“资本主义一般”的分析框架无疑对其是适用的。然而,我们的分析不能停留在一般的理论层面,因为它只能解释存在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现象。我们认为,实现从一般到特殊的跨越,需要从现实和理论两个方面着手。从现实方面看,我们需要进一步考察韩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性,分析其特殊的矛盾、危机以及压迫女性的特殊机制;从理论方面看,我们需要揭示女性主义理论在韩国的发展及其对女性意识、发展和运动的影响。
下文主要从上述两个方面展开分析。除了在现实方面考察韩国资本主义的矛盾、危机及其压迫女性的特殊机制,理论方面我们主要关注两点:第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理论的后现代转向及其对韩国的影响。韩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女性运动则从70年代就蓬勃发展起来。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对韩国早期的女性运动和女性主义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起,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逐渐衰落,发生了女性主义的“文化转向”,“在后现代主义背景下,第三波女性主义逐渐远离了生产议题,转而关注语言、话语和表象”。(11)范春燕:《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方法和论题——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分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第11-17页。韩国从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了经济自由化进程,新自由主义左右了经济政策的制定。与之相伴的是,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在韩国广为传播,对韩国女性的意识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与儒家传统观念一起加重了职业女性的压力。第二,资本对女性身体的开发与重回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必要性。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并未起到消除性别不平等和性别压迫的作用,反而发挥了为资本积累培养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的作用。随着韩国财阀垄断资本日益将女性身体的开发作为牟利的工具,有必要抛弃后现代女性主义视角,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
二、韩国式资本主义的矛盾、危机与影响
韩国资本主义既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共性,也有其特殊性。一方面,韩国经济受到财阀的绑架,财阀掌控了经济权力,垄断了从原材料到产品的定价权,使中小企业缺乏生存空间。另一方面,韩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使市场机制的自由运行受到多方面的限制。这两个方面使韩国式资本主义既具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普遍存在的矛盾,如收入分配不平等和失业加剧等,也存在缺乏公平竞争环境和福利制度缺失等特殊问题。在政治上,韩国财阀通过贿赂官员、捐献政治献金等方式施加政治影响,甚至公开挑战政府权威;在经济上,财阀利用控股权大量剥削公司财产和侵犯小股东利益,通过多种方式将公司利润和财产转移给自己。(12)周建军:《韩国财阀改革的政治经济学:以小股东运动为例》,《开放时代》2010年第2期,第106-118页。韩国高丽大学教授张夏成将韩国资本主义的问题和矛盾总结为五点:收入再分配政策失败,出现无就业、无工资、无分配的“三无”增长,非正式就业劳动者的规模居高不下,企业与家庭生活不均衡增长,过度的企业内部公积金。(13)[韩]张夏成:《韩国式资本主义——从经济民主化到经济正义》,邢丽菊、许萌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7-36页。可以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矛盾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暴露出来的,韩国式资本主义的矛盾则是由于其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完善性,而韩国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完善性很大程度上是由财阀垄断和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造成的,这两者都是计划经济的遗留物。
韩国自20世纪90年代起采取了经济自由化政策,虽然有学者认为韩国并非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但韩国采取了新自由主义政策是毋庸置疑的。韩国的新自由主义化改革开放了资本与金融市场,打破了“终身雇佣”的劳动体制,大企业迅速解雇了30%左右的员工,虽然很快走出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泥潭,但只是在短时间内把经济危机转化为社会危机。(14)王晓玲:《韩国“经济危机世代”问题研究》,《学术论坛》2019年第6期,第69-77页。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陷入多重危机之中,严重依赖对外贸易的韩国经济同样面临严重的危机。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重构和意识形态重塑的共同作用下,韩国的经济金融化快速发展,住房金融化发挥了重要作用,2020年韩国住房交易数量和价格都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2021年韩国首尔房价涨幅接近20%,创造了近14年来的最大涨幅。(15)李连波、黄泽清:《住房金融化与〈论住宅问题〉的时代价值》,《当代经济研究》2021年第4期,第16-26页。受新冠疫情的冲击,2020年第一季度韩国经济增速创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纪录。根据经合组织发布的数据,韩国2020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1%。(16)《韩2020年第四季度GDP环比增长1.1%全年增速-1%》,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zwjg/zwxw/zwxwyz/202101/20210103034084.shtml。
近年来,韩国女性运动频发与韩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密切相关。根据一些学者最新的研究,经济危机对不同人群的影响是不对称的,危机的影响既是性别化也是种族化的。这些学者将性别分析法广泛应用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理论研究中,解释了女性在金融危机中所遭受的严重冲击,以及性别歧视观念与金融危机的相互影响机制。(17)郗希:《性别差异视角下的金融危机理论研究动态》,《经济学动态》2015年第4期,第121-129页。无论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韩国女性都是最大的牺牲者,是公司裁员优先考虑的对象,而韩国政府应对失业的政策并未充分考虑性别因素。在新冠疫情中,韩国女性也首当其冲,不仅遭受了职场危机,也成为易感染人群。韩国学者金世罗(Saerom Kim)等从性别的视角分析了韩国应对新冠疫情的过程,考察了女性在感染新冠病毒方面的脆弱性,并从隔离政策和安抚政策两个方面分析了应对疫情的性别差别。(18)Saerom Kim,Jin-Hwan Kim,Yukyung Park,Sun Kim,Chang-yup Kim,“Gender Analysis of COVID-19 Outbreak in South Korea:A Common Challenge and Call for Action”,Health Education &Behavior,Vol.47,No.4(2020),pp.525-530.在疫情面前,性别差异经常被人们忽视。疫情对性别的差异化影响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包括生物学差异,性别规范、价值和行为,存在性别歧视的健康体系,以及社会性别不平等。韩国的女性更易感染新冠病毒,在2020年5月9日的10 840名感染者中,女性为6 434名(占59.4%)。(19)《大韩民国新冠肺炎最新情况(截至2020年5月9日)》,http://www.cdc.go.kr/board.es?mid=a30402000000&bid=0030。从全球范围来看,男性感染者的数量多于女性,韩国则与之相反。韩国疫情的性别化传播途径有两个:一是以女性职员为主的工作场所聚集性感染,二是女医护人员被感染。
韩国经济危机也加剧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对立,许多男性认为女性夺走了他们的工作机会。实际上,由于经济长期低迷,当代韩国年轻人面临激烈的竞争。文在寅政府推行了许多旨在推动两性平等的政策,虽然获得了女性的支持,但失去了年轻男性的支持,“上世纪9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成为阶层身份较父母出现下滑的第一代人。对男性年轻人而言,身边学业成就更加优秀、经济活动参与欲望日益高涨的女性带来了竞争压力,男性年轻人中逐渐出现了憎恶女性的现象”。(20)王晓玲:《韩国女性话题背后的阶层矛盾与社会分裂》,《世界知识》2020年第1期,第69-71页。近年来,韩国社会“厌女文化”的流行与之密切相关。
三、资本逻辑与身体生产的政治经济学
韩国是女性整容率最高的国家,美容和整容构成了庞大的产业,女性在追求“美丽”的社会氛围和媒体的鼓动下将大量收入花费在身体的塑造和维护上。根据韩亚金融投资株式会社2020年5月19日发布的报告,截止到2019年,韩国的美容整形市场规模约为5兆韩元,占全球市场规模的25%,每万名韩国人的平均整容手术次数是135次,位居世界第一。(21)[韩]韩亚金融投资株式会社:《美容整形和超重》,首尔:韩亚金融投资株式会社,2020年,第5-6页。这背后是资本逻辑的驱动,即资本将女性身体的开发作为牟利的工具。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有两个因素与之密切相关:一是韩国财阀垄断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过剩资本迫切寻求新的投资领域;二是韩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包括韩国经济的金融化,垄断资本日益将个体作为榨取利润的对象,大众传媒则通过将消费文化、审美标准灌输给个体,便利了资本对女性的剥削。
根据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理论,垄断资本主义的市场结构能够使垄断企业以高利润的形式将生产力增长成果的最大份额攫为己有,从而必然会产生大量的经济剩余,这些剩余得不到吸收将会导致经济停滞;除了用于消费和投资以外,剩余只能以非生产性的方式浪费掉,包括营销费用、政府民用支出和军事支出等。(22)[美]保罗·巴兰、[美]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73页。韩国作为典型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财阀攫取了经济发展成果的最大份额,同样面临过剩资本的吸收问题,韩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一问题始终无法得到解决。
韩国的美容和整容产业构成了过剩资本的重要吸收渠道,这些产业的高度发展与财阀垄断资本的存在密切相关。进一步讲,这些产业很大程度上直接以女性身体的开发为对象,将女性身体作为增殖手段,加剧了对女性的剥削与压迫。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女性的身体日益成为资本直接榨取利润的对象。资本的运作最终改变了韩国的大众审美观,从而为消费资本主义的崛起和资本积累铺平了道路。咸仁姬分析了韩国社会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身体“殖民化现象”,将之与高度的消费资本主义联系起来。(23)[韩]咸仁姬:《20世纪60年代以后韩国社会的身体殖民化现象研究》,梨花女子大学韩国文化研究院“韩国学特性研讨会”会议论文,2005年,第67-91页。对韩国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电视广告的分析表明,韩国70年代以前的审美标准在于皮肤美白程度;韩国经济在80年代以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整容外科广告开始出现;90年代中期以后,减肥广告数量暴增,消费资本主义正式登场。
在资本逻辑的运作下,韩国社会已形成了外貌至上主义,是否美丽、苗条成为衡量女性价值的标准。为了拥有更年轻和美丽的外貌,越来越多的韩国人不断投入时间和金钱。特别是对于女性来说,外貌已然成为重要的“肉体资本”,尤其是在求职和婚恋市场,对女性外貌的评价和歧视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减肥已经成为当代韩国女性生活的常态,越来越多的女性试图通过整容来改变外貌。根据韩国女性政策研究院2019年出版的研究报告《韩国社会的性别及健康不平等研究(Ⅲ)——以外貌压迫和美容整形为中心》,52.9%的韩国年轻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曾因外貌而受到不公正对待,30%以上的女性遭受过朋友和亲人对于自己外貌的贬低,这些数据都远高于男性;46.4%的韩国年轻女性曾接受过美容整形手术,34.1%的中老年女性接受过美容整形手术,而年轻男性和中老年男性的比例仅为18.9%和14.5%。(24)[韩]金东植等:《韩国社会的性别及健康不平等研究(Ⅲ)——以外貌压迫和美容整形为中心》,首尔:韩国女性政策研究院,2019年,第69-87页。“外貌压迫”是所有年龄段的韩国女性都共同经历过的,它让个人对自己和他人的外貌产生歪曲的思考,严重威胁到女性的健康。其结果是,很多韩国女性患有厌食症、暴食症等进食障碍疾病,甚至引发心理、情绪上的不安和抑郁,不得不接受心理咨询和治疗。
外貌至上主义实际上体现了女性的从属地位,即女性的价值在于取悦男性,而非女性本身所具有的价值。这一套评价和诱导女性的话语有深刻的经济、文化根源,已经通过大众媒体的宣传渗透到韩国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郑才哲以韩国MBC电视台的谈话类节目为对象,对其中的“减肥”“整形”等与女性身体有关的话语进行了批判性反思,指出“身材管理肯定话语”将身材管理与人的自由和意义相结合,将身材管理与商业以及外貌至上主义相结合,是对女性的差别对待,最终有可能成为压迫其他女性身体的机制。(25)[韩]郑才哲:《关于韩国的女性身体话语的批判性研究:基于〈MBC100分钟讨论〉之“身体的时代,减肥热和整形热”的考察》,《舆论科学研究》2007年第3期,第292-318页。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韩国社会形成了批判“肥胖”的风气。借此机会,健身产业快速发展起来。韩国的各种娱乐节目为了迎合商业主义,歪曲了美的价值,甚至给观众灌输了虐待自己身体的观念。也就是说,对于韩国资本主义,身体不仅是生产的主体,而且也成为自我表现的手段和消费的对象,对身体管理的认识已经超越了审美层面,扩展到在竞争中不被淘汰的生存层面。财阀垄断资本对女性的剥削和压迫已经超出了生产领域,渗透到生活和消费领域。再以韩国的减肥真人秀节目为例,有韩国学者分析了这些节目中的话语在界定性别政治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它们加强了韩国女性必须将塑造体型作为自身任务并养成良好习惯的认识。(26)Yoonso Choi,“‘One is not Born,but rather Becomes,a Korean Woman’:Gender Politics of Female Bodies in Korean Weight-Loss Reality TV Shows”,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Vol.54,No.8(2019),pp.1005-1019.首先,减肥真人秀节目倾向于夸大韩国女性体重超标的程度,只集中于正常女性,而无视体型大小;其次,韩国女性的身体护理受到“爱面子”想法的影响,这被看作独特的民族文化特征,即关注周边人对自己的评价;最后,这些节目创造了一种“节食色情”(diet pornography)话语,强调减肥后的理想结果,以及所受到的尊重和积极评价,而对普通人所经历的痛苦过程轻描淡写。这些减肥真人秀节目无疑强化了韩国文化背景下占据主导的性别政治。
四、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韩国女性传统角色的冲突
随着韩国的对外开放、经济现代化和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受到冲击,女性的独立意识和平等意识进一步增强。与20世纪90年代韩国经济自由化相伴的是,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在韩国广为流行,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对女性价值观、职业发展和婚姻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韩国女性仍然无法摆脱传统观念赋予自己的社会角色,难以在工作与家庭之间实现平衡,不得不经常做出自我牺牲,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理论所描述的理想状态根本无法实现。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韩国女性传统角色的冲突进一步加重了韩国职业女性的压力,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正是这两种观念冲突之下的不同选择。
在新自由主义政策持续削减社会福利保障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要求女性完全靠自己实现个人幸福,持续投资自己的人力资本,和男性在职场展开竞争,并由自己承担个人选择的一切后果。这种女性主义的变体针对的是少数女性特权精英,仍然宣扬以市场为中心的解决方案,拒绝政府干预,因而不可能真正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当代著名女性主义理论家南茜·弗雷泽指出:“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的目的是精英统治,而非平等。它的目的不是废除社会等级制度,而是使其女性化,确保最高层的妇女能够达到与本阶级的男性平等的地位。顾名思义,其受益者是那些已经拥有较高社会、文化和经济地位的人。”(27)[美]南茜·弗雷泽:《女性主义宣言》,《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7期,第66-78页。实际上,作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起到维护阶级统治,为资本积累创造条件的作用。凯瑟琳·罗滕贝格认为,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有助于维护生育和照料工作的话语,即确保这些劳动的责任完全落在有抱负的女性肩上,它通过这种方式暂时性地解决了自身的结构性张力——生育和照料工作的两难困境;这是一种高度个体化的女性主义,它劝告女性个体规划自己的生活,以实现“工作—家庭的愉悦平衡”,煽动女性将自己视为人力资本,鼓励她们投资自己,把受过教育的、向上层流动的女性完全转变为一般的、无性别的人力资本。(28)[英]乔恩·贝莱斯:《凯瑟琳·罗滕贝格: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10期,第1-8页。
韩国人口已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适龄女性的生育率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倒数第一。韩国人口增长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生育率下降,而且女性的平均生育年龄呈不断上升的趋势,生育率最高的年龄段是30-34岁,25-29岁的生育率逐渐降低,35-39岁的生育率则呈逐渐上升趋势。(29)[韩]金炳彻、[韩]都南希:《低生育率危机背景下韩国家庭福利政策变迁研究》,《社会保障评论》2020年第2期,第117-130页。晚婚甚至不婚导致韩国近年来“黄金单身女”的数量激增。韩国“黄金单身女”指的是大龄未婚女性,这些女性大都有结婚的意向,但在家庭和工作的冲突中最终选择了晚婚。“黄金单身女”体现了韩国女性婚姻观的变化,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倡导女性持续投资自己的人力资本,沿着职业阶梯向上攀爬,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学者指出,韩国“黄金单身女”人数增加的原因有女性的高学历化、更多参与经济活动及收入增加和婚姻观的变化等;这些“黄金单身女”的特征有,重视自我实现、对自己毫不吝惜地投资、工作优先而最后婚嫁的观念以及享受单身自由。(30)李美景:《韩国“黄金单身女”现象研究——“黄金单身女”晚婚现象分析》,《青年研究》2012年第2期,第83-93页。“黄金单身女”现象既反映了韩国女性独立、平等意识的增强,也表明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理论所倡导的“工作—家庭的愉悦平衡”的失败。
人口负增长和“黄金单身女”等现象揭示了韩国资本主义在维持劳动力再生产与促进资本积累之间存在的冲突,以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韩国女性传统角色之间存在的冲突。女性成为这两种冲突的牺牲品,面临要么为了职业而牺牲家庭生活,要么选择家庭生活而放弃职业发展的冲突。随着冲突的加剧,越来越多的韩国女性开始选择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
就第一个冲突而言,资本主义社会将劳动力再生产的任务交给工人家庭,通过无酬的女性家务劳动确保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供给。同时,资本积累单靠男性工人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将女性吸收到雇佣大军之中。从量上看,这是为了满足资本积累对追加劳动力供给的需求;从质上看,资本建立起了性别化的剥削模式并系统性压低了工人工资。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韩国资本主义一直未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进一步压缩了社会福利支出,加之房价和子女教育成本的高涨,使得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不断增加。同时,韩国女性通过教育提升了自己的“人力资本”,越来越多的女性放弃了家庭主妇的角色,选择职业女性的道路。人口负增长和“黄金单身女”现象就已表明,韩国资本主义并未在满足资本积累对劳动力的需要的同时,确保劳动力再生产能顺利进行。
就第二个冲突而言,许多韩国职业女性仍难以摆脱韩国女性传统角色的束缚,当其与职业女性角色冲突时,她们或者通过晚婚晚育努力在两者之间实现平衡,或者不得不牺牲个人的职业发展,或者干脆选择不婚或不育。受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的影响,韩国女性存在双重的社会角色,使其存在严重的价值冲突,表现为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的矛盾以及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的矛盾。(31)全信子:《韩国女性参政的社会环境浅析》,《当代亚太》2007年第5期,第58-62页。有研究指出,韩国女性在生育子女时往往离开了劳动市场,几年后才重返劳动市场,即韩国女性一生中的劳动力参与路径呈M型。(32)Margarita Len,Young Jun Choi,Jong-soon Ahn,“When Flexibility Meets Familialism:Two Tales of Gendered Labour Markets in Spain and South Korea”,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Vol.26,No.4(2016),pp.344-357.工作时间长的工作文化、无法获得高质量工作以及男女工资差异过大,使得韩国高学历女性生完孩子后的职业生涯发生了中断。韩国对儿童保育的高投资并未改善女性的就业前景,不足以抵消劳动市场的负面影响。为韩国职业女性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需要进一步消除性别不平等政策,以及破除男性为养家糊口者的传统观念。
五、结语
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韩国性别压迫问题的根源,揭示了韩国人口危机背后的深层原因。从女性的角度看,韩国的人口危机与其长期存在的性别压迫密不可分,而这需要从韩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矛盾、危机及其压迫女性的特殊机制,以及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对韩国女性的影响方面寻找原因。从本文的分析中可以得到两点启示:第一,资本主义存在多样性,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第二,中国同样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是在女性解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关键在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瓦解了剥削、压迫女性的经济土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破除了贬低、歧视女性的意识形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所强调的,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把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当代中国妇女运动的时代主题,促进男女平等,发挥妇女在各个方面的积极作用,组织动员妇女走在时代前列,在改革发展稳定第一线建功立业。(33)《习近平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并发表重要讲话》,《妇女研究论丛》2018年第6期,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