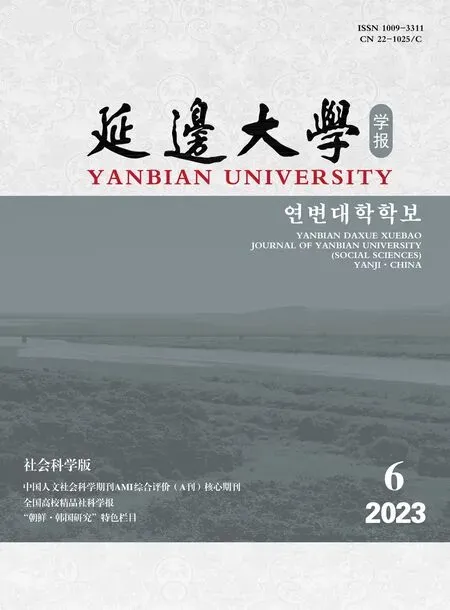万历援朝时期大规模征召沙民海防事宜探析
许 轫
在江苏沿海地区及长江口两岸,由于江流中的河沙上冲下淤,形成了大片沙洲。自东晋以来,大量失地百姓被迫移居至沙洲生活,形成“沙民”。他们长期居住在贫瘠险恶的环境下,沙民这一称呼遂成为贫穷落后、地位低下的沿海沙地居民的代称。他们开辟沙洲,倚海而居,常年劳作于海上。在清代所撰《山东通志·卷之二十·海疆志》中就有记载:“水战非乡兵所惯,乃沙民所宜。盖沙民生长海滨,习知水性,出入波涛如履平地,在江南太仓、崇明、吴淞等处有之,故船曰沙船,但沙船仅可于各港协守、内洋出巡”。(1)[清]岳浚:《山东通志》卷二十,清乾隆元年刻本,第24页a,https://fz.wanfangdata.com.cn/details/oldItems.do?Id=FZ202120740。万历年间倭寇大举入犯朝鲜,对中国环渤海湾区域也构成重大威胁,朝廷急需兵源补充海防军力,沙民成了当时的优选对象。宋应昌、邢玠等任事官员为了巩固海防和抵抗侵略,首次计划大规模从民间征募沙民沙船应对危机。
这一事件对后续海域边民的治理机制产生了微妙的影响,但学术界对于这方面的探讨不足,且以往的研究多止步于主政者的构思和预想。大规模征募沙兵作用于海防的真实情况和实际功效究竟如何,尚缺乏深入探讨。通过系统收集整理明代首次大规模征募沙民海防事宜的史料,综合研究影响和制约政策制定和实践的诸多因素,可以还原相关万历援朝史细节专题中的断裂环节,并且弥补明代海防史研究的盲区。
一、对大规模征召沙民海防策略的争议
沙民的生存环境恶劣,常常受到风暴海浪威胁和海盗劫掠侵扰,因此,他们的性格和行事风格粗野彪悍。他们熟悉近海水域且战力彪悍,有时与海贼争利甚至沦为盗匪。在心存偏见的迂腐官员眼中,常常把沙民与西南山隅的夷民相类比,均将其视为难以管治的社会群体。
自明代嘉靖中后期开始,面对愈演愈烈的倭寇侵扰,就有很多地方官员和有识之士提议,或可招募沙民作为水军后备兵源。曾任台州推官、湖广布政司参议等官职的地方名宦吴子孝,就具有远见性地显露出希冀招募沙民从军的意愿,他说:“太仓、崇明、三沙(崇明岛侧沙洲)之人,惯于舟战。下海遇寇,往往杀之而取其货。今宜访其豪杰,用之以统诸水卒。彼既不能为盗,既杀盗以取功耳”。(2)[明]郑若曾:《筹海图编》,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81页。长洲生员陆炫也曾经在上书中先是介绍“崇明各沙居民或鬻贩私盐,或江洋捕贼,舟楫便利,技艺精能。然各有土豪,自能役使”,(3)[明]郑若曾:《筹海图编》,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81-682页。继而建议官府向沙民中有威望的人物颁发搜捕盗匪的官方文书,同时授予他们低阶武官名号并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让他们自发招募人员船只,对抗为祸一方的盗匪及豪强。上述开明的官绅们期盼一方面朝廷能将沙民组织成为辅助治安的民团武装,实现维护地方稳定的目的;另一方面,则在鼓励沙民止暴治乱、守卫疆土的前提下,给予他们论功行赏和晋级升迁的机会,从而提升其社会阶层。
然而,上述倡议也受到一些质疑。反对者们认为初衷虽好,但实际运作中沙民内部可能出现不法奸徒,假借官府授权通吃黑白两道,即“将见外挟官法,以要盗贼之常例;内挟盗贼,以要官府之优待”。(4)[明]郑若曾:《筹海图编》,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82页。因此,不论是中央内阁还是地方官府对于招募沙民一议都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审慎态度,虽有支持者勇于实践尝试,但在招募和管理过程中也会对沙民多加限制约束并严格监控,且在赏罚激励事宜的落实上,主事官员们的想法也大相径庭,安抚策略摇摆不定。如面对东南倭寇侵扰时,奉敕监军御倭的巡按御史周如斗就上疏朝廷,建议对于有杰出立功表现的沙兵耆民照例论功行赏,其中有不愿接受行赏者,则准许其子弟读书入学,不读书者则充当吏员。此外,上述受赏人员还有机会可以承接举人、监生等身份,叙功加级选用。持异见者则认为:其一,此议案是出于因时应急考虑,作为特例,朝廷必须严加审查,避免私滥授予官职;其二,沙民素多粗悍,是否能通过对其进行读书教化达到转化思想、矫正恶习的目标,多有要员也持怀疑态度。朝廷经过反复讨论,大部分官员都主张按惯例安排文官御史作为监军对沙兵军伍进行约束,在监管军费开支的同时,严格论叙功次。(5)[明]郑若曾:《筹海图编》,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80页。
嘉靖后期,顽固侵扰东南沿海多年的倭患在朝廷大力清剿之下,渐渐归于平静。原先应急所招募的少量沙兵也被遣散归业,但朝廷中的部分官员仍视他们为潜在的海防后备力量,若有急需就会再次动议招募成军,但限制发展的态度并没有改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规模征召沙民海防的策略存在争议,实践到底效果如何,我们通过进一步研究史料来找寻答案。
二、万历援朝时期第一阶段(壬辰倭乱)大规模征召沙民海防的实迹
在万历十九年(1591年)间,明朝陆续收到关于日本丰臣政权将会大举入侵东亚大陆的海外预警后,下令沿海涉事的各地方督抚要员需有所准备。针对朝廷所发战备预警,往昔经常受到倭寇侵扰的地区积极做出快速反应,它们主要集中在东南部沿海如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一带。而未来受到战乱威胁所波及的辽东地区和环渤海湾的京畿重地,此刻的防御重心还主要集中于防控北虏,至于防倭事务尚处于次要考量。由于当时无法准确获知此番威胁的规模和范围,因此沿海地方督抚的防御措施也多着重于完善所辖地区的卫所或水寨的功效,补充官军份额及提升装备水平,最初并无大规模征募沙民用于海防的计划。
至万历二十年(壬辰年,1592年)上半年,倭寇正式大举入侵朝鲜半岛,自釜山登陆后长驱直入,数月间就攻陷了朝鲜国都汉阳和西京平壤,朝鲜国王李昖急向明朝求援。在确定日本大规模入侵的事实后,辽东、北直隶、山东等往昔忽视海防事务的近海地区,皆成为必须加强海防战备的重点区域。同时,保障内河漕运经济动脉安全也成了明朝亟须考虑的问题。虽然日本水军在全罗道受到朝鲜舟师的拦截,难以沿岸溯流南上,但在侵略军小西行长所部占领汉阳后,敌方仍然有可能顺流汉阳旁侧的汉江跨出海口,进而沿线穿越渤海湾,直接威胁到大明国都北京及周边地区的稳定。此时明朝迫切需要抓紧时间做好防御部署以应对挑战。
(一)海防部署规划及征召沙兵的计划
朝廷于壬辰年(1592年)八月正式任命兵部右侍郎宋应昌往保蓟辽东等处经略备倭事宜,宋应昌临危受命,迅速推行统一战略部署。他认为当前首要任务并不是仓促出境退敌,而应该优先加固和完善国内防御,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巩固环渤海湾地区海防。
随着形势变化,天津成了重要的海防战略据点和军需中转要地,必须部署相当数量的专业水军重点防御。为此,宋应昌向朝廷上呈《议处海防战守事宜疏》,其中特意指出“今天津蓟门止于海防”。(6)[明]宋应昌:《议处海防战守事宜疏》,《经略复国要编》卷三,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第205页。为保天津地区万无一失,他有意在天津以西海面,自辽东旅顺至山东登莱一线的岛屿间部署水面重兵据守。他在奏疏中就写道,“复将调来沙兵七千名,沙船二百只;应天船兵九百五十名,沙唬船八十只;兵一千五百三十五名分布各岛”,(7)[明]宋应昌:《议处海防战守事宜疏》,《经略复国要编》卷三,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第207-208页。宋应昌有意大规模征募沙兵充实海面防御军力,且从数量上来看,他规划募调的沙兵数量远高于同期一省的水军官兵总数。随着浙江和南直隶当地督抚根据经略指令,在保全本地区防御需要的前提下勉力抽调官兵和战船前赴天津待命后,宋应昌随即优化调整部署方案,但征募沙兵的原定计划依旧不变。他向朝廷上呈《议题水战陆战疏》(8)[明]宋应昌:《议题水战陆战疏》,《经略复国要编》卷三,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第209-220页。汇报称,根据海面布防所需而拟订的水兵份额,其中天津新造大小战船预期配套兵员4 500余人;(9)[明]宋应昌:《议题水战陆战疏》,《经略复国要编》卷三,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第219-220页。已征调到位的浙江沙唬船随军1 500多人和南直隶应天沙唬船随军900多人;加之计划调募的沙兵7 000人和福兵3 000人。(10)[明]宋应昌:《议题水战陆战疏》,《经略复国要编》卷三,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第220页。如此一来,本轮筹划动员的水军总量即将达到17 000多人。宋应昌计划将预期招募到的7 000名沙兵作为海防前哨部署于渤海湾口周边外岛一线,让他们与防守天津海口的官军水兵相互配合,从而保障海防前线固若金汤。
(二)征召计划的实施部署情况考实
虽说预期计划如此,但维持如此庞大的水军队伍需要配套政策支撑和资源保障,而当时的内阁中枢正处于平定宁夏哱拜叛乱的紧要关头,跨境入援朝鲜的军事行动也即将大举展开,财政紧张的朝廷是否能够全力支持这项国内海防规划,作为经略的宋应昌并无把握。事实上,宋应昌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沙兵征召计划自制定到施行一直颇为坎坷曲折。
关于相关信息的记录最早可追溯到壬辰年(1592年)八月间,就在宋应昌出任经略同期,兵部经过咨询调研,最终批准了民间人士杨允恭所献招募南直隶地区江南沙船沙兵充当水军精锐的策略。当下正式决定任命杨允恭为海营中军署都指挥佥事,派赴当地开展招募事务,并获准动用太仆寺马价银及南京兵部草场租银作为招募沙船沙兵开支所需。(11)《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之二百五十一,万历二十年八月辛亥》,《明实录》,https://sillok.history.go.kr/mc/id/msilok_011_2510_0010_0010_0210_0010。除杨允恭奉命招募沙兵外,还有记载称,时任南京中军都督府佥书提督狼山副总兵沈思学(12)《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之二百五十三,万历二十年十月丙申》,《明实录》,https://sillok.history.go.kr/mc/id/msilok_011_2530_0010_0010_0080_0040。标下把总许元也被授予部劄把总名号,其被安排前往江北地区的通州(今南通地区)、海门等地招募沙船50只、沙兵1 700余人赶赴天津应援,(13)[明]邢玠:《守催闽直水兵并募江北沙兵疏》,《经略御倭奏议》卷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第137-138页。相应费用从北京马价银及南京草场马价等银内支取。上述所预期招募到的沙兵正是宋应昌整体海防部署规划中的重要环节。
自壬辰年(1592年)末,招募沙兵事宜按部就班地被推进。其募兵的进度从今人视角观察会比较缓慢,尚需拖延至半年有余方有初效。虽然上述沙兵相关的部署落实情况在官方明文中并无详细记载,但通过相关史料细节仍可窥见端倪,如山东巡抚孙鑛曾在同年末向朝廷上呈的《防倭疏》中,针对申请调拨水陆精兵协防山东的提案内涉及过沙兵。鉴于山东海防军力薄弱,孙鑛建议能将正在选募过程中的7 000名沙兵分调一半,连同沙船军械及其他友军发往长山岛驻防。(14)[明]孙鑛:《防倭疏 万历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姚江孙云峰先生全集》卷一,清嘉庆十九年甲戌本,第5页a-第8页b。至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初,由于朝廷招募7 000名沙兵项目进展缓慢,孙鑛希望能从中抽取半数充实山东海防的构想遥遥无期。同年正月七日,朝廷下令陈璘出任统领蓟辽保定山东等处防海御倭副总兵一职,(15)《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之二百五十六,万历二十一年正月壬戌》,《明实录》,https://sillok.history.go.kr/mc/id/msilok_011_2560_0010_0010_0050_0010。由其专任负责相关海面军务。随后,孙鑛只得退而求其次,恳请水兵统领陈璘能分拨部分到位天津的水军协防山东登莱一线,(16)[明]孙鑛:《与陈副将璘书 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姚江孙云峰先生全集》卷四,清嘉庆十九年甲戌本,第45页a-第45页b。但陈璘未予反馈。陈璘只是统领浙江和应天2 000余名水军全数聚集天津港内防守,并无余力能够巡防渤海湾口,(17)[明]孙鑛:《又与石东泉书 二十一年二月十九日》,《姚江孙云峰先生全集》卷四,清嘉庆十九年甲戌本,第51页a-第52页b。为此,孙鑛还专门批评上述部署军力局促且效率低下。(18)[明]孙鑛:《与石东泉书 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姚江孙云峰先生全集》卷四,清嘉庆十九年甲戌本,第68页a-第68页b。由此可以发现环渤海湾区域水面军力依旧薄弱,除抽调异地的2 000余名水军官兵外再无其他部伍协守。通过上述一系列蛛丝马迹可以推论,在壬辰年(1592年)末至癸巳年(1593年)初的战局关键时机,宋应昌之前计划招募的沙兵还并未实际到渤海湾口外岛一线布防。
随着战局进一步变化,征募沙兵系列事务不是拖沓迟缓就是再无持续督导跟进。有关沙兵的动向渐渐地销声匿迹,甚至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由此推论朝廷对招募沙兵及规划布防渤海湾区域事务的重视度持续下降。究其原因,一是率军跨境入援的提督李如松自癸巳年(1593年)初一举收复平壤,继而迅速光复开城,与驻守汉阳的侵略军主力在临津江两岸相互对峙数月,使敌方无法分兵跨海。同期,朝鲜杰出将领——全罗左道水使李舜臣依旧全力堵截日军北上水路,我方所面临的海面威胁骤然降低。二是朝廷多位要员都乐观认为,依靠已到位的2 000余名异地水军作为主力驻防天津海口,加上云集周边应援的陆军已能满足京畿重地海防的基本需求,出于节省军费开支的目的,再无大规模征募沙兵的必要。尤其是自同年下半年起,明、日双方尝试商洽议和,明军业已收复汉阳,日寇退驻釜山并且开始过半数逐步撤离朝鲜半岛,征调守备天津的2 000余名异地水军也奉命撤回原驻地,时局形势日趋平稳。待到甲午年(1594年)间经略宋应昌卸任及入援明军全数撤回后,顾养谦、孙鑛先后作为蓟辽总督接手兼理朝鲜事务,明、日双方外交磋商也正式过渡到议封的阶段,原先由宋应昌所制定的海防部署规划几经削减,早已时过境迁,至于有关沙兵部伍的更新动向及善后处置就再无任何要员关注了。
万历援朝时期第一阶段(壬辰倭乱)已招募到的沙兵后续状况如何?通过现有资料可知,一方面,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八月,也就是在兵部有意对首轮入援朝鲜的功绩进行评定的同期,明朝下令让海营中军署都指挥佥事杨允恭作为守备驻防掘港(今江苏名镇南通如东县地界),(19)《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之二百七十六,万历二十二年八月乙亥》,《明实录》,https://sillok.history.go.kr/mc/id/msilok_011_2760_0010_0010_0230_0060。未再提及将所募沙兵用于协防渤海湾的相关规划。待到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四月,由于议和前景貌似顺利,沿海防御事务日趋松懈,朝廷听从漕运总督褚鈇和江北巡按蒋春芳所奏,将守备杨允恭革任回籍。(20)《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之二百九十六,万历二十四年四月己酉》,《明实录》,https://sillok.history.go.kr/mc/id/msilok_011_2960_0010_0010_0100_0020。另一方面,部劄把总许元受命所招募的沙兵1 700余人也因南直隶江北抚按上本请留,因而朝廷也并未将该批兵力派赴天津,而是让他们协防狼山长达数年之久。后续久无战事,许元也因故被削军职,他一怒之下遣散募兵,部众随即流散。(21)[明]邢玠:《守催闽直水兵并募江北沙兵疏》,《经略御倭奏议》卷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第141页。直到丁酉再乱时期,日军再度大举入侵,明朝才不得不再度重新大规模临时招募沙船沙兵以应缓急。
分析上述史料推断,万历援朝时期第一阶段(壬辰倭乱)征调招募沙兵计划的推进落实波折且缓慢,受到战局变化的影响,招募沙兵事宜逐渐不再受到朝廷重视。直至壬辰倭乱暂息议和,沙兵队伍并未按照宋应昌原定规划实数到编,且未能遵循前期部署计划布防于渤海湾口诸岛。事实上,他们极大可能全数作为护卫南直隶漕运安全的军力补充,被划归于地方政府管理。除有明确记载的许元招募人数为1 700余人(22)[明]邢玠:《守催闽直水兵并募江北沙兵疏》,《经略御倭奏议》卷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第138页。以外,杨允恭所募兵数记载不详,但根据其守备职衔的权责惯例,推测领兵不超过千余。由此来预估本轮募兵数量的话,实际招募沙兵总数或不超过3 000人。已招募到的沙兵也在本轮战事暂息的四五年间趋于裁撤解散。可以说本轮招募沙兵的实践算不上圆满,但却为下一轮大规模征召沙兵工作的开展进行了实地调研和舆论宣传,奠定了思想基础。在丁酉年间再度大规模征召沙兵时,由于之前协防狼山的沙兵所部原本的军械战船留存,许元旧属一呼百应,这使朝廷可以优先考虑重组狼山水军应急备敌。
三、万历援朝时期第二阶段(丁酉再乱)征召沙民海防的实迹
随着大明册封使团无功而返,明、日双方谈和事宜彻底搁浅。丁酉年(1597年)初,日寇陆续再度渡海并重据旧寨,明朝为此迅速召集各部科道九卿讨论对策。(23)《万历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辽东都指挥使司咨朝鲜国王(都司咨会九卿科道会议东征)》,《事大文轨:一名东国史略》卷二十,第1页a-第34页b,https://dl.ndl.go.jp/pid/1114536/1/1。在商议时,众臣对于再援的原则并无异议,但在难以保障入援水军官兵(尤其是浙江水兵)数量充足、质量稳定且军需银饷充裕的情况下,大多数人顾虑对敌水战也只能保证驱散,无法一劳永逸,长此以往难免陷入“水兵海舟远募则靡费,不习水利无济于事”(24)《万历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辽东都指挥使司咨朝鲜国王(都司咨会九卿科道会议东征)》,《事大文轨:一名东国史略》卷二十,第7页a,https://dl.ndl.go.jp/pid/1114536/1/8。的窘境。因此,众议认为扩充临时募兵最为妥当,遇有急用,则加紧派发作为声援。明朝遂下决心再度大规模调募水军士卒备战,其中,招募沙兵事务又成为征兵工作的重心。
(一)丁酉再乱兵力部署情况及招募计划
时不我待,丁酉再乱爆发后,日军在万历二十五年(丁酉年,1597年)七月的漆川梁之战中大破朝鲜舟师联军,友方水军几乎全军覆没,尤其在全罗左道水军大本营闲山岛失陷后,附近沿海无所防备,半岛以南水面一线再无友军堵截敌寇。日军可乘此机会,扬帆北上如入无人之境,一方面可游动至全罗道西面并威胁我国天津、登莱、淮扬等地区;另一方面,可顺流进攻汉阳并截断援军船运粮道。此时,明朝仅在国内沿海战略要点布防,还没有派遣水军进入朝鲜战场。紧急抽调入援的浙直水军3 000士卒刚刚抵达旅顺,而福建、吴淞两地近2 000水兵尚在征调途中,都难以及时救援,仓促之下,远水难救近火,海防局势捉襟见肘。
新任主持援朝事务的经略邢玠得悉后,一方面立即下檄文严令明、朝联军死守汉阳以西的汉江和大同江以堵截日军;另一方面,向朝廷上疏请求增派更多的水军部队入援朝鲜。邢玠在奏疏中向朝廷强调,先前所调拨的水军数量对于战局已然杯水车薪,尤其“以今之时势计论,守则须再得一万,战则须再得二万方可济事”,(25)[明]邢玠:《催发水陆官兵本折粮饷疏》,《经略御倭奏议》卷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第110页。再次请求明朝从南京、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等官军处限期速调万余应急,后续再招募和抽调人员补充军力。
自此,明朝大规模紧急动员各地水军部署迎战。在已征调上述5 000水军的基础上,又从南京抽调3 000名在编水兵星夜兼程派发,同时再增调吴淞、福建各1 000人;正式下令招募江北、狼山地区沙兵三五千人,补调浙江、广东各3 000人,预期调拨水军共计21 000人应敌。(26)[明]邢玠:《守催闽直水兵并募江北沙兵疏》,《经略御倭奏议》卷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第133-143页。其中,计划部署10 000名水军防守朝鲜的江华岛等重要海口;5 000名水军作战之用;3 000名水军防守旅顺;3 000名水军防守天津;山东登莱、南直隶淮扬等地则依靠现有驻守水军严加戒备以防不测。(27)[明]邢玠:《守催闽直水兵并募江北沙兵疏》,《经略御倭奏议》卷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第135-136页。
(二)再次征召沙兵计划的施行及相关部署考实

入援的狼山沙兵旧部归属于福日升统辖,福日升籍贯存疑,在朝鲜文献《象村稿》中记为直隶扬州卫人,(31)[朝]申钦:《天朝诏使将臣先后去来姓名 记自壬辰至庚子》,《象村稿》卷三十九,《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七十二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年,第291-295页。而在清代所撰修的地方志《莱州府志·卷五·兵防》中则记为金山卫人。(32)[清]严有熙:《莱州府志》卷五,清乾隆五年庚申本,第10页a,https://fz.wanfangdata.com.cn/details/oldLocalchronicle.do?Id=fz_old_1047。不论出身何处,按照籍贯推测当为世代军户。福日升受命率领狼山水兵1 500余人待命备战。(33)[明]邢玠:《催发续调兵马疏》,《经略御倭奏议》卷四,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第237页。在《象村稿》中记录他以钦差统领山东直隶水兵游击将军署都指挥佥事的身份执行任务。经过近三个月有余的重募编组,所部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正月二十六日到达山东灵山卫境内等候季风出行。外派朝鲜负责现场协调战事的经理杨镐在战术部署中预备把福日升所部派驻于全罗道的群山岛、珍岛等处作为前哨,(34)《宣宗昭敬大王实录卷之九十八,宣祖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朝鲜王朝实录》,https://sillok.history.go.kr/id/kna_13103029_006。并隶属水路都督陈璘管辖。福日升率狼山水兵于戊戌年即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九月底同王元周、李天常所率吴淞等处水军一起赶到全罗道外洋柚岛,参与了联军水陆夹攻顺天倭城的战役。但由于狼山水兵先前未能按期到位而被上峰论罪,福日升被责以白衣从军。后在驱逐日寇的最终对决——露梁海战中由于其率部护卫主帅且作战英勇而被论功行赏,福日升又被官复原职。战后,他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四月间返程归国,(35)[朝]申钦:《天朝诏使将臣先后去来姓名 记自壬辰至庚子》,《象村稿》卷三十九,《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七十二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年,第291-295页。其所统辖的沙兵部队回国后参照同期惯例应为大部裁革解散或者挑选精锐填补地方卫所及水寨士卒。福日升本人的后事也记载模糊,但在《莱州府志》所收录的莱州营守御官列表内参将任职名录里留有他的姓名。由此推测战后其仍旧任职于官场,且在万历年间后期接替刘炳文成为莱州营军事主官。
江北沙兵所部则由籍贯是直隶淮安府大河卫的梁天胤统辖。(36)[朝]申钦:《天朝诏使将臣先后去来姓名 记自壬辰至庚子》,《象村稿》卷三十九,《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七十二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年,第291-295页。此前由于能供调拨的官兵数量有限,邢玠决定在南直隶地区大量招募熟悉水性的沙民沙船以弥补水军的不足,因此特请当地巡抚受命按照往年优厚待遇再度招募人员。把总梁天胤自称招募了部众5 000人待命,故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九月间,邢玠商议调拨梁天胤领江北兵5 000人支援,(37)[明]邢玠:《守催闽直水兵并募江北沙兵疏》,《经略御倭奏议》卷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第142页。在《象村稿》中记录梁天胤以钦差统领南直水兵游击将军署都指挥佥事的身份出战。但需要注意的是,有载邢玠在尚未核查实数的情况下唯恐梁天胤虚报兵员,故而邢玠依旧让当地官府继续招募水兵以防有失。(38)[明]邢玠:《催发续调兵马疏》,《经略御倭奏议》卷四,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第227-228页。后续有确切记录称,梁天胤统领江北沙兵3 000人于戊戌年即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正月二十日从外洋出海,(39)[明]邢玠:《催发续调兵马疏》,《经略御倭奏议》卷四,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第237页。等待海路冰封解冻后前往朝鲜。经理杨镐也在战术部署中把其所部纳入规划,预备让他与福日升等一起分布于全罗道的群山岛、珍岛等处。(40)《宣宗昭敬大王实录卷之九十八,宣祖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朝鲜王朝实录》,https://sillok.history.go.kr/id/kna_13103029_006。后续由于杨镐离任,主事官员交替,落实相关入援水军到位要务督导不力,这就导致江北沙兵部伍在后续一段时间内动向不明,其战绩从现有官方记录上无迹可寻。虽然在《象村稿》中有记载称,梁天胤于同年七月率水军正式进入朝鲜境内,但在九月间联军夹攻顺天倭城至十一月间露梁血战中缺乏参战记录,无法确知该部是否赶赴现场行动,抑或该部只是作为预备队用于护卫朝鲜半岛以西沿岸海路。后续,唯有从《朝鲜王朝实录》查询到的相关记录称,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三月间即日寇彻底败退后,朝鲜国王李昖曾行幸过梁天胤的馆舍。(41)《宣宗昭敬大王实录卷之一百一十,宣祖三十二年三月十日》,《朝鲜王朝实录》,https://sillok.history.go.kr/id/kna_13203010_003。不久,梁天胤被监察官员指控侵盗兵饷而被朝廷严命提拿追赃。(42)《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之三百三十四,万历二十七年闰四月丙申》,《明实录》,https://sillok.history.go.kr/mc/id/msilok_011_3340_0010_0010_0170_0020。随后,大明户部对出征军费中的部分大额花销提出质疑,其中重点内容就包括梁天胤所部开支。户部指控他以募兵为借口,在淮扬、登莱、旅顺等地区逗留观望,虚费帑金接近4万两,待所部抵达朝鲜,日军已经败退,而梁天胤称十一月迄今又该补饷38 000余两。为此,户部甚至给出了“朝廷未得毫末之力而縻费已不赀矣”(43)《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之三百三十七,万历二十七年七月癸丑》,《明实录》,https://sillok.history.go.kr/mc/id/msilok_011_3370_0010_0010_0040_0010。的评判,据此强烈建议朝廷对该笔款项支出重新审计并削减抵扣。明神宗以东征将士劳苦为念不予追究,仍命照数发放。梁天胤所部在同年中旬启程归国后也应为迅速裁革解散,被问罪的其本人也后事不明,再无记载。
综上所述,对比壬辰倭乱阶段,在万历援朝时期第二阶段(丁酉再乱)征召沙兵事务呈现以下两点进展:第一,再度招募沙兵效率提升。首度招募沙兵计划人数为7 000人,而实际招募或不超过3 000人;再度招募计划人数则调整为3 000-5 000人,实际招兵总数与目标接近,但征兵进度明显提速。第二,从对沙兵的部署使用来看,前度招募的部伍未按照原定规划到位渤海湾区域,仅有用于南直隶地区守土防卫的记录;而再度招募的沙兵按战略规划到位了朝鲜主战场,且在战绩方面,狼山沙兵有不俗表现。同期,国内沿海多地仍有他们保家守土的身影,使用功效获得提升。但是,两度招募的沙兵在战后均被发放养家银饷继而裁革解散或者挑选精锐填补地方卫所及水寨士卒,虽可见朝廷实际上已经遵循论功行赏的原则,按照战绩给予他们一定的资金补助和晋升机会,但仍未能从根本上系统解决他们的民生问题。
四、万历援朝时期征召沙民海防事宜的启示
从整个历史阶段来看,大规模征召沙民防海政策得到了积极实践,沙民群体成为备受朝廷重视的水军后备兵源。广大沙民对保家卫国表现出高度热情,踊跃响应号召,积极投军应募,并且在战争中取得了实际的成绩,展现出具备独当一面的发展潜力。此役之后,朝野上下对于在紧急状态下打造严密海防体系的战术思路形成了普遍共识,即采取大规模征召沙兵广布巡哨于外洋、官兵主力防守沿岸港湾,加之民防烽堠预警协助,力图海防布局周密完整。
然而,查阅后续史料可以发现,朝廷始终将征募来的大量以沙民为主的民间海防武装视为潜在麻烦和不安定因素,加之国库赤字和岁入有限等因素影响,朝廷总在危机解除后立将其迅速裁减驱散以稳定统治。沙兵这支本可以为国积极效劳的重要海防助力反复落入无所适从的尴尬境地,难以持续稳定地发挥更加有效的海防保障作用。而沙民群体的福祉和可持续发展并未成为封建王朝关注的民生经济问题。沙民群体生存环境依旧贫瘠险恶,社会地位始终低下。
究其原因,一方面,相关措施执行缺乏远景规划及配套政策,后续难以长效推进。政府把招募沙兵仅简单视为战时应急策略往往陷入临渴掘井的境地,同时,朝廷在动员、招募、调配使用及督查激励等制度建设过程中举措失当所造成的贻误也不容忽视。例如,虽然早有倡议者提出平日里就应将沙民人员现况及当中威望领袖信息登记在册,日常按照官府的计划开展定期民团训练,意图提高他们的军事素质和快速动员能力以便必要时可迅速招募征调。朝廷原则上同意动议并令地方官府着力落实,但实际上各级官员并不重视且或有忌惮民间武装做大的顾虑,大多不愿徒惹事端,依旧采取事急时仓促张罗、事缓时敷衍放任的态度。要言之,朝廷官府对于沙民长效系统的管理机制从未形成且朝廷内部的政治较量和人事纠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保障措施的执行。另一方面,明朝的国防预算支出不足以维持庞大的水军部队的存在。明朝中后期年度财政收支常常处于刚好平衡的境地,仅能在表面上基本维持海防所需。不论是在编或者是预备军力,往往在长期无事后就立即裁并人员及军械装备以节省开支。倘若遇到紧急危机时官府才会考虑加紧补足人员及装备的份额。如恰好国库空虚,自中枢内阁到地方官府只能想方设法从各处拆借资金以作周转,勉强应对一时。简言之,由于朝廷大规模招募沙兵政策的系统谋划不足,上述缺乏长期稳定政策支持,加之维系经费不足等不利条件都必将成为制约沙兵存续的决定性因素。
五、结语
总的来说,万历援朝时期大规模征募沙民融入海防事务,可以说是明代国家施政效能与海防治理机制相互作用的一个外在缩影。通过对相关事件全貌的梳理,不仅展现出中国军民在抵抗外敌侵略过程中所显露的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和大无畏精神,同时也从侧面折射出明朝统治晚期的施政困境和财政危机,进一步揭示了东亚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笔者希冀由此抛砖引玉,一方面协助相关专家学者拓展东域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将历史事件和区域问题放置在东亚政治、文化格局的复杂体系中进行探讨;另一方面,促使国人能够铭记历史并从中汲取经验,牢固树立国家海防安全意识,这对于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