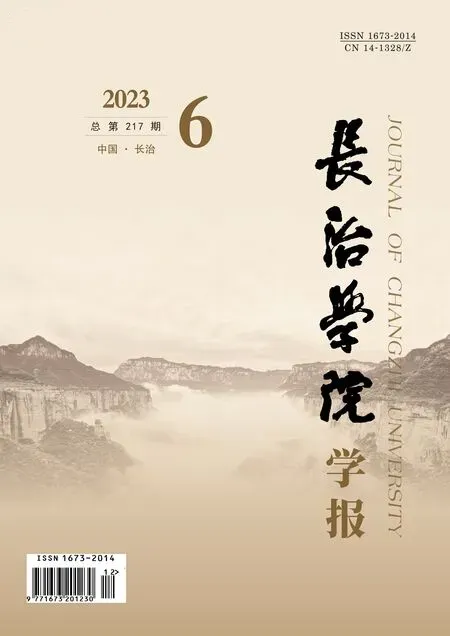山之有神:传统时期村民对山的精神构建
——以山西泽州地区关于山的信仰为中心
杨 波
(山西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山区的村民常常需要和山打交道,他们在南山种树,北山烧香,东山放羊,西山求雨,他们知道翻过东山是另一个村,而那个村的人却用西山来称呼同一座山,山是山区村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从地理学角度给山下个定义是容易的,无非是用相对高差或者坡度等地理指标来界定。然而这样的定义是苍白无力的,要想真正理解山对村民的意义需要回到丰富的历史事实之中。泽州多山,顾祖禹说:“州境山谷高深,道路险窄。”[1]村落碑文中这样描述山:“如吾乡之北,有山名曰白华山,层叠而来,其风脉盖有本矣。下□四境之内,桑株林木,阜林平川,一为取用之资,一为风脉之本,甚不可有以剥削也。”①道光十年《(无题名禁碑)》,现存高平秦家庄玉皇庙戏台西侧,壁碑,高79cm,宽37cm。一方面,山为“取用之资”,既为人类提供了各种物质资源(植物、动物与矿物),又在交通上带来阻隔。另一方面,山为“风脉之本”,影响着村民的思想和文化,村民又反过来在精神文化上构建山的形象。村民在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完成着对山这种自然物的“人化”过程。本文主要是从民间信仰的角度关注村民对山的精神构建。
一、山的人格化:山与山神信仰
山与信仰的关系在最浅层面上表现为山的人格化和神灵化。泽州山神信仰有其不同于其它类型信仰的特征。
和其它山区一样,泽州地区也广泛存在着将山“神灵化”和“人格化”的祭祀场所——山神庙。泽州的人们是这样理解山神的:
从来山之有神,所以庇山中之老幼男女而无物患也;神之在山,所以驱山中之虎豹财狼不为人害也。故山各有神。村之近山者,往往庙宇恢宏。神灵赫濯,四时之享祀不忒,一时之灵应昭彰,乡村无不崇祀焉。②道光二十三年《重修山神庙碑记》,现存高平东山村山神庙,笏首方趺,高160cm,宽58cm,厚22cm。
首先,无论是“山之有神”的“无物患”,还是“神之在山”的“不为害”,两种说法对山神的理解都是中性的表达,“患”和“害”都是担忧的词汇,似乎山神并不是赐福的神,而是以“御灾捍患”为主的神。这表现出人们对于山的一种陌生感和畏惧感。其次,碑文也强调了山神奉祀的普遍性:“乡村无不崇祀焉”,这话并不夸张,泽州地区几乎每个村都有山,凡有山皆有山神庙。最后,山神庙虽然很多,但是山神在整个泽州的神灵谱系中是很小的神,地位很低。原因就在于山神所管辖的范围是很小的。“杜赞奇曾经饶有兴趣的引述满铁调查中关于土地神和关帝的区别。“村村都有土地庙”和“村村都有关帝庙”是完全不同的现象。关帝是管辖所有村庄的大神,而每一个土地都是只管辖自己这一小片土地。[2]在这一点上,山神和土地是类似的。总的来说,山神是以“御灾捍患”为主的神,在山区普遍存在,但规模和辐射范围都很小。
从历史的演进过程来看,山神庙也有其特色。即便是在泽州这种庙宇林立、碑刻众多的地区,独立的山神庙的修缮碑极少出现,出现山神庙记载的碑刻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地亩四至碑。宋金时期碑刻中就出现了不少山神庙的例子。这些例子几乎都是出现在大型庙宇的庙产四至碑中,山神庙在其中是作为地理标志出现的。例如定林寺金代碑:“本寺地土数目:一处,山神庙岭西地一十五段,计九十八亩。”①金大定二年《大金泽州高平县定林寺重修善法罗汉二堂并郭公施功德记》,现存高平米山镇定林寺,笏首方趺,高116cm,宽65cm,厚22cm。山以山神庙而得名,可见山神庙创建很早。类似这样的碑在明清时期屡有出现,性质几乎完全一样。例如乾隆四十八年高平企甲院二仙庙村社地亩四至碑、乾隆四十九年高平李庄村观音堂《李庄村合社公议五处神庙四至碑记》等等。山神庙在这里具有某种山岭产权宣示标志的含义。另一方面,修缮山神庙的记载常常出现在其它更大的庙中,在全村范围的较大修庙工程中偶尔提及山神庙。例如同治九年高平石门玉皇庙的《重修补修庙宇碑记》、道光七年东沟常家沟炎帝庙《炎帝庙古佛堂观音堂山神庙补修碑记》。类似例子太多,不再一一列举。这表明山神庙出现很早,但一直处于停滞的状态,基本是不变化的。总的来说,山神庙产生很早,但却始终停留在一种比较原始的阶段,数量多、规模小、地位低、辐射范围小。
泽州村落大多散布在群山之间的山谷、河谷和盆地之中。山虽然不是和村落对立的,但又是和村落保持着一定距离的。如果说村落对于村民来说是完全熟悉的、敞开的,那么,山在一定程度上是陌生的、被遮蔽的,山还存在一些模糊的、未知的东西。这种遮蔽既带来了恐惧与依赖,又带来了好奇与探究。简言之,人类聚落与其周围的山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而这种张力是信仰与山的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从山神信仰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种张力的存在。从物质利益的角度来说,人们对山可以有一种趋利(利用山的资源)避害(规避山的风险)的行为。从精神文化的角度说,人们对山是既依赖又害怕,这种复杂而又矛盾的集体心理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非常重视对居住地的选择,选择的主要依据就是聚落周围的山水环境,其中山是最主要的,这就是风水信仰。
二、山的结构化:山与风水信仰
如果说山神反映的是老百姓一种模糊的、非系统化的、比较原始的集体心理的话,那么风水信仰②众所周知,风水所代表的术数这种知识形态汉代一度地位很高,位列七略之一。但是,至少在宋以后,虽然术数作为一种“一般思想”仍然很重要,但其主要性质是民间的,邵康节几乎成为那个时代之后的绝响,此后鲜有进入主流的高级知识分子再醉心于术数的研究。就是传统社会底层文人所完成的系统化的知识体系。从这个角度说,风水信仰比山神信仰更加精致和复杂。泽州的风水信仰主要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首先,风水信仰中的山有龙脉、来龙、来脉和风脉的说法,意思基本一致。具体来说,还有祖山、主山、青龙、白虎、案山和朝山等一系列的说法,这些风水中用来描述山的用语都是给山赋予了一种文化意义。在中国传统复杂的风水理论和实践中,山作为一种文化要素参与到了村落的构成中。风水信仰对村民影响很大:
中村宁静观,即炎帝庙,为一村主庙。鹿野园,即观音坡,为一村主山。统属阖村十小社及西沟一小社。凡庙、主山之事,十一社共相辅助,而观音坡山中之木,惟主庙、主山之工得以砍伐使用,十一小社不得妄动。①民国八年《中村炎帝大社整理观音坡地界及主权碑记》,现存高平中村观音寺。
以中村为核心的、由十一个小社组成的村社集群既是围绕着炎帝庙这个主庙展开的,又是围绕着观音坡这个主山展开的。主庙和主山共同构成了村庄的精神核心。风水理论赋予村落周围的山一种文化结构,在村民的信仰体系中占有了原比原始肤浅的山神要重要的地位。
其次,上述例子也体现出作为地理要素的龙脉与作为人工建筑的庙宇结合了起来,它们相互支撑,其作用得到了强化。这进一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正向的功能强化:“村北大庙,乃合村龙脉托落之地,群神会聚之所。凡在村中者,家不拘贫富,人无论穷通,其兴衰祸福、吉凶灾祥、嗣续繁衍、寿命延长,均赖神灵之保佑焉。”②道光十年《重修大庙并合村堂阁殿宇表颂碑记》,现存高平市神农镇中庙村炎帝庙二进山门内西侧,笏首方蚨,高218cm,宽75cm,厚25cm。“龙脉托落之地”成为了最佳的建庙之所,山强化了庙,庙又反过来强化了山。另一种更为常见的情况就是用庙宇来补龙脉的缺,弥补龙脉的不足:
请堪舆先生言说庙门不宜正开,理宜改为偏门,东南、东北俱有缺陷,东边居民亦□散涣,理宜修补,始为一村之盛,……卜吉日以鸠工,祖庙寅门改为亥门,正东修文昌阁一所,东北修关帝庙一座,东南修文笔一支,庶几散涣者而完聚,缺陷者而丰满矣,岂非村中只盛举乎。③道光十七年《创修关帝庙文昌阁文笔改修正门碑记》,现存高平冯庄村小冯庄自然村观音阁。
冯庄村小冯庄自然村的这次修庙工程规模不小,可以说整个村庄的庙宇格局都是按照堪舆先生的指点来建设的,风水其实起到了村落规划的意义。总之,庙(及其它风水建筑)与山的结合是“天”和“人”的结合,人力可以顺天而兴,也可以逆天而补,“天人合一”进一步强化了山在村民精神世界中的重要性。
最后,为了保护龙脉,官方和民间都会制定禁止兴窑挖矿的禁令或规约,这类碑刻数量极多:
高平县正堂白,为永禁凿窑保存龙脉事。照得大粮山为米山镇来龙正脉,盖镇生齿所系,千家坟墓攸关。亘古以来,从无行□取煤之事。因被奸民张国龙、张德威凿山开窑,有伤龙脉。本县亲履其地,立行填塞,仍勒石永远禁止。④康熙十一年《高平县正堂永禁凿窑碑》,现存高平米山镇定林寺。
这种禁令和上面的建庙、建塔成为互补,一是以人工建筑来修补龙脉之缺憾,另一个是禁止破坏龙脉的行为,体现了同样的文化心理。
在风水信仰中,山决定了气的流行汇聚的结构,由此衍生出复杂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解远比山神要复杂,也更精致,但风水仍然是人的居住环境,人和山仍然是对立的,山仍然是为人的生活服务的工具,风水信仰中仍然充满着对象化的色彩。
三、山神的异变:山神与村落主神
在滥封祀典的宋代,一大批或知名或不知名的山神成批量的出现在《宋会要》之中。在宋代社会经济和民间信仰高度发展的背景之下,山神也开始发生了一些有趣的异变,和村落主神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
有些神灵在泽州村落信仰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常常是村落主庙或大庙的主祀神灵,这些神灵就可以称作村落主神。三嵕是泽州地区常见的一种村落主神。高平河西村宋天圣十年碑中的三嵕神灵有明显的山神特点:
春秋冬夏,挥律候( )以明定四时;暑往寒来,吹灰管而潜分八节。而又三才共立,七气同分,显威风而以镇云雷,化雨露而苏草木;牧圉得牺牲之滋盛,丁壮有黍稷丰登。在境土(圡)之黎民,赖神祇之重德。⑤天圣十年(1032)《三嵕庙门楼下石砌基阶铭》,现存高平河西镇河西村三嵕庙。
这一段话主要是说天时、气候以及由它们所决定的好的收成,其中“牧圉”是指牧业,而“黍稷”是说农业。更多碑文直接将三嵕视作山神。北宋宣和四年《紫云山新建灵贶庙记》:“潞之长子县紫云山灵贶庙者,实出于屯留三嵕,盖山神也,或谓后羿,或曰三王,语尤不经,莫可考据。有司以灵应事迹上之,朝廷赐名庙额。”[3]金崇庆元年《创修灵贶庙记》也有“夫建祠立像,为神化去,与民祈福。有在世立功于民灵显致应其所祀者□□可所掩。今端氏明庄紫金山巅有灵贶庙者,实出屯留三嵕。盖山神也,或□□羿,或曰三王,语尤不经,无可考据。”①崇庆元年《创修灵贶庙记》,现存山西高平寺庄镇明家沟村公家山自然村。《宋会要》明确表明三嵕的山神性质:“三嵕山神祠,在屯留县。徽宗崇宁三年十二月赐庙额‘灵贶’。”[4]《宋会要》这部分记载也是在“山川祠”的类别之中。总之,官方和民间两方面的史料都表明三嵕是山神是当时的共识。
虽然像“三嵕”一样以山的名字流传下来成为村落主神的例子非常罕见,但其实其它村落主神大多也和山的信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泽州地区影响巨大的汤王信仰和析城山山神有密切关系。《宋会要》载“析神山神祠,在泽州阳城县,神宗熙宁十年封诚应侯。”②《宋会要辑稿》第20 册《礼》20《山川祠》之91,中华书局,1957 年,第810 页。析城山神祠是奉祀山神的,与汤王并不是一回事,是两个不同的神灵。政和六年《敕封嘉润公记》说得很清楚:“政和六年四月一日,敕中书省、尚书省:三月二十九日奉圣旨,析城山商汤庙,可特赐“广渊之庙”为额,析城山山神诚应侯,可特封嘉润公。”[5]山神和汤王是同时得到赐封的。何以汤王会和析城山神紧密联系在一起呢?《太平寰宇记》载“析城山,在县西南七十五里……山顶有汤王池,俗传汤旱祈雨于此。”[6]析城山上有汤王池这样的遗迹,流传着商汤在此祷雨的传说。这种传说可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至少在五代到宋初已经很流行,才会被收入地理志中。无独有偶,羊头山与炎帝也是类似的情况。《太平寰宇记》卷四十五引用的《上党记》“神农庙西五十步有石泉二所,一清一白,呼为神农井。”③《上党记》是山西现存最早地方志,学者考证其创作年代为魏晋时期。上述引文与年代考证均可参看刘纬毅:《〈上党记〉辑轶》,《山西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 年第2 期。《魏书》中也有类似记载:“羊头山下神农泉,北有谷关,即神农得嘉谷处。”[7]羊头山上也很早就有炎帝的传说和遗迹。泽州地区宋代开始兴起的一批神灵占据了历史较为悠久村落的主神位置,④明清时期兴起的村落或出现了严重历史断裂的村落多以明清时期流行的全国性神灵为主神,如关帝、真武(祖师)之类,与宋元时期差异较大。它们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类似二仙这样的纯粹依赖民间传说兴起的神灵,尤具有唐代仙话故事的余韵,宋金以后才开始伦理化转变;另一类就是依托古帝王圣贤传说兴起的神灵。后者往往总是和某座山有着密切的关系。大体上,在北朝至唐代,泽州地区一部分山就已经开始流传着一些帝王圣贤的传说,并有相应的遗址遗迹,这些传说和遗迹使得它们具有了与其它山不同的地位。在宋代社会经济发展、国家支持或放纵、祈雨的现实需求等因素的推动下,帝王圣贤的形象逐步掩盖了原来山神的形象,在区域内传播,这些山开始逐步成为区域性的信仰中心,那些帝王圣贤则成为区域性的神灵,山神的形象则有点变得暧昧不清了。⑤三嵕的特殊性恐怕主要是因为后羿或奕形象的暧昧不清,导致三嵕得以以山的名字流传。关于后羿与羿的争论参看赵红:《二十世纪以来羿神话研究综述》,《太原大学学报》,2009 年第3 期。关于三嵕神的复杂性参看王潞伟、姚春敏:《精英的尴尬与草根的狂热:多元视野下的上党三嵕信仰研究》,《民间文化论坛》,2016 年第5 期。
无论村落主神是以帝王圣贤形象出现还是以山神的名称出现,这都改变不了村落主神与那座或远或近的山之间紧密的联系,我们常常会将他们的名字与其起源的山连起来称呼,如析城山汤王、羊头山炎帝,而起源之山上的庙也被习惯性称作“祖庙”,成为这一信仰共同的圣地,在村民精神世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四、庙在山上:山的非对象化意义
山神信仰、风水信仰与村落主神信仰中所反映的村民与山的关系还是很粗浅的,因为它们都是一种对象化的关系。所有对象化的关系都已经是非常疏远的关系,是“见仁见智”的问题,而真正切近的、奠基性的、原始性的关系是那种主客彼此交融的“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关系,这种关系无法从对山的信仰的直接叙述中领会,而只能从村民与“山上的庙”打交道的活动中去窥探。这时,核心的概念不再是抽象的山神,而是实在的作为物(建筑)的“山庙”,从“山之有神”发展到“山上有庙”,从“神之在山”发展到“庙在山上”。当精神外化为庙宇建筑的时候,庙宇建筑这个物又完成了更深层次的精神构建,从而将村民对山的精神构建推向顶峰。
山神长期处于村落信仰体系的边缘意味着其本身内容的简单和贫乏,风水信仰的复杂理论并不能掩盖其叠床架屋式的苍白乏味和功利实用的江湖色彩,与山神有密切关联的村落主神信仰也只是将祖庙所在的“远山”放在遥远的背景板上。相对而言,佛道教这类建制性宗教对山的理解要深刻得多。所谓“深山藏古庙”、“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佛道教喜欢将庙观建在名山胜境之中,道教甚至为此造作出洞天福地的一整套完整的说法。①参看[唐]杜光庭编撰;《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年。这样一种现象绝非偶然,而是无意之间反映出了信仰与山之间的一种本质性的关联。佛道教的职业宗教徒们实际上是一些中介者,他们身处尘世之中,但又宣称以出世为志向。惟其在山上才显得出世,惟其在名山才显得神圣,何以又不能在深山秘境,而非要在名山胜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不完全脱离尘世,而又树立出世的形象。建在山上的庙观象征着沟通圣俗之间的通道,既能够超凡脱俗,又不是遥不可及。
相对于佛道教构建洞天福地这种有意识的地理意识而言,像泽州这样的山区村落的村民更像是无意识地为山构建了一种精神意义,没有系统的理论,没有职业宗教徒作为中介者,更没有成佛修仙的对象化目的,一切都融入到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村民与山的关系最鲜活地体现在人们“入山朝拜、登山拜佛、爬山进香”这样的日常的非对象化的活动中:“奉香火,执豆觞,登山入庙”②康熙三十五年《创建玉皇庙记》,现存高平常乐玉皇庙。,“登山入寺,瞻礼法相”③康熙二十二年《定林寺七佛殿创修东阁记》,现存高平米山镇定林寺。,“天空一碧浮云悬,以逾忙种苗未按。天旱不雨人心慌,奉请诸神登山颠,虔诚祈祷求雨泽,南海大士发慈念”④民国二十四年《(无题名墙壁题诗)》,现存高平石末村神山庙南墙。。海德格尔在其哲学中使用了一个源于法语的词汇Lichtung,作为对其哲学核心概念“此在”的描述。这个词汇本来的意思是“林中空地”。“林中空地”是在一个陌生的、被遮蔽的地方(森林)开辟出来的一片敞开的空间(空地),以使得我们能够去通达它。⑤参看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7 年,第63-64 页。“林中空地”的意象和“山中庙宇”的意象是非常契合的。村落是人们生活的地方,是完全敞开的空间,没有神秘性和未知性,也就缺乏了神圣性。与村落相比,山是人们偶尔进入又不生活于其中的地方,是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的空间,这种遮蔽就带来了一定的神秘和未知。在山上建庙就在人与山之间开辟了一条通道,正如林中的空地一样。韦伯将宗教分为此世(this-world)的和彼世(otherworld)的两种理想型⑥Max Weber,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Boston: Beacon press.1964.,中国人习惯说入世和出世。山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出世与入世之间的过渡。完全的出世而成仙成佛就和世俗世界没什么关系了,完全的入世就无法与世俗产生一种张力,山正好提供了一种出世与入世之间的过渡。山庙这种形式意味着村民仍然将信仰作为应对未知世界的一种工具。
在与村庙相对比的意义上,我们才可以更好的理解山庙的意义。金元时期,泽州很多原来位于山上的庙搬迁到了村里,村里也建了很多新的庙,这个历史进程可以称作“下山进村”。焦河炎帝庙嘉靖碑详细记载了庙宇从山上迁入村内的过程:“村西北高岗有古建神农庙,按其识,盖创于金明昌元年也。……嘉靖乙酉岁,庙之故址高峻崎岖,人皆苦□升降。询谋佥同,遂卜于村北古道之次。”⑦嘉靖四年(1525)《迁修炎帝神农庙碑记》,现存山西高平焦河村炎帝庙。焦河炎帝庙原位于村外“西北高岗”的山上,嘉靖重修过程中迁入村内。主要理由是“庙之故址高峻崎岖,人皆苦□升降。”何以以前几百年不苦“升降”,而这一时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庙建在了村里呢?恐怕还是庙的功能发生了较大变化,越来越多承担起了祭祀之外的村落世俗社会管理的功能。庙所需要具备的那种神秘、未知和神圣的特点不再是最重要的了。当村庙逐步成为主流,山庙就逐步退回到背景之中,而这恰恰是在村民对周围山林环境改造力度加大之后完成的这种历史性的转变。
五、结论
山神信仰、风水信仰、与山有密切关系的村落主神信仰、非对象化的山庙,它们代表了传统时期村民对山所进行的精神构建的四个层级,也是逐步深入的四个层级。山神是一种原始的万物有灵论的信仰,风水是一种类科学的前现代地理观念,村落主神成为了某种地方性知识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作为物质化形态的山庙则成为了村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这四个层级中,山越来越被深入地纳入到了村民的精神世界之中。
山越来越深入地进入村民精神世界的过程,也是越来越深入到日常生活的过程。山神作为一种工具只有在其被使用的时候才是重要的,风水这种地理结构只有在与村落相对立的意义上才有价值,村落主神大多抛弃山神形象也表明山终究会被推到背景上去。所有这些抽象的观念总是会在历史长河中浮浮沉沉,或轻或重,作为物质形态存在的山庙却通过爬山拜庙这样的日常化的身体行为而被纳入到了日常生活之中。庙可以被拆毁,神可以被遗忘,而山却总是在村民记忆之中挥之不去,成为乡愁的一部分。
任何的自然地理要素都只有通过人类的精神构建才能够成为人类社会的一部分,自从年鉴学派兴起之后,自然地理的叙述几乎成为历史学研究的“标准动作”,但也越来越流于形式,一定区域范围之内自然地理要素的特征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这些地理要素与特定区域社会的精神文化是如何关联起来的。本文即是这方面的一个简单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