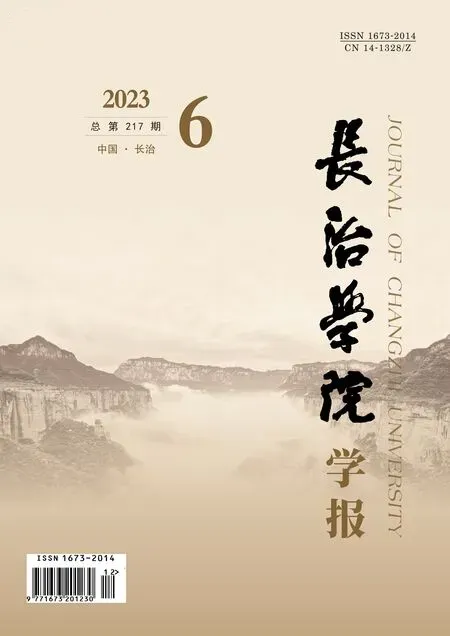峰贯星汉…太行妙场:中古名山河内白鹿山生成史
王仁磊
(河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以白鹿为名的山存在于全国10 多个省区,至少有20 多处,其中较为著名的有黑龙江逊克、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山东文登、河南辉县、河南义马、浙江绍兴、湖南益阳、四川彭州和广东英德等处。本文所探讨的白鹿山是指今河南省辉县市西北之白鹿山,是南太行山的一部分,因地处古代的河内地区,为与他处的白鹿山加以区分,本文也称之为河内白鹿山。魏晋之际,孙登及竹林七贤等名士曾在此游历隐居。西晋以后,随着佛教在中原地区的迅速传播,白鹿山一带秀美的山水吸引了众多佛教信徒,同时仍有其他儒道人士等隐居游历于此。特别是北朝隋唐时期,白鹿山异常兴盛。北宋以后,白鹿山开始衰落。可以说,自魏晋至隋唐的中古时期,白鹿山是一座具有全国影响的文化名山。
一般认为,白鹿山得名于魏晋时期。人们多引用北朝文人卢思道《西征记》所言:“孤岩秀出,上有石自然为鹿形,远视皎然独立,厥状明净,有类人工,故此山以白鹿为称。”[1]卷56,1158此外,白鹿被古人认为是祥瑞的动物,传说仙人、隐士等多骑白鹿或乘白鹿所驾之车,白鹿山的得名或许与此有一定的关系。河内白鹿山在魏晋以前被称为孟门山,《左传》等史书中已有记载。魏晋以后直至明清,均称为白鹿山。近代以来,白鹿山这一名称已淡出人们的视线,人们更多的称这一带的群山为关山、南关山、薄壁山等。以现在的地理观念来看,白鹿山主要是指今河南省辉县市石门河(即古代的清水)至修武县天门山百家岩的南太行山区。[2]狭义的白鹿山指今辉县市上八里镇鸭口村西北一带玄极寺所在的山体。
以往学术界对河内白鹿山的相关研究较少,王东等地方文史学者对白鹿山的地望等问题进行了探讨,[3,4]王尚义、陈习刚在对太行八陉之一的白陉的研究中对白鹿山也有所涉及。[5,6]近年来,姜虎愚对白鹿山《玄极寺碑》等材料中佛图澄地方传说进行文献及宗教地理学角度的考察,对佛图澄与中古早期的山林佛教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但也认为白鹿山“本就是引人瞩目的山地景观,在佛图澄以前很可能已成为著名的隐修场所”,[7]7也就是说,白鹿山在佛教势力进入以前已经是名山,山林佛教活动只是推动了其名山地位的进一步发展。侯甬坚曾经指出:“一座名山的成名过程……是多种社会力量在自然史和人类史上缓慢汇聚而生出的顺其自然的一种结果。”[8]中古时期河内白鹿山的成名,也应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仅仅从佛教山林活动方面似仍无法全面揭示白鹿山的名山生成史。本文不揣浅陋,拟在前贤研究基础上,从中古时期白鹿山的政治地位、交通地位、资源物产、儒道隐士和佛教活动等五个方面,对其成长为中古文化名山的原因与过程略作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地处京畿的政治地位
河内白鹿山之所以能够在中古时期成为全国文化名山,首先是与其地处京畿的政治地理位置以及国家最高权力密不可分,这是普通的地方州郡之山所无法比拟的。
包括河南、河内、河东在内的三河地区地处“天下之中”,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也长期是先秦秦汉时期的经济重心所在。位于太行山和黄河之间的河内地区,土地肥沃、雨水充沛,粮食产量高,人口密度大,自三代以来就是经济发达地区。魏晋南北朝隋唐直至北宋,政治中心多在洛阳、邺城和开封等城市。这些古都距离河内白鹿山均不远,使得白鹿山在上述城市作为都城时成为京畿地区,具有优越的政治地位,并受到了来自都城的巨大影响。
汉魏嬗代,汉献帝刘协被魏文帝曹丕封为山阳公,到河内山阳地区安度余生,其地正是在白鹿山一带。此后不久,在魏晋易代之际,竹林七贤活动于河内山阳(即太行山南麓)一带,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文化事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水经注·清水注》云:
(清水)又径七贤祠东,左右绮草列植,冬夏不变贞萎。魏步兵校尉陈留阮籍,中散大夫憔国嵇康,晋司徒河内山涛,司徒琅邪王戎,黄门郎河内向秀,建威参军沛国刘伶,始平太守阮咸等同居山阳,结自得之游,时人号之为竹林七贤,向子期所谓山阳旧居也。后人立庙于其处。庙南又有一泉,东南流,注于长泉水。郭缘生《述征记》所云白鹿山东南二十五里,有嵇公故居,以居时有遗竹焉,盖谓此也。[9]805-806
王晓毅认为,白鹿山麓的河内山阳地区,“处于邺至洛阳之间,魏晋之际为达官贵人的庄园别墅区,属政治敏感地区,竹林之游发生于此地引人注目”。[10]90今辉县市鲁庄与山阳村之间的竹林寺(七贤祠)遗址,即为嵇康的故居——山阳园宅。距竹林泉庄园西北25 里左右的嵇山,即今天修武县北天门山百家岩一带,是嵇康竹林之游的第二个处所——嵇山别墅。[10]94可见,至迟在魏晋之际,白鹿山一带已经成为京畿人士在受到政治因素影响后首选的隐居目的地。
在十六国时期,一些割据政权的都城距离白鹿山不远,使得白鹿山成为这些政权统治者兵败后首选的退居目的地。如《晋书·慕容垂载记》记载:
翟辽死,子钊代立,攻逼邺城,慕容农击走之。垂引师伐钊于滑台,次于黎阳津,钊于南岸距守,诸将恶其兵精,咸谏不宜济河。垂……遂徙营就西津,为牛皮船百余艘,载疑兵列杖,溯流而上。钊先以大众备黎阳,见垂向西津,乃弃营西距。垂潜遣其桂林王慕容镇、骠骑慕容国于黎阳津夜济,壁于河南。钊闻而奔还,士众疲渴,走归滑台,钊携妻子率数百骑北趣白鹿山。农追击,尽擒其众,钊单骑奔长子。[11]卷123,3088
此事在《资治通鉴》东晋太元十七年(392)条中有更为详细的记载:
六月,燕主垂军黎阳。临河欲济,翟钊列兵南岸以拒之。辛亥,垂徙营就西津,去黎阳西四十里,为牛皮船百馀艘,伪列兵仗,溯流而上。钊亟引兵趣西津,垂潜遣中垒将军桂林王镇等自黎阳津夜济,营于河南,比明而营成。钊闻之,亟还,攻镇等营;垂命镇等坚壁勿战。钊兵往来疲暍,攻营不能拔,将引去;镇等引兵出战。骠骑将军农自西津济,与镇等夹击,大破之。钊走还滑台,将妻子,收遗众,北济河,登白鹿山,凭险自守,燕兵不得进。农曰:“钊无粮,不能久居山中。”乃引兵还,留骑候之。钊果下山;还兵掩击,尽获其众,钊单骑奔长子。[12]卷108,3405-3406
后者所言“北济河,登白鹿山”比前者“北趣白鹿山”更为准确的反映了翟钊败退的路线。翟钊自翟魏都城黎阳(今河南浚县)和滑台(今河南滑县)一带来到白鹿山,一是因为白鹿山是离黎阳和滑台最近的高山,容易藏身于此。二是因为在白鹿山险可守、败可退——事实也确实如此,他在兵败后通过白陉逃往了上党地区西燕都城长子(今山西长子)。
北朝时期,河内白鹿山是京洛人士出逃首选的隐匿目的地。据《魏书·萧宝夤传附兄子萧赞传》记载:
宝夤兄宝卷子赞,字德文,本名综,入国,宝夤改焉。……及宝夤反,赞惶怖,欲奔白鹿山,至河桥,为北中所执。朝议明其不相干预,仍蒙慰勉。[13]卷59,1325
萧赞在萧宝夤反叛后因惧怕受牵连而从都城洛阳外逃,而其出逃的隐匿目的地即是河内白鹿山,只不过他在过黄河时被捕。
隋唐时期,河内白鹿山由于靠近东都洛阳,成为想靠近中央政权的地方士族特别是河北士族的重要隐居目的地。唐代赵郡李氏西祖房的李栖筠曾在入仕前“居汲共城山下”,[14]卷146,4735据有学者考证,其地应是河内白鹿山。[15]176李栖筠“在共城居住,由于接近政治中心洛阳,能够更为及时地了解到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16]他通过在白鹿山下的隐居学习,考中进士,从而进入中央政权,最后官至御史大夫,其子李吉甫、孙李德裕更是官至宰相。从一定意义上说,与唐代长安附近的终南山有“终南捷径”之称一样,靠近东都洛阳的白鹿山成为一些士人步入仕途的“白鹿捷径”。[15]178
二、连贯四方的交通地位
河内白鹿山连贯四方的重要交通孔道地位,其与周边地域社会的紧密联系,也是其成为中古时期文化名山的重要因素。
谈论河内白鹿山的交通地位,便不得不提到太行八陉之一的白陉。太行八陉是古代华北平原与山西高原之间穿越太行山脉的八条交通要道,包括轵关陉、太行陉、白陉、滏口陉、井陉、飞狐陉、蒲阴陉和军都陉。白陉是太行八陉中自南向北的第三陉,一般认为因其途径白鹿山而得名。严耕望最早提出了这一问题,在述及白鹿山与白陉时,指出:“白鹿山与太行白陉甚近。”“岂白陉、白鹿之名有相互关系欤?”[17]1418陈习刚经考证认为:“白鹿山一名在白陉出现之前已经存在,而且其方位也是在修武、辉县接界的太行山范围,白陉与白鹿山相近,白陉一名很可能源于白鹿山一名。”[6]173
学界通常认为,白陉也叫孟门陉,亦称紫霞关,《山海经》《左传》《吕氏春秋》等书中即有对孟门的记载。《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载:“齐侯遂伐晋,取朝歌,为二队,入孟门,登太行。”杜预注:“孟门,晋隘道。”[18]一般认为,此孟门即为后来的白陉。可见在春秋时期孟门就是联系山西地区与中原、山东地区的交通孔道。《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吴起言:“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19]此孟门即孟门山,也即后来的白鹿山。史书记载无不显示了孟门的重要地位。
白陉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从白鹿山东出白陉,可南渡黄河,深入中原,东入齐鲁,出白陉向北可达邺城,纵入河北,通过白陉亦可西退太行腹地,到达上党及太原地区,是一个可攻、可守、可退的战略要地。
我们现在对白陉的认识并不丰富,王尚义认为:“白陉的历史很难考,这大概有两种原因:其一是史籍中有关白陉的记载缺漏;其二是白陉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利于交通往来。八陉中的大多关陉附近都是河谷狭口,而白陉只是盘旋在山峰中的崎岖小道,交通往来十分不便……”[5]70白陉只是“崎岖小道”,但仍能与其他七陉一起并称为太行八陉,这一事实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白陉具有特殊的军事及交通地位,在分裂割据时代显得尤为重要。
从白鹿山而上可以到达上党地区,是中原地区乃至山东地区通往山西地区的重要交通孔道之一,而白鹿山的山前大道则是关中、洛阳与邺城及河北之间的主要通道。据严耕望考证:“洛阳、大梁为黄河南岸古代两大都市,由此两都市北渡黄河,沿太行山脉走廊北行至幽州,为古今中原通向东北之最主要大道,故古代建都往往在此道中。……东晋南北朝时代,中山、襄国、邺城亦为偏霸所都。古代国都丛聚于此道一条路线上,其在古代交通上之重要性可以想见。……至唐……全线置驿称为‘大官道’……”[17]1513由此可见包括白鹿山山前大道在内的太行山东麓南北走廊驿道的重要性。
河内地区地处中原,具有重要的地理位置,并且其与周边地区联系紧密。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河内与河北一体,河内与河南一体,河内与上党一体。[20]而白陉与白鹿山正是联系上述几个地区的纽带与中心。
三、异常丰富的资源物产
河内白鹿山一带地处中原,既有南太行壮丽的自然风光与资源,又有河内平原丰富的农作物等物产,具有成为名山的异常丰富的资源物产基础。
白鹿山自平地而起,从海拔不足100 米的河内平原,突然上升到海拔1500 米左右的高山,相对高度超过1000 米,极具视觉冲击力。而且其间基本上没有山前丘陵浅山区,突兀而起,直入云端,气势雄伟,异常壮丽。在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望去,白鹿山既有泰山之雄浑,又有嵩山之挺拔。《述征记》有云:“登滑台城,西北望太行山,白鹿岩、王莽岭,冠于众山表也。”[1]卷9,162白鹿山壁立千仞,代表了阳刚之美,特别是登临白鹿山山崖,俯瞰中原大地,远眺滔滔黄河,使人心旷神怡。对于白鹿山的“山状”,北齐河清四年(565)白鹿山《玄极寺碑》有经典的描述:“嵯峨忽起,峰贯星汉。阳乌之所藏光,望舒于是回泊。南瞩平野,千里而见江河;北瞻岱岳,仿佛五台之岭。左带沧海,美氛氲之气;右拒孟门,眺□□□极。晾乃日下之高峻,大(太)行之妙场。”[21]78-79白鹿山的这种地势在南太行山的其他地段是不多见的,因而引起古人极大的兴趣是不足为怪的。
进入白鹿山区以后,其风景更是美丽如画,碧水丹崖,瀑布山谷,令人陶醉,既有华山之险峻,又有黄山之秀丽。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这样描写清水上游黑山与白鹿山一带的优美风光:
上承诸陂散泉,积以成川,南流西南屈,瀑布垂岩悬河,注壑二十余丈,雷扑之声震动山谷。左右石壁层深,兽迹不交,隍中散水雾合,视不见底,南峰北岭,多结禅栖之士,东岩西谷,又是刹灵之图,竹柏之怀,与神心妙,达仁智之性,共山水效深,更为胜处也。其水历涧流飞,清泠洞观,谓之清水矣。[9]798-799
可见,中古时期南太行白鹿山一带水量丰沛、林木茂盛、风景优美。南来北往、东奔西走的人们从白鹿山一带经过,无论是在平原上远眺白鹿山之雄伟,还是在进入山区后近观白鹿山之秀丽,必定会被这里优美的风光所吸引。
白鹿山一带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型气候,受高大的南太行山脉的影响较大,夏季多降雨,因而白鹿山水资源丰富,泉瀑溪潭遍布其间,而“临近井(泉)等清洁水源,是山居的重要条件”,[22]这为众多人士隐居白鹿山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而且白鹿山水资源丰沛这一优越条件,并非临近的太行山其他地区所能比拟,这成为白鹿山的比较优势。白鹿山植被丰富,特别是竹林密布、果木药材众多,不仅满足了文人隐士的雅兴,也满足了实实在在的食用及治病强体之需。
白鹿山下的河内平原是华北大平原的一部分,这里物产丰富,是当时著名的粮仓,给居住于白鹿山一带的人们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屏障。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卫州共城县有百门陂(今辉县市百泉),“百姓引以溉稻田,此米明白香洁,异于他稻,魏、齐以来,常以荐御”。[23]462可见,白鹿山所在的辉县一带至迟从北朝时期就已经开始大量种植水稻,呈现出一派北方江南风光。而水稻的种植只是河内平原物产丰富的一个缩影,粟、黍等农作物的种植也很普遍。以上这些都为白鹿山成为文化名山提供了物质保障。
四、儒道人士的游历隐居
曹丕代汉,献帝刘协被封为山阳公,生活在白鹿山一带。魏晋之际,南太行的苏门山、白鹿山一带有隐士孙登和竹林七贤的足迹。这对此后白鹿山儒道等游历隐居者的汇聚和文化名山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北魏高允族孙高和仁“少清简,有文才……常有高尚之志。后为洛州录事参军,不赴,服饵于汲郡白鹿山。未几卒,时人悼惜之”。[13]卷48,1092高和仁之所以选择在白鹿山修道,应是白鹿山此前业已成为修道的圣地。
东魏北齐时期,河内人张子信曾长期隐居白鹿山,据《北齐书》记载:
张子信,河内人也。性清净,颇涉文学。少以医术知名,恒隐于白鹿山。时游京邑,甚为魏收、崔季舒等所礼,有赠答子信诗数篇。后魏(应为后主之误——引者注)以太中大夫征之,听其时还山,不常在邺。[24]
安定朝那(今宁夏固原东南)人皇甫亮,也曾隐居白鹿山,据《北史》记载:
(皇甫)和弟亮,字君翼,九岁丧父,哀毁有若成人。齐神武起义,为大行台郎中。亮率性任真,不乐剧职,除司徙东阁祭酒,思还乡里,启乞梁州褒中,即本郡也。后降梁,以母兄在北,求还,梁武不夺也。至邺,无复宦情,遂入白鹿山,恣泉石之赏,纵酒赋诗,超然自乐。复为尚书殿中郎,摄仪曹事。[25]
隋代入白鹿山修道之人络绎不绝,形成了较大的规模。我们从《玄怪录》的记载中可窥见一斑:
裴谌、王敬伯、梁芳,约为方外之友,隋大业中,相与入白鹿山学道,谓黄白可成,不死之药可致,云飞羽化,无非积学,辛勤采炼,手足胼胝,十数年间。无何,梁芳死……敬伯遂归,谌留之不得。[26]
虽然《玄怪录》在接下来的叙述中有颇多诡异之事,但上述三人在隋代相约入白鹿山学道之事应大体可信。
唐代形成了“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27]白鹿山成为东都洛阳附近重要的隐居目的地,隐居白鹿山之事不绝于书。如相州(治今河南安阳)人邓世隆:
大业末,王世充兄子太守河阳,引世隆为宾客,大见亲遇。及太宗攻洛阳,遣书谕太,世隆为复书,言辞不逊。洛阳平后,世隆惧罪,变姓名,自号隐玄先生,窜于白鹿山。贞观初,征授国子主簿,与崔仁师、慕容善行、刘顗、庾安礼、敬播等俱为修史学士。[28]卷73,2599
又如深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崔良佐,“居共白鹿山,门人谥曰贞文孝父”。[14]卷58,1467濮州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杜鹏举,也曾“与卢藏用隐白鹿山”。[14]卷126,4422
魏州繁水(今河南南乐西北)人马嘉运也曾有隐居白鹿山的经历,据《旧唐书》本传载:
少出家为沙门,明于《三论》。后更还俗,专精儒业,尤善论难。贞观初,累除越王东阁祭酒;顷之,罢归,隐居白鹿山。十一年,召拜太学博士,兼弘文馆学士,预修《文思博要》。[28]卷73,2603
《新唐书》本传记载则略有不同,特别指出了其在白鹿山开展了上千人规模的私家讲学活动:
少为沙门,还治儒学,长论议。贞观初,累除越王东阁祭酒。退隐白鹿山,诸方来授业至千人。十一年,召拜太学博士、弘文馆学士。[14]卷198,5645
后来官至宰相的张仁亶也曾在白鹿山游学。据《广异记·阎庚》记载:
张仁亶幼时贫乏,恒在东都北市寓居。有阎庚者,马牙荀子之子也,好善自喜,慕仁亶之德,恒窃父资以给其衣食,亦累年矣。荀子每怒庚云:“汝商贩之流,彼才学之士,于汝何有,而破产以奉?”仁亶闻其辞,谓庚曰:“坐我累君,今将适诣白鹿山,所劳相资,不敢忘也。”庚久为仁亶胥附之友,心不忍别,谓仁亶曰:“方愿志学,今欲皆行。”仁亶奇有志,许焉。庚乃私备驴马粮食同去。……其后数年,仁亶迁侍御史、并州长史、御史大夫知政事。后庚累遇提挈,竟至一州。[29]
值得一提的是,张仁亶本就是在东都洛阳居住,后来通过赴白鹿山游学作为跳板,最终又步入政界。
此外,前文提到的李栖筠,其本名为李卓,[30]从其改名“栖筠”来看,或许是受到了竹林七贤的影响,与其在白鹿山下隐居游学的经历应有一定的关系。
可见,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白鹿山是邺城、洛阳附近的名山,有着其博大的包容性,大量儒道等各界人士隐居游历于此。这些人士或许是慕白鹿山之名而来,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也扩大了中古名山白鹿山的文化内涵。
五、早期佛教的山林活动
西晋以来,特别是十六国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原地区得到了长足发展,特别是山林佛教的发展,对白鹿山名山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白鹿山上建立寺院的最早记载见于北齐河清四年的白鹿山《玄极寺碑》,其载:
玄极寺者,盖石赵之世,爰有天竺名僧佛图橙(一般写作‘澄’,碑文为‘橙’——引者注),头陀之所,其橙法师四阶上地,应感人间,涂掌神咒,则洞窥未兆,临流引脏,则秘奥难测。权实互显,不可思议。遍历名山,至此顿步,遂因峰构宇,凭岩考室,图像岿然,云生梁栋。[21]78
这里明确指出石赵(即后赵)时期的佛图澄曾在白鹿山头陀,创建了玄极寺。佛图澄(232—348),西域人(本姓帛氏,应是龟兹人),或言为天竺人(据《魏书·释老志》),是魏晋十六国时期的著名僧人,享有“神僧”之称。西晋怀帝永嘉四年(310)来到洛阳,后投奔后赵石勒,深得石勒及侄石虎的宠信,被称为“大和尚”。
白鹿山玄极寺是否真的是佛图澄所创建,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魏斌认为:根据《高僧传》,石赵时期佛图澄一直在石勒、石虎左右,也就是住在襄国(今河北邢台)和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因而,佛图澄头陀白鹿山的说法只不过是一种地方记忆,不足为证。[31]姜虎愚的态度较为折衷,认为:“佛图澄时期佛教盛行,寺院数量随之膨胀,白鹿山中很可能建立了寺院,但是否为佛图澄亲为,很难确认。”[7]15笔者认为,在没有更多证据的情况下,暂不能完全否定北齐《玄极寺碑》的记载。首先,《玄极寺碑》刻立于北齐河清四年,距佛图澄活动的年代只有200多年,属于较为接近历史发生时间的史料记载。其次,从南朝萧梁僧慧皎所撰《高僧传·佛图澄传》的记载中,也能找到佛图澄头陀白鹿山的可能性。
据《高僧传·佛图澄传》记载,佛图澄“以晋怀帝永嘉四年来适洛阳,志弘大法……欲于洛阳立寺,值刘曜寇斥洛台,帝京扰乱,澄立寺之志遂不果”,于是他便“潜泽草野,以观事变”。《玄极寺碑》所说的佛图澄头陀白鹿山很有可能是在这一时期。因为白鹿山地处黄河北岸的太行山南麓,距离西晋都城洛阳不远,紧邻华北平原,又背靠太行山与黄土高原,既可以北上到达河北地区,又可以西行前往河东地区和关中地区,是一个便于“观事变”的绝好地域。我们推测,佛图澄在离开洛阳后,很有可能来到了白鹿山。不过不是在《玄极寺碑》所称的“石赵之世”,而是在西晋末年佛图澄投奔石勒之前。此时(据《资治通鉴》,在西晋永嘉六年),[12]卷88,2776-2777“石勒屯兵葛陂,专以杀戮为威,沙门遇害者甚众”,而佛图澄“悯念苍生,欲以道化勒,于是杖策到军门。勒大将军郭黑略素奉法,澄即投止略家,略从受五戒,崇弟子之礼”。[32]137
佛图澄在郭黑略的引荐下,得到了石勒的支持,不久以后,“中州胡晋略皆奉佛”,佛教在中原地区得到了传播。《高僧传·佛图澄传》又载:“(佛图澄)受业追游,常有数百,前后门徒,几且一万。所历州郡,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与先矣。”[32]144也就是说,佛图澄在后赵统治地区弘扬佛法,推行道化,追随他的弟子,常有数百人,前后的门徒,多达一万人。他所游历的州郡,建立的佛寺有893 所。这是佛教进入中原地区后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发展,得到了封建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包括白鹿山在内的南太行地区作为石赵统治中心襄国、邺城的周边地区,佛教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僧众前来修行。
佛图澄头陀白鹿山、建立玄极寺,对此后白鹿山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直至明清时期,白鹿山上的碑文以及辉县的地方志等仍对此念念不忘,引以为豪。
北魏末年,都城洛阳的一些僧侣潜入白鹿山隐居修道,成为宗教中心洛阳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对洛阳城内寺院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洛阳崇真寺僧人慧凝,“亦入白鹿山居隐修道。自此以后,京邑比丘,悉皆禅诵,不复以讲经为意”。[33]似乎反映了白鹿山对当时整个中国北方地区佛教风气的发展动向具有引领作用。
北朝末年至隋代,也有不少研习佛教人士隐居白鹿山,据《隋书》记载:
卢太翼字协昭,河间人也,本姓章仇氏。七岁诣学,日诵数千言,州里号曰神童。及长,闲居味道,不求荣利。博综群书,爰及佛道,皆得其精微。尤善占候算历之术。隐于白鹿山,数年徙居林虑山茱萸涧,请业者自远而至,初无所拒,后惮其烦,逃于五台山。地多药物,与弟子数人庐于岩下,萧然绝世,以为神仙可致。[34]卷78,1769
这段史料不仅记载了河间人卢太翼曾经隐居白鹿山,他后来又徙居林虑山和五台山,也表明白鹿山、林虑山和五台山等这些佛教名山之间是有紧密联系的。
隋唐时期,白鹿山地区又有法住寺、显阳寺、白云寺等多所新的佛教寺院兴建。2006 年白云寺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8 年,包括玄极寺、白鹿寺、法住寺、显阳寺等寺庙在内的白鹿山寺院群旧址被列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余论
中古时期多种史书地志对白鹿山的名山地位均有记载。如《魏书·地形志》“司州林虑郡共县”条载:
二汉属河内,晋属汲。天平中属。有星城、凡城、卓水陂、柏门山。桓门水,南流名太清水。有檐山、白鹿山。[13]卷106 上,2460
《隋书·地理志》“河内郡共城县”条载:
旧曰共,后齐废。开皇六年复置,曰共城。有共山、白鹿山。[34]卷30,848-849
《元和郡县图志》“河北道卫州共城县”条载:
白鹿山,在县西五十四里。[23]462
《新唐书·地理志》“河北道”序云:
河北道……其名山:林虑、白鹿、封龙、井陉、碣石、常岳。[14]卷39,1009
可见,白鹿山被列为唐代河北道六大名山之一。同书“卫州汲郡共城县”条云:
卫州汲郡……共城,上。武德元年以县置共州,并析置凡城县。四年州废,省凡城,以共城隶殷州。六年省博望县入焉。有白鹿山。[14]卷39,1012
随着地处京畿的政治地位的丧失,连贯四方的交通地位的削弱,在北宋以后白鹿山逐渐走向衰落。据白鹿山法住寺南宋建炎二年(1128)《宋太行忠义记碑》记载,河东路、河北西路的抗金武装曾在这里举行盟誓,这也成为白鹿山经历的最后辉煌。而或许也正是战争的破坏,加速了白鹿山走向最终的衰落。
金元明清时期,已不见白鹿山有重大事件的记载,只是在正史《地理志》中偶有提及。据《金史·地理志》“卫州苏门县”条:
本共城,大定二十九年改为河平,避显宗讳也。明昌三年改为今名。贞祐三年九月升为辉州,兴定四年置山阳县隶焉。有白鹿山、天门山、淇水、百门陂。镇一早生。[35]
可见在金代,白鹿山尚为所在的苏门县(今辉县市)的名山,白鹿山前的早生镇(今辉县市冀屯镇早生村)是该县名镇。另据《明史·地理志》“河南卫辉府辉县”条:
西有太行山。西北有白鹿山。又有苏门山,一名百门山,山有百门泉,泉通百道,其下流为卫水,故又名卫源。又西南有清水。又西北有侯赵川、西有鸭子口二巡检司。[36]
可见在明代,辉县西北的白鹿山仍为名山,是河南、山西两省之间的重要交通孔道,其山下设有鸭子口巡检司(今辉县市上八里镇鸭口村)即为明证。但总体看来,除了在上述二书《地理志》中对白鹿山有记载外,未在《金史》《新元史》《明史》《清史稿》中检索到其他关于白鹿山史事的记载。结合白鹿山寺院群现存碑刻来看,在金元明清时期,由于政治中心的远离,白鹿山已从全国名山降格为地方名山。
近代以来,白鹿山很少见于文献记载,逐步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更为甚者是在当代,文献对白鹿山的记载很少,就连大多数当地人也不知道白鹿山了。以1992 年版《辉县市志》为例,仅有两处述及白鹿山。一处是在介绍境内山岭时有50 余字对白鹿山的简单介绍。[37]94另一处是在介绍白云寺景区时述及“包括白鹿山多处佛教寺院”,白云寺附近有元极寺(即玄极寺)和白鹿寺,“现两寺均废,遗迹尚存”。[37]133寥寥数语,轻描淡写,让人不禁有沧海桑田之感。
纵观河内白鹿山近两千年的发展变迁,从魏晋时期形成名山,到十六国北朝时期名山地位进一步发展巩固、隋唐时期的文化鼎盛期,再到北宋以后其地位的衰落,直至近代以来销声匿迹,亦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整个中原地区历史地位的变迁。当洛阳、邺城等中原城市作为都城时,白鹿山所在的河内地区属京畿之地,其时白鹿山则具有全国性名山的地位。而在中原地区丧失政治中心地位之后,其文化影响力也在日渐下降,白鹿山则降格为地方名山,直至近代以来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值得欣慰的是,当历史的车轮来到21 世纪的今天,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产业成为发展迅速的朝阳产业,白鹿山之名被这一区域人们熟知的新地名所取代,如八里沟、关山、宝泉、云台山等,这些地方作为著名的旅游景区已经成为河南人民乃至全国人民和国际友人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也许,这正是中古文化名山白鹿山另一种形式的重生,山地历史的一种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