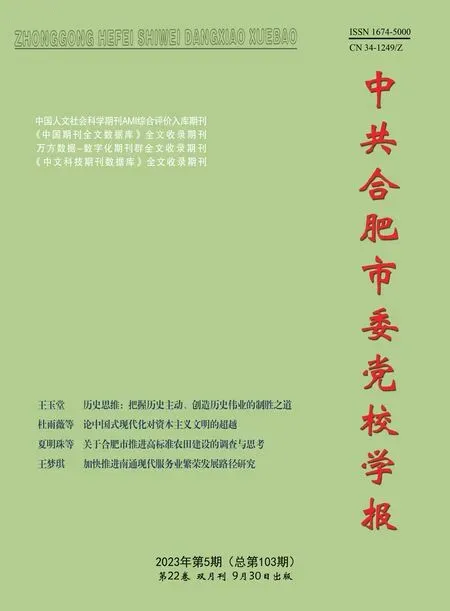马克思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历史性考察
——基于《论犹太人问题》的解读
王启立
(南开大学,天津 300350)
恩格斯曾经说过,“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 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1]12。这种历史感在形式上最直观的展现是,黑格尔不是像其他哲学家那样将世界视为静止的哲学体系,而是运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三段式,将世界理解为一个处在运动、变化之中的精神体系。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进行了批判性的改造,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唯物辩证法,他没有摒弃黑格尔 “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三段式,而是为其赋予了深厚的社会历史内涵。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最为著名的三段式出现在其后期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研究对象分别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生产资料所有制,而对于其早期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有关“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三段式,学者们一般较少论及。故而,本文力图梳理清楚马克思于《论犹太人问题》中针对这一问题的三段式思路。
一、政治性的市民社会与基督教国家的原初融合
1843 年,为反对鲍威尔在犹太人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马克思写作了《论犹太人问题》一文,并于次年发表在《德法年鉴》上。马克思主要在三个问题上驳斥了鲍威尔的观点,这三个问题按照写作顺序依次为:犹太人能否在不放弃本民族宗教的情况下获得政治解放? 犹太人的宗教和人权是否彼此冲突? 犹太人究竟应该采取哪种方式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在讨论第二个问题的时候,马克思谈到了政治解放实现之前的旧式社会的历史情况。“旧社会的性质是怎样的呢?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述:封建主义。”[2]186具体而言,封建社会下,不仅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没有被严格区分,而且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也没有实现分离。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是相互渗透、彼此交织在一起的,共同构成了政治解放之前的封建社会。根据马克思的论述,这种社会实际上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政治性的市民社会与基督教国家。
(一)封建的市民社会是政治性的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这一概念作为理论术语起源于十七、十八世纪,在斯密、李嘉图和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被用于指称基于分工和市场而形成的交往关系及社会组织,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商品经济关系。通过对西欧历史的深入分析,马克思不仅洞察了资产阶级理论家们所揭示的市民社会的现有内涵,而且也精准把握了市民社会的历史内涵或原初含义。他指出:“旧的市民社会直接具有政治性质,就是说,市民生活的要素……已经以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的形式上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2]186一般而言,市民社会的各种要素如私有财产、个体劳动、商品交换等都是同政治领域无关的从属于私人的存在,可是,在封建主义下,政治性不仅是封建国家的本质属性,而且是处于它的统治之下的市民社会的直接特性。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具有封建色彩的市民社会不是斯密、李嘉图和黑格尔所谈论的市民社会,而是旧式或政治性的市民社会。处在这种市民社会中的人,他的经济属性就是他的政治属性,他的私人特性就是他的公共特性,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是几乎重合在一起的,物质因素就是给社会人群划分等级的政治依据。所以可以说,政治性的市民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如帮工、行会师傅等,都可以在自己的经济所得中确认自己在社会中的政治所得。
众所周知,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经济因素是全部社会生活的决定性因素,不过,在封建社会中,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限制,经济因素对社会生活所起的决定作用尚未显著地表现出来。取而代之的是,代表政治权力的皇帝、国王、领主等事实上掌管了全部社会生活,如此,政治因素便在各种社会因素中起决定作用。政治性成为封建社会的本质特性,政治力量成为代表封建社会的唯一力量,“市民社会等级与政治等级具有同一性,市民社会实际上就是政治社会”[3]。
(二)封建国家是基督教国家
在《论犹太人问题》这篇论文里,有关基督教国家的论述出现于马克思与鲍威尔的第一个问题讨论之中,即犹太人能否在不放弃本民族宗教的情况下获得政治解放。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得出了与鲍威尔截然相反的结论。在鲍威尔眼中,犹太人问题是纯粹的宗教问题,如果犹太人想要使自己获得解放,就应该放弃自己的犹太教,因为普遍性的政治解放是以废除宗教为前提的。“只要国家还是基督教国家,犹太人还是犹太人”[2]164,就没有任何一方可以获得解放。马克思则认为,如果说犹太人问题是宗教问题,那么,这只是适用于还没有实现政治解放的德国。“在德国,不存在政治国家……犹太人问题就是纯粹的神学问题。”[2]168可是,在那些已经完成了政治解放的国家,犹太人问题便不再是单纯的宗教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世俗问题。
不同于英法等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德国由于在政治制度上落后于其他先进国家,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国家,而是基督教国家。“所谓基督教国家,就是不完善的国家,而且基督教对它来说是它的不完善性的补充和神圣化。”[2]176也就是说,基督教国家之所以需要基督教来补充自身,是因为这种国家是还没有实现政治解放的封建国家,而封建国家是无法像现代国家那样实现人在政治领域中的普遍性的。与之相反,在英法等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现代国家,由于已经在政治领域之中实现了人的普遍性,即把每一个人都变成具有普遍意义的公民,国家便不再需要宗教来补充自身。因此,只有现代国家即民主制国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基督教国家充其量只是一种还没有成为国家的国家。
虽然基督教国家不是真正的国家,但它也无法使自身成为真正的基督教国家。马克思说:“它对自身来说,始终是一个可疑的对象,一个不可靠的、有问题的对象。”[2]178为什么基督教国家会产生这种自我怀疑呢?原因在于,代表彼岸世界的普遍性的宗教,会同代表此岸世界的特殊性的封建君主发生冲突,这是基督教国家凭借自身力量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基督教国家在把基督教奉为国教的同时,理应把自己视作奥古斯丁所断言的上帝之城的人间化身。在这种情况下,它就需要把宗教在幻象领域所实现的人的普遍性,变成在现实领域中真正存在的人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基督教国家从其本质而言是前资本主义阶段的落后的封建国家,它事实上维护的是以封建君主为首的土地贵族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它不可能实现人在现实世界中的普遍性,所能实现的只是人的特殊性。因此,基督教国家只能是一个自我分裂的、内在冲突的政治实体,它的宗教目的同它作为国家的世俗目的是彼此矛盾的。马克思认为,“这个国家只有成为天主教会的警士,才能摆脱自己的内在痛苦。”[2]178这不禁让人联想起十二、十三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在那种情况下,德皇、法王、英王等世俗君主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天主教会的警士”。
综合以上论述,无论是在私人领域还是在公共领域,封建社会都不能真正地实现人的普遍性。尽管封建君主及其附属集团充当了公共领域的代表,但却只具有形式上的普遍性,实质上所代表的还是少数统治阶级的利益,始终“表现为一个同人民相脱离的统治者及其仆从的特殊事务”[2]187。而如果使宗教在彼岸世界中所许诺的人的普遍性成为现实,就不能通过所谓的基督教国家这一途径,必须要通过资产阶级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即政治解放。
二、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论
《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与鲍威尔对于如何看待政治解放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由于当时德国的政治制度处在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以鲍威尔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高调鼓吹政治解放的历史作用。在鲍威尔看来,政治解放是以消除人的特殊性为前提的解放,这种解放能够使人在现实社会中获得真正的解放,而对于如何解决犹太人问题,他同样诉诸政治解放。鲍威尔认为,如果犹太人想要使自己从政治上受压迫、受歧视的状态中解放出来,首先应该放弃自己的犹太教,因为政治解放是使人摆脱宗教束缚的真正的解放。马克思并不否认政治解放所具有的重要历史作用,“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2]174。可是,马克思认为,鲍威尔只是看到了政治解放在人类历史中所产生的积极作用,而没有发现它所具有的内在局限性。正是由于鲍威尔理论分析的片面性、狭隘性,他在谈论解放问题时实际上把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混淆在一起,将政治解放误认为人的解放,从而夸大了政治解放所具有的有限意义。
(一)社会境遇、人的生存的二元化
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最突出、最明显的局限性在于它导致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彼此分离甚至对立。通过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政治革命,以资产阶级为首的人民群众推翻了封建贵族的统治,用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国家取代了传统的封建国家即基督教国家。由于不需要宗教来充实自身本就具有的普遍性维度,政治国家同宗教这一私人领域的要素实现了脱离,国家真正具有了公共性、普遍性的内涵。在国家同私人领域分离的同时,市民社会也同公共领域实现了分离。马克思认为,“政治革命是市民社会的革命”[2]186。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是市民社会通过革命运动使自己从封建国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清洗掉自身所具有的政治因素。通过这种剥离,政治革命催生了新型的、纯粹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的各种要素,“只有当国家宣布它们是非政治的因而让它们自行其是的时候,它们才开始获得充分的存在。”[4]317因此,政治解放导致的结果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化:一方面形成了只与公共领域事务相关联的政治国家,另一方面形成了已丧失掉任何公共属性、只具有私人属性的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这种分离带来了资本主义下人的生存的二元化,即每个人都生活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双重状态之中。马克思说:“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2]172“天国”所对应的是政治国家的成员即公民(citoyen),“尘世”所对应的则是市民社会的成员即市民或人(homme)。一方面,在政治国家中,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及其观念被彻底抛弃,自由、平等成为现实,人在政治共同体中具有了现实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在市民社会中,尽管人人生而平等得到社会普遍认同,但是各个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却依旧是最直接的、赤裸裸的社会现实。每一个人始终是作为利己的存在物而生存的,都把自己视作最高目的,而把他人看作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可见,政治解放并没有带来真正的解放,人实际上是生活在彼此对立的两种状态之中,在前一种状态下,作为公民的人是社会存在物,在后一种状态下,作为市民的人是个体存在物。
(二)二元化中的颠倒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在理解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市民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时,所持有的是一种颠倒的、错乱的、不合理的态度。既然政治国家体现着人的类本质,是人的普遍性在公共领域的真正完成,那么,它就应该成为市民社会的目的。因为与政治国家所代表的普遍性相比,市民社会所代表的只是特殊性、有限性,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不是具有普遍性的人,而只是具有特殊性的个体。可是,现实历史中所呈现出来的情况却恰好相反,除了在革命的高涨时期如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时期,政治国家曾经短暂地成为目的外,在绝大多数时间,政治国家都沦落为市民社会用以实现自身的一种手段。
另一个颠倒性的关系存在于市民与公民之间。作为公民的人所体现的是人作为社会存在物的属性,是人所应该具有的类的普遍性,是人之为人的类本质。所以,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只有成为公民,才能使自身作为真正的人进行行动。与之相反,在私人领域,人是一种依旧处在特殊性之中而并未上升到普遍性的人,所充当的只是一种不真实的人即市民。按照这种区分进行理解,代表普遍领域的公民理所当然是代表特殊领域的市民的目的,然而,现实情况正好相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并不把自己的公民身份看作自己的现实存在,而是把不具备普遍性的市民身份视作自己的真实的、本真的存在。在政治国家中,“人是想像的主权中虚构的成员”[2]173,只有身处市民社会,人才感觉到自己是活生生的、真实的存在。由此,本应是目的的公民变成了手段,本应是手段的市民却变成了目的。
以上所说的颠倒且不合理的二元关系恰恰暴露了政治解放的局限性,即政治解放只是而且也只能是在政治领域中赋予人们以普遍性。在马克思看来,政治解放之所以是政治解放,正在于它是对其他社会领域不加触动而只是解放政治领域的解放,所以,它必然对市民社会采取不加批判的态度,并且把它当作对政治国家而言的天然的社会前提。而且,政治国家也只有在同市民社会保持对立的情况下,才能够将自己确认为政治国家。正是由于政治解放对市民社会的非批判性,市民社会才会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成为政治国家的目的,市民才必然比公民更加真实。
政治解放对市民社会的非批判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是人们并没有获得真正的、直接的解放,而只是得到了虚假的、间接的解放,即通过中介实现的解放。马克思说,“国家是人以及人的自由之间的中介者”[2]171。正是在如何看待政治国家所能实现的解放程度上,鲍威尔错误地把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理解为个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与之相反,马克思认为,国家所能实现的只是间接的解放,而不是直接的解放,所以,国家摆脱宗教的束缚并不妨碍个人依旧信仰宗教,国家自由的实现并不意味着个人能够获得同样的自由。“摆脱了宗教的政治解放让宗教持续存在,虽然不是享有特权的宗教……就像当时北美的福音派运动。”[5]由于政治解放无法解决宗教问题,同样也无法解决犹太人问题,马克思认为,“只有对政治解放本身的批判,才是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批判”[2]167。
三、真正的共同体是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扬弃
“由于国家是客观精神,所以个人本身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6]254马克思认为,通过政治国家的中介所实现的解放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解放,真正的解放是个人无需通过任何中介,只是在自己的感性生活、自己的个人存在中就可以直接实现的解放。这种解放是人的解放,由于个人的自由不再需要经由政治国家的中介,政治国家会丧失自身存在的历史必然性而趋于消失。并且,与政治国家相对立的市民社会也会趋于灭亡,类的普遍性会成为全部社会领域中人的现实属性,人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感觉到自己是类存在物。由此可见,人的解放的完成必然意味着社会结构有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政治国家所代表的人的普遍性将完全成为现实,导致政治国家失去了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二是由于全部社会领域中普遍性的实现,市民社会这一特殊性的堡垒被彻底摧毁。
代表人的解放实现的真正的共同体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扬弃自身的结果。“劳动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抗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市民社会;从此再不会有原来意义的政权了。”[7]275正是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废墟上,真正的共同体这一社会组织得以建立。《论犹太人问题》中,关于真正的共同体或实现人类解放的社会组织到底是什么样子,马克思并没有详加论述。但是从仅有的阐述来看,我们可以发现真正的共同体是具备以下三个特质的,并且这些特质都同之前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有所关联。
(一)人真正地成为类存在物,一切异化随之消失
鲍威尔高估了政治革命对于人的解放的意义,马克思认为,政治革命只是使个人在政治领域中获得了普遍性,在政治领域之外,个人仍旧像从前一样是特殊性的存在。由于政治解放没有使个人真正地摆脱自己的特殊性,具有类的普遍性的人之本身的力量,就只能以一种异化的形式返回,这带来了政治国家的异化以及市民社会中的各种异化现象。
“人在公共领域的自由(即国家的自由),并不等于人在私人领域方面的自由,不等于人的自由。”[8]160尽管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政治革命使人们在政治领域获得了自由与解放,但这种自由是通过一种特殊性的中介来实现的。马克思认为,“正像基督是中介者”[2]171,“国家也是中介者”[2]171,是一种在人之外并同人相对立的异己性存在,由此导致政治国家的异化。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经济领域之中,由于每个人都是特殊的、孤立的原子,把各个原子即特殊个体联系起来的社会中介便成为一种异化存在。这种中介正是人人都渴望得到的金钱或货币,它带来了市民社会中最为根深蒂固的异化现象即货币拜物教。
与政治解放不同,真正的共同体可以使人获得完全的解放。“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2]189但是,只有真正的共同体所代表的人的解放才能够使人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都取得类的普遍性。正是由于普遍性的本质力量复归到了人自身,政治解放所导致的政治国家的异化以及货币拜物教在真正的共同体中都走向了消亡。
(二)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类存在与个体存在的矛盾将得到真正解决
在实现了政治解放的条件下,公共领域同私人领域的矛盾之所以无法得到有效解决,是因为政治解放只是对政治领域即公共领域进行变革的解放,它把市民社会即私人领域中的各种要素当作无需论证的天然前提。这种无法解决的矛盾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社会处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个人处在市民与公民的双重状态之下,并且,这双重状态之间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颠倒的、错乱的和不合理的关系。真正的共同体恰恰是对这一矛盾的真正解决,在这种共同体中,人们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不再相互隔绝而是彼此交织在一起,真正的共同体的成员将会“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2]189。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公共领域同私人领域、类属性同个体属性的统一正是对政治解放所导致的二者分离的超越。
(三)宗教由于失去了自身赖以存在的世俗基础而在未来走向消亡
马克思认为,宗教之所以能够在人类历史中长期存在,是由于个人是同其他个人分离开来的、只具有特殊性的人,是还没有获得普遍性的人。具体到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政治解放没有从根本上变革市民社会的特殊性,反而把这种特殊性视作自己的天然前提,宗教也就不可能真正地走向消亡。所以,只有彻底变革市民社会以及其所包含的各种私人要素,使现实的人成为具有普遍性的人,宗教问题才能得到真正解决。这恰恰是人的解放的旨趣所在,这种解放用真正的共同体取代了象征特殊性的市民社会,用作为共同体成员的人取代了作为市民的人。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人不再是彼此分离的原子,而是共同体中的成员,因而便不再需要宗教这一幻象中的普遍性来充当人们的精神慰藉,宗教就此踏上了它的消亡之路。
从以上分析可见,真正的共同体既是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否定,也是在人的解放的条件下对二者所代表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所做的一次崭新探索,这可以称得上是一次扬弃。真正的共同体克服了许多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单凭政治解放而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
真正的共同体是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既批判又继承、既克服又保留的结果。在马克思看来,这一新型社会组织正是对犹太人问题的真正解答,因为犹太人问题就本质而言不是鲍威尔所声称的宗教问题,而是市民社会中的犹太精神问题。“鲍威尔要通过扬弃宗教而实现人的解放,马克思则要通过废除私有财产达到这一目的”[9],犹太精神是建立在市民社会的私有财产基础上的货币拜物教或拜金主义,而如果市民社会被一种新型社会组织即真正的共同体所取代,犹太精神自然也会随之消失。“如果有一种社会组织消除了做生意的前提,从而消除做生意的可能性,那么这种社会组织也就会使犹太人不可能存在。”[2]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