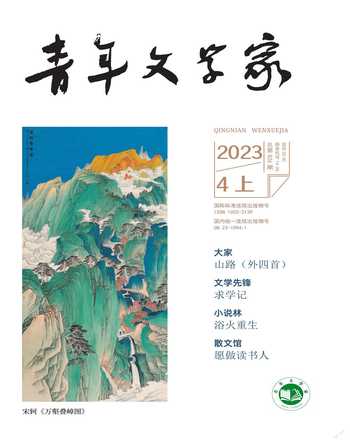祖母
李保林
祖母出生于中条山下冷口村一个姓郭的大户人家,十五岁那年嫁入我们留孟李堡村李家。
祖母善于持家,是一位非常贤惠的女人,干净利落。曾祖父母去世后,家务便由祖母一手操持料理。芒种时节,田地一片金黄,正是“龙口夺食”的紧要关头,家里雇了人干活儿,全由祖母一人做饭。祖母“咣当咣当”带有节奏感的擀面动作非常优美,一把四五十厘米长的切面刀落案有声,看似沉重的刀身在祖母的手里变得轻盈灵巧,切面一气呵成,粗细均匀的面条就出现在了祖母的手下。在祖母的指导下,我十来岁便学会了擀面。那个年代,鞋子、衣服全靠手工纺棉、织布制作。祖母的炕头上,常年放着一架纺棉车。每天晚上,我就在祖母纺棉的“嗡嗡”声中入睡,清晨又在“嗡嗡”的纺棉声里醒来。
祖母心灵手巧,能蒸出好多花样的喜馍,还会用红纸剪出各样的喜字。祖母还乐于助人,谁家办喜事都请她去帮忙,她总是有求必应,欣然前往,即使累得胳膊疼、腿疼,也乐在其中。
祖母视孙如命,当老师的父亲偶尔给祖母买点儿好吃的,祖母总要留给孙子。我们兄弟和堂兄弟十几个,满院里跑着、闹着,她看着哪个都可爱。我小时候调皮,母亲脾气又暴躁,教训起我来往往是往死里打。但由于我时常陪着祖母住,祖母对我便格外疼爱。我杀猪般的号叫揪着祖母的心,这时,祖母就会出来把我护在胸前,呵斥母亲教育孩子太简单粗暴。晚上临睡前,祖母要上厕所,我便点上马灯在前面照路。在当时,我们家的厕所是极超前的,跟平常盖房一样,设有顶棚,下雨、下雪都不受影响,而且祖母每天都把里面打扫得很干净,别人都很羡慕。
祖母每年都要回娘家几次,由我陪着。大人说,我们村到冷口有五里地,但我感觉非常远。祖母拄着拐杖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冷口河里有水的时候多,河里垫脚石过宽的话,祖母是跳不过去的。我便搬一块石头放在中間,再在前面拉着祖母的手小心翼翼地过河。有一回,路过工农兵食堂,火烧的香味撩拨得我不想走。一个火烧六分钱,祖母摸遍了口袋也没掏出来六分钱,我便哭着满地打滚儿,祖母心疼得哄着我,又无奈得像做错了事的孩子。上小学四年级那年,我学会了骑自行车,一条腿从车梁下掏过去跨着蹬半圈。这样,祖母再回娘家的时候,我便能用自行车驮着她去了。平路上我骑着,上坡时就推着。到河边时,我先把自行车扛过去,再回来牵着祖母的手过河,来往的人都夸我。
祖母一生养育了四个孩子,有我的伯父、我的父亲,还有两个姑姑。祖母除了回娘家外,也到姑姑家小住。祖母一生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小姑。小姑从小体弱多病,那时医疗条件落后,落下了残疾。出嫁后,家境又不怎么好,孩子又多,日子非常难过。小姑家住着一孔破窑洞,窑顶很高,上面有一棵苍老的柏树,老远就可以看见。到了小姑家里,祖母一刻也闲不下来,把所有的被褥浆洗一遍,还要给外孙们做几件衣裳。小姑家的土炕上跳蚤猖狂,我怕咬,便急切地盼望着去大姑家。
大姑无论是样貌还是性情都像极了祖母,漂亮、聪慧、善良、贤淑,尤其是那双深邃、美丽的眼睛,永远透露出智慧与慈祥。大姑父在外有工作,光景相对要好些。大姑总是把家里打理得干净利落、井井有条,祖母去了竟找不出什么事可做。但她的心永远在小姑那里,到老都没有放下……
祖母最后的那段日子,为了不给儿女添麻烦,她从未把痛苦表现出来。有一天晚上,祖母没有让我吹灯,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林儿,奶奶要走了,陪奶奶说会儿话吧。”我嘴上答应着,却不知不觉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窑里一片寂静,看着祖母安详的睡颜,我连叫了几声“奶奶”,都没有回声。那一年,我十六岁。
如今,祖母离我而去已四十余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好多事情已经逐渐淡忘,而祖母的音容笑貌在我的脑海里越来越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