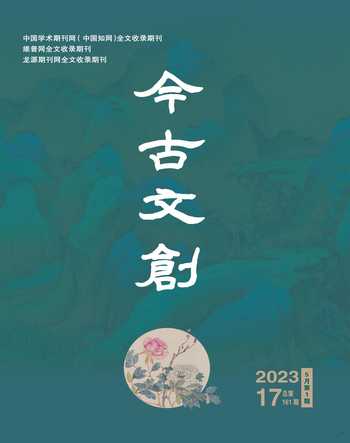热拉尔·热奈特叙事学理论视角下的《爸爸呢?》叙事策略分析
【摘要】 《爸爸呢?》不仅反映了俄罗斯的社会文化中被忽视的伤痛,而且在叙事形式,尤其是在叙事声音与观点、聚焦书写形式上,展现出了作者高超的叙事技巧,更体现了重要的跨文化研究价值。本文借由法国学者热拉尔·热奈特的叙事学理论,就其中的叙事声音、观点以及聚焦形式,结合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的关系,对文本的叙事层次和节奏进行剖析,分析这篇作品如何以精练的语言述说故事,又如何抒发感情。以此来探索先钦的书写技巧,并且证明叙事学理论对俄罗斯文学亦有指导作用。
【关键词】 跨文化研究;叙事理论;热拉尔·热奈特
【中图分类号】I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7-0029-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7.009
一、引言
罗曼·瓦列里耶维奇·先钦 (Роман Валериевич Сенчин)出生于1971年,是俄罗斯当代著名小说家、评论家。俄罗斯文学评论家谢尔盖·别利亚科夫曾评论道:“……我们将通过先钦的故事和小说来研究1990年代和2000年代的俄罗斯,就像我们通过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和埃米尔·左拉的小说研究十九世纪的法国。” ①《爸爸呢?》是罗曼·先钦的一部短篇小说,叙述了一个四岁多的男孩戈尔杰伊因为父母离异,被母亲送到外婆家,后又因母亲再嫁被接走的故事。小说情节简单,言语简练,但是在作者的叙事策略之下,呈现出别样的审美趣味。本文以欧洲经典叙事学奠基者热拉尔·热奈特的叙事学理论作为理论依据,分析《爸爸呢?》的叙事者以及聚焦角度。
二、《爸爸呢?》的叙事者(Narrateur)
《爸爸呢?》的叙事者类型是故事外而异故事的叙事者,作者担任了叙事者的角色。他拥有上帝视角,无所不在、无所不知,能够完全并且权威地掌控叙事,提供给读者非常多的故事发展细节,可以随意进入人物的内心、精神世界,评价人物的所作所为、情节的发展走向,对读者进行警示等。
如在作品开始之处,叙事者以回忆戈尔杰伊在父母离异之前的生活展开叙述,评论道:“只有斑驳的眩光,让他隐约感觉到,那里有重要的东西——好的和坏的,那些已经消失的东西。它们逐渐模糊、蒸發、烟消云散。”为整篇小说设下基调——淡淡的朦胧与伤感、几分迷茫与无措。全知叙事者以其权威性完全掌握了叙事基调。不仅如此,“无处不在”的叙事者,熟谙一切内情,在所有场合都可进出无阻。小说伊始,在主线开始之前,叙事者就展开了对戈尔杰伊童年的回望:“也许,在此之前,戈尔杰伊曾有过一段时间。也许,他哭过,笑过,看电视,玩玩具,给沙箱挖洞,结识伙伴,和小男孩、小女孩吵架。”戈尔杰伊母子俩辗转多地来到外婆家的过程中,叙事者也如影随形,在火车站上对众生百态的描写更是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状况:“汽车短短的,有一扇门,里面有一条狭窄的过道,人却很多,所有座位都坐满了。站着的人纷纷指责妈妈,抱怨她的几个袋子太占地方。”车上的人们对一个单独带着幼童的母亲毫无怜悯,不仅没有帮助之意,反而指责他们妨碍了自己的出行。先钦的作品风格一贯倾向于反映俄罗斯社会状况,叙事者对汽车集体的描述,表面是表现戈尔杰伊母亲的不容易,更深层次是意在体现那个时代的俄罗斯人情冷漠,生活水平普遍不高,难以在保证自己生活水平的基础上还对陌生人施以援手,抑或是民众受教育水平有限,道德水平较低。
全知叙事者无所不知,可以进入人物心理,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描写。本文的人物情感描写集中在主人公戈尔杰伊上。例如,戈尔杰伊在旅途中对母亲暴躁态度的恐惧:“戈尔杰伊想说自己会走,但他想了想,觉得不能说。现在不能和妈妈争论,甚至不能和她说话。最好保持沉默。”作者如神明般,跟随着戈尔杰伊母子俩的行程,潜入戈尔杰伊的内心,感知他隐藏的惊慌无措和害怕。在母亲离开之后,戈尔杰伊和小伙伴们的玩耍以及最后母亲回来接走戈尔杰伊的全过程,叙事者就像是站在戈尔杰伊面前,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目睹了他成长中的所有忧伤和无措,见证了他在父亲角色陡然缺失下的改变,被母亲的话误导以为山羊是自己的父亲,而他的母亲逐渐变得暴躁无奈,愤恨不已,却最终又选择再嫁。
叙事者有时可以以其至高的身份来与读者进行对话。本文中,叙事者很多次都介入文本,发表意见。比如戈尔杰伊不喜欢汽车上的氛围,叙事者对此加以评论:“而汽车上就是一个集体。这个集体不友善,但仍然是一个集体。”当戈尔杰伊沿着街道走路,不认识坑坑洼洼的土地中灰色的、嘎巴作响的东西时,叙事者又评论道:“也许,以后,等戈尔杰伊长大了,他就会知道,那是煤炭充分燃烧后留下的渣滓。”事实上,叙事者很多次对戈尔杰伊的心理描写,都不仅仅局限于直接描写这个五岁不到的男孩的情绪状态,而是叙事者以自己上帝视角的身份,做出了超越孩童认知能力的更深入的分析。比如“也许,他之所以不记得,是因为那时候一切安好、清晰明了——干吗要去记呢?”这不是一个四岁孩童足以达到的思想境界,而是叙事者以全知视角做出的评价,一方面直接点明戈尔杰伊的生活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另一方面烘托了他的无助与迷茫。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叙事者尽管持有上帝视角,却有意隐藏了故事的很多重要线索,并且以主人公孩童的身份作为掩护,一味引导读者跟随主人公的思考方向,导致了读者的误读。比如主人公的母亲说他的父亲是一头“山羊”,主人公信以为真,实则是母亲在骂父亲。②而读者并不一定能立即理解作者故意隐藏的信息,而是需要迂回地结合对话细节以及俄罗斯的文化风俗,这就起到了一定的戏剧效果。
除此之外,在《爸爸呢?》中,作者大量借助人物的观点与声音来叙述。例如,之后解释母亲为什么回来接走戈尔杰伊,是通过她和外婆说的话:“是啊,遇到了这样一个人!他同意带上这个拖油瓶……”叙事者的全知干预被人物的声音降低,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读者对故事的诠释与想象的权力。读者对叙事客体的认知不再是透过全知叙事者,对故事的了解不再是单向的。读者可以更有力地感受人物的情绪,而人物的形象也因此变得更生动鲜明。
三、《爸爸呢?》的叙事聚焦 (Focalisation)
在《爸爸呢?》中,零聚焦叙事是由故事外而异故事的叙事者即传统所谓的第三人称全知叙事与全知观点所组成。作品中的零聚焦叙事共有五种不同的叙事功能:一是奠定小说的气氛基调;二是对故事细节的最大程度把握(叙事者在本文中有意的选择隐性和显性信息);三是编排情节的发展;四是描述人物的内心;五是通过叙述越界(métalepse narrative)对人物以及事件进行评价,为小说塑造了多层次的叙事结构。转喻是西方古典修辞学意义上一个被忽视的概念,法国学者热奈特从修辞学中借用了这一概念,使其从最初纯粹的修辞格术语演变成叙述学意义上的“转叙”,并将之运用于叙事文本中换层叙述的研究。热奈特用叙述转喻(métalepse narrative)来指代叙事的越界,有别于修辞学意义上的转喻,此叙述转喻即为“转叙”。在2004年的新作《转喻:从修辞格到虚构》中,他进一步对叙述转喻做了全面论述,转喻不只是修辞格或风格学意义上的手法,而是揭示“故事世界”与“讲述故事所在世界”之间界限被逾越的普遍状况。他认为“转叙”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赋予文本的写作主体——作者以非凡的创造力。也就是说,作者可以利用进入文本虚构世界的权力尽量发挥自己的文学想象力和虚构功能。叙述者在叙述活动中的创造性作用使得叙述者有可能在虚构叙事活动中违规进入故事层。因此,热奈特提出了转喻在叙事中具有“越界、变换故事层”的作用。其常用的做法就是换层讲述,将另一个故事嵌入或插入正在讲述的故事层中,破坏或者干扰故事层的区别。
开篇对戈尔杰伊童年生活的回顾:“那段时光就像是清晨的一场梦,已被遗忘。”这为后文他和妈妈背井离乡做了铺垫。这篇小说的开头情节发生在故事主线之前,打乱了正常的时间顺序,但不干扰第一叙事,属于外倒叙。后文戈尔杰伊在去外婆家的路上感到很多不适应,作者采用了预叙的手法:“也许,他之所以不记得,是因为那时候一切安好、清晰明了——干吗要去记呢?而现在发生的一切,他知道,他得记住,并且得用很长一段时间去弄清楚……”这就为后文戈尔杰伊在外婆家的小心谨慎奠定了叙事基础。也使读者产生一定的心理预期,会在之后的每一环叙事中寻找符合自己心理预期的细节,并逐渐加深原先的认知。
零聚焦在叙事作品中也时常用来掌握故事的细节。在戈尔杰伊和新伙伴们的交往中,由于初到新环境,他对待小伙伴并不很真诚:“戈尔杰伊想问什么是地铁,但是他不敢。如果问了,他们会觉得他愚蠢。”又如:“不过他不打算说出自己看到了那个老头的幻影。”但是戈尔杰伊之后却勇于制止尼基塔对山羊扔土块,只因为他误以为山羊是自己被施了魔法的父亲。在陌生环境下,支撑戈尔杰伊生活下去的动力是山羊父亲的存在:“尽管日子过得单调乏味,却转瞬即逝。而且雨水越来越多。戈尔杰伊学会了如何打发这些日子——他躺在床上,尽量不动,这样床垫就不会吱呀作响,他幻想着爸爸摆脱魔法变回原样,然后他们——他、妈妈和爸爸一起回到以前居住的地方,那段日子他已经记不得了,他只记得一件事——他们在那里过得很好……”这些细节都没有被叙事者忽略。戈尔杰伊前后性格的对比突显了他对父亲的爱,而所谓“父亲”却不过是母亲怨毒的咒骂,他和父母团聚的愿望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样的情节安排更激发了读者对戈尔杰伊的同情与怜悯。尽管具有全知视角,但作者有意隐藏了关于“山羊”一词的真正含义,读者,尤其是外国读者,第一遍阅读的时候无法理解它的内在意味,所以对戈尔杰伊和山羊的互动产生一定的期待——是否有奇迹会发生呢?但最后母亲的出现打破了这个幻想,在查阅资料后可以了解到山羊在俄罗斯文化里的意味,对戈尔杰伊就更加怜悯了,这起到了一定的戏剧性,为文本增添了几分审美意趣。
安排情节的发展,也是零聚焦叙事最主要的一项功能。在《爸爸呢?》中,全知叙事者不仅无所不知、拥有上帝视角,而且还能够脱离故事发展原本的时间顺序,对其重新进行剪辑和编排,或是详细描述,或是一笔带过,一切安排都被用来突出主题。叙事者在开篇运用了倒叙手法,回顾了戈尔杰伊在父母离异前的生活,并在文中穿插预叙,对戈尔杰伊长大些更懂事的状态做出畅想。不仅如此,小说里的故事时间与叙事的伪时间或约定时间也不总是保持一致。叙事者对于戈尔杰伊和母亲一起坐车、戈尔杰伊和小伙伴一起玩耍这些情节都用了大量笔墨来叙述,但是高度概括(总体上来说、详细来说)凝练概括(概念不清楚)了戈尔杰伊遇到山羊之后,以此为支撑力量度日的叙述:“尽管日子过得单调乏味,却转瞬即逝。”叙事者对于妈妈的回归叙述很突然,仅仅一句话:“妈妈出乎意料地回来了。”小说叙事节奏在叙事者的有意把控之下,跌宕而有序,这增添了故事的可读性。
对人物内心的掌握,也是全知叙事者经常涉足的领域。本文的心理描写主要是对于人物戈尔杰伊,例如:“戈尔杰伊想问什么是地铁,但是他不敢、如果问了,他们会觉得他愚蠢。”而对于次要人物外婆以及母亲,主要靠语言描写来体现他们的心理变化,例如:“去他的吧”,她恶狠狠地笑了笑,“反正我是再也不想生孩子了……戈尔杰伊,爬上来。赶紧!”以及后文:妈妈把他搂入怀中,低声说:“孩子……我可怜的孩子……孩子……”通过妈妈和外婆的对话,不难看出外婆的婚姻也有诸多坎坷,尤其是妈妈回来后,外婆的声音格外刺耳:“塔尼亚外婆的声音很刺耳。透过妈妈的惊喜亮相,戈尔杰发现,塔尼亚外婆从没用这样刺耳的声音和他说过话。”塔尼亚外婆知道了妈妈又遇到了新的男人,出于某种不可言说的情绪,她对此感到不满。在叙事者以各种方式展现人物内心的同时,人物形象也被塑造的愈加丰满。
在全知叙事中,叙事者也时常介入文本,对人物或者故事做出评价。比如:“他听到了妈妈和塔尼亚外婆之间的一段不大明白的对话。更准确地说,他不想明白,以免害怕。”孩子的思考尚且达不到这个地步,是叙事者站在上帝视角的立场上,以成年人的思考境界对此做出判断。叙事者面对年幼的戈尔杰伊,畅想几年后:“然后他俩沿着街道走着,这不是柏油路。取代柏油路的,是坑坑洼洼的土地。也许,以后,等戈尔杰伊长大了,他就会知道,那是煤炭充分燃烧后留下的渣滓。”一语双关:道路环境从柏油马路变成了坑坑洼洼的土地,这改变象征着过去美好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隐含了生活环境比以前差,等待着戈尔杰伊的将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模式。戈尔杰伊的不理解表面上是对新马路构成成分的困惑,实则是对新环境的迷茫,对未知生活的无措。
四、结论
综上所述,罗曼·先钦作为故事外而异故事的叙事者,以零聚焦作為聚焦模式,结合转叙、内倒叙、预叙以及转叙等手法,构造了一个具有多叙述层次且节奏多变的故事。虽然故事情节线单一,且主要人物是个不足五岁的孩童,但先钦巧妙的叙事技巧使戈尔杰伊、妈妈以及外婆这些人物形象都十分立体,即便是从来没有正面描写的“父亲”角色,那不负责任的形象都跃然纸上。叙事者以误认“山羊”为父亲作为全文最重要的隐藏线索,全文前后暗含对比,突出了“父亲”角色缺失对戈尔杰伊的影响之深厚,戈尔杰伊对父爱渴望之迫切,也表现了单身妈妈的诸多不易。如前文所述,塔尼亚外婆同样婚姻不幸,那么,父亲的角色缺失,是否是那个年代俄罗斯社会的普遍现状呢?
以法国学者热拉尔·热奈特的叙事学理论作为理论依据,以天然的跨文化视角分析俄罗斯文坛新生代领军人物罗曼·先钦的作品,证明叙事学理论对俄罗斯文学亦有指导作用。
注释:
①С. Беляков, Роман Сенчин: неоконченный портрет в сумерках, ?Урал? 2011, № 10. Цит. по: Все о Сенчине. В лабиринте критики, сост. и предисл. В. Огрызко, Москва 2013,с.388.
②在俄罗斯文化中,将某个人特别是某个男性称为 “山羊”,是对他的极大侮辱。这就类似于汉语中的“畜生”,再附加上淫荡、不负责任的含义。刘早:《罗曼·先钦的“不知情者”叙事》,《世界文学》2020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M].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
[2](法)热拉尔·热奈特.转喻:从修辞格到虚构[M].吴康茹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
张然,女,汉族,安徽铜陵人,安徽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