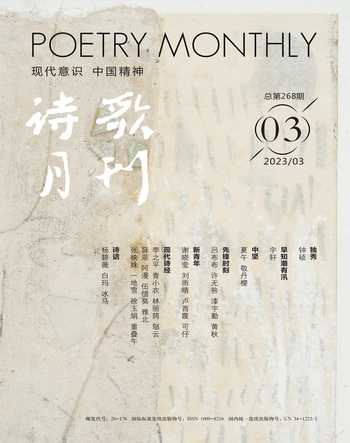从“超性别书写”谈起
女性主义研究审视男权的历史,在西方总得从柏拉图开始追踪,一到中国,就总会从周公之礼、孔孟之道说起。本文不是思想史考古,单举明代一例以证。胡震亨在《唐音统签》里盛赞薛涛“薛工绝句,无雌声”,试问一下,这到底是赞呢还是贬呢?或者说,这无非是传统诗歌批评史中男权话语系统的必然价值逻辑。评判女性诗歌以绝无女性视角和声音为最佳标准,此并非孤例。
接下来我们看看在已然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某青年学人如何以王小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晚期以来的作品为案例,“提倡”女性诗歌的“超性别书写”的。他统计王小妮诗文本的人称代词词汇表后,发现其诗几乎不使用“她”这一人称代词,进而武断声称,“她的诗歌抱负不允许她将诗歌局限于‘女性这一狭小的范畴之中,她一直追求诗歌最大的包容度、最大的自由,而像‘性别写作这种作茧自缚的事情,她是绝对不会去做的。王小妮说她从来没想过使用‘她,可见对于狭隘的诗学观念的警惕已经融入她的血液”。这种对所谓“超性别写作”的粗浅描述,甚至带有对1980年代女性诗歌实践中深度表现性别意识、女性个体生命经验所结出的历史硕果的情绪化否定,几近是对1980年代“女性诗歌”实践的主题、题材、语言特征和表现出的思想性的矫枉过正式的否定。这种所谓超性别写作的浅表化界定,和胡震亨“无雌声”的单极男性批评立场和态度,有何差异?两相对比,让人有“今夕何夕”之恍惚。
但王小妮南下深圳不久后写下的组诗《看望朋友》,从个体对“病”的经验出发,抒写生命的脆弱、无常,从他人的病躯里,“我亲眼看见了疼”,“我亲眼看见/一个人被无声折断”,“我亲眼看见了死的/接近”,看见了“没有一根羽毛还有力气飞翔”。诗人面对疾病甚至生离死别的敏锐、细腻体悟,切肤之痛,其诗之言语何尝不是深伏着女性对客体物象的敏察本能,体现了融会自我情感、生命经验乃至社会阅历的心象的抒写能力。
女性诗歌,按崔卫平的理解,在1980年代实际上可以统称为当代中国的“女性主义诗歌”;然而,当时间线跨进1990年代,诗歌中的女性主义表达已经完成了它的阶段性历史使命。如果联系四十年来的整体女性诗歌史,并将其比喻为一位女性个体发育、成长旅程的话,那么1980年代那段风云际会也大旗变幻的狭义“女性诗歌”史,就是“她”的叛逆期:她感觉到了自己的性别,焦虑如何表达自己作为“另一个”性别生命体的欲望、身体感受和爱的本能;她渴望独立,在一个逐渐走向开放的社会变革大语境中,她通过诗歌这一文体形式,甚至以声嘶力竭的音调“发表”着自己,就像九十年代被介绍进中国的法国女性作家西苏所言,“女性必须书写自己”。她们首先以诗的样式把自己写下来,写进来,写出来。
这是女性在练习表达自己、在努力替自己发声的“雏声”实验期;她们反复调适自己的声调、语调和节奏,努力地清晰表达自我的欲望和生命经验。不破则不立,这是她们“成长”的必由之路。否则,那个评价女性诗歌书写至高成就的“无雌声”标准,怎么被推翻直至被重构?为什么到了提倡女性的“超性别写作”者这里,1980年代的女性诗歌先贤们依然如此不被理解和认同?
当个体女性写作者开始走向成熟,“她”的叛逆可能更多地必然朝向自我。翟永明早在写完“女性诗歌”开山之作组诗《女人》后,便以《静安庄》开启了自我反叛式书写实验。可以说翟因其书写的自觉性,孤独地走在了整个八十年代女性诗歌的先锋处。她在《女人》最后一首《结束》中,六次执着地发出疑问:“完成之后又怎样?”同一诗句通过复沓与循环的方式,既构成了诗节之间的往复、重生节奏,也形成了一种声音的环绕、放大、共鸣效果,将诗人内心的自我犹豫、质疑扩大到内心之外,极富感染力地传导给读者,引导读者作进一步思索。她在1995年曾说,“长期以来潜伏在我写作中的疑惑恰恰来自《女人》的完成以及‘完成之后又怎样?的反躬自问。”八九十年代之际,伊蕾、小君、唐亚平等人,陆续从女性诗歌的书写实践中退隐,翟也曾隐忍不发三年左右,最终以《咖啡馆之歌》(1992年),同王小妮一道打破单一的女性主义化表达和抒情语法结构,迈进了具备真正“女性风格”多元化,丰富化形态的探索和实验时期。
然而,在她们孜孜以求地进行女性书写的探索时,诗歌批评界却大踏步退缩了,大而化之地提出了“超性别写作”这么个概念。批评家以此割裂了八九十年代之间的“女性诗歌”持续发展的整体性,却对女性到底应该如何“超越”其性别,语焉不详;更无法具有说服力地回答这一问题。
批评家们归纳认为,以翟永明、唐亚平、伊蕾和海男为代表的1980年代女性诗人,创造了一种中国式的“女性”创世神话,将“黑色”“黑夜”“红色”等等非具日常生活价值意义的色彩语汇,建构为意象体系,并以此作为“她们”的重要抒情方法。而在对1990年代的“新”女性诗歌文本特征进行总体概说时,他们则说,“她们”以书写实践着力表现“失去象征的日常世界”(耿占春语),从1980年代女性诗歌“不食人间烟火”的抒情结构,“回到尘世”(董秀丽语),重返“人间”琐碎的日常生活,从中去寻找、发现诗意,仅仅“飞翔在‘日常生活与‘自己的心情之间”(罗振亚语)。这便是他们所认为的“超越”了性别意识和意志的女性诗歌的“新”形态、“新”结构。循此逻辑,后来的“女性诗歌”,比如余秀华那些“越轨”的女性欲望书写,难道不也是诗人作为独立女性个体,在进行自身情感、爱欲的日常经验表达的同时,依然承续了1980年代中后期“女性诗歌”追求二元性别差异伦理基础上的“女性主义”精神特质?难道不是依然在抒发诗人自己追求两性平等的女性主义理想吗?
女性诗歌,在1980年代通过一批诗人艰苦卓绝的书写实践,完成了对男权话语及其抒情语法结构的“反题”和“破题”;自1990年代始,它在语言风格、题材、主题、抒情语法等不同维度和向度,朝向更为开放的结构转型转折,朝向多元化深入嬗变。面对如此书写实践态势,批评家们在新世纪之初却仅仅征用一系列“概论”1990年代以降汉语诗歌整体演变动态的术语,诸如日常化、叙事性等,作一种普泛化解读,暴露出了理论失语之态。更显意外的是,他们在飞越1980年代的“先锋意识”之后,却一步退回到了性别社会的“前现代”,滑向了男权话语的边缘。
法国晚期女性主义理论家露丝·伊丽格瑞认为,“女性风格”这一总体化范畴具有的美学特征,包括“她们”生理需求与反应的多元化、性别意识与意志的丰富性、精神取向和语言风格的复杂性,以及建立在男/女二元“性别差异伦理学”基础上的、与男性互为平等和互为丰富的性别身份及其价值追求。当代中国女性诗人四十年前即已开始且经过十来年努力之后,便初步完成了对男性诗歌话语的反抗使命。进入1990年代,“她们”从自反、超越1980年代诗歌单一的“女性主义”抒情语法结构再出发,继续以书写实践促进女性诗歌前进、嬗变,并朝向更为纵深发展的新起点掘进。
可惜,“她们”依然走在孤獨之路上。譬如有一些通俗易懂的诗作,无非记录了诗人为人妻母的对日常生活场景的悉心观察和对情感经验的琐碎体悟,竟然遭到网络空间狂欢式的污名化。如此看来,即使女性退回到传统或古典的伦理、道德价值体系中去书写,却也依然可能被打入另类。雌声也好,“无雌声”也罢,狭义的女性诗歌也好,广义的女性诗歌也罢,作为普通读者,我们能否真正建立起一种等距的“镜像”阅读方式,而不以“我们”的价值观凌驾于“她们”之上?作为诗歌批评家的专业读者,我们能否不以自己的学术偏见或性别伦理,在讨论“她们”时以偏概全?
冰马,文学博士,创意写作硕士,广西河池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师。
——细读《孔雀东南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