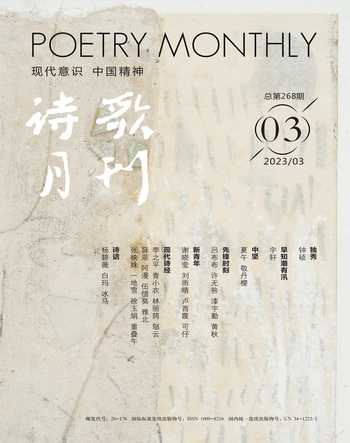雨天(组诗)
给佳怡
试着记下感到快乐的事物,
比如红色、绿色的辣椒。
昨天的晚饭穿过喉咙,进入贫乏的心——
又像小蝶在胃里乱舞。
还有红色、绿色的地板。
当身体从漩涡中坠落,
地板是我的摇篮。
它坚固、沉默,同我很亲近。
我也有红色、绿色的颜料:
两对色彩姊妹,
从很远的地底,或者天上降生。
夜晚悄悄把它们缝进我的衣兜里。
上天赋予我的色彩不多,只有这两种。
我并不感到可惜。
我在红色的火光中取暖,醒来去
照料绿色的树荫,
这已足够。
只是如今,
红色、绿色,和它们之间生长着的
——喷涌的蓝,
(连同它背后的无数只手)
竟瞬间混融成
从未见过的色彩,
全部奔跑到我的眼前。
雨天
去紀念馆的路上,
你光脚踩亮水池为我们开路。
远方的伙伴醒了,循着雨的轨迹飞到你身后
我们牵引着雨之链,
让坠落的雨包裹所有人的脚踝,
(一双脚也不能舍弃)
雨仍不费力地下,雨声中我们激越着浪花,反复溺水。
我的耳朵卷起裤腿,
倾听水花与心之间交错的变奏:
我们踩水,水也跳上来踩我们,
在彼此的身体里温和地游泳,
任凭细密的支流汇聚,不断刮擦我们的身体。
是水,是它的透明让我们抱在一起,
是它浑浊,有点苦涩让我们的身上遍布沟壑,
是它的清澈令我们不断踩水,
踩破一切与古老的水无关的负累。
我说:我的心将舍弃思想,
告别最初孕育我智慧的近亲——
我只是跑着,以至无穷。
不必说“需要”,去看看雨帘,抱紧彼此的手臂,
不必说“恨”,愤怒滑到嘴尖顷刻被雨淋湿,
不必提起人,和你们在一起,就是和更大的雨在一起。
奔跑中,我们忘记今天是纪念馆关门的日子:
它门窗紧锁,内里空无。
我们不识纪念馆的雕像,一开始也不知为何赶来,
我们浪费了鲜花和蜡烛燃烧的时辰,
浪费了从泥水中挣脱的气力,浪费了我们自身……
“被纪念的事物终于都消失”——
我们松了口气,
干脆去纪念,
无数颗荡涤在水中的爱之心,永恒地撞击着彼此——
所有的头发、睫毛都被雨打湿,
你的一整个衣袖也不是干的,
我是从那时起感到你的可贵。
夏夜泳池
慢慢地,我学会手臂伸展,追赶
划水的姿势,将傍晚的泳池
推到角落。被太阳晒得暗红的水
全部向我涌来。
这一轮潮汐被连接,泄了气的游泳圈
已被翻出太多次
回去吧,在还没学会游泳的时候
体会第一次换气,顺水自然向下,
让重力,这一质朴的元素替你抉择。
而如今,我已熟习太多泳姿,以至于让
水都感到恐惧。于是不再有瓷砖围成的
蓝色地带了,不再有戏水的笑声,和来自投机者们的爱了,
我被栅栏重重包围,
丧失掉池水的地面游向自己。
脆弱的夜
为何总在这里结束?
既不是一年中最冷的一天,也不是深夜。
你打翻了水,我去接,在盆中的倒影里,
我们又开始砌墙。
手指,凝视它。留在门把手的指纹一并
消失,你黯然睡去。
暴雨过后,工人再次走上大街
爬上每一栋楼,铸造多灰尘和响声的工作。
暗处有喇叭声:
尚未被解释的部分将来也不会到达。
我们必须先学会等待,等待着,
忍受真实被置换成蒸气,同别的时空联谊
而被打翻的水,因重构的平衡宽恕一切,包括
它易碎的部分
顺利挨过了今晚。
可仔,1999年生于成都,有作品发表于《诗刊》《诗歌月刊》《上海文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