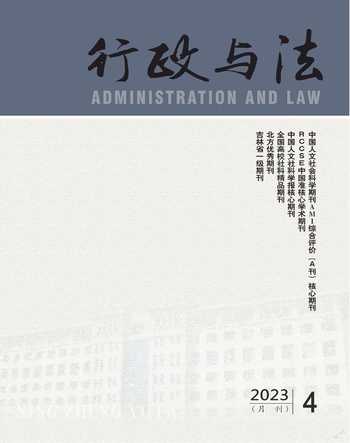刑事被告人财产说明义务的加重及其规制
摘 要:为弥补公诉方指控违法所得不足、解决法官裁判违法所得困难,我国刑事立法中出现被告人说明财产合法来源的规定,以被告人不能说明财产合法来源,证成涉案财产没收的正当性。这种由被告人说明财产合法来源,而非刑事追诉方查明涉案财产性质的规定,实则给被告人施加一种说明义务,且这种说明义务存在说明对象扩张、说明属性不明、说明标准模糊的加重风险。被告人说明义务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但应在司法适用中确立限制规则,在侦查机关履行全面收集涉案财产证据职责的前提下,以“客观限制”标准划定被告人的说明对象,明确被告人说明义务为客观证明责任产生的主观证明责任,适用优势证明标准。
关 键 词:违法所得没收;被告人说明;说明对象;说明标准
中图分类号:D924.3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23)04-0117-13
收稿日期:2023-02-27
作者简介:张遥远,河南大学诉讼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学。
项目基金:本文系2021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黄河流域环境犯罪类案类判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1BFX016。
为减缓刑事涉案财产性质的证明困难,立法呈现对“被告人不能说明财产合法来源”规定的青睐。在法律层面,该规则用于确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非法所得”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孳息、收益”。在司法解释层面,该规则用于认定网络赌博犯罪的“赌资”、电信网络诈骗的“违法所得”以及其他涉众型信息网络犯罪的违法所得数额。在司法实践层面,被告人的财产合法性说明已经成为司法机关办理以上三大类案件,划分、认定涉案财产性质的重要依凭。然而,被告人的财产合法性说明存在适用风险,具体表现为办案机关过度依赖被告人说明,被告人说明义务加重。对于被告人的说明义务,有学者认为被告人对账户资金来源进行说明属于举证责任倒置;[1]有学者认为被告人说明财产合法来源,并提供相应证据的行为属于被告人辩解;[2]还有学者认为,要求被告人说明财产合法来源,既属于“举证责任”,也属于“说服责任”。[3]既有研究大都停留在被告人财产说明性质的探讨之上,较少关注被告人财产说明的适用对象、说明性质和说明标准。因此,为合理限制“被告人不能说明财产合法来源”规则的适用,发挥被告人说明财产合法来源的正当功能,需根据被告人说明义务加重的表现,分析被告人说明义务加重的原因,并阐释被告人财产合法性说明义务的具体意涵,进而规制被告人说明义务的加重风险。
一、被告人财产合法性说明义务加重之表现
被告人财产合法性说明义务加重,主要是指涉案财产证明中,司法机关任意解释和适用该规则,依靠被告人说明进行财产性质认定,造成涉案财产举证、质证、认证形式化,使被告人承担过重的合法性说明义务。在司法实践中具体表现为:被告人财产说明对象扩张、说明性质界定不明以及说明标准由法官自由裁量。
(一)被告人财产合法性说明对象扩张
在涉案财产查证中,司法机关承担查明涉案财产性质的司法职责,即使需要被告人说明财产合法来源,也仅针对部分查证存在客观困难、司法机关未能查明性质的涉案财产。然而根据公安部的工作规定和司法机关的实践做法,被告人的财产合法性说明已经适用于全部或绝大部分涉案财产中,呈现出说明对象扩张的趋势。
一方面,司法机关已经将被告人的财产合法性说明延伸至审前程序中,适用于大部分涉案财产性质的查证中。以公安部发布的《公安机关反有组织犯罪工作规定》为例,该规定实质上已经将被告人说明扩张至审前程序中,且适用于查封、扣押、冻结的全部或绝大部分涉案财产。《公安机关反有组织犯罪工作规定》第四十九条“高度可疑财产说明来源”的规定: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在犯罪期间获得的财产高度可能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孳息、收益,公安机关应当要求犯罪嫌疑人说明财产来源并予以查证,对犯罪嫌疑人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应当随案移送审查起诉,并对高度可能性作出说明。根据该条规定,侦查机关对涉案财产的违法性产生高度可疑后,即可要求犯罪嫌疑人进行说明。其一,这种“高度可疑”的认识难以把握,司法实践中,办案人员会根据涉案财产与违法犯罪行为的联系,产生高度可疑的认识,涉案财产与犯罪行为之间紧密的形式联系会使司法办案人员乃至普通民众,都会先入为主地产生来源非法的合理怀疑。其二,侦查机关为简化涉案财产查证,会将合理怀疑指向了全部或者大部分涉案财产,进而要求犯罪嫌疑人对查封、扣押、冻结的全部涉案财产的合法性进行说明。侦查机關只需对犯罪嫌疑人的说明进行查证核实,不能说明的即可认定为违法所得。侦查机关的涉案财产查证任务得到简化,犯罪嫌疑人的财产说明义务则会加重。
另一方面,司法机关任意扩大被告人说明对象范围的行为,已经引发辩护方的异议。如李某涵诈骗案中,辩护人提出:本案非确因被害人人数众多等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逐一收集被害人陈述的,原公诉机关也未对此作出说明,且在证据上还欠缺通话记录、银行账户交易记录等,属有罪推定。①肖某锋、邹某清等开设赌场罪、开设赌场罪案中,辩护人提出起诉书指控的庄某鹏分红284800元并认定为违法所得,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有合法经营和合法收入,本案不适用“被告人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认定为赌资”①。辩护方在具体案件中,提出无法查明的客观限制并不存在,不能“适用被告人不能说明财产合法来源“的规定,这也显现出司法机关为简化涉案财产证明,任意扩大该规范适用案件范围的办案倾向。由于法律规范的抽象性和模糊性,适用被告人说明的对象范围、前提条件并不明确,这就导致司法机关任意适用该规定,形成一种对辩护方不利的涉案财产处置状况。
综上,司法机关为简化涉案财产证明,忽视涉案财产证据收集,必然使被告人说明的对象扩张,突破法定的适用范围。司法实践中的涉案财产裁判的完整性与合法性饱受质疑,具体表现为涉案财产裁判缺乏详细的财产违法性证明推理与论证,涉案财产处置概括化、模糊化。学者将这种现象归因于“重定罪量刑,轻涉案财产处置”、“涉案财产缺乏正当程序规制”和“刑事对物之诉套用对人之诉的办案思维”,但也不能忽略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未能全面收集涉案财产证据。[4]在涉案财产违法性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法官只能集中于“被告人说明”的审查,被告人不说明、不提异议,涉案财产就被认定为违法财产。在司法机关怠于涉案财产证据查证的司法实践中,被告人说明义务适用对象的范围不可避免扩张至全部涉案财产或绝大部分涉案财产。
(二)被告人财产合法性说明的性质与标准不明
因法律未明确被告人说明的性质,未设定被告人说明的具体标准,造成了控辩审三方对“被告人说明”的性质和适用标准存在分歧。具体在涉案财产裁判中,不同法官对待被告人的财产合法性说明的认识不同,把握被告人说明财产合法来源的标准上也存在差异。
案例1——被告人李某涵说明:其仅诈骗20000元,其他的钱是做导游和微商的收入。法院审查:李某涵辩解所称存在做微商、导游等收入,在侦查阶段并未提及,庭审中对做微商所代理产品的品牌、产地等不能回答,不符合常理,且其和辩护人亦未能提供有效线索或证据证明②。
案例2——被告人王某平说明:其仅分得几千元,在公安机关所做的供述不属实,公安机关从其家中扣押的四万多块钱中有三万多是之前卖车的钱。法院审查:根据各被告人在公安侦查机关所作的供述,其于2016年9月25日凌晨被抓,其于2016年9月26日所做的关于2016年9月24日夜晚分钱的事实的供述,应当较之庭审上的供述更为准确,记忆更为清楚,且被告人对于其当庭辩解意见,均未向法庭提供证据证实,故本院对其当庭辩解意见均不予采纳,采纳其在公安侦查机关所做的供述③。
案例3——被告人林某斌说明:公诉机关指控违法所得数额600万与事实不符,巨奇公司收取10%维护费,林某斌按照20%股份领取分红,林某斌的数额不可能超过164万元,按照胡某伟转账计算,不超过131万元,其中还包括正常玩家充值的数额。法院审查: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林某斌的违法所得数额6001905元,均为梳理银行账号转账记录得来,证据不足,以巨奇公司收取10%维护费后的股份分配比例计算,综合认定被告人林某斌的违法所得为245.6万元④。
案例4——被告人吕某说明:我与咸某贺之间有借款往来五百万元,2017年8月开始至2018年11月间我和咸某贺之间的往来是我个人赌博的钱,不是我开设赌场的钱。法院审查:被告人咸某贺、吕某、李某原始供述,均證明咸某贺与吕某之间有借款往来,咸某贺与吕某当庭亦辩称二人之间有借款往来五百万元,且李某萍当庭提供证据能够证明借款发生的根据系因吕某经营手机店而产生,故对三被告人提出的发生借款往来500万元的意见予以支持①。
案例1和案例2属于被告人说明不被采纳的案例,法官给出的审查判断理由可以概括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未能提供有效线索或其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案例3和案例4属于被告人说明被采纳的案例,法官采纳的理由可以概括为被“被告人明确指出检察机关指控错误或被告人的说明有其他证据印证”。从上述法官的裁判理由中,可以得出法官在把握被告人说明的性质和说明标准上,缺乏较为客观的限制标准,存在较大的主观性,亟需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一方面,立法或司法解释的规范用语为被告人对财产合法来源进行“说明”,而庭审中法官要求被告人“证明”,“说明”是否保持与“证明”相同的含义不得而知,且该规定中“说明”用语仅是要求被告人提出合理疑点,还是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并不明确。另一方面,在多数案件中,法官仅给出综合在案证据不予采纳被告人之说明,而未详细论证,虽然有被告人未提供线索和证据材料的客观原因,但笼统不采纳或不采信被告人的说明,有过度拔高被告人财产合法性说明标准之嫌。被告人财产说明义务的性质和说明标准尚不清晰,法官进行自由裁量的空间较大,极易受刑事诉讼程序轻视涉案财产处置观念的影响,而对性质不明涉案财产进行非实质化裁判,形成对被告人不利的财产认定,进而加重被告人的说明义务。
二、被告人财产合法性说明义务加重之原因
“被告人不能说明财产合法来源”的规定,在实践中承担多种诉讼功能的实现和证据问题的解决,对于解决涉案财产性质不明的僵局具有重要意义。但错误认识“被告人不能说明财产合法来源”规定的内涵,过度扩张被告人财产说明的功能,则使其陷入适用窘境,不当地加重了被告人的说明义务。
(一)强化被告人的纯粹义务性说明
公诉机关证明涉案财产的违法性达到一定标准后,被告人不能说明涉案财产合法来源,性质不明的涉案财产就被认定为违法财产,由此可见,被告人能否说明财产合法来源,关乎涉案财产的认定结果。这种附随不利后果的被告人财产说明,是被告人的义务,即说明涉案财产合法性的义务,这种说明义务在性质上属于一种纯粹的义务,并非是被告人的说明权或者兼具权利、义务双重属性。
一方面,不能以刑事对人之诉中的辩护权类推解释刑事对物之诉中被告人的财产说明。在奉无罪推定为基本原则的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无须自证其罪和公诉机关负有对犯罪事实完全的证明责任,[5]这衍生出被告人有权针对公诉方指控提出辩解、反驳、质疑。被告方通过攻击、质疑公诉方指控中存在的可疑之处,来动摇法官的临时性心证,被告人所进行的说明、辩解都是行使辩护权利的表现。因此,有学者认为,在“刑事对物之诉”中被告人说明财产合法来源的说明应当也属于被告人辩护权的延伸,因为被告人在侦察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只需要对涉案财产合法来源的线索或证据进行说明,进行查证、核实则由负有客观义务的司法机关负责进行,[6]这种观点是从被告人是否需要积极举证、积极证明等具体提出证据的角度来分析被告人涉案财产说明义务的性质,忽视了权利与义务的根本性区别,未能关注到被告人不能说明财产合法来源所引发对被告人的不利后果。
另一方面,应以被告人不能说明财产合法来源的不利后果为根据,明确被告人的财产说明为纯粹性的义务。在法理上,权利与义务的根本性区别在于,权利属于个人的自由选择,他的不作为不一定引起不利的后果;义务属于个人的强制负担,他的不作为一定会引起不利后果。[7]根据“被告人不能说明涉案财产合法来源”的规则,若被告人不说明涉案财产的合法性来源,其面临的是该涉案财产被认定为违法财产,进而被没收的不利局面。并非是涉案财产处于性质不明的状态时,遵循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将涉案财产返还给被告人。所以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网络赌博犯罪、电信诈骗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对物之诉”中,被告人说明财产合法来源是一种纯粹义务性的说明,不能够说明财产合法来源即面临被没收的不利局面。这种纯粹义务性质的说明必须法定化、明确化,否则依然会引发因被告人说明属于说明权或者兼具权利、义务双重属性等似是而非的错误观点,使被告方轻视涉案财产的举证和辩护,使得性质不明涉案财产被认定为非法财产。
(二)弥补公诉方指控违法所得之不足
被告人能够说明与不能说明属于被告人财产说明的结果,均对刑事对物之诉中事实发现起重要补足作用。被告人能够说明财产合法来源,有助于检察机关履行客观性义务,纠正指控错误;被告人不能说明财产合法来源,也证成了涉案财产的违法性,弥补了公诉方的违法性指控之不足。
涉案财产追缴作为刑事指控体系的应有内容,是检察机关对刑事指控体系的重要完善,[8]但出于涉案财产证明的特殊性,公诉机关的涉案财产指控往往存在不足。在实体真实发现原则下,涉案财产追缴指控需达到准确查明、判定财产权属、来源、性质、用途及价值,并严格区分合法财产与非法财产,这其实是对司法机关查明涉案财产事实的过高期待,忽视了财产类待证事实的特殊性及其证明困难。其特殊性之一体现在财产类事项属于个人生活情况中极为隐秘的事项,对财产情况的说明理应由能够提供最好答复之人——被告人来承担说明义务,所以立法设置一种可反驳的推定,由被告人对合法性财产进行说明,进而反驳公诉机关证成的形式联系。被告人的说明性反驳在维护了自身的合法财产权益、行使辩护权的同时,客观上帮助公诉机关履行客观真实义务,并推动性质不明涉案财产法律事实的建构。其特殊性之二体现在涉案财产事实的查证对被告人供述和被害人、证人的陈述或证言等言词证据具有较强依赖性,这种依赖较“定罪量刑”尤为严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财产处置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八条①规定涉案财产的来源、性质、用途、权属、价值这五大事项均可以由被告人供述和被害人、证人的陈述或证言等言词证据予以证明,而财产流转凭证类书证和财产价格鉴定、评估意见类鉴定意见只能证明涉案财产的部分事项或者用来印证言词证据的真实性,仅凭这些证据断然无法构建涉案财产流转的整体事实面貌。对言词证据的依赖也反映出司法机关缺乏专业性的涉案财产性质甄别机制,金融调查制度尚不健全。在这种背景之下,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进行涉案财产追缴指控时,涉案财产的指控绝然达不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指控标准,查明有利与不利于被告人的涉案财产事实也是很难实现,属于不完全证明。因此,公诉机关对“被告人不能说明涉案财产合法来源”的规定持积极态度,会要求被告人对财产合法来源进行说明。
(三)解决法官裁判违法所得之困难
“被告人不能说明财产合法来源”的规定,施加给被告方财产合法性的说明义务,与公诉方的财产违法性指控职责相辅相成。这种控辩双方的互动机制,为法官认定涉案财产性质,提供了有效的事实认定机制,有助于法官对涉案财产的性质形成内心确信。
事实是确定权利义务的基础和前提,法律事实建構需遵循事实、证据、事实认定的递进性逻辑链条,[9]事实认定作为事实发现过程的最后一环,是一种动态性的法律事实建构结果。具体到性质不明涉案财产的裁判中,其法律事实的建构需要法官对财产违法性进行形式联系和实质联系判断。法官需要先判断公诉机关的没收申请是否满足性质不明涉案财产与犯罪行为之间的形式联系,而后在庭审中依据被告人的说明状况来判断实质联系是否稳固建立。为证成实质性联系,立法者以“被告人不能说明财产合法来源”“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被告人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和“被告人无法说明款项合法来源的”等规范性表述,在满足形式联系的前提下,被告人不能说明财产合法来源,就可以将性质不明涉案财产认定为违法所得及其孳息、收益的事实认定机制。
这种事实认定机制之所以能够被正当地适用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网络赌博犯罪、电信诈骗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涉案财产处置中,是因为其背后隐含着刑事对物之诉中最为重要的“主体间性事实认识”的哲学理论,这种事实认识理论认为诉讼认识活动所要处理的核心关系是各怀主张、诉求迥异的多方主体之间的诉讼关系,多方主体之间进行互动、交涉和论辩等互动性模式是刑事诉讼的事实形成机理。[10]为了深化刑事涉案财物的事实认定,有学者提出“刑事对物之诉”这一独立性概念,来区别与“刑事对人之诉”,意在推动涉案财物追缴成为独立诉讼标的。[11]刑事对物之诉要求法官基于诉讼主体的共同参与,通过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对涉案财产作出裁判,[12]但也需要关注在涉案财产证明中所投入的司法资源,不能过分拖延诉讼。各方主体共同参与,以简洁有序的事实认定规则来对性质不明涉案财产的性质做出认定,体现了主体间性事实认识理论和诉讼效率的有机结合。性质不明涉案财产的处置属于特殊的“刑事对物之诉”,如若缺乏相应且必要的证据规则指引,会陷入法庭辩论的泥潭并难以作出裁判。所以涉案财产裁判必须依照涉案财产与违法犯罪行为之间的形式联系和实质联系,实现法律事实的发现与生成。公诉机关证明性质不明涉案财产与违法犯罪行为之间具有形式联系,且将涉案财产的违法性证明至相应的标准;辅之以被告人博弈性的合法财产来源说明,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形成一种简洁、高效和易于操作的涉案财产事实认定机制。这种事实认定机制能够有效缓解刑事对物之诉中证据较为缺乏、财产违法性事实难以形成的问题。
综上,立法者为解决“刑事对物之诉”中来源多样、法律关系复杂和极具隐私性的涉案财产证明困难,以“被告人不能说明财产合法来源”的规定,强化被告人说明的义务性,促使处于争议事项之中、靠近信息、证据以及容易陈述相关事实的被告方,尽早提出有效的积极抗辩,发挥被告方在刑事对物之诉中的主体性作用。但当前司法机关“重定罪量刑轻涉案财产处置”,极易出现公诉方忽略涉案财产证据的收集,大量“性质不明涉案财产”适用“被告人不能说明财产合法来源”的推定规则,造成庭审中涉案财产证据缺乏,法官被迫审查被告人能否说明涉案财产合法来源,并对涉案财产进行模糊化裁判。这也是裁判文书中大量篇幅用于论证犯罪事实及涉案数额,[13]对涉案财产处置缺乏详细证据运用、证据分析和证据论证的关键症结所在。所以,“被告人不能说明涉案财产合法来源”的推定规则,承担司法机关多种诉讼功能的实现和证据问题的解决,易被过度使用。
三、被告人财产合法性说明义务之澄清
“被告人不能说明财产合法来源”的规则承载着多样化的诉讼功能,这是引发控辩审三方产生冲突性认识的根源。需具体化阐释被告人涉案财产合法性说明义务的适用对象、义务来源和适用标准,澄清被告人涉案财产合法性说明义务的根本性意涵。
(一)说明义务之对象:性质不明涉案财产
客观上难以证明性质的涉案财产笼统被称为性质不明涉案财产,[14]认定和没收性质不明涉案财产于打击贪污腐败、网络赌博、电信诈骗及黑恶势力等涉案财产来源特别广泛的利得型犯罪意义显著。“性质不明涉案财产是指因客观条件的桎梏而使得涉案财产难以通过具体的证据,来证明或还原每一筆或每一部分涉案财产的来源、性质、用途、权属及价值等事项。被告人不能说明涉案财产合法来源”的推定规则,仅规定于认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非法所得、网络赌博犯罪的赌资、电信网络诈骗的违法所得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违法所得中,且仅适用于这四类犯罪中的性质不明涉案财产。准确把握客观限制的存在,是将涉案财产合理划分为可查明的涉案财产和性质不明涉案财产的具体标准,是厘定被告人涉案财产说明义务的适用对象的必备要件。
性质不明涉案财产与违法所得的逻辑联系可被分为形式联系与实质联系,满足这两种联系是性质不明涉案财产没收的正当化基础。一方面,与违法犯罪行为具有形式联系是相关财产进入刑事诉讼视野,成为涉案财产的准入门槛,[15]犯罪嫌疑人开设账户用于赌资接收、流转或用于诈骗犯罪,账户中的资金很可能用于违法犯罪或者属于违法所得;暂时性查封、扣押、冻结的被追诉人财产曾处于收受贿赂、贪赃枉法的公务人员和长时间从事黑恶势力犯罪的集团及组织成员的控制之下,在形式上呈现出与违法犯罪行为联系密切。这些财产与犯罪行为之间紧密的形式联系,会使司法办案人员乃至普通民众都对这些财产先入为主地产生来源非法的合理怀疑,如谋取非法利益为目的组织赌博、诈骗的犯罪人员、普通公职人员或者长期从事黑恶势力犯罪行为的集团及其组织成员所享受的奢侈生活、高消费状况与正常、合法收入状况相比较存在较大差距。但在缺乏客观证据的情况下,仅依靠这种先入为主的有罪推定式主观怀疑,并不能满足现代程序正义对性质不明涉案财产正当性没收的要求。
另一方面,与违法犯罪行为具有实质性联系是合法没收涉案财产的正当性根据。直接证明涉案财产与犯罪行为的实质性联系存在客观困难,①而通过“推定式”立法间接实现涉案财产与违法犯罪行为之间的实质联系成为学界和实务界共识,在法律规范层面也有所显现,具体表现为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到网络赌博犯罪中“被告人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被告人无法说明款项合法来源”,至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被告人不能说明财产合法来源”的规定。在具备形式联系后,被告人无法说明涉案财产合法来源,成为性质不明涉案财产与违法所得之间实质联系的证成强化条件,如被告人无法说明财产合法来源,该性质不明涉案财产被推定为违法所得,进而得以没收。
客观限制的存在是判断涉案财产属于或包含性质不明涉案财产,适用被告人财产说明义务的前提。客观条件的限制是指因客观原因存在,无法逐一证明、逐人核实被告人占有财产的性质,但在上述四类犯罪中,把握客观不能查明的标准却是不同的。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敛财、牟利犯罪行为的持续期间是判断客观限制的标准,两类犯罪都表现出在一定时期内,行为人重复多次或持续不断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获取非法财产,一一查明涉案财产具体是由哪一笔犯罪行为获取则困难重重。大型电信诈骗犯罪中,犯罪嫌疑人用于诈骗犯罪的银行账号中往往有成千上万笔汇款记录,一一找到被害人并制作笔录,查明具体被骗数额既复杂又无必要,[16]这种客观限制主要存在于涉案人数众多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在网络赌博犯罪中,参赌人员的数量是衡量性质不明涉案财产存在的标准,例如在大型网络赌博平台上,参赌人员动辄成千上万,不具备向所有参赌人员逐一取证,认定每一笔参赌数额的可能性。综上,被告人的财产说明义务的适用不仅要限定于这四种犯罪,还需要动态把握客观限制的存在,综合涉案财产数额、犯罪周期、受害人数和参赌人数等因素,综合判断客观限制是否存在。
(二)说明义务之来源:基于客观证明责任产生的主观证明责任
公诉机关将涉案财产与违法犯罪行为的形式联系证成之后,若涉案财产仍处于性质不明的状态,则由被告人承担涉案财产被认定为违法所得的法定风险,在这种法定风险的驱使下,被告人必须负担说明义务,该说明义务是基于客观证明责任而产生的主观证明责任。
性质不明涉案财产与违法所得的逻辑联系被分为形式联系与实质联系。形式联系是相关财产进入刑事诉讼视野,在证据意义上具有足够的违法性嫌疑。在起诉阶段,公诉机关须就涉案财产的违法性承担独立的证明义务,未能履行证明义务,则承担涉案财产指控被驳回的不利益负担。因此公诉机关承担涉案财产与违法犯罪行为形式联系的客观证明责任;公诉机关将涉案财产的违法性证明至一定标准,使法官形成初步内心确信,这是公诉机关的主观证明责任,该主观证明责任被称为公诉机关的证明义务。[17]在公诉机关履行证明义务,法官形成临时心证后,“被告人不能说明涉案财产合法来源”的推定规则发挥了转移客观证明责任的作用,[18]将客观证明责任从公诉机关转移至被告人一方,被告人承担涉案财产性质不明的法定风险。因此,从被告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角度出发,推定规则实际上发挥着附条件的客观证明责任转移之功能。[19]
被告人的涉案财产说明义务是基于客观证明责任产生的主观证明责任,主观证明责任是一方当事人为了避免败诉,通过自己的行为对有争议的事实加以证明的责任。[20]法律规范采用“说明”而非“证明”的用语,易引起理解困惑,这并不表明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责任,而是基于证明事项的特殊性、与公诉机关证明义务加以区分和延续立法用语统一性的特殊考量而做出的選择。其一,证明事项的特殊性体现在,涉案财产合法性说明并不限于严格的要件事实范围,而包含具体涉案财产的来源、性质、用途、权属和价值等事实的全面说明;其二,“刑事对物之诉”的核心理念尚不完整,对于突破“对人之诉”中被告人无须自证其罪的原则缺乏支撑,在刑事对物之诉中被告人是否承担证明责任并不确定,故使用“说明”二字,与公诉机关的“证明”进行区分;其三,为延续刑事立法的一致性,在四种犯罪违法所得的认定中,均采“说明”二字,方便司法人员的统一适用。综上,法律规范使用“说明”的用语仅仅是为被告人的“证明义务”遮盖了一层面纱,实质上是被告人承担涉案财产的证明责任。
(三)说明义务之标准:优势证明标准
在司法实践中,被告人之涉案财产合法性说明较难被法官采信,这固然有涉案财产均为违法所得的客观情况;但缺乏被告人说明的法定标准,法官对被告人的财产说明进行自由裁量,这也是使被告人的财产说明不被采信的重要原因。被告人的说明义务实则为被告人的证明义务,所以对被告人说明义务标准的探讨,仍处在证明标准的框架之内。学界在“刑事对物之诉”证明问题的研究中,着重探讨公诉机关的指控标准和案外利害关系人财产合法性的证明标准,鲜有论及被告人证明涉案财产合法性时的证明标准,被告人在四种特殊犯罪案件中的证明标准研究亟需补足。可以参照可反驳的推定中,被告人进行反驳时所需达到的标准,并结合涉案财产事实的特殊性,确定被告人证明所要达到的标准。
出于平衡控辩双方的诉讼能力和涉案财产特殊性的考量,被告人财产说明义务的标准应为“优势证明标准”。其一,在引入民事诉讼证明机制的“刑事对物之诉”中,被告人的涉案财产合法性主张适用“优势证明标准”。刑事对物之诉属于刑事诉讼属性抑或是民事诉讼属性还是所谓的中间属性的探讨,既影响被告人说明义务的证明标准也决定公诉机关应予承担的证明标准。依《反有组织犯罪法》,该法第45条3款①中的立法表述之明确了公诉机关的证明标准为高度可能性,相较于“对人之诉”中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稍降一级,既防止公诉机关滥用推定规则也有利于打财断血,表现出在坚持刑事诉讼基本框架之内,有选择性地适用民事诉讼证明机制的趋向。民事证明采优势证据标准,这是基于错误风险分配理论①所作出的选择。民事诉讼旨在平衡对原被告所造成的错误并减少错误总量,以建构民事诉讼,故被告人的财产合法性主张可以适用“优势证明标准”。其二,在可反驳的推定中,被告人的财产合法性主张作为独立性的反驳事实,并不需要达到与公诉机关同等的证明标准,证明标准只需要达到“优势证明标准”即可。被告方进行的反驳表现为,提出一个与推定事实完全相反的事实主张,反驳推定事实的不能成立。[21]在公诉机关将基础事实证成,即涉案财产高度可能属于违法犯罪所得,涉案财产已经被推定为违法所得。此时,被告方需要提出涉案财产合法性的主张并加以证成,这种主张类似于积极抗辩,只要所证明事实的盖然性与对方相等即可,不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同时考虑到被告人身陷囹圄,取证能力受限,所以被告方的财产合法性说明,只需要达到“优势证明标准”。
四、被告人财产合法性说明义务之规制
“被告人不能说明涉案财产合法来源”的规则能够有效解决贪腐犯罪、网络信息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的涉案财产证明难题,实现对“违法所得”更为彻底的没收,但也要防止该规则泛化适用,需要督促侦查机关查证涉案财产的性质,调动被告方承担证明责任的积极性,通过积极举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从而优化该规则的适用。
(一)侦查机关履行全面收集涉案财产证据的职责
对性质不明涉案财产的违法性认定,体现了刑事“对人之诉”和“对物之诉”的核心区分,即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在涉案财产处置中的非绝对化适用。被告人对特殊案件中性质不明的涉案财产负有说明义务,如若不能说明或者说明不被采信,性质不明涉案财产将被推定为违法所得而被追缴、没收,并非涉案财产性质存疑时,作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但这种推定式立法在强化被告人纯粹义务性说明和简化公诉机关的证明时,还必须严格限制其适用对象范围,防止侦查机关过于依赖“被告人之说明”而怠于履行涉案财产查证职责。同时为解决法庭审判环节涉案财产证据缺乏、涉案财产裁判模糊化的问题,需要对侦查机关适用该规则进行限制。
一方面,侦查机关在贪腐犯罪、网络信息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应履行收集涉案财产证据,查明涉案财产性质的职责。尽管涉案财产来源广泛、法律关系复杂、权属问题不明,在查证上存在一定困难,但相关法律规范均提出侦查机关应全面收集涉案财产证据的要求。如《关于办理信息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全面收集证明涉案财物性质、权属状况、依法应予追缴、没收或责令退赔的证据材料,在移送审查起诉时随案移送并作出说明。人民检察院应当对涉案财物的证据材料进行审查,在提出公诉时提出处理意见”;《反有组织犯罪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对涉案财产审查甄别。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时,应当对涉案财产提出处理意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财产处置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八条规定:“公安机关对于采取措施的涉案财产,应当全面收集证明其来源、性质、用途、权属及价值的有关证据,审查判断是否应当依法追缴、没收”等法律或司法解释中,均明确规定了公安、检察机关的涉案财产证据收集、审查职责,并要求提出书面涉案处理意见,倒逼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重视涉案财产证据的收集。尽管存在查证的客观困难,但侦查机关应该加强金融调查能力的建设,任用兼具金融工作和法律工作背景的司法人员参与引导侦查,逐步确立金融调查手段在涉案财产证据收集中的重要地位,[22]不断提升涉案财产的证据调查与收集能力。
另一方面,坚持“以审判为中心”,提高涉案财产裁判的标准,强化对审前程序中涉案财产查证的制约和要求。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为规范刑事涉案财产的裁判的重要文件,其第六条要求:“作为刑罚执行依据的裁判文书,裁判内容应当明确、具体,满足可执行性的要求”,但近些年来涉案财物裁判主文表述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问题依然较为明显。这既有部分法官疏于涉案财产审查裁判的问题,但也不能忽略缺乏涉案财产证据材料,导致法院在审判执行环节承担了大量超出自身职能所无法解决的难题。[23]因此,应当发挥审判对审前程序的指引和制约作用,以涉案财产裁判的要求,制约公诉机关的涉案财产违法性指控的证据不足问题。其一,法官依职权审查能否适用被告人不能说明财产合法来源的推定规则,法官以“客观限制”为审查标准,判断“性质不明涉案财产”是否存在,进而严格限定被告人说明义务的对象;其二,对公诉机关提交的涉案财产违法性证据,以证据充分度①为审查标准判断是否需要退回公诉机关补充侦查。
(二)被告方积极承担财产说明义务
在贪腐犯罪、网络信息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案件中,被告人承担涉案财产性质不明时的不利益负担,故需要积极举证、质证和辩论,说明涉案财产的合法性。这种基于客观证明责任产生的主观证明责任,决定了涉案财产说明属于纯粹性义务。被告人必须以这种纯粹义务的视角,看待“被告人不能说明涉案财产合法来源”推定规则,转变消极、被动的认识,树立积极、主动参与涉案财产认定的观念,收集涉案财产合法性的相关证据,推动涉案财产处置的诉讼化与规范化。
一方面,被告方应转变消极、被动的认识,积极承担证明责任。在遵循具体犯罪行为与涉案财产统一裁判的处置模式之下,被告方易产生涉案财产裁判会类推适用疑罪从无原则的错误认识,试图通过故意不说明或者轻视涉案财产性质的举证、辩护使涉案财产陷入“性质不明”的僵局而避免财产被没收,如韩某可诈骗案判决书中,其辩护人提出:一审法院认定的50500元不能证明全部为诈骗所得,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无法排除是否包含其他性质的款项(其他违法所得或不当得利)②,但未被法官采纳。辩护方错误地认为在涉案财产处置中,会适用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忽视了涉案财产的举证、质证,这也是导致涉案财产未经裁判或裁判流于形式化、空洞化的原因。公诉机关将性质不明涉案财产与违法犯罪行为的形式联系证明至高度可能性后,法官形成临时性心证,客观证明责任即转移至被告人一方,被告方要承担客观证明责任。而公诉机关的形式性联系的证明任务,已经在定罪量刑证明阶段予以履行,如果被告方不提出涉案财产异议与合法性说明,就会被认为被告人不能说明涉案财产合法来源,性质不明涉案财产就会被推定为违法财产。所以在庭审过程中,被告方需及时、主动提出涉案财产合法性的主张,并提交相关的证据材料,使部分涉案财产的性质成为庭审争点,进而推动涉案财产审判实质化。
另一方面,要完善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的程序机制。从理论角度看,虽然被告方对于己方的涉案财产的性质、来源、權属等事项有一个更为细致的认识,更靠近证据,但被告人在判决前既处于被羁押状态也缺乏相应的取证、质证的法律知识,这种举证能力的不足,冲击着理论上被告人易于对涉案财产进行举证、质证的假设。所以被告人承担涉案财产合法性证明责任,需要配套更充分的程序保障机制,才能尽可能地实现控辩双方的平等。首先,要更为充分的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强化辩护律师的诉讼参与,保障辩护律师正当行使辩护权,通过辩护律师帮助被告人取证、质证,使被告方有效承担涉案财产的说明义务。其次,应将涉案财产证据开示纳入庭前会议的证据展示程序。重定罪量刑、轻涉案财产处置的思维,也会影响庭审会议中的涉案财产证据的提交与展示,庭前会议的主要功能在于组织双方展示证据、归纳争点,进而将全案证据分流为“有争议的证据”和“无争议的证据”,并将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分流为“争议焦点”和“非争议焦点”,[24]将涉案财产的相关证据在庭前进行展示,既可以为被告人提供表达财产合法性主张提供平台,让法官充分获知被告方对涉案财产性质的异议,也可以使被告人了解公诉机关的涉案财产指控证据,进而针对性的取证、质证。最后,需要探索建立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涉案财产裁判程序。相较于定罪量刑事实,涉案财产事实属于独立的证明对象,其拥有独立的证明责任分配方式,证明标准设置上也不同,依附于定罪量刑程序,则会消弭涉案财产证明的特殊性。涉案财产还牵涉案外利害关系人的财产利益,必须为案外利害关系人参与涉案财产处置提供程序保障,设置相对独立的涉案财产裁判程序,为案外利害关系人表达合法财产诉求,提供有效的程序参与机会。总之,在涉案财产裁判中,通过施加给被告人涉案财产合法性说明义务,更加强调被告人在财产证明中的协同参与;同时也要设置相应的程序保障机制,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的正当行使。
【参考文献】
[1]陈国庆,韩耀元,吴峤滨.《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理解与适用[J].人民检察,2010,(20):41-45.
[2]黄河,张庆彬,刘涛.破解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五大难题——《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解读[J].人民检察,2017,(11):32-40.
[3]龙宗智.推定的界限及适用[J].法学研究,2008,(1):106-125.
[4]徐岱,毕清辉.黑恶势力犯罪涉案财产处置程序完善路径探析[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1,(2):100-114.
[5]陈光中,张佳华,肖沛权.论无罪推定原则及其在中国的适用[J].法学杂志,2013,(10):1-8.
[6]施鹏鹏.刑事证明责任理论体系之检讨与重塑[J].中国法律评论,2022,(6):49-59.
[7]张斌.三论被告人承担客观证明责任——应用于刑事辩解和刑事推定的知识论阐释[J].证据科学,2009,(2):184-191.
[8]閔春雷,王从光.以事实为面向:中国刑事指控体系建构的新思路[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3):19-32.
[9]步洋洋.论“根据在案证据裁判规则”[J].法商研究,2022,(4):103-116.
[10]杨波.刑事诉讼事实形成机理探究[J].中国法学,2022,(2):163-183.
[11]陈瑞华.刑事对物之诉的初步研究[J].中国法学,2019,(1):204-223.
[12]方柏兴.论刑事诉讼中的“对物之诉”——一种以涉案财物处置为中心的裁判理论[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7,(5):119-132.
[13]初殿清.对物之诉视角下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赃款没收范围[J].中国刑事法杂志,2022,(4):145-160.
[14][22]李海滢,付祎.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涉案财产的处置——以澳大利亚无法解释财富制度为参考[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6):149-160.
[15]闫永黎.刑事诉讼中涉案财产的基本范畴[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145-151.
[16]周加海,喻海松,李振华.《关于办理信息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理解与适用[J].中国应用法学,2022,(5):32-37.
[17]林钰雄.严格证明与刑事证据[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168.
[18]陈瑞华.论刑事法中的推定[J].法学,2015,(5):105-116.
[19](美)罗纳德·J·艾伦.艾伦教授论证据法[M].张保生,王进喜,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211,214.
[20](德)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M].庄敬华,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117.
[21]何家弘.论推定规则适用中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J].中外法学,2008,(6):866-880.
[23]严照良,张爱萍,严烨青.“黑恶”案件财产审查的实践检视及困境纾解——以Z省“黑恶”案件公开刑事裁判文书为实证样本[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21,(5):96-103.
[24]万毅.论庭前证据调查准备[J].东方法学,2021,(1):166-178.
(责任编辑:赵婧姝)
The Aggravation and Regulation of the Criminal
Defendant's Property Explanation Duty
Zhang Yaoyuan
Abstract:In order to make up for the lack of illegal gains charged by the public and solve the difficulty for judges in adjudicating illegal gains,Chinese criminal legislation has provisions to strengthen the defendant's explanation of the legal source of property,so that the defendant cannot prove the legitimacy of the generalized confiscation of property involved.This kind of stipulation that the defendant should explain the legal source of the property rather than the criminal prosecution party to find out the nature of the property involved in the case actually imposes an obligation of explanation on the defendant,and this obligation has the aggravating risk of expanding the object of explanation,unclear explanation attribute and vague explanation standard.The defendant's explanation is reasonable,but the restriction rule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that is,under the premise that the investigation organ carries out the responsibility of comprehensively collecting the evidence of the property involved,the object of the defendant's explanation should be defined by the standard of“objective limitation”,and the defendant's explanation should be defined as the subjective burden of proof generated by the objective burden of proof,and the standard of explanation should be applied to standard of proof of superiority.
Key words:confiscation of illegal gains;defendant's explanation;explanation the object;explanation stand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