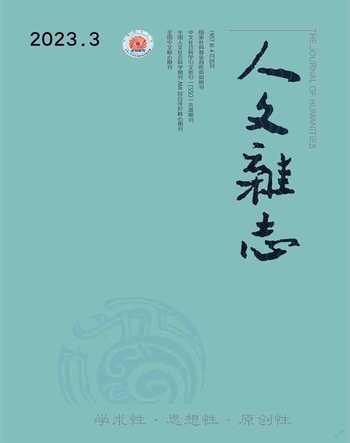混于酒而饮
贡华南
关键词陈白沙 酒 醉 混于酒
在明代,饮酒被视作“日用之需”。在这种社会氛围下,思想家对酒的态度格外宽容与肯定。朝廷推行海禁政策,不再开眼看外在世界,而是转向内在世界。相应地,通过饮酒开拓内在世界,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
陈白沙为学主张先静坐以自得,然后以典籍博之,再就人伦日用随处体认,以此涵养自得之心,最终归于“自然”。此即其所谓“立本贵自然”,①“此学以自然为宗者也。”②“自然”与智力机巧、人为谋划相对,后者乃陈白沙所说的“安排”。“本于自然不安排者便觉好。”③ “道是安排绝。”④ 在陈白沙看来,“安排”出于人意,乾坤之妙用在“安排”之外。“不安排”“绝安排”则归于自然,回归乾坤。“自然”首先指不假人力,包括人的谋划、主张。其次,“自然”不仅仅指个人修行而达至的心灵境界,也关乎此境界所熏染而化的周遭世界。陈白沙诗云:“天命流行,真机活泼。水到渠成,鸢飞鱼跃。得山莫杖,临济莫渴。万化自然,太虚何说?”⑤在此境中,万化自然、人伦日用皆备。对人来说,“自然”还包括自然的生活:以博大胸怀容纳万物,并以真情、真性接人待物。
对于在人世之中生存的人来说,达到这个境界并非易事。个体精神觉解的提升不易,人在与天地万物及人群的具体交往行动中证成觉解更困难重重。精神觉解的提升需要静坐、养护此心,也需要将“理”落实到“心”。陈白沙寻求使“此心与此理凑泊吻合处”,⑥对此投入极大精力。与人群的交接关乎我与人群之间差异、边界的流动转换。具体说,就是突破个体身心的限制,突破自我的边界,最终融入天地万物之中,成就天人一体。陈白沙频繁饮酒、醉酒,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饮酒让人心氤氲不已,与天地万物持久地感应,由此实现“心”与“理”的凑泊吻合。
一、生前只对一樽酒
“生前只对一樽酒”①是陈白沙对自己一生的简短总结。“只对一樽酒”并不是说陈白沙不面对人,不面对天地万物。事实上,陈白沙对富有生机的万物兴趣盎然,青山白云、江风朝霞让其迷恋不已,高堂友朋、陌旅渔樵也让他不能割舍。不过,陈白沙与天地人物交接更愿意通过酒展开。带着酒意对世界,世界与自己都会呈现出新光彩。酒意笼罩下的花月更美,人情更醇,酒意笼罩下的世间的隔阂快速被弭平,成见、是非更快被超越,界限容易被融化,这也保障着我与人之间能够自由交往。他的人生是酒意熏染的人生,他的世界是酒意熏染过的世界。关注自己的切身感受,从自己感受出发思考世界人生,这是陈白沙思想的首要特质。可以理解,陈白沙的思想世界何以少有河图洛书、无极太极、五行八卦等宏大语词,也与汉宋学者高扬的道器理气、形上形下等抽象概念迥异。在陈白沙观念中,心为道舍,道通萬物,心亦通万物。他自言:“栽花终恨少,饮酒不留余。”②“吟诗终日少,饮酒一生多。”③ 他的世界里有酒有花,有诗书画、有江山鱼鸟,有风月,有逝水,有百物,有少长朋俦,有君臣夫妇。他的思想世界贴近他的生活世界,所谓“四时万物无非教……溪上梅花月一痕,乾坤到此见天根。谁道南枝独开早,一枝自有一乾坤。”④这个世界鸢飞鱼跃,有活泼生机。其开显离不开饮酒,为其自得却不神秘,自然而不离人伦日用。
真正的思想不在著作里,而在活泼泼的生命中。陈白沙倾尽精神栽花、饮酒、看山、观物,并以诗记述。他活泼泼的生命就在其诗里,诗即其“心法”。⑤ 如我们所知,诗本于人性,每个人生之朴、和都可发而为诗。“受朴于天,弗凿以人;禀和于生,弗淫以习。故七情之发,发而为诗,虽匹夫匹妇,胸中自有全经。……会而通之,一真自如。故能枢机造化,开阖万象,不离乎人伦日用而见鸢飞鱼跃之机。若是者,可以辅相皇极,可以左右六经,而教无穷。”⑥“人”指人为,“习”指习惯、习俗。破除人刻意为之,拒绝因循故习,人才能回归天朴、和生。在对待“诗”的态度上,陈白沙贯彻了他的“自然”理念。他说:“诗之发,率情为之。”⑦“诗之工,诗之衰也。……率吾情盎然出之,无适不可。”⑧ 理想的诗是真情的自然流露。诗出于其他目的或其他意图之安排,刻意雕饰媚俗,这都有悖天和。“莫笑狂夫无著述,等闲拈弄尽吾诗。”⑨率情为诗,其生命就在诗中,有无著述并不重要。
饮酒的作用,就在于破除刻意安排与因循故习,使人回归诗意。如我们所知,醉酒而狂以破坏、否定为其基本特征,包括对世界人物的攻击。陈白沙酒后或高歌,或醉卧,其旨趣指向认同、欣赏天地人物。他有不少诗都抒发着眷爱人物生命观念。如:“美人遗我酒,小酌三杯烈。半酣发浩歌,声光真朗彻。是身如虚空,乐矣生灭灭。”⑩其高足湛若水解曰:“若夫望月、饮酒、放歌,乐由此生,则先生之乐在于生,是以生而灭灭。……乐生者,日用动静与时偕行,何有于灭?”瑏瑡乐生则只会欣赏天地人物之生机,而不会破坏万物生机,更不会毁灭其生机(“灭灭”)。陈白沙所谓“生”不限于动植物之生命,还包括养育动植物的各种要素,比如山川风水等。“一痕春水一条烟,化化生生各自然。”瑏瑢在他眼中,春水、青烟都在变易生化之中,都有其自然生机。“酒”亦是天地间一物,陈白沙对酒也有独特领悟:“路旁酒价知天道”。瑏瑣酒由五谷酿造,酒之成由五谷生长、收成决定,由此可由酒价知天道,这个说法一方面表达陈白沙的爱酒之意,另一方面,也可看出陈白沙对特定物———酒的深入思考。与动植山川风水一样,酒也通天道。
陈氏热爱天地间所遇之物,他更乐于醉入期间。“酩酊高歌掩旧书,青山日月笑居诸。一番春雨无分付,枉种桃花三两株。”①“旧书”泛指书册典籍。在书册典籍与现实世界之间,陈白沙更关注现实生活与现实世界。醉酒高歌,欣赏青山白云、春雨桃花。物与人一般,生机盎然。人有自我,而自限自小,则天机反不如普通物。在《木犀枝上小雀》一诗中,陈白沙写道:“翠裙白领眼中无,飞上木犀还一呼。乾坤未可轻微物,自在天机我不如。”②“天机”乃天然的生机活力,乃自然而然之机。人的天机常为俗见私意所羁绊、损害,破除俗见、私意才能重见天机。饮酒无疑是人重见天机之重要机缘:“昔者东篱饮,百?醉如泥。那知此日花,复与此酒谐。一曲尽一杯,酩酊花间迷。赤脚步明月,酒尽吾当回。”③ 木犀(桂花)后菊花十日开,比菊花冷淡。其香入人更深,使五脏和平而无乖戾。我对木犀而饮,可配东篱之醉,可复自在之机:赤脚步明月,行藏安于所遇,尽情复朴矣。
二、酒杯中我自忘机
酒的重要功能是陶冶情操,所谓“宜以酒陶情。”④ 饮酒何以能够陶冶情操?这与酒的性味相关,也涉及饮酒对人的意味。酒的性味甘辛、大热,饮酒可让人情绪高涨,进而化解忧愁烦恼,更能让人遗忘世情,超越世人难以摆脱的俗见,比如功利意识、狭隘的成见等。“使来遗一尊,百金不愿易。”⑤在陈白沙看来,饮酒使人超越声利,它所开启的是世俗之外、价值自足的生活方式。“高人谢名利,良马罢羁鞅。……但忧村酒少,不充侬量广。醉即拍手歌,东西卧林莽。”⑥“高人”之“高”就在于他能够辞拒名利,如马之脱羁鞅。凭借自己的力量自给自足,而不以耕种为羞。减少自己的欲望,安于村居,以酒怡情,醉则歌笑草野之间。陈白沙安居草野,饮酒为乐,这与陶渊明有几分神似。甚至,他时有归往醉乡之想。如:“江上花边到一壶,春风日日要人扶。数篇栗里乃何趣,五斗高阳非酒徒。……醉乡著我扶溪老,白璧黄金惠不如。”⑦江畔寻春,对花举觞,陈白沙酒兴高涨,每每醉而归(“日日要人扶”)。在他看来,酒中之趣非烂饮的高阳酒徒所能知,醉乡的魅力也远非白璧黄金所能比。世人看重声名,往往为名所累。弃名而归饮山林,生命会更自在、更充实。陈白沙对此有高度自觉:“我始惭名羁,长揖归故山。……醉即拍手歌,东西卧林莽。”⑧“拍手歌”“卧林莽”表达的是快乐、自足又自在的生命姿态。从“名羁”中解脱,自由饮酒,这被视作通往自足、自在生活的前提。不肯饮酒,则与此生命、生活无缘。“生前杯酒不肯醉,何用虚誉垂千春。”⑨在陈白沙看来,不肯饮酒者,大多是看重外在名誉的人。酒眼超越货利视角、势利眼光,摆脱认知—控制架构,让天地人物按照自身面目呈现。以酒眼看花草、观云月,用酒(醉)起兴,用酒营造和乐氛围,则可以打开新生命、新世界。
对于饮酒之妙用,陈白沙有深沉的体会:“酒杯中我自忘机。”⑩ “机”是机巧,即处心积虑地謀划、安排。“忘机”就是“绝安排”,饮酒使人自然,无疑也近于道。在人的日常交往中,礼俗、声利都会让人失真。借助酒,去除应酬面具,这是达到自然生活的捷径。陈白沙的这个说法让我们想起陶渊明“对酒绝尘想”之说。一切尘想都是机心的表现,“忘机”也就是“绝尘想”。尘想绝,尘世时空也随之移易。陈白沙言“万古乾坤半醉前”,瑏瑡万古乾坤随着酒意而到来,而呈现,此正是酒的妙用。
饮酒而忘机,“醉”则机心尽忘。如我们所知,“醉”悬置自我、成见,进而消解世间各种界限,而让人、物、我相互通达。在此意义上,醉打开了各种限制而呈现出无间的广大世界。在《赠胡地官》中,陈白沙谈及自己醉酒的感受:“引满花下杯,延缘坐中客。醉下大袖歌,孰云此门窄?”瑏瑢醉、舞不仅表现陈白沙知足知止的精神修养,同时也都在不断突破空间之封限———向内拓展自由天地。对于普通人来说,醒来则回归世俗生活,重新开始计算安排,也就再次远道矣。醒来后,自我回归,人、物、我界限重新显现,相互通达的广大世界重新被隔开,世界因此呈现出逼仄、狭隘,道也被遮蔽。陈白沙说“醉去乾坤小”,①可谓精彩绝伦。
陈白沙求存心、用心、任心,求深思而自得。自得,也意味着自得本心之乐。② 陈白沙发明“静坐”工夫,养其善端。静坐通常要闭眼,所谓“瞑目坐竞日”③是也。如我们所知,视觉指向自身之外,通常也会把心意带向自身之外。“瞑目”意味着停止向外投射,而把心思拉回自身。就其内涵说,静坐而默坐澄心,达到虚境,由此“断除嗜欲想,永撤天机障。”④涵养善端,进而达到活泼泼的氤氲境界。在持养心体工夫时,他像宋儒一样随时保持戒慎恐惧。然而工夫成熟,心体则表现为“至无有至动,至近至神焉。”⑤“酒”的品格、功能同于心体之“至无至动”“至近至神”。饮酒同样可以断名利,入氤氲。原本无形有体的酒进入人体,人体逐渐舒展活络,心思随之活跃起来。酒浸润了的心目投射并赋予周遭世界异样的光彩。心物相互感应不已,物我共同进入神奇的新样态。陈白沙留恋这个异乎常态的状态,不惜醉,甚至不惜“疯”几回。“一曲一杯花下醉,人生能得几回疯。”⑥“疯”来自世俗之眼,对于陈白沙来说,“疯”为其自得之乐,为其自然之态。
三、一身燮理三杯内
饮酒忘机,涤除俗虑,这主要是“破”的工夫;调和身心,开显乾坤,则尽显酒的积极妙用。陈白沙谈到自己饮酒的感受时说:“一身燮理三杯内,万古乾坤半醉前。”⑦ “燮理”指和谐的机理,“一身燮理”指整个身心和谐融洽。饮酒可以调节身体机能,使血脉和顺。酒也可以热力化解郁积的忧愁,所谓“世上闲愁酒可通”⑧也。在陈白沙心目中,酒之所以能够使人进入氤氲之态,是因为酒本身自带氤氲之气。他曾写道:“何处氤氲姜酒气,香风吹入野人卮。”⑨姜酒氤氲,其气芳香,诱惑人引用。氤氲又作“薩”,指阴阳二气交互缠绵,而有气息和畅之态。瑏瑠氤氲也就是“感应不已”之态,所谓“万理都归感应中”。瑏瑡“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系辞》)万物因天地二气交密而化育醇厚,广而言之,阴阳交感而事物通泰,由此早就生生之态。在《周易》思想影响下,中国传统思想一直将“氤氲”视作最理想、最有生机的状态,包括天地万物,以及人的身心。陈白沙接受并强化了这个观念,在他著述中,氤氲是身体最好的状态。比如他说:“氤氲复氤氲,东君欲放春。”瑏瑢“微风巾袂细氤氲,楚畹丛中别有春。”瑏瑣“香逐西风起,氤氲入杳冥。”瑏瑣“朝来溪上弄花丸,天地氤氲日月还。”瑏瑥“两间和气氤氲合,五色卿云烂漫浮。”瑏瑦氤氲而有了春,而有了秋,日月随之推移、更替。天地日月因氤氲而有序,和气氤氲而有“五色卿云烂漫浮”。“氤氲”对物如此,对人同样重要。“睡息氤氲,四体舒布,血肉增长。”瑏瑧睡觉作息时一呼一吸能够正常展开,则身体可以自在伸展,生机可得恢复与增强。
一元复始,自然界气息蒸腾,人随天地的氤氲节奏而变换自身节拍,胸中阔大、流动、激荡不已。所谓“一月薰蒸来,氤氲在肝膈。”瑏瑨“肝膈”是人的内在脏腑。不仅外在形体在氤氲中健全发育,内在脏腑之氤氲同样显露出生机。作为生理、心理、精神一体的心,其氤氲则不仅会改善人的生理气质,它同样能够生发出精神性愉悦。陈白沙对此有精彩的论说:“真乐何从生,生于氤氲间。氤氲不在酒,乃在心之玄。”瑏瑩真乐生于氤氲,但氤氲却与饮酒没有直接关系,其决定者是“心”。如我们所知,同样事件,其效果取决于人的精神觉解。饮酒可让人心跳加速、血脉飞腾。世俗之人醉后或疯狂,或烂如泥,思想停止,与草木无异,其醉酒与氤氲之境无关。这样心理气质性状态并不必然导向精神性的“乐”。能够饮酒生发出真乐,需要以自觉的和乐世界观为前提,同样需要一贯追求真乐的心灵为担保。不过,对于白沙来说,氤氲虽然不在酒,却同样也不离酒———酒醉起兴可入氤氲。陈白沙饮酒而醉往往会兴起神致:不仅可以推自己入氤氲之境,也能够打开自身之在的精神氛围,为自己烘染出氤氲氛围。心玄发酒玄,酒玄亦可发心玄。有了这样的精神准备,饮酒、醉酒而氤氲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了。陈白沙说“浩浩春生酩酊中”,①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大醉“酩酊”生出浩浩之春,也生出自然之乐。“自然之乐,乃真乐也。”② “酩酊”即“氤氲”,“氤氲”即“酩酊”。
陈白沙描述的“乐”也是人间一种世态,所谓“人间一种惟予乐,只在溶溶浩浩间。”③“溶溶浩浩”指宽广、流动、激荡不定态,这是陈白沙最为欣赏、着力追求的境界。这个境界就是神气相得的氤氲,陈白沙又以“熙熙兼穆穆”描述其特征:“神往气自随,氤氲觉初沐。……调性古所闻,熙熙兼穆穆。”④“熙熙”意为和乐,“穆穆”意为和敬。在陈白沙生命中,“熙熙”“穆穆”之和气氤氲不必由酒得,却往往也不离酒。
当然,陈白沙与友朋聚饮时也常有节制饮酒之念。“酒酣独高歌,呼儿续我断。诸君极留恋,十觞亦不算。虽无孟嘉量,且免落帽乱。”⑤饮酒不贪多,不在量的多少,而在于尽情、尽兴。至醉而止基于个人酒量、个人情致。“饮酒何必多,醺酣以为期。不辞亦不劝,三卮或五卮。”⑥不过,陈白沙以醺酣为期之说仍然在孔子“无量,不及乱”的范畴之内。“放歌当尽声,饮酒当尽情。”⑦以“尽情”为准的,醉或不醉皆可。陈白沙饮酒已经超越了“意必固我”。“尽情”是饮酒的一个重要目的,酒尽则情尽,坦荡自然。故他时常言醉,所谓“盏内须鮃长醉酒”⑧“手中玉休辞醉”⑨皆是。醉酒为尽情,为“乐”,并不是为了酒。白沙一再申言此意。“水南有酒$,酒熟唤我尝。半酣独速舞,舞罢还举觞。所乐在知止,百年安可忘。”⑩“所乐在知止”明确了酒醉、歌舞的精神意图在于“知止”。不过,陈白沙之所乐虽不在酒,但却也一直没有离开过酒。
由人的精神品格成就的酒精神异于通常意义上无精神的“酒”,也不是寻常人心目中陷入死寂或狂乱的“醉”。陈白沙追求精神性的“醉”,也自别于寻常人心目中的“醉”。他吟道:“饮酒不在醉,弄琴本无弦。”瑏瑡湛若水解:“饮酒在得酒中之味而不在醉。”瑏瑢湛若水所说的“味”非物之性味,而是指精神性的情味、意味。得味说深合陈白沙旨趣,比如陈白沙言:“六经,夫子之书也。学者徒颂其言而忘味,六经一糟粕耳。”瑏瑣“味”是六经对个人的具体影响、作用。饮酒亦如此,重要的不是生理性之“醉”,而是饮酒对人的意味。陈白沙并不怕醉,也不逃醉,但其意不在醉。于酒亦然,那些无思想的酒并非入陈白沙法眼。“敛襟欲无言,会意岂在酒。”瑏瑤酒因人的精神混入而有灵魂,若只看到酒而不见意味,那是见外而未见内。在此,我们可以玩味陈白沙对酒的两重态度:意不在酒,同时意不离酒。
在陈白沙的精神运化中,酒往往被精神化。借助这种精神化的酒,更利于澄心、契道。“诸君为饮会,老子不须期。尽数篱前菊,一花拈一卮。九九八十一,去来无穷期。元精为我酒,大块为我卮。”瑏瑥如果说陶渊明、邵康节还限于以酒醴对山花,陈白沙则以狂痴精神将酒泛化。在酒意弥漫的氤氲之境中,“元精”可以为酒,“大块”可以为“卮”,在天地间啜饮元精就成为精神性会饮。所以,我们看到,陈白沙可以不饮酒而“醉桃花”“醉牡丹”“醉野塘春”“醉杏园春”“醉洞庭”“醉千峰”“醉春风”。无酒而醉,“沉醉”也,“陶醉”也。自然沉浸在天地万物之中,物我交融,天人深契。
四、混于酒而饮
对陈白沙来说,饮酒而醉是正常的事。其看重“醉”不在生理性、气质性宣泄,而在于醉能够化解人世间种种隔阂、界限,进而打开广大的新境界。陈白沙曾不无夸张地写道:“歌放霓裳仙李白,醉空世界酒如来。”①“空世界”“如来”即指酒醉对世俗观念的消解,以及醉促成的物我之冥契。
陈白沙频繁饮酒,终生如一,他自谓:“到处能开观物眼,平生不欠洗愁杯。”②“洗愁杯”指酒杯,不欠“洗愁杯”喻持续饮酒。“观物”指无功利地欣赏万物,持续饮酒才能保持观物眼到处开。当然,陈白沙与同道欢聚更离不开酒。“时时呼酒与世卿投壶共饮,必期于醉。醉则赋诗。”③陈白沙与弟子李世卿一起,朝夕欢论名理,相得甚多。“必期于醉”乃相契而激发出来的豪情快意。对待其他朋友,陈白沙也总是相邀同醉:“相逢杯酒喜共醉,相忆诗情还自深。”④ “同歌同醉同今夕,绝胜长安别后思。”⑤ 杯酒开启诗情,共醉更胜相思。白沙一人独饮,亦时常醉:“惠来姜酒,喜饮辄醉。”⑥在白沙观念中,“醉”让自己随时契入天地万物,也让自己随时进入氤氲之境。因此,他会“有酒终日醉”。⑦无酒未能醉时,他也会生遗憾之意,所谓“恨我未能终日醉”⑧是也。对“醉”的眷恋使白沙与传统儒者拉开了距离。
陈白沙对自己饮酒有高度自觉,此即他所谓“混于酒而饮”。“混于酒”就是自觉将人融入酒中,与酒为一。他曾在《书和伦知县诗后》中写道:“屠沽可与共饮,而不饮彭泽公田之酿,古之混于酒者如是,与独醒者不相能而同归于正。虽同归于正,而有难易焉。醒者抗志直遂,醉者韬光内映,谓醉难于醒则可。今之饮者,吾见其易耳,非混于酒而饮者也。呜呼,安得见古醉乡之逃以与之共饮哉。”⑨“抗志直遂”指放任自己的志趣,按照自己的是非观念行事;“韬光内映”指自觉消解封闭的自我观念,融入世俗。“混于酒”即“韬光内映”之具体表现。不同于不满于现实又找寻不到出路的“托于曲蘖”“逃于酒”者,“混于酒而饮”是人积极主动地投入、融入酒,人的精神主动融入酒的精神之中。在混于酒的过程中,酒与人不再是外在关系,人主动放弃狭隘自我,放弃基于以狭隘自我在世的诸多物质的、精神的考虑,而按照酒的精神品格展开自身。
从中国思想史看,苏轼等人的“以酒为命”说强调融酒入人,把酒当作人内在的有机部分。瑏瑠相较于此,陈白沙“混于酒而饮”虽也追求酒与人为一,却更强调融人入酒,即以人作为酒的内在有机部分。前者是酒成就了人,后者是人成就了酒。依据后者的精神旨趣,酒中有人,酒精神含摄了人的精神。人酒相混就是“韬光内映”之“醉”,虽醉但却内心光明。“混于酒者”在固守本真的同时,也能混迹于俗,与俗共处,所谓“屠沽可与共饮”也。酒精神依据人的精神塑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理解心玄发为酒之玄,道之玄发为酒之玄。人成就了酒,酒精神依据人的精神塑造,中国酒精神的建构更为自觉。
混于酒者也期待与“醉乡之民”共饮。如我们所知,“醉乡”远离这个世界,其品格近于庄子“齐物之世”———万物一齐、人物安泰。但是,“醉乡”不是与清醒、生机对立的虚无寂灭。在白沙眼中,醉乡中生意激荡,生生不已。“浩浩蒲团上,还同在醉乡。”瑏瑡“浩浩”指生意激荡不定之态。“蒲团上”指静坐。静坐养出端倪,也孕育出激荡不定之生意。混于酒者既能“韬光内映”而与屠沽共饮,当然也不会象俗儒一样害怕醉、回避醉乡。醉乡之民皆富有深沉的智慧,白沙自然觉得醉乡之民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所以,白沙感慨:“放意自名狂者事,到头谁是醉乡人?”瑏瑢醉酒而狂,扬己抑人,这个精神与醉乡并不契合。醉乡接纳的是酒醉即卧者,其安静、内敛而非向外伸张。陈白沙自陈其酒醉后大都是醉卧:“黄柑白酒谁宾主,不放今朝醉似泥……尽日醉眠崖石上,莓苔茵厚不沾泥。”瑏瑣酒醉而眠,“睡乡”与“醉乡”无异,所谓“睡乡原自醉乡分,醉兴深时睡兴深。”①“睡乡”的精神是“醉”,而不是“醒”。能長眠醉乡理所当然为白沙所向往,“何处醉乡眠此翁”②正道出其心意。
陈白沙偶入醉乡,但并没有像王绩那样流连其间。“偶对泥樽开口笑,先生不是醉乡人。”③ 陈白沙之醉的目的地并非远离尘世的“醉乡”,他坚持在人伦日用中超越,对尘世不离不弃。这个态度也就是他所说的“混俗”:“醉以溷俗,醒以行独。醒易于醉,醉非深于《易》者不能也。汉郭林宗、晋陶渊明、唐郭令公、宋邵尧夫,善醉者矣。”④陶渊明、邵尧夫醉辞名利,以醉酒超越尘想,而层层敞露真朴之性。郭林宗清议于草野,不为危言骇论,处浊世而能保身。郭子仪功高、位尊、奢侈而主不疑、众不妒、人不非,高寿而终。四人善醉的表现就是既能够混俗,也能够行独。混俗者与世俗安然相处,能通俗又能保持自身高洁。混俗能“变易”,能平易,行独为“不易”。兼能“变易”“平易”与“不易”,实可谓“深于《易》者”。
醉将世俗一同卷入浑然之境,醒则不然,人与世俗始终分离、对视。“醉则高歌醒复悲,老仙那有独醒时。”⑤醉则高歌呈现的是乐,一直醉则一直乐。醒要正视世间俗事与争名夺利之徒,以及种种苦难、不公平。据此,陈白沙时不时表露出不愿醒的意愿。所谓“几醉几醒醒复醉,世间何事合留情。”⑥ 正基于他对醒与醉的深沉思考。作为儒者,陈白沙不能长居醉乡。他需要醒,对“醒”也有严格的要求:“不有醒于涵养内,定知无有顿醒时。”⑦“醒”基于“涵养”才能面对世情而始终保持自身,也才能免于由此而来的悲苦。这表明,“醒”与“醉”一样扎根于思想深处。
五、余论:饮酒乃学问之事
酒、饮酒、醉与醒在陈白沙思想与存在中有其位置:一方面,饮酒、醉酒与其所追求的“自然”“自得”“真乐”思想内在贯通;另一方面,他也自觉以饮酒、醉酒促成这些境界。不难发现,与自得、自然思想相贯通的饮酒俨然成为思想之事。⑧ 它既异于世人无思想之饮,也异于传统儒家以礼饮却怕醉的态度,与通过醉酒而保持形全、神全的道家亦有参差。白沙弟子李承箕对此有清晰的认识:“予观白沙诗多言饮酒,……私谓必如白沙者,始可称能饮者也。盖其得趣于心之氤氲,以心之玄为酒之玄,举天地之元精,胥融液于醇醪之内,而以大块为卮,万物为肴,是非犹夫人之饮也。昌黎称颜氏子操瓢与箪,曾参歌声若出金石,彼得圣人而师之,汲汲乎若不可及。其于外也固不暇,尚何曲蘖之托而昏冥之逃?噫,得孔子而师之,与不得孔子而师之,存乎其人焉耳。白沙从孔子千余年后,吐六经之糟粕,含一心之精华。醉之而不厌,道之旨发为酒之旨,是真所谓中圣中贤也者。盖得孔子而师之,然后可以游于醉乡如是也。”⑨“融液”指象液体一样交融为一体,“融液于醇醪之內”也就是陈白沙自陈的“混于酒而饮”。“举天地之元精,……以大块为卮,万物为肴”“游于醉乡”等也确实反映陈白沙饮酒的玄妙境界。但认为饮者“曲蘖之托”等同于“昏冥之逃”,这并非实情。陈白沙意不在酒,同时意不离酒。完全以“心之玄”“道旨”消解酒醪之功,则未免失当。饮酒令人远世,让人升腾、突破,让人与天地万物冥契。与被动逃于酒者不同,白沙是主动混于酒。他之所以愿意混于酒,恰恰因为酒本身具有移易人身心的力量。消解酒醪入心归道,“混于酒”则成为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