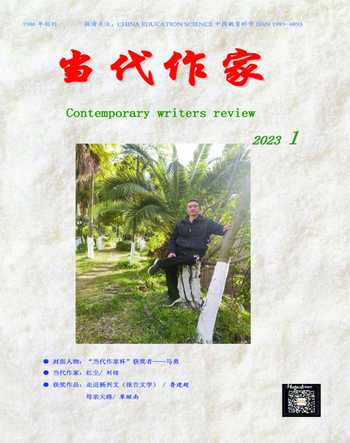回忆慈母
2023-05-30 21:57:49赵勤学
当代作家 2023年1期
赵勤学
小时候,母亲对我是很严格的,就像严寒的冰雪铺盖着麦地。
文革初期,一場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席圈全国,不幸的是,这场运动的烈火己烧在了父亲身上。父亲中标了,我也跟着倒霉了,在村里,脚不踏,腚不挨,猪不吃,狗不啃。父亲不行了,那还有我狗喝的糊涂,几天不挨揍就算很幸运了,就算我躲在家里,也在劫难逃。特别是到了中午,我也就离挨揍没多远了。
我家院子很大,到了中午,临居们好来这里吃饭。一天,一位临居哥哥吃罢饭,然后手一伸,给屙屎唤狗的那样:"过来,过来,小大眼珠子″给我刷碗去″。小大眼珠子是我的外号,因为眼睛大,人们称谓我大眼珠子。
话音刚落,我马上从地上拾起碗,马上执行这一光荣任务去了。一会儿,厄运终于降临到我头上,只因没刷干淨碗,挨了两个耳光。我无力反抗,可怜巴巴的蹲在地上,捂着脸,不时地发出赖猫似的哀呜,那少气无力的哀呜声,流露着无奈和乞饶。我有什么法子,人家叫我难看,我就难看了,人家叫我难受,我就难受了。
这时,母亲劝道:"您哥哥,别生气″。接着,母亲一边示意我快快地躲开,一边批评我:"你这个小孩子,以后做什么事情要认认真真地做,下次注意吧!别凑在这里惹您哥哥生气了″。
几年后,父亲被上级认定为贫农成份,从那以后,我的腰杆也挺起来了。又过了七,八年,父亲去世了,上级又认定父亲为地下党。是的,父亲又搞地下工作去了。
上个月,母亲去世了,临终前的那几天我问母亲:"娘来,我从小好挨揍你还记得吗″?!
母亲两眼潮湿,轻轻地点了点头:"记得,要爱别人,也要爱自己的仇人″。
2023年1月11日
猜你喜欢
幼儿智力世界(2024年3期)2024-06-20 11:03:55
都市(2022年1期)2022-03-08 02:23:30
小学生作文(低年级适用)(2021年10期)2021-10-29 09:00:54
金秋(2021年22期)2021-03-10 07:58:48
快乐语文(2020年26期)2020-10-16 03:06:16
数学大王·中高年级(2019年3期)2019-04-19 00:00:44
小学生导刊(2018年31期)2018-12-06 08:36:50
军营文化天地(2018年1期)2018-02-10 05:19:28
小天使·一年级语数英综合(2015年8期)2015-07-06 06:37:52
作文周刊·小学一年级版(2015年34期)2015-05-30 10:4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