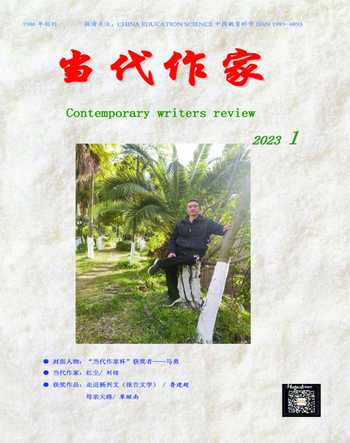矿工往事(中篇小说)(节选)
王玉军
诗云: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往事,但有的人往事平淡无味,有的人往事却是值得记录下来,哪怕是平凡人的往事。这是一平凡矿工上半生的亲身经历,也是当年许多矿工的经历,在六七十年代三线建设时期,有许多的家庭、许多的孩子跟主人公一样,大人去了三线,孩子被留在老家,寄养在爷爷奶奶或其他亲人那里,就如同现在很多在打工家庭一样,年轻的父母在外打拼,孩子被留在了老家跟老人生活,只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同。人的青春多是美丽的、灿烂的、甜蜜的、暂短的,而主人公张丰的青春却是黯淡的、枯萎的、苦涩的、漫长的。他的父母远离家乡,他的童年、少年跟随着年迈的爷爷奶奶渡过,时隔八年上中学以后才回到父母身边。时间把他和父母、姊妹之间的感情隔开了,割断了,竟很难愈合。有人说东西放在别人那里久了,就忘了是自己的了,孩子也一样。主人公经历的耐人寻味。
-———题记
一、北京小子
张丰的老家是北京郊县延庆某乡某村的,他母亲家是丰台区的,故起名张丰。张丰的父母均是知识分子,七十年代初,响应国家的号召,支援“三线建设”拖家带口的去了祖国大西南的一座叫十里沟煤矿,带走了年幼的妹妹和弟弟,把家里的老大张丰六留给年迈的爷爷奶奶,而张丰也只有六岁。隔辈亲把张丰宠坏了,在村里、学校里没少惹祸,他的爷爷奶奶处处维护孙子,对张丰惹祸不以为然,旁人说教二老还不高兴。等张丰上了初中,越发顽皮贪玩,学习成绩更是麻绳穿豆腐,没法提。初一年级下学期,他又考了个全年级倒数第一,老师找上门来,列举了张丰在学校诸多不端品行,说这样下去非得犯事不可,孩子最好还是父母带得好。
老师的话很管用,爷爷奶奶虽然舍不得大孙子离开,可真怕张丰会“犯事儿”,二老都已经年近八旬,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在张丰初一放暑假的时候,当爷爷的亲自把孙子送到了千里之外的一座煤矿。那座煤矿地处川滇交界,崇山峻岭,十分荒芜,时那里还是保密单位,对外称作4-16号信箱,距离北京二千五百公里,祖孙二人汽车、火车地折腾了两天三夜才到地方。张丰不喜欢这地方,也不喜欢陌生的家。他很少与家里人说话,也很少开口叫爸爸妈妈,更舍不得爷爷走,央求爷爷再把他带回北京,他不喜欢这个破地方,还保证说一定好好学习,不在惹祸。最终爷爷还是走了,值得一说是爷爷背着儿子、媳妇给了张豐一笔钱,在当时称得上是一笔“巨款”。爷爷临走偷偷带着张丰去了矿区的一家农业银行,变戏法似的从身上拿出一大叠大团结钞票,一共五十张,也就是五百块,相当于张丰爸爸的一年工资。老爷子用张丰的名字存了活期存折,可以随时取用。爷爷一再嘱咐张丰把存折放好,别告诉任何人,当然也再三强调把钱用到娶媳妇上面,别乱花。张丰的父亲逼问过张丰多次,爷爷给了他多少钱?他宁可挨爸爸的耳刮子也没承认。他父亲写信去问老人,反招来一顿埋怨。后来爷爷奶奶去世,无法对证。
为什么当爷爷的给了一个半大的孩子这么多钱呢?就连张丰自己也说不清,但他一辈子都记得这让自己读书的时候不差钱,是学校里的打款,更记着爷爷奶奶对他的好,在他的心里爷爷奶奶是他最亲近的人。张丰从小就跟爷爷亲,也特别佩服爷爷,爷爷会武术,没少教他。还有爷爷会做买卖,办事稳重,快八十岁的人了,做事从不丢三落四,就像那些大团结钞票,他们从老家出来几千公里的路程,人多,小偷也多,爷爷把钱放在什么地方?张丰一点都不知道,也没看出来。
张丰回到父母身边是一九八三年夏天的事,那一年他满了十四岁。张丰的父亲把他带到矿属中学,找的管事的校长,顺利地办完转学手续,张丰被分在了十里沟中学初二一班,开学那天,班主任刘老师让张丰到讲台上作自我介绍,他满嘴京片子(北京话)告诉同学他打小在北京长大,他姥姥家到天安门广场只有五里路,去天安门跟遛弯似的。这两句说完,教室里就乱了,班上四十五名同学里面没几个去过北京,北京天安门是当时大人小孩都十分向往的地方,因为他们都会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同学们看着张丰,就像看天安门城楼,眼睛闪闪发光、交头接耳,羡慕地议论这位北京小子。
张丰的长相不赖,一米六八的个儿,留着小分头,身板匀称结实,皮肤白净,小长脸上五官端正,特别的是他那双丹凤眼,招人稀罕,也很撩人。他的穿戴在当时很时髦,花格子衬衫扎在深蓝色的裤腰里,脚上穿了很精致的皮凉鞋,手腕上还有块铮亮的梅花牌手表,那是他爷爷奶奶送给他的离别礼物,至今这块手表张丰还保存着呢。
张丰见那么多眼睛望着他,就紧张了,京片子说的也不流利了,他眼睛低下来的时候,丹凤眼瞄见了教室第一排一张课桌上的两位女生,葛晓玲和赵美英,她俩不但都非常漂亮,而且长得像,张丰以为她俩是双胞胎,张丰完全被两位小美女吸引了,总不由自主地瞄她们。关键是他们三双眼睛时不时和她们的目光交汇、碰撞、短路,不知怎么张丰下面的“小弟弟”就挺了起来,把裤裆都撑大了,他差点拿手去按“小弟弟”。接下来,张丰不知道要说什么了,一脸的通红。刘老师以为他紧张,让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那天张丰被眼前的两位女生吸引住了他的个头在班上算高个儿,被分在教室的最后一排,跟张月新一桌。张丰对此十分满意,因为张月新是他才交下的朋友。
张月新见张丰回来,连忙用衣袖把张丰面前的课桌撸了两下。张丰坐下来,偷偷摸了下自己的“小弟弟”,任然是直挺挺的,像个木橛子,他悄悄伸手按了几下也没管用。老师讲的什么?他听得三心二意,脑袋瓜里仍是前排那两个女生,忍不住打听她们。张月新说她俩是表姐妹,一个叫葛晓玲,一个叫赵美英。
张月新听到张丰对葛晓玲和赵美英感兴趣,爆料说她们是四川乐山那嘎子的,张丰听了眼睛贼亮,说他奶奶也是乐山的,接着他沉浸在不加思考的异想天开中,哪有心思听课。
令张丰魂不守舍的两位女生着实漂亮,虽然她们还处于豆冠年华,长得已经是含苞待放,都是饱满光洁的额头、白皙的鹅蛋脸 、水灵灵的大眼睛、玲珑的鼻子、小巧的嘴巴,绝对的两个小美人。
张丰对张月新说,四川的姑娘比北京的漂亮。张月新也傻呵呵的说,也比他们东北那嘎达的漂亮。两个坏小子不好好学习,不管上课还是下课没少谈论葛晓玲和赵美英。也不怪两个熊孩子成绩差,考不上高中。每次考试,她们的分数总是排在最后几名,为此她们没少挨老师的批评,父母的收拾。张丰对张月新说:“我回四川不是上学来了,是要完成我爷爷交给我的光荣任务,找个四川的媳妇带回北京去。”他让张月参谋葛晓玲和赵美英谁更好?
张丰的爷爷老是念叨让孙子娶四川的媳妇,一半是思念远方工作的儿子一家,一半是拿孙子开心。他常张丰说:“嗨,小子,你得像爷爷似的,找个四川媳妇回来,你看,你奶奶就是我从四川乐山娶回来的。”张丰一点也看不出他奶奶是四川人。他问爷爷,奶奶咋是四川的呢?爷爷便给张丰讲他当年如何去四川做买卖,怎么在乐山大佛脚下一眼相中了一位漂亮的四川姑娘,然后天天围着姑娘转,在姑娘身上舍得花钱,很快就把姑娘带回北京当了张丰的奶奶。张丰在读初中以前,还真不知道奶奶是四川的,他没发现奶奶跟村里人有什么不一样。奶奶告诉张丰,她是因为家里穷,被张丰的爷爷用钱买回来的。一晃大半辈子了,没回过四川,连四川老家啥摸样都忘了。
张丰问爷爷,奶奶真是用钱买回来的?
爷爷乐呵呵的说:“对,没错,是买回来的。娶媳妇就得花钱。”
一次爷俩又说起娶四川媳妇的事,张丰对他爷爷说:“我也没钱娶四川媳妇啊?”爷爷笑着拍着张丰的脑袋瓜子说:“钱不是问题。”张丰不解其意,直到爷爷送他回四川,临走留给他一笔钱,才知道爷爷不是说着玩的。所以张丰见到葛晓玲和赵美英,知道他们是四川的以后,不免想起他爷爷的话,想用爷爷给的钱娶在她们中间选一个当媳妇。
张丰对张月新说他对葛晓玲和赵美英一见钟情。张月新说他也是,让张丰选好了以后,分一个给他做媳妇。这两个小混蛋,想的倒挺美。张月新和张丰简直是穿一条裤子,整天价黏在一起。班主任刘老师说他俩是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王八。可张丰对同学说,他和张月新是梁山兄弟,是不打不相识的铁哥们儿。因为张丰转学来的那天,他和张月新较量了一番。
事情是这样的,张丰在班主任那里报完到,就去教学楼找初二一班的教室,他在三楼找到了班级的教室,教室外面的墙上贴着班上分组和分坐位的名单,一些同学正围着看,他也凑上前看。这时候,张月新用东北话问:“哪个王八犊子叫张丰?”张丰正好听见,就回了句:“你才是王八犊子。”周围的同学哄笑起来。张月新个头儿比张丰高半头,块头也比张丰大不少,是班上的打架大王。他丢了面子,骂了句:“你个小逼崽子,我整死你。”说着用大手爪子来抓张丰,张月新压根没把张丰放在眼里。
张丰不示弱,把书包往地上一甩,和张月新支巴起来了。没想到三五个回合张丰把张月新摔得半天没爬起来。张丰把张月新從地上拽起来,谦虚的说自己不是他的个儿。张月新捂着被摔疼的屁股还真信了,又和张丰摔,还是被张丰撂倒了。张月新问张丰,你练过咋的?张丰说:“我跟我爷爷学过武术和摔跤,咱两个别摔了,做哥们儿吧。咱们都姓张,五百年前是一家呢。”张月新一手摸着屁股,一手摸着下巴,转了会儿眼珠子,同意了。
尽管张丰学习不好,德行还是不错的。张丰转学不久,多数同学都喜欢他,比方说他会两下子,却不主动跟人动手过招,施展拳脚欺负人。就像他在教室外面把张月新撂倒后,没有盛气凌人模样,还把张月新扶起来,主动和张月新交上朋友。这让张月新到死都佩服张丰,做他的“死党”。所以,张丰从讲台上自我介绍下来,张月新忙不迭的用袖口为他擦桌子。张丰见张月新不计前嫌,中午放了学,请张月新吃了好几根冰棒。自此张丰和张月整天形影不离。他们的友谊一直牢固的保持着,直到张月新在井下工亡。
张丰在学校有个外号叫“蟑螂”,是张月新给起的,不过之前张丰给张月新起了个外号叫“下巴哥”。张月新下巴外凸,有点地包天。张丰从认识他的第一天就叫张月新“下巴哥”,后来班上的同学也这么叫。张月新心里不喜欢大家这么叫他,但外号是张丰给他起的,也就哼哈的应承下来。而他给张丰起“蟑螂”的外号,纯属无心。卫生课测验的时候,有道“四害”的填空题,张月新只填了苍蝇、蚊子、老鼠,剩下的一个怎么也没想出来,不知怎么顺手把张丰的名字填上了。老师考评卷子的时候,全班都知道张丰是四害之一蟑螂了。张月新给张丰的解释也合情合理,他说一边考试一边想着考完试和张丰一块去学校后面摩梭河里去游泳,一着急把张丰的名字填上去了。张丰虽然相信张月新说的,但也怀疑张月新有报复自己意思。对这个外号,张丰一点没埋怨张月新,还挺乐意同学们这么叫他。做法给别人解释说,他是“张郎”而不是满地爬的蟑螂。张丰在老家的时候张丰没少跟着爷爷奶奶去看京戏,他尽管听不太懂,可戏剧里面总有什么张郎、李郎的主角,总让花枝招展、搽脂抹粉的娘子喜欢。他想当张郎,让葛晓玲或者赵美英做他的娘子。
张月新大张丰一岁,老家是辽宁阜新的,父母也是支援三线来的十里沟煤矿。他父母都是医生,到了矿上又去支援地方医疗卫生建设去了,一起去了一个偏远的乡村医院,据说那里有麻风病,他们不让张月新去,也很少回家。他们家就张月新一个孩子,张月新由爷爷奶奶照顾张月新,也是惯的不成样子,在班上、学校里是出名的捣蛋鬼。张丰转学来了以后,同学们本想看他俩二虎相争,必有一伤,没成想他俩成了哥们儿,这样一来班上的大多数同学成了他们的小喽啰。那时候的中学生,特别好打架,拜在他们门下少挨欺负。
葛晓玲和赵美英就是因为张丰替她们出头打架几乎同时答应了和张丰偷偷搞对象的。前面说了,张丰转学的第一天就相中了葛晓玲和赵美英,没多久便偷偷的给她们先后写过情书。两个女生虽然情窦初开,可面对张丰的殷勤和情书,她们没有任何反应,班上和学校追求她们的也不止张丰一个人,再说了,学校和家里是严禁中学生谈恋爱的。所以,两个女生接了张丰的情书直接撕了、烧了,见面仍跟没事人一样。初二下学期的时候,一天下午放学,初三班级的几个坏小子在路上拦住了葛晓玲和赵美英,非要和她们搞对象。那是个炎热的下午,张丰正在操场上光着膀子和同学打篮球。他得到快报,衣服都没穿,赤膊飞奔到拦截现场,初三班的三个男生见张丰来管闲事,直对着张丰动手了,却被张丰连摔带打,把他们都撂翻在地了。等到他的铁哥们张月新带着援兵赶到时,战斗已经结束了。张月新挥舞着大拳头教训那几个小子,说:“张丰的爷爷是北京的武林高手,张丰受过真传,就你几个瘪犊子,十个也不是对手,弄死你们几个小逼崽子像踩死几只蚂蚁,不信试试。”那几个坏小子连滚带爬的跑了。两个漂亮的女生目睹了张丰救她们的武打动作,顿生爱慕。这件事以后,整个学校都知道张丰会两下子,他还代表学校参加过市里的学生运动会的武术表演。这样张丰成了学校的英雄人物。自古美女爱英雄,葛晓玲和赵美英过后不久给张丰递纸条同意和他搞对象一点儿不奇怪。不过她们都让张丰发誓不能让别人知道,因为她们姐妹俩个也是相互保密的,这样张丰和那姐妹俩谈起了三角恋爱。
张丰嘴上不谈他恋爱的事,但从他的表现里可以看得出来,比如他衣着更讲究了,小分头梳的更亮了,花钱更大方了。惹得同学们经常谈论他,就像现在年轻人经常谈论明星一样。好的方面说张丰会武功、北京话说的地道、不差钱、人仗义、号召力强等等。不好的说他成绩不好、经常抄作业、见着女生眼睛冒绿光、在家经常挨他爸的大嘴巴子等等。还有一个谈论,是说张丰脸上开始长青春痘了,这一年他十五岁。
张丰仗义主要是张月新认为的,那个大块头,自打张丰来了后,整天黏糊着张丰,让张丰传授他武艺。这家伙好像缺心眼,张丰说啥他信啥。不过张丰也特别相信他,自己的钱都放在张月新那里保管,除了教他几招武术,还经常把手腕子上的梅花手表让他戴个几天,把张月新乐的屁颠屁颠的,把“张丰绝对够哥们儿意思,绝对仗义。”挂在嘴边上。
张丰不差钱,那是他爷爷留给他的私房钱。在八十年初代,一个初中生身上有个百八十块钱,那是相当牛逼的。在同学中间,有人私下议论说:“那个北京来的小子真他妈的有钱。有钱就是大爷啊,他用钱把班上不少同学糊弄的团团转,有的成了他的跟屁虫、有的心甘情愿的为他做作业、有的替他值日打扫卫生,还有女同学给他写情书呢,等等一些羡慕嫉妒恨的言语。”学校开家长会,老师提醒张丰的父母不要给孩子过多的钱。张丰的父母很少给他钱,知道是爷爷留给他的,追问过几次,张丰嘴里就俩字“没给。”为这他没少挨他爸的耳刮子。前面說了,孩子跟谁学谁,在管理钱方面,张丰像他爷爷很会藏匿钱,无论是同学还是他家里的人都不知道他把存折和钱放什么地方?他藏匿的地方很绝,竟然把存折藏到矿医院太平间后墙的一块砖后面。那鬼地方,不但令人害怕,还必须从一棵高高的桉树上翻过去,怕只有张丰想得出、做得到。他到用钱的时候,会说:“我去太平间后面拉泼屎去,谁跟我去?”。跟他一起的同学,一听都撒丫子跑了。张月新有时候跟他去,可他不会爬树,只能在墙这边傻等着,他知道张丰的秘密,但一次没问过张丰,也没对任何人说过。等张丰回来,只说你拉完了?张丰取了存折到银行取了钱再把存在放回去,钱全部放在张月新那里。张月新是张丰的好管家,钱放在他那儿,无论时间长短都毫厘不差,并且安全可靠,保密程度更不用说。以至于张丰的父亲多次搜查他均一无所获。
至于张丰的号召力强,跟他不差钱有关系,因为钱可以收买人心。初三的时候,河门口公园新开了个旱冰场,张丰在一个晚自习上豪迈地说:“明天谁跟我去溜冰?车费、租鞋、门票、吃饭我包圆了。”有十多个同学立即响应。第二天十二个同学真就跟他去了,在学校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学校经过调查,认定多人逃学的罪魁祸首是张丰,对他进行了全校通报批评、班上作检讨、请家长。张丰又挨了父亲的耳刮子,对他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搜查,结果,一分钱也没搜到。他只承认,钱的确是爷爷奶奶给的,不过去滑旱冰都花光了,张月新还垫了伍块钱呢,他的铁哥们张月新供认不讳。
张丰经常挨他爸的打好多人都知道,还知道他爸喜欢扇他的耳刮子,因为有好几次张丰的脸上有明显的“五指扇”手印子。张丰的爸爸是矿上的工程技术人员,看起来很和气,可不知为什么爱打张丰。张丰的母亲是矿上档案室的管理员,待人和善,可对张丰态度十分生硬,有人说,自己的东西放别人那里太久了,就忘了是自己的了,这孩子跟东西也差不多,就像张丰的父母,把六岁多的张丰留给了爷爷奶奶抚养,刚开始他们还惦记老家的张丰,可慢慢的就不怎么想了,一晃七八年,因为工作忙,他们也没回去看看父母和儿子,也没让张丰暑假或者寒假到他们身边待个十天半月的。张丰来到他们身边,总感觉张丰不像他们的孩子,张丰回来后不招待见,家里吃的穿的偏向老二老三轻易可见。他们对待张丰学习不好,给他们添乱,就两个字,打骂。他们甚至埋怨爷爷奶奶把张丰惯坏了。但在爷爷奶奶眼里张丰孝顺着呢,总说张丰一到冬天就给他们老两口倒尿罐子,遇到阴天下雨给他们捶腿按背。
人和人的亲密关系是日久生情,张丰长时间不在父母身边,与家里人一直有隔膜。那时候矿上的生活也比较困难,比如在饭桌上,妹妹、弟弟时常埋怨他吃得多、吃得快,父母也呵斥他让着点小的,不像在爷爷奶奶总是可着他吃好、吃饱。在家里他感到自己像外人,也很少说话,他满口京味,他父母说的是夹着京味儿的普通话,而妹妹、弟弟一会儿北京,一会儿普通话,还有时候冒几句四川话,比张丰小六岁的弟弟张涛开始在他面前还一口一个老子,一口一个锤子。他问啥意思啊?张涛告诉他,老子就是你爸的意思,锤子就是鸡巴的意思。还没等张涛说完,张丰便按住张涛一顿爆锤,嘴里嚷嚷着,看你小兔崽子还敢老子?锤子不?你以后再敢在哥面前说老子、锤子,我非得整死你丫。那年张涛才八岁多,被张丰修理的哇哇哭了半天。要不说教育得从儿童抓起,张涛挨了哥哥的一顿胖揍,真就长记性了,从那以后,在四川那么多年再也没听他说过四川话,一直说普通话,但比父母说道标准,没一点京味。因为他离开北京郊县的时候还是个小屁孩呢。张丰修理了弟弟没得着好果子吃,中午就挨了父亲的耳刮子。多年来,他害怕父亲,也不喜欢父亲,甚至怀疑自己脸上的青春痘常年不退跟经常挨耳刮子有关,把脸皮扇的失去了抵抗细菌侵入的免疫力。
关于张丰的在学校搞对象或者说初恋恋爱,说来也就是昙花一现,用张丰后来的话说,他只是摸过她们各一次。进入初三下学期,两个女生为了应对中考,都先后跟他黄了。张丰向张月新透露了搞对象的事,让张月新帮着分析两位美女跟他黄了的原因?张月新分析,她们说要好好学习,考重点高中,只是托辞,多半是张丰脚踩两只船穿帮了,人家两个是表姐妹。张丰不同意张月新的分析,他则怀疑是脸上的疙瘩影响了爱情,那段时间, 张丰脸上的青春痘堪称满园春色关不住。
张丰脸上的青春痘是回到父母身边以后才开始长的,从零零星星的个体向密集型全面发展,他父母以为他是青春期或者水土不服,也没多管,没想到张丰的青春痘一长就是十多年。那些疙瘩着实令人厌恶,连他自己也厌恶。张丰的好朋友张月新称之为“骚疙瘩”。张丰时常用手挤、抠、捏脸上的骚疙瘩,那些疙瘩破了便流出红白相间的粘液,令人恶心。张丰脸上的疙瘩感染或者结痂一次,他的面部便被破坏一次。张丰的脸不算大,屡次遭受破坏。
青少年的爱情大多都是昙花一现,张丰并没有因为失恋十分痛苦和失魂落魄,他感到在矿上的生活不快活,他还想着要是考不上高中,还是回北京老家去,他觉得跟爷爷奶奶在一起比找四川媳妇重要。他给父母表露过,父母也同意了。他给爷爷写过信说了这件事,爷爷奶奶高兴的不得了,盼他早点毕业回到他们身旁。但张丰没能如愿,深爱他的爷爷奶奶在他中考期间,先后病重住院。参加完中考,父亲带着他回到老家,爷爷奶奶在医院跟他们见过面,就像商量好了似的,没过两天就双双撒手人寰了。亲戚告诉张丰,爷爷奶奶是想他想死的,张丰嚎啕大哭,嗓子都哭哑了。他披麻戴孝给爷爷奶奶办完丧事,像男子汉大丈夫一样在亲戚面前郑重宣布,他要为爷爷奶奶守灵一年。他的父亲张世平说,你不回去上学了?他张口顶撞说:“上个屁。”张世平恨恨地看看个头已经跟他一般高的张丰,没给他大耳刮子。那时候张丰的个头儿是一米七六,是个大小伙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