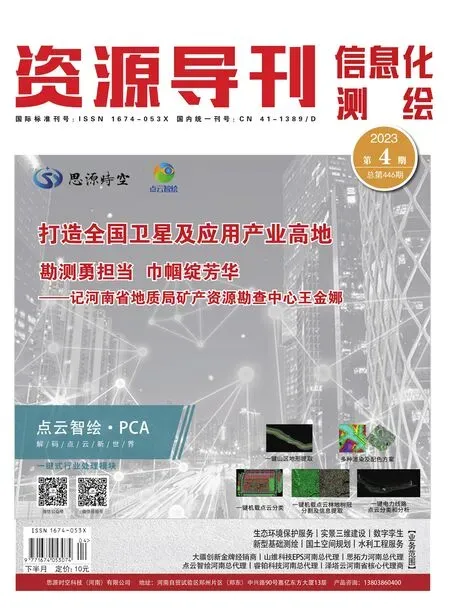“中华第一龙”发掘见闻
◎ 赵洪山
中国是龙的故乡,中华龙乡在濮阳。
中国最早的“龙”形象是河南省濮阳市西水坡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中华第一龙”,同时出土的还有“虎”。龙和虎都是用蚌壳摆塑而成,经考古专家和史学家多年论证推断,墓主人可能是五帝之一的颛顼。
濮阳古称帝丘,据传是“颛顼遗都”,故有帝都之誉。1983 年9月,濮阳市成立,40 年倏忽而过,如今的濮阳已是高楼林立。濮阳,这座年轻的城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付出了艰苦努力,闯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跨越式发展道路,描绘出一幅秀水绕城美如画、一步一景景醉人的美丽画卷。尤其是西水坡出土的“中华第一龙”,更是让濮阳的历史文化再添浓墨重彩。
濮阳在史前的遗存以原始社会后期龙山文化最为丰富,城址内外及城墙夯土中龙山文化遗物俯拾皆是,文化层由上而下为:汉代、春秋战国、龙山文化,三代城墙相互叠压,成为中国城市文化发展的生动范例。经考古发掘,其地下具有丰富的文化层,如一部卷帙浩繁的史书,凝结着中原大地的历史烟云与岁月沧桑。
颛顼之谜
1977 年9 月,我从河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来到安阳地区文化局文化科工作,和我同一天报到的还有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张相梅。从此,我和考古发掘结下了不解之缘。
记得当时殷墟考古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我和张相梅骑着自行车到中央考古工作站安阳小屯考古工地看发掘。那时的工作站院里还是一片荒地,正北有一长排坐北朝南呈“山”字形的瓦房,既是考古人员的办公宿舍和文物仓库,还是陈列陶器、青铜器、甲骨文的标本室。文物仓库里,来不及整理的出土甲骨装在纸盒里,整齐摆放在文物架上。
有一次,我和张相梅来到院子里,当时的殷墟考古工作站站长杨锡璋拿起一块甲骨递给我说:“你见过甲骨吗?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叫甲骨文,殷墟是我国最早文字的发现地。”我以前未曾见过这些龟甲,在回去的路上,张相梅感叹说 :“那可是难得一见的宝贝,有卜辞的甲骨很珍贵。”这以后,我每次去考古工地,看着考古人员在探方里小心翼翼地清理甲骨,内心都激动不已。
后来,安阳地区开展了多次文物大普查,主要由孙德萱、赵连生、张相梅、周同书、杨松山等人负责。每次到县里调查时,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到文化馆去看看,尤其关注安阳地区的文物景点。
1983 年9 月,安阳地委在第一招待所会议室召开大会,宣布濮阳市成立。我们随后搬迁到濮阳老城煤店街杂技团办公,并开始筹备文化局机关的基建工作。
1985 年晚秋的一天,孙德萱敲开了我办公室的门:“洪山,走,出去看看。”在孙德萱的带领下,我开着面包车七拐八拐来到了“西水坡”(当时称为“五代城”)。
我们沿着东边城头上的小路、拨开荒草登上了城墙。夕阳西下,一抹红霞照耀在城墙上,给人一种苍凉幽深之感。同行的濮阳县文化局负责文物的同志不解地问:“孙局长,您为何带我们来到这里?”孙德萱踩了踩脚下的砖,拨开眼前的荒草,指着前方,用洪亮的声音说:“我一直怀疑,传说中的颛顼遗都就在五代城下面。”顺着他的手指望去,只见一个大片洼地,里面长满了芦苇,一眼望不到边。
孙德萱说:“你们可不要小看这片洼地,说不定下面就有我们未知的秘密。这段古城墙建于五代时期,过去的壮丽风采已不复存在,但它留下了许多问号,等待我们去解答。这里是否为颛顼遗都尚不确定,但这片洼地肯定有我们待解的秘密。今日的发掘,便是为了让这些历史的见证物为后人所见。”
这时,我们方才明白,孙德萱是想要发掘这片洼地!濮阳,虽为千年古城,但文化沉淀根基尚浅。作为濮阳土生土长的学者,孙德萱想对曾被世人遗忘的遗址进行发掘,让无数人记起濮阳昔日的辉煌。当天晚上,在孙德萱办公室,他向我讲述了许多濮阳历史上鲜为人知的故事。
濮阳之名始于战国时期,因地处濮水之阳而得名。它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素有“颛顼遗都”“舜帝故里”之称。
“为何濮阳是颛顼遗都呢?”我问。
相传,颛顼是五帝之一,他早期的州在高阳(今河北省高阳县),后从高阳迁往帝丘(今河南濮阳),并以帝丘为都城。颛顼在位78 年,活到98 岁去世,据说葬在内黄。
后世为了纪念颛顼的功德,在内黄县梁庄镇建立“颛顼帝喾陵”,俗称“二帝陵”,民间称“高王庙”。后来,我和张相梅还专程到陵地拜谒。陵地古属东郡濮阳,金大定七年(1167 年)划归滑县,1940 年划归新置的高陵县,1949 年划入内黄县。
碑载说明:史载二帝葬于“鲋山之阳”,即指此处。封土冢南北长约65 米,东西宽约54 米,顶高25 米,陵墓底部残存有高1 米左右的砖砌陵墙,南面陵墙镶嵌有 “颛顼陵”和“帝喾陵”石碑各一通。据院中元代石碑记载,砖砌围墙系元代天历二年重修时所筑。在二帝陵庙前的高台地上,还残存有元代至元十一年重修的陵庙拜殿和左右配殿。
从碑刻和墓区的青砖绿瓦来看,没有6000 年建筑的痕迹。而从陵墓保护级别来看,这里也并非颛顼真正的埋葬之地,应是后人祭奠“二帝”之所。至于陵墓建于何年,并无原始资料,只有史书记载“从宋徽宗正和二年开始,确立历代所祭之陵墓祠庙,在澶州祭高阳颛顼和帝喾”。
二帝陵前碑碣数量之多,是其他各地帝陵少有的。陵区发现有大量仰韶文化时期的泥质夹砂红顶砵陶片,以及龙山文化时期的遗物,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

● 西水坡考察发掘现场
究竟有无颛顼此人?颛顼遗骨究竟葬在何处?颛顼的遗都建在何地?西水坡编号M45 墓的主人究竟是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丁清贤老师在研究所会议室向有关专家表示:“墓主就是颛顼。”然而,丁老师的结论遭到了否决。若真如丁老师所言,这尊“遗骸”就是颛顼帝的遗骨,濮阳的历史定位将实现一个飞跃。可惜的是,尽管在1995 年濮阳“龙文化与中华民族”学术讨论会上,众多考古专家推断这尊“遗骸”就是颛顼,但由于缺乏深入探究,最终仍无定论,这个千古之谜仍留待后人考证。
“蚌龙”出土
1987 年春节刚过,市领导决定在西水坡修建蓄水池,引黄济濮,解决濮阳市群众的饮水和“大化”(即中原化肥厂)的用水问题。我得知这一消息后,第一时间告诉了孙德萱。
孙德萱及时向市政府主管领导汇报了西水坡文物保护的发掘意见。在文物发掘批复之前,蓄水池建设提前动工,市里专门成立了供水指挥部负责工程建设,同时组织人员开始发掘。
1987 年3 月,蓄水池工程建设开始清理现场,挖土机、大卡车、数十辆装载机不停地把土运到堤坝上,工地上到处是一片机器轰鸣声。张相梅带领考古人员来回巡看,发现墓葬立即插上保护标志,并让其停工予以保护。在此先后发现了春秋战国、汉代、西晋、唐、五代、宋代等墓葬56 座,还发现了一处重要的仰韶文化遗址,后来取名“西水坡遗址”。

● 西水坡遗址出土的龙虎图
蓄水工程开工不久,就在西城墙附近发现了仰韶时期的陶片,孙德萱立即向政府领导汇报。当时,市政府拿出专款,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由市考古队配合工程进展同步开始发掘。从1987 年6 月起,经国家文化部批准,由孙德萱负责,濮阳市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合署办公,濮阳县文管所抽调技术力量,开始对西水坡遗址进行布方,由北向南展开大面积的科学发掘。
1987 年8 月上旬,酷暑季节,考古队员在炎热的探方里埋头发掘、清理标本。一天,我来到发掘现场,正巧遇见孙德萱、赵连生和张相梅在指导发掘工作,一个年轻姑娘正在清理基坑,我好奇地问赵连生:“这么热的天,为什么让一个女孩来工地挖土方?”赵连生尴尬地笑了笑:“有人觉得我偏心,把自家孩子安排在单位干轻松活儿,这不,我让她来现场锻炼锻炼。”那个女孩听到我们的谈论,转过身来。我仔细一看,眼前这个灰头土脸的姑娘竟是赵连生的女儿赵岩。但见她中等个子,乌黑的头发扎着两条大辫子甩在脑后,身穿浅红色短袖衫,俊俏的脸上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美丽且优雅。后来,在赵岩负责发掘的探方里,竟然有了惊人发现,这就是编号为M45 的墓葬。
8 月中旬,从安阳小屯殷墟发掘工地派来两名师傅,指导赵岩等人仔细清理墓葬,然后发现一具完整的骨架,头南足北,在其两侧分别为蚌壳龙虎图案。龙虎相背,龙在东侧,虎在西侧,清晰可见。
9 月中旬又发现蚌壳,有龙、虎、鹿、石斧等图案,虎在西,鹿在东,头皆向北,相向而立。龙在虎南,张嘴伸舌,可见上下牙齿,嘴南有近圆形蚌堆,龙身叠压在虎身之下。
后来又发现一只奔虎蚌图,头西尾东,背南足北,作跷尾奔跑状。与虎背对背为一龙,头东尾西,昂首作腾飞状,龙背骑一人。
三组蚌图,造型独特、规模宏大、内涵丰富,在仰韶文化考古史上是首次发现。“龙图”有丰富的想象力,“虎图”又是那么逼真,一堆蚌壳从收集加工,到摆放在逝者身边作为陪葬,从图案构思到绘成图形,即使在现代也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
据说,中国国家博物馆在调 “蚌龙”进京时,主要理由是它有极高的天文学研究价值。中央考古所冯时研究员对西水坡仰韶文化出土的蚌图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特别是天文学方面。中国是世界上较早进入农业文明的国家之一,为了确定农时服务农业生产,人们不断地观测日月五星的行度,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即是其中代表。在这组蚌图中,龙虎的摆放位置恰是“东苍龙”“西白虎”方位,结合墓主人脚下的勺形图案,组成了一幅星象图——“北斗栓二象”。这一研究成果,为今人解读古人宇宙观提供了线索。
作为陪葬品,蚌塑龙虎无疑显示了墓主人非同寻常的身份和地位,可究竟是何人能享受如此高规格的葬礼?
海内外专家众说纷纭,有人说墓主人可能是伏羲,有人说可能是蚩尤,而大部分专家都倾向于“墓主人是颛顼”的说法。同时专家们一致认为,“蚌龙”在考古断代上属仰韶文化早期遗迹无疑,在形态上是北京故宫里各种龙的正宗祖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把标本送往比利时格罗宁根大学同位素研究中心做碳十四测定,测定结果是6465±45,即6465 年的遗址。专家们遂誉称“蚌龙”为“中华第一龙”。
1988 年1 月,经河南省文物局批准,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派出以李京华为领队的考古队,到濮阳帮助发掘。记得当时参加发掘的还有北京大学、郑州大学考古专业的学生,仅仅几个月,一排排春秋晚期墓葬被发掘出来。
1988 年8 月,考古发掘已近尾声。一天,在第三组蚌图发掘现场,孙德萱、张相梅等人围坐一团,与我分享着喜悦,讨论如何保护这组无价之宝。
“我想申请就地保护。”孙德萱一边说,一边用手指在地上画了一个圆圈,又画了两条杠。
张相梅不解,疑惑地问:“孙局长,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孙德萱回答说:“在池子东南方修一道廊桥直通墓区,就像西安的兵马俑,建一个保护罩,在四周建道围墙做基础,既保护了文物,又不影响蓄水。”
张相梅一听笑了:“你的建议如果实现了,西水坡不就成濮阳的兵马俑了!”
之后的一天下午,孙德萱约我一起向市领导汇报保护方案,即就地保护,蓄水池另行选址,把西水坡建成遗址公园。
由于种种原因,就地保护方案未获批准,孙德萱便安排赵连生为起取“蚌龙”做准备。1988 年11月,赵连生、丁清贤等人和中央考古所的两位师傅,先后指导考古人员起取了三组已经发掘完毕的“蚌龙堆”。据赵连生介绍,蚌龙堆起取过程非常复杂,先是把蚌龙周边的土清理出来,用木板固定住蚌体,再从下面把土清空断开,垫上木板加以固定。
12 月2 日上午10 点左右,中原油田派来了大卡车,等我赶到发掘现场,看到的却是一溜尘土扬起的飞沙,随着远去的汽车,这里的一切都成为历史。
遗憾落幕

● 西水坡遗址发掘现场
我在中国地质博物馆工作十余年,一边拍摄中国地质图片,一边研究地球几十亿年来形成的各类地质构造,并发表了大量相关文章。在此过程中,我曾有幸采访了与 “北京人头盖骨之谜”紧密相连的胡承志先生。1929 年,当裴文中首次在北京周口店发现“北京人”头盖骨时,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复制与丢失,时至今日仍是未解之谜。
由此,我又忆起了西水坡的考古发掘。从“蚌龙和骸骨”的发掘到西水坡蓄水,结束了一代人对颛顼帝的怀念与思古。“北京人”头盖骨丢失和“颛顼遗骸”之谜虽成因不同,但两大“撼世”之谜都有待后人解开。
在2018 年春节前举办的“美丽中国”摄影展和2019 年“镜头中的濮阳自然之美”摄影大赛启动仪式后,我与孙德萱在濮阳迎宾馆进行了两次畅谈。那时孙德萱已年近80 岁,精神依然矍铄。面对多年的老友,他侃侃而谈。“为弄清西水坡遗址的文化内涵和三组蚌图的关系,1988 年,我们耗时半年多,又组织了大规模的遗址发掘工作。经过发掘,我们又发现了房址、窖穴、陶窑、墓葬等各种遗迹和大批遗物,不仅掌握了西水坡遗址的文化内涵和分布情况,也搞清了蚌图的层位和相互关系,取得了重大成果。”孙德萱坚定地表示,“我认为,西水坡的发掘远远没有结束!”
我赶紧追问:“你认为哪些需要继续发掘呢?”
孙德萱顿时把声音放得很低,像是喃喃自语:“西城墙下的仰韶文化遗址还未发掘;颛顼的都城还没找到,颛顼遗骨也没有得到认可;五代城下的谜底尚未完全揭开……”
2023 年2 月11 日夜,孙德萱的儿子孙长征给我打来电话,由于我已经休息,未接。2 月12 日凌晨4 点41 分,孙长征给我发来微信 :“家父凌晨三点五十九走了。”孙德萱这位在考古“战场”上奋斗一生的功臣走了,他给我们留下了一座“城”,一座“颛顼”居住的“都城”。
“颛顼遗都”,给世人留下了千古之谜。“西水坡”,这个地名也将永远被历史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