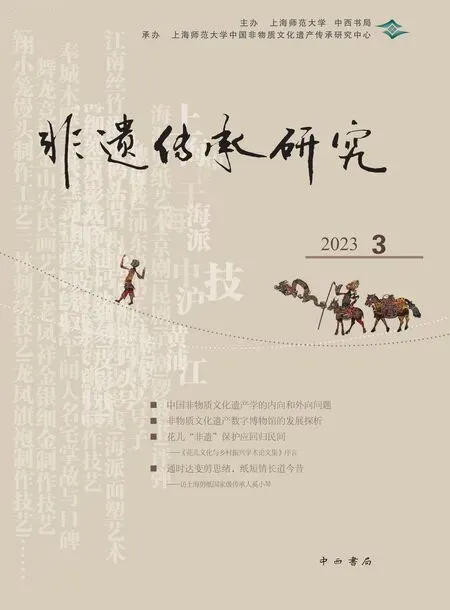想象与重构:论当代非遗题材电影的共同体叙事*
张春 陈雨桐
在现代民族影视发展的过程中,非遗题材电影无疑是后来崛起的一匹黑马。虽然出现时间较晚,发展至今也仍然不够系统、完整,但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再加上此类题材所聚焦的异质文化本身具有相当的吸引力,非遗电影成为了荧幕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非遗电影,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或者非遗传承人作为主要题材。它借助现代成熟的电影技术,“通过造型形式和运动来表现非物质世界”[1]。与早期的博物馆保存和纸质记载的方式相比,非遗影像优势明显,不仅保存时间更久,也更能保留非物质文化遗产所特有的“活态性”。早期的民族志电影、人类学纪录片、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等都可以视为非遗电影的雏形。前两者主要采用观察模式,强调弱化叙事,具有珍贵的史料研究价值,而后者则为非遗电影的诞生提供了更多的创作经验。
我国民族电影创作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掀起了第一个高潮,涌现出不少经典作品,如《暴风中的雄鹰》《五朵金花》《刘三姐》《冰山上的来客》等。这一时期的创作承担着“询唤一种均享国家意义主体的社会功能”[2],文化政治属性很强,电影呈现出了在“他者”视野下各民族一派和谐、热情友爱的大繁荣景象。改革开放之后,被“他者”凝视的格局依旧没有得到改变,市场的竞争又促使民族影视走向更为“奇观化”的表达,无论是《婼玛的十七岁》中美丽的云南哈尼梯田风光、《西藏往事》中绵延不绝的圣洁雪山、还是《黑骏马》中广袤无垠的大草原等,都还停留在猎奇与想象的层面上,未曾真正触及文化认同的内涵。随着2004年电影体制改革,一批少数民族创作者万玛才旦、丑丑、宁才、毕赣等从文化承担者的“主位”视角出发,开始思考民族文化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所遇到的现实困境:赖以生存的家园生态遭到破坏,外来文化的冲击致使本民族文化得不到传承,许多珍贵的习俗濒临消失等现象都导致了民族认同感逐渐降低。
“主位”视角能够更加深入到少数民族文化核心,但在叙事过程中若以自我族群为中心进行文化认同,单向度地弘扬本民族文化,反而会使其走向更加狭隘的境地,因此,把握电影创作的共同体意识至关重要。民族是建立在历史文化背景上形成的想象共同体,[3]且少数民族文化本身也是一种想象性资源。[4]非遗题材电影“有奇观但不止于奇观、有禁忌但不止于禁忌、有民族但不止于民族、有文化但不止于文化”[5],通过平衡外族想象与真实还原各民族文化特色、民俗仪式的“原生态风貌”来促进民族身份体认,实现重新构建中华文化共同体景观的根本目的。同时,创作者们也并不回避传统与现代、本族与外族的冲突,在传承过程中重点关注人的情感与需求,再融合自身想象、巧妙嫁接故事元素,创作出了《凤冠情事》《花腰新娘》《阿娜依》《别姬印象》《皮影王》《长调》《盛世秧歌》《高甲第一丑》《雪花秘扇》《爱在廊桥》《蹩鼓小子》《窗花》《百鸟朝凤》《老腔》《侗族大歌》《天公苏作》等优秀作品。总而言之,非遗电影以想象的力量弥补了当代人传统文化观念的缺失,唤醒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让这些绚丽的文化瑰宝得以光彩永驻,其蓬勃发展对中国民族电影类型体系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美学的构建,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构建中华文化共同体的空间想象
英国学者菲利普·韦格纳认为,空间既是一种由人类和社会发展干预而成的“产物”,又是一种能够对其产生反作用的“力量”。[6]利用具有象征性的元素,电影能够调动长期潜伏在人们脑海中有关生活空间的记忆。例如电影《摆手舞之恋》《寂寨》《爱在廊桥》都以“落叶归根”为题,标识性的摆手舞、苗歌、北路戏等,指引他们心灵返航。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指出,记忆与想象之间是存在关联的,记忆中的过去可能是一些纯粹的想象,但也的确是个体在当下所产生的真实感知。[7]对于人们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漫长岁月中的演变过程是不可见的,但非遗电影却让“不在场者可以拥有一个‘感性真实’的瞬间”[8]。这种瞬间唤醒了刻在每一个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基因,找到这种中华民族想象中共同的情感空间,构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就是非遗电影的意义之一。
文化记忆理论认为,一旦形成“符合身份认同的结构性符号系统”[9],就可以控制人们的文化记忆。而这种符号系统包括多种参与要素,其中地点是引发回忆的关键主体,它能够使人们的记忆得到有效证实。[10]非遗电影抓住了“中国文化侧重视觉与空间”的特点,[11]打造出民族文化氛围浓郁的独特景观。例如《别姬印象》中的云南红河州的独特风光,《侗族大歌》中贵州黔东南自然纯净的侗族村寨,《花腰新娘》中的边陲彝族风情,《高甲第一丑》中蕴含闽南文化的传统渔村、热闹的戏台,《尔玛的婚礼》中被当作旅游景点展览的羌族村寨,以及《寂寨》中神秘的大山等,都作为重要符号凸显了非遗发源地的地方文化特色,引发地域性观众产生归属感,构成其文化记忆里共同的乡愁。对“他者”而言,这些异质文化同样透过影像呈现出了更具生活气息的文化空间。
扬·阿斯曼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凝聚性结构的概念,它是由共同的经验、期待和行为空间构成的,其中的“空间”起到了连接和约束的作用。[12]阿莱达·阿斯曼有关“空间隐喻”的观点也指出,除了特定的载体之外,像建筑物、庙宇等空间也可以作为记忆的媒介。[13]由此可见,空间是记忆的载体、想象发挥的场所。而仅仅展现空间还不够,电影还需通过打造一些充满地域特色的具体场景进一步完成人们记忆的复现,如《黄土地》中具有宗教色彩的腰鼓舞与祈雨祝祷,再如以戏曲为主要题材的非遗影片《皮影王》《荞面旦》《爱在廊桥》《高甲第一丑》等中出现的热火朝天的练功和演出场景,《花腰新娘》中的舞龙,《阿娜依》中的苗绣和苗歌等。这些符号性的语言共同建构了人们的共时性记忆。对“共同体的追寻”,首先体现在寻求记忆的认同,这也是“人类的境况”的本质。[14]
“强调归属又正视差异其实并非易事”[15],空间的转换同样容易引发个体对民族身份认同甚至国族身份认同的焦虑。但将个体记忆上升为集体记忆之后,便能够抚平焦虑,最终到达文化记忆的层面,凝结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充分发挥非遗在增进文化认同、维系国家统一中的独特作用”[16],这便是非遗影片的价值所在。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社会群体存在一种共同的集体记忆,[17]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植根于地方社会特定人群的文化传统”[18],就是人们记忆的关键。电影《寂寨》中悠长的苗族古歌,唤醒了无数漂泊在外的湘西苗族人的家乡记忆。同样,影片《高甲第一丑》也用高甲戏连接着菲律宾华侨们对祖国的思念之情。这就说明,“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对所归属群体的认知完成”[19],是与民族文化记忆的写入是相辅相成的。
如果说电影空间承载着人们的想象,“总是以‘不在场的在场’存在于人们内心中”[20]的文化记忆,非遗则是想象基础上的现实依据,也是促进文化认同的关键。由于各族群生活空间不同,文化风俗不同,因此要想实现集体性的文化认同就要从文化理念、思维模式、行为规范方面寻找共通点。[21]文化“并不是风俗和信仰的随意结合”,而是“社会遗产”的积淀。非遗电影中充满象征性的非遗符号打造了陌生化的生活空间,但日常性的充满生活气息的个体生命活动,例如节日庆祝、婚嫁矛盾等,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观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同根同源,我们的文化本就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呈现出不同的姿态。这样一来,“他者”的身份就变得模糊,文化归属感逐渐提高。电影《尔玛的婚礼》结尾可以清晰地看到,真正地尊重和接纳各族文化,以主动的姿态参与到新的共同记忆建构当中,才是消除民族文化壁垒唯一的解决方式。
非遗从久远的光阴里走来,口耳相传、师徒相传的传承方式实在是过于单一,因此不仅是外族人容易产生理解上的困难,进而导致文化认同障碍,甚至是本族人的文化记忆也模糊不清。然而,电影语言有着天然的叙述优势,非遗电影塑造出的叙事空间,凸显了中国传统美学中的诗化意境,勾连出言而有尽而意无穷的无限想象。法国著名作家勒克莱齐奥说过,想象是行动的形式,它可以激发人的记忆活动。[22]以电影《长调》为例,蒙古族女歌唱家意外失声,回到家乡之后因喂养一只奄奄一息的驼羔而重新获得了生命的自信,在家乡草原的怀抱里重新唱起了蒙古长调,那神秘的低声吟唱轻诉着无法被替代的古老情思。少数民族的文化记忆不能被改写,只有文化才能够给予民族尊严。一个地区的非遗代表着一个地区的自身形象,而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文化记忆凝聚为一体,才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灿若星河的宝贵财富。
二、凝聚人类情感共同体的角色想象
在情感人类学中,人的情感被认为是“镶嵌在社会关系中的文化习俗”[23],体验共同情感是我们理解个体与社会制度以及文化习俗之间关系的关键。在非遗传承中真正的主体,是人的表达。非遗电影深入观照传承人的内在生命情感,围绕着对角色形象的想象打造出了由三层情感积淀而形成的人类情感共同体,塑造出了有血有肉的传承人形象。首先,影片中塑造出的大国工匠形象,不仅具有难能可贵的坚守精神,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热爱,也容易使观众产生强烈的情感认同。其次,电影通过展现传承人的工作状态和生活状态,还能将观众带入影片并产生情感共鸣和连接。最后,创作者们还透过传统技艺关注到匠人们的生存境遇,体现出了浓郁的人文关怀,促进社会思考。这种以情动人,以诚感人的叙事方式,书写出了生生不息的中国工匠精神。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提出了“集体情感”概念,即社会成员之间会产生一种让他们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具有相似性的共同情感。[24]非遗电影所打造的情感共同体,是属于中国人的一种纯粹的情感场域,其中,情感起着维系社会关系的纽带作用。[25]观众在观看影片时,结合创作者对人物形象的想象以及个体经验,可以达到“共情、认同与沉浸”的体验。[26]电影《天公苏作》在吴侬软语中描绘出了一幅桨声灯影里充满苏州韵味的画面,其中镜头与影调、声音的表现形式,让观众能够从工匠们小心翼翼的肢体动作和专注严肃的面部表情中感受到一丝不苟的专业态度,也更容易对一生择一业、一业钻一生的匠人精神产生极高的认同。而影片中娓娓道出的温情故事,又于情感更细微处关注了匠人们生活中的喜悦与烦忧,观众在共情他们的梦想和坚守时也更深入地感受到文化传承背后的情感激荡。
从激发情感认同到产生情感连接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从角色类型上看,非遗电影中的人物形象大都有着一些泛化的特征。其中“正向型”的角色类型例如《百鸟朝凤》中的天鸣、《老腔》中的白毛、《皮影王》中的王大江以及《窗花》中的田窗花等,他们身上带有着鲜明的民族精神特质,在时代的洪流中具有着涂尔干所说的“舍弃个人性、朝向社会性”的超越的力量。[27]但这种角色本身故事性并不强,要想触动观众产生情感共鸣,还需要“逆向型”角色的对比衬托。“逆向性”的角色身上有着更加复杂的人性情感,他们往往占据优越的先天条件,却耐性不足,例如《百鸟朝凤》中的蓝玉。他们十分渴望出人头地,或许也曾为传承坚持过,但因欠缺责任和使命感,最终向现实放弃。他们是时代里悲哀的渺小缩影,在他们身上观众更能感受到文化传承在现代社会的举步维艰,也更能理解传承人的使命与担当。
通过关注个体的生活状态来反映社会整体的生命意识,这正是非遗电影中人物形象塑造的人文关怀和价值所在。[28]作为基于中国本土历史文化的文艺作品,非遗电影讲述着符合中国人价值观的本土故事,反映着中国真实的民间生活和鲜活灵动的人民面貌。电影《爱在廊桥》《皮影王》《侗族大歌》都以传承人之间的感情线为题,传递出平凡烟火气中的温暖人情味。而《一个人的皮影戏》则聚焦于人心,影片中泰城皮影戏的唯一传人马千里,是无数个失意的传承者的缩影,他们在漫长的岁月里蹉跎着寂寞。马千里的执着让人感动,但他面临名利时的动摇也令人感到唏嘘。这种真实的人性与创作者赋予的完美形象的杂糅,更能让观众获得丰富的情感体验。
英国学者Chris Berry 认为,中国电影有“反个体主义”的美学特征,[29]把握住非遗电影的中华文化内核,就要从中国人共同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情感逻辑入手,凝聚中华民族情感共同体。与个体相对的是集体,家庭是中国文化中集体的一个代表。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家本位”观念占很大的比重。[30]“家本位”既包括“家庭本位”也包括“家族本位”,即我们所说的“光宗耀祖”。这种责任伦理,是非遗电影中传承人的主要精神驱动力。所谓“师徒父子”,涵盖了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师父与徒弟的责任,前者侧重于“教”而后者侧重于“学”。例如《天公苏作》中的香山帮父子,面对营造技艺后继无人的现实困境,老匠人有自己的执拗,而年轻一代也有着创新变化的想法,最终沉睡的技艺被中国式的亲情所唤醒,这也是中国人共同的情感选择。
总而言之,非遗电影要构建的共同体情感,即“社会成员对所属社会产生的归属感,是对于共同需求的认同和参与公共生活的动力”[31]。它体现着人们的理想需求,在动荡的社会大环境中既实现了人们想要回归安稳环境的愿望、打造了世外桃源般的理想空间,同时,电影不再是观众对异质文化“看图说话”的工具,匠人的“人”性增加了影片的真实性,并使其具有人文美。影片中个体的情感呈现折射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让观众能够相当直观地感受当地文化的价值内涵所在。此类影片中方言俗语的使用,也营造了共同的文化语境,“构造出基于情感的共同体”[32],例如《长调》《老腔》中古老淳朴的故乡腔调以及《寂寨》《阿娜依》中的苗歌苗语等。这些电影中的细节,既还原了非遗传承人们最本真的样子、彰显出浓郁的文化情怀,也在迷失方向的青年人心里种下了恒久的精神寄托的种子。
三、夯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想象
巴勒斯坦著名文学理论家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指出,19 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东方文化既“神秘、有趣”又“原始、专制”,[33]他们对东方世界的认识完全基于虚无缥缈的幻想,“东方成了怪异性活生生的戏剧舞台”[34]。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国际地位显著提高,西方世界中又出现了一种汉学东方主义倾向,[35]即以中国为主要对象对东方文化进行再研究。与此同时,形象各异的中国面孔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西方影视剧中,但依旧只是作为零散的中国元素被移植嫁接在异国土壤中,刻意地营造出一种东方“奇观式”的景象,以满足西方观众的猎奇心理,例如《木乃伊三:龙墓之隐》《功夫之王》《唐人街》等。这对于中华文化的输出并无益处,也让我们意识到重构中国想象,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守护住民族根脉刻不容缓。
在经济全球化、文化扁平化的时代,各国都在试图通过挖掘电影的民族价值,推出带有民族特色的佳作,提高本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但凡是被冠以“民族电影”的作品,都是那些具有浓郁地域风情和民族个性、有着明显民俗元素的影片,它们给观众留下了鲜明深刻的印象。[36]例如科技感强、西部风格浓郁的美国电影、以动漫和武士精神闻名的日本电影以及色彩绚烂、载歌载舞的印巴电影等,它们都在潜移默化之中输出着本国文化。而凭借独特民俗元素的中国电影也一度在国际上崭露头角,例如《红高粱》《霸王别姬》《饮食男女》《卧虎藏龙》等,创作者运用“镶嵌、点染、象征”[37]等手法在片中引入了少量非遗文化元素,虽然现在看来算不上真正的非遗电影,但这些植根于中国本土文化的创作,为我们提供了用非遗文化弥补中国想象、打造中国电影品牌的新思路。
“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走向共同命运的历史。”[38]作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文化中具有世界意义的话题,在全球化的空间中具有深远的公共价值。共同体可以看作是想象的产物。以国家共同体想象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想象做区分,前者即爱国情感,而后者则是“作为人类一分子与全人类共同命运息息相关的普遍性情感”[39]。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家文化命运与世界文化命运息息相关。推动非遗电影共同体美学发展,既体现着中国电影的文化自觉,又是借中国想象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电影《凤冠情事》聚焦昆曲文化,以半纪录半剧情的方式体现出了中国戏曲“假象会意,自由时空”的表演精髓。影片中一方小小的戏台凝聚着中华民族记忆深处的集体想象以及民族意识,体现着中国美学讲究的意境之美。同时,美学上的共情也有利于中国文化融入世界文化的时代洪流中。
重视非遗保护对延续历史文脉,增强人民的文化自信厥功至伟。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文化自信,习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40]。而从想象的中国到自觉的中国想象,非遗影像的创作者基于自身对于中国记忆以及对社会文化的理解也做出了新的审美建构,[41]在一屋两人三餐四季的古典韵律中凸显出独属中国的浪漫。一方面,电影中的民俗符号让观众一眼就分辨出这是来自中国的作品,例如皮影戏、唢呐、苗族服饰、羌族村寨、小桥流水、剪纸窗花、鞭炮、红灯笼等。而另一方面更能把握到民族风格精髓所在的则是电影通过情节设置、人物关系等多种途径委婉含蓄传达出的东方情怀。例如《图雅的婚事》中不肯放弃残疾的前夫巴特尔,坚持要带其再嫁的图雅,象征的是中国人重情重义的美德。而这份情谊也为苍茫的草原和孤独的蒙古包平添了一份传统韵味。
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文明断层的国家,中国在漫长的岁月中经过多民族的文化交流与碰撞,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电影被人们视为一种由文化书写的民族志,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民俗文化更为观照的非遗电影,记录了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在国家和政府大力扶持之下,非遗影像的创作大有方兴未艾之势,但从市场传播的角度上来看还是存在着“叫好不叫座”和“只唱高调不叫座”等的问题。《百鸟朝凤》当年上院线的百般不易还历历在目,现如今创作者又在电影中针对本土文化对外传播的思考做出了冰冷的现实讽刺。电影《雪花秘扇》作为一部西化的中国电影,从西方的角度阐释了中国传统民俗文化——江永女书。女书在影片中作为交流的工具,本应表现出中国女性坚韧、忠诚的优秀品质,但大量的文化堆积不仅没有触及中国文化的内涵,反而还让电影落入了满足西方期待的东方主义陷阱之中。
我们无法阻挡时代的变迁和外来文化的涌入,但我们更不能忘记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而去重构新文化。当今世界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42]。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为世界人民提供新的集体认同”[43],守护住中华民族文化根脉就是题中应有之义。每一门民间传统艺术都曾建构了“乡村礼仪秩序、行为规范,提升了人的基本道德准则”[44],是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和心理依赖。然而,就像电影《百鸟朝凤》结尾游天鸣孤身一人在焦三爷的坟上吹奏起凄凉的乐曲,我们才惊觉,民俗文化已经消失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太久,那些童年里真切的记忆都成了遥不可及的传说。至此,路漫漫其修远兮,让非遗艺术在现代语境中重新绽放,就是我们为实现中国想象和文化自信所需要做出的坚定选择!
四、结语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的灿烂文化在时间长河里共同凝结成了中华民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见证,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血脉生生不息地传承下去的保障。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全人类的文化根脉。“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的中国,民俗文化极为丰富,面对民族差异,我国始终本着和而不同的优秀传统文化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56 个民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45]。然而,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外来文化的入侵,传统民族文化却被我们逐渐淡忘了。作为记录人类文明的新形式,非遗电影出现的时间并不长,但发展势头一片向好,为非遗建构文化中国的新形象做出了重要贡献。创作者们利用现代传媒的手段,唤醒了民族共同记忆,展现出过去的辉煌、现在的坚守和未来的希望。电影的宣传效果也促进了非遗保护工作的开展。与此同时,非遗电影也面临着巨大的考验,部分创作者的创作层面依旧停留在追求奇观式的视觉效果上,不惜塑造了伪民俗元素来博取噱头,对中国文化的传播造成了极差的影响。创作内容也比较泛化,大同小异的剧情容易让观众失去兴致。特别是在快速消费时代,相比短视频的优势明显,非遗题材电影的未来发展该何去何从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总而言之,我们的创作应在尊重并了解民俗文化的前提下,再通过不断演进、现代化的过程提炼文化精粹加以展现,确保中华传统文化古脉得以传承。另外,电影的创作还要注重可看性,不仅要可看还要好看。提升文化吸引力,为影视创作增加文化的价值,降低观众对非遗文化的敬畏感,拉近他们与传统文化的距离,避免观众从踏入影院就带着一颗“上课”的心。这就要求创作者们巧用故事元素,在叙事上下功夫,塑造出一个个性格鲜明有血有肉的传承人形象,用这些珍贵的精神财富,记录中华儿女勤劳善良的可爱面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上再次强调我们要“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46]未来,创作者们应继续承担起传承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担。在创作过程中通过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方案,让中国想象得到全世界的现实认同;通过展现新时代国家风采、坚定文化自信,让非遗电影真正成为助力中国梦实现的新力量;通过输出中国式价值观念,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美好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