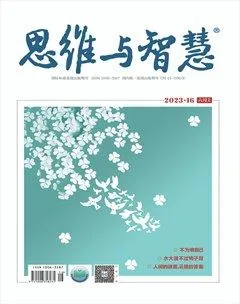同一种雨季
章铜胜
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里,写了马孔多的一场雨,一场下了四年十一个月零两天的雨,那场雨多么漫长啊,长到即使在我打开的书页上,也能感受到马孔多那湿淋淋的水汽。在这样的一场雨里,人会怎样,那些在野外的植物和动物又会怎样呢?或许想象太过有限了,无论怎样费尽心思,大概也想象不出一场如此漫长的雨季。我第一次在阅读文字时,害怕一场雨。
尽管马孔多的雨季再漫长,也不会成为我的噩梦,我还是会喜欢上一些雨季,一些我觉得应该喜欢的雨季。
雨季中,只要雨下得不是太大,我还是会在空闲的时间里,出去走走,在雨中感受一种在平时难以感受的情趣。我喜欢微雨的清凉意,像是有意在提醒你,也像是在逗弄你,可能也是在以一种你不易感知的方式,与你交流。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懂得微雨的凉意,但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这种春日的微凉,这样就足够了吧。
雨中,我喜欢到人们不常去的地方漫步,一个人沿着或熟悉或陌生的道路,慢慢地走。一路上遇不到什么人,更难以遇上熟悉的人,这样更合我的心意。平日里,生活已经吵闹得可以了,雨中独步,再遇上熟人,在雨中说着可说可不说的话,又何必呢,至少也减少了在雨中行走的一些趣味吧。雨季中,我常去长江边的步道,或是郊外一段新修的路上走,穿着雨靴,撑一把伞,选在清晨,或是午后,这样人会少一些。
长江上的雨,清亮一些,也茫然一些。看见江面上压得低低的雨云,有点压抑感。而眼前的雨滴,模糊的远岸,岸上绿树和绿树掩映下的村庄,更加模糊不清,似乎只是一些更为模糊的光影,又多了几分画意。多数时候,能想象出它们的位置和形状,可能更多的情况下,想象是基于之前对于它们的一些印象。有时雨停了,对岸的一抹绿色更深一些,似乎也更清新清晰。长江里的浪始终在涌动着,看不清雨点落在江面上的情形,流动着的江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雨滴入江,瞬间便遁于无形了。我的目光,在雨中的江面之上,也会迷失,甚至有些茫然。
郊外的雨中,生机盎然,植物在生长,一些花低下了头,花瓣落了一些。偶尔能看见一只鸟藏在树枝间,缩着脑袋,在雨中,它们的羽毛更加鲜艳。雨中,和一只鸟对视的机会很少,而那些不同形状的绿色的叶子,却以深浅不同的绿色,涌进视野里来,让我一时詞穷,不知道该怎样形容那么多种深浅不同的绿,或许那样丰富的绿色本来就是无法描述的一种存在。喜欢雨季,是因为雨季给我带来一种无法描述的丰富,仅仅一种绿色,就让我穷于应付了。树上褪尽的残红,地上的落红,枝上残留的花朵,叶间新结的果实,都将那一份最初的青涩藏在了雨中。
每个人的雨季,都给自己留下了一些别样的念想。又下雨了,忽然就想起汪曾祺先生的文章《昆明的雨》,那是他文字中的雨季。他在文章中说,自己是到了昆明以后,才感受到所谓雨季的。昆明是他的学生时代的记忆,正是多愁善感的年纪,那样的雨季定然是可爱的。“雨,有时是会引起人一点淡淡的乡愁的。”雨季里的一天,汪曾祺先生从西南联大新校舍,到莲花池去,在附近一条街的小酒店里,看见院子里的一架大木香花,“一棵木香,爬在架上,把院子遮得严严的。密匝匝的细碎的绿叶,数不清的半开的白花和饱涨的花骨朵,都被雨水淋得湿透了。”雨季中的木香花,给汪曾祺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四十年后,他在文章中写下那棵木香花,还在文末写下了一首诗,“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在文章的结尾,汪曾祺先生写道:“我想念昆明的雨。”雨季将来,我开始想念那些独自漫步的雨季了。
(编辑 兔咪/图 槿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