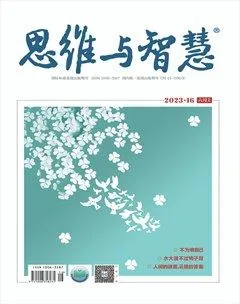剃头挑子两头热
陈柏清
放了学,刚进院子,看见一副剃头的挑子放在门口,一把木拐倚在挑子上,我撒丫子跑,一个箭步越过小院墙,“嗖”一下钻进黄瓜秧架,忍着瓜叶浓密的黄瓜架里的闷热,忍着秧叶上的小刺拉得脸、脖子火辣辣地疼,大气不敢出,连带刺的小黄瓜撞到了鼻子也顾不上,因为我知道河对岸的曹舅舅来了。
我怕见到曹舅舅,不是因为他是走街串巷的剃头匠,不是因为他跛足,走路需要架拐,而是因为他老想做我干爸。曹舅舅是妈妈的姨表兄弟,是姨姥收养的,和母亲没有真正的血缘关系。但他像亲儿子一样照顾母亲年老的姨父姨母,这令母亲感动。有一次曹舅舅来我家,酒酣耳热之际,他说,你们家老幺招人疼,给我做干姑娘吧,等我到了66岁,也有人给我包饺子。曹舅舅年轻时因为家境和身体都不好,没有结婚,所以没有孩子。我听到这话吓得心提到嗓子眼,生怕母亲应允,幸好母亲没有接住他的话茬,这件事儿就模糊过去,可是我老担心哪天母亲心思一动,我就去姓曹。
尽管母亲没有答应,但曹舅舅认定我是他干女儿,一见到我就“幺儿幺儿”地喊。每次我都吓得一溜烟跑得远远的,让跛足的曹舅舅望尘莫及。曹舅舅不但心里这么认定,行动也跟上,经常给我带小玩意,大多是他自己做的,木头刻的小人,尽管刷了油漆,可是那油漆刷得斑斑驳驳、捉襟见肘,一准是谁家装修捡的剩儿。带花的小辫绳,粗劣的做工昭示了它的来源地。粗制滥造的饮料,包装拙劣的饼干、曹舅舅都很认真地送来,还一再叮嘱母亲,一定要交到我手上,他知道我会躲着他。可当母亲把那些东西交到我手上,它们最终的归宿就是南园子的小墙下,我愤愤地用木棍挖一个洞,把它们埋在里面。
有一次曹舅舅竟然现身我午间放学的路上,他放下小板凳,非要让我坐,并且说他给我烤了红薯。就在他从挑着的炉子里往外拿红薯时,我从板凳上跳起来跑掉了。第二天我避开小路,从高高的水渠上悄悄瞄着路口,看见曹舅舅正在路口给人理发,我赶紧溜进麦子地,像一只地鼠穿过麦地跑回家。
整个的童年,我似乎都在和曹舅舅玩着这种猫鼠游戏。尽管他多皱的眼角和浑浊的眼睛看不出恶意,腮帮子上浓密的胡茬包裹的、略带干涩的笑意也只显露出窘迫,可我仍愤愤不平为什么选我做干女儿,仿佛那是莫名的奇耻大辱。在一次跟姐姐拌嘴时,因为她喊出你就该去姓曹,我破天荒一个星期都没有跟姐姐说话。
虽然我从不曾喊一次他干爸,他还是按照乡俗,逢我生日他会包红包,买红腰带。母亲有时很为难收下这些,可是曹舅舅总是说:“幺儿还小呢。”直到我上高中,他没办法说幺儿还小,母亲推让,他眼泪汪汪地说:“你就替她收下,我还求什么,过66寿日那天幺儿帮我包66个饺子就行了!”
母亲对我描述,也含着泪。我很烦恼听到这些,便扭身走开。
我大学毕业上班的第一份工资,除了留下生活费,其余给母亲买了她爱吃的糕点、喜欢的衣服,都寄回了家,还嘱咐母亲给曹舅舅送二百元钱。母亲在电话里沉默半晌,说:
“你曹舅舅刚过完年就去世了。”我突然想起小园南墙根下的物冢,里面斑斑驳驳的小木人、拙劣的小头饰,大概早已坏掉的饼干、飲料、辣条……敞开的窗子,柳絮儿在和煦的春风里荡来荡去。我对母亲说:“好吧。”然后挂掉了电话。
好吧,曹舅舅。有一刻世界那么安静,仿佛一切都被屏蔽了,我想起了你,想起了你一直盼望的、66岁寿日的66个饺子。
(编辑 雪彤/图 槿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