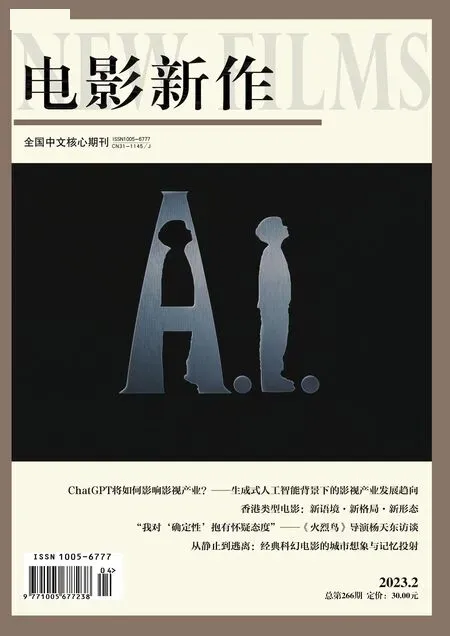香港体育电影:流变、风格及文化表达(1997-2022)
许 琦
2022年,随全球瞩目的体育盛事——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中国体育电影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对优秀体育电影作品的市场渴求和对以电影为载体讲好中国体育故事的理论探讨都达到历史高点。2022年,同时恰逢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以类型化为突出特征的香港电影,在两地创作共融、市场共荣、文化共容的新语境下,从作品数量、商业思维、类型规约、风格探求等多个方面,为中国体育电影的蓬勃发展做出不容小觑的贡献。《少林足球》(周星驰,2001)、《头文字D》(刘伟强、麦兆辉,2005)、《激战》(林超贤,2013)、《点五步》(陈志发,2016)、《夺冠》(陈可辛,2020)等优秀作品,不仅承载着无数国人的体坛银幕记忆,更发挥香港所长参与中国体育电影的多元探索,为中国体育电影迈向彰显民族特质、并轨世界影坛的发展之途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发展流变:从路径依赖到类型规范
从历史上看, 在香港电影的类型矩阵中,相较于更具在地性的武侠片、动作片、喜剧片等主导样式,体育电影虽不具代表性,却也于百多年的发展中创作连绵成线,在与中国母体血脉相连、同声相应的同时,舒展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其中,香港拍摄的首部体育电影——1934年由海外联华声片有限公司出品的《破浪》(关文清,1934)即是沪港两地频密互动的产物。影片以游泳运动为题材,用年轻人在游泳场和人生情场的角逐结构全片,取景广州近郊及岭南大学、启用广州女子游泳冠军本色出演等艺术选择,体现出较强的奇观性、现代性和地域特征。又如,香港电影工业奠基期由 “电懋” 出品的《体育皇后》(唐煌,1961)一片,既与上海电影传统形成了某种跨越时空的镜像互文,又彰显了片场实力、青春文化及香港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时代症候。在步入20世纪80年代黄金发展期后,“嘉禾”“新艺城” 也自觉拓新推出《波牛》(袁振洋,1983)、《飞跃羚羊》(郑则仕,1986)等体育题材影片,以之作为动作、喜剧主导类型的补充,但遗憾的是均因票房失利而折戟沉沙,在商业挂帅、娱乐至上的香港影坛未引起足够重视。整体而言,1997年前的香港体育电影在工业和艺术上都较为边缘化,也缺乏像《女篮5号》(谢晋,1958)、《沙鸥》(张暖忻,1981)这样锐意创新、扣动人心的时代文本,更有论者指出,“香港极少有比较纯粹意义的体育电影,所谓体育电影都只是略带比赛性质而已”。1
事实上,自1928年明星公司的《一脚踢出去》(张石川、洪深,1928)开启中国体育故事片历史以来,题材,而非类型思维长期主导着我国体育电影的创作实践。无论是民族危亡时刻传递 “强身强种”的时代吁求,抑或 “十七年” 间对身体和思想的集体形塑,及至新时期以奋力拼搏的体育精神书写时代的精神匾额……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体育电影在银幕上织就体育救国强国之梦的同时,一直承载着远超体育电影力与美的表达、自我实现的励志旨归。对照审视,如果说同时期内地体育电影以体育题材承载家国命运的厚重主题,香港体育电影则走的是以体育题材搭载成熟类型的越界杂糅之途。的确,“类型化是香港电影称霸亚洲的不二法门,而类型化也形成了香港电影的路径依赖,香港电影所有的创造力都在类型化的内部展开”。2

图1.电影《少林足球》剧照
而回归以来,尤其进入后CEPA时代,香港体育电影在两地创作力量及观念的助推互补中,闯出一条由路径依赖到类型规范的发展之路,如盐化入水般实现了中国体育电影的美学升维,完成了由题材到类型的创作观念嬗变。
(一)类型中的作者:创意切口
回首20世纪90年代中期,类型化由造就香港电影黄金年代的法宝变为导致影业盛极而衰的隐忧,“类型电影偏于单调” 成为 “香港电影之死” 的重要诱因。3面对亚洲金融风暴、好莱坞大举压境、市场版图缩减等系列危机,以创意为核心竞争力的香港影人希图凭 “类型电影+创意+明星”4的公式闯出新天地。其中,既能彰显香港电影动作美学的金字招牌,又能引发港人砥砺奋进情感共振的体育题材,成为备受青睐的创意切口,杜琪峰、周星驰等 “类型中的作者” 相继试水,引发了新世纪前后香港体育电影创作的一个小高潮。
其中,《 少林足球》 以世界性的足球运动包裹在地性的功夫奇观,笑中带泪的悲悯情怀取代了此前的无厘头恶搞,大量数码特技的加入形成强烈的漫画感,由粤语俚语到少林功夫的 “动作转向” 轻松实现跨文化传播。影片在打破多地票房纪录的同时也斩获各项大奖,成为周星驰喜剧电影创作中具里程碑意义的自觉转型之作。创建港式黑色电影典范的杜琪峰,在《柔道龙虎榜》(杜琪峰,2004)中舍弃惯常经营的警匪模式,诚意致敬黑泽明的侠义世界,以极具风格化的导演技巧讲述发生在热爱柔道的年轻人间的激越青春故事,因浓烈的艺术个性和个人情怀表达成为导演自陈最为中意的作品。刘德华同样把拳击题材的《阿虎》(李仁港,2000)定为从影百部、形象转轨的界碑之作,泰拳元素、日本女星、曼谷外景都彰显了颇具野心的亚洲市场拓展策略。而素有 “香港电影第一剪” 之称的麦子善,则在徐克的帮助下完成了由剪辑师到导演的身份蜕变,凭在方寸间营建紧张氛围、以激烈实战颠覆套路表演的处女作《散打》(麦子善,2004)闯荡国际影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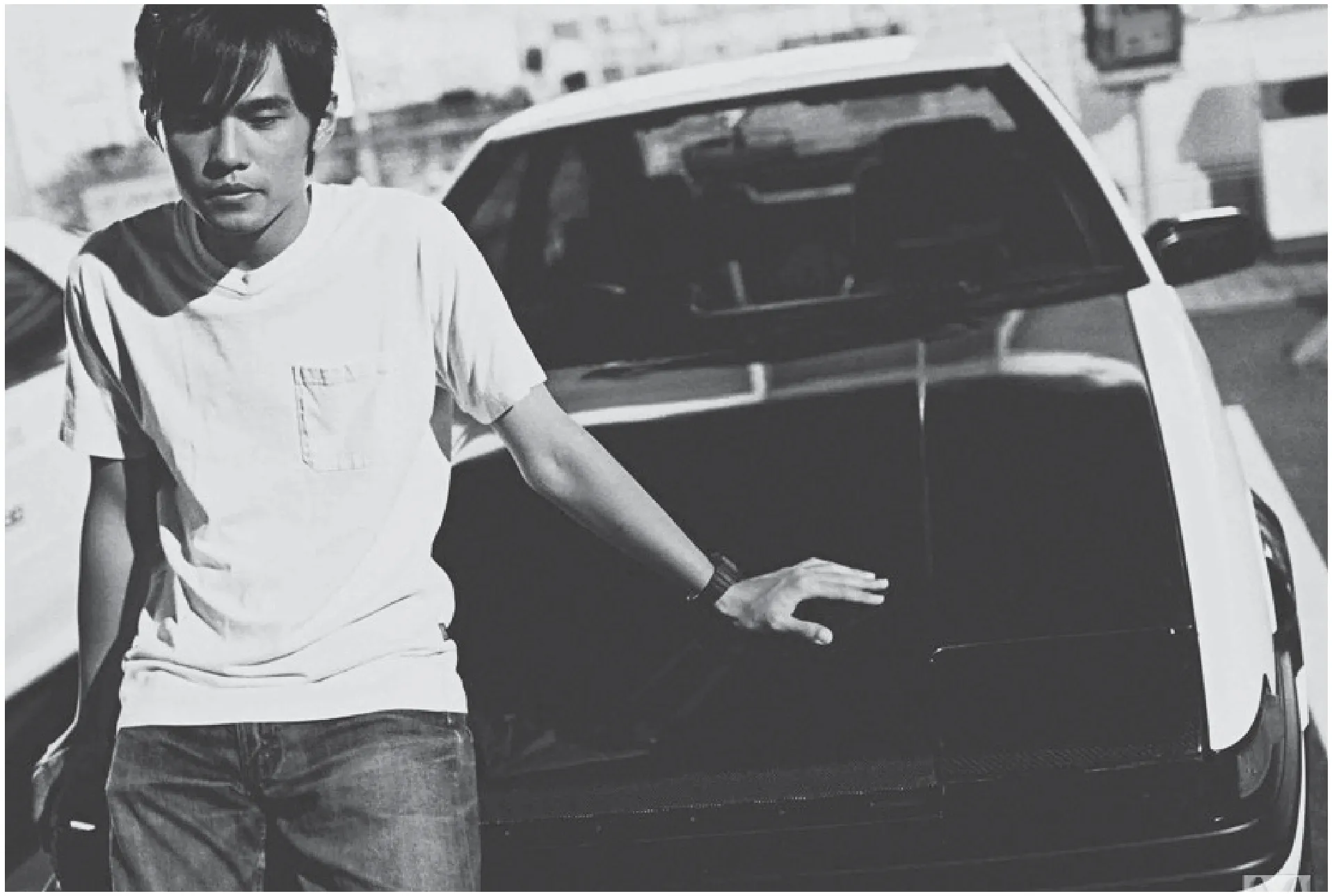
图2.电影《头文字D》剧照
(二)商业元素:跨地重组
事实是, 面对固有市场的萎缩沦陷、亚洲及北美市场的拓展乏力,香港电影唯有 “北上” 才能获得新的发展空间。2004年CEPA政策的实施,给香港影业注入澎湃动力,灵活应变的 “北上大军” 在资源共享、观念碰撞中悉力摸索适应内地市场的创作规律。类型策略方面,因两地电影管理体制的差异及文化肌理、价值观念的隔膜,长久以来港人擅长的赌片、鬼片、警匪片等类型,或难以通过审查规章的检视进入内地市场,或需于叙事模式、价值体认层面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校,在创作磨合、融合阶段,合拍片长时间深陷古装、武侠的同质化泥淖。
在此情势下, 重动作、 正能量、中小成本的体育电影,无疑是契合价值观念、聚合人才资金的应变创新之选。尤其是2001年北京获得第29届夏季奥运会主办权,标志中国体育电影迈入奥运叙事时代,国家的日益强大和体育盛事的到来都使体育叙事成为中国电影创作的热点。具备较强商业意识、类型经验、专业素养的香港影人的深度介入,给这一时期的中国体育电影创作带来新变。虽然因逐利动机不免泥沙俱下,其中不乏“大牌明星+简单故事+快速拍摄+搞笑情节”5的粗线条赶制之作,但整体呈现出乐观明朗、注重娱乐的特色风貌,一扫此前内地体育电影的严肃沉郁之气。涉及涵盖的体育项目也包括足球、篮球、短跑、赛车、自行车、龙舟、综合格斗等诸多类别,表现领域日益多元。
以赛车题材为例,这一阶段的《头文字D》与《赛车传奇》(罗义民、韩之夏,2011)、《极速天使》(马楚成,2011)等影片以技术革新再现竞速奇观,对此前 “黑帮+赛车” 的路径依赖模式进行了反拨,打破观众以飙车为危险、禁忌的刻板印象,奠定青春励志、积极正向的基调。而擅长动作表现的中生代导演林超贤也深耕体育类型叙事,完成了《激战》《破风》(林超贤,2015)两部口碑不俗的精品之作,通过体育电影对梦想、成长、正能量的泼墨书写,林超贤似乎已经找到对接类型美学和内地主流价值观的频段密码。上述这些影片均有跨区域流动资金的挹注及多地演职人员的加盟,在跨文化、跨区域合作中尽显香港电影 “超地区想象” 的特色传统,初步完成了合拍体育电影在产业链条、价值表述方面的整合重组。
(三)类型深耕:新主流( 新生代)
“CEPA之后的香港电影,像极了一个巨大迷局,在本土坚守与北上融合之间焦灼博弈着……以类型为契机,香港电影实现了困顿迷局中的突围。”6就体育电影而言,2016年前后同样是重要的转折点,在电影人类型深耕的自觉下,无论合拍路径抑或本土制造都不断涌现堪称典范的精品之作,类型成熟度和美学高度都有较大突破,中国体育电影的整体素质得到优化提升。
在 “北上” 行动方面,香港导演的类型经验与内地文化理念的融合达到妥洽匹配,迎来 “内地主流价值观与‘港味’美学中的类型美学和港式人文理念充分对接”7的新主流电影创作繁盛期。陈可辛、李仁港等中生代导演在《攀登者》(李仁港,2019)、《夺冠》中重返历史现场,通过重要体育事件、重大体育赛事的回溯与重现询唤观众的自豪与自信之情,织就民族崛起的强国梦。这些作品在不断创新类型要素的同时寻找体育题材与观众情感共振的最大公约数,“合拍” 的外在属性已逐步淡化。
地方转向方面,受益于香港特区政府的优惠政策及影业内部的支持扶助,新世代的创作潜力开始被激活,《点五步》《逆流大叔》(陈咏燊,2018)、《一秒拳王》(赵善恒,2020)、《妈妈的神奇小子》(尹志文,2021)等一批更具在地性格的作品相继涌现。这些新锐导演并未沉溺于青春絮语的文艺表达,而是考衡商业要素、重视类型力量,以体育故事作为银幕首秀,在类型范式内张扬理想主义姿态,高歌迎难而上的“狮子山精神”,体育电影渐趋成为青年导演养成的重要类型。上述影片或植根真实事件、或弥散怀旧气息、或充溢浓郁的“地方感”,带给素以娱乐至上的香港电影以额外的厚度和温度。
可以欣喜地看到,近年来史诗气度与励志小品两种不同的创作走向正形成一种参差的复调,在汇合与分流中共同促成中国体育电影独特风格的彰显。
二、风格特质:香港电影传统的渗透与延异
从类型生成的角度考衡,与电影艺术几乎同时诞生的现代体育,因其运动性、奇观性、仪式性及神话特质,天然适合银幕展现。而体育确然为电影 “提供了一个好故事应该具备的一切:英雄和反派、胜利和灾难、成就和深渊、紧张感和戏剧性。由此,体育为电影供给扣人心弦的叙事,电影则成为体育展现的生动媒介”。8不过长期以来,因受众的限定性及作品的良莠不齐,加之常与爱情、喜剧等类型越界糅杂出现,即使在以体育为重要流行文化的美国,体育电影能否被视为独立类型仍被学者不断探讨。里克·阿尔特曼指出:“当此前的形容词——如‘西部追逐’电影中的‘西部’——演变为名词,并能征服整个文本且显示出独立驾驭它们的明确能力时,一种类型就此出现。”9在由 “关于体育的电影”向 “体育电影” 的滑动过程中,其叙事特征、视觉符码、主题价值经由无数经典作品得到确立。布鲁斯·巴宾顿分析认为,体育电影的“典型场景是作为‘梦想之地’的体育场馆或比赛场地,主要视觉图谱和情节构成都围绕体育活动展开”, 主题则与获得尊重与认可紧密相关,这些都使体育电影拥有类型的独立性。此外他也指出,由于 “好莱坞在影业历史上的统御地位,决定了体育电影不仅由美国出品所主导,同时也由表现美国体育运动的美国电影所主导……向好莱坞体育电影的过度认同发起挑战”10,审视不同国别及文化中的体育电影表现,将极大补充我们对体育电影类型特质的认知。
香港电影是杰出的中国区域电影。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汇的要地,香港 “成为一个文化中转站,对各种文化先吸收再转手。早先是以借鉴引进他人经验为起点,各种文化进来以后就模仿、翻拍,掌握其中奥秘之后,融合多种因素,再重新拼装组合翻新改造”。11具体到体育电影创作,香港影人一方面借鉴模仿了好莱坞成熟样式,另一方面则本着“拾荒” 美学对其电影传统中的成功要素、桥段进行“延异”(différance)处理,在模仿、拆解、重构中形成了独特的类型表述。
(一)反英雄的底层逆袭叙事
“任何类型的叙事语境都浸透着饱含意味的惯例。”12与类型有天然亲缘性的体育活动本身即 “植根于隐性的叙事结构——它是一种基于特定规则的竞争形式……体育赛事抛出了‘谁会赢’这个问题,并承诺予以回答”。13只不过体育竞技是一场没有剧本、不可预测的战斗,而体育电影则是对既有叙事惯例的悉心排演。具体而言,作为欲望目标指向性极强的体育片,为获得观众共情并造成戏剧性效果,往往会重复处于边缘、弱势的个人/团体经由不懈努力,与自身弱点及局限性进行全面抗争,最终获得胜利的叙事套路。
“逆转胜” 的神话建构,在香港被放大成草根的底层逆袭叙事。《少林足球》中栖居天台、拾荒为生却依然眼里有火、心中有梦的阿星;《流浪汉世界杯》(关信辉,2009)中踯躅在繁华都市底层,因足球获得新的家庭、重拾自信的流浪者;《逆流大叔》中深陷事业、家庭危机,在一场同舟共济的龙舟赛事中挑战人生逆流的中年大叔;《妈妈的神奇小子》中参加四届残奥会、获得六枚金牌却缺乏基本生活保障,坚韧对抗身体残缺、生活艰辛的香港著名运动员苏桦伟……这些逆境求强的小人物身影是香港草根文化的重要表征,在人生的抑扬起落中引发观众对人性的深入思考。体育场域的拼搏奋进与深广的社会图景并置,极大拓展了中国体育电影的人性展现之维和现实表现力度。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香港体育电影中还塑造了较多独具魅力的反英雄形象。例如《阿虎》《柔道龙虎榜》《激战》等影片的主角均是曾经风光无限却因错误的人生选择跌下神坛、沦落底层的失意者,在故事中他们因不同契机重返赛场,在全力一搏中找回初心并最终寻回自我。这种叙事走向 “实际上沿袭了《阿郎的故事》等港片中男性英雄创伤与回归的创作模式”14,在放大主角瑕疵、加重困境抉择的同时暗合体育电影自我超越、自我救赎的主题表达。
(二)双重主角的二元句法结构
“ 类型电影展现正反两极化的文化价值观对立,这通常依赖于双重主角和二元结构……以竞争为中心的体育电影则强化了这种二元论。”15如果说美国体育电影是通过对手定义主角的话,香港体育电影则以 “师徒/同伴” 关系打破了好莱坞的个人主义焦点,形成了别样的双重主角设置。
体育电影中的教练、同伴,在叙事学领域被普罗普分别指认为重要的角色/行动范畴——施惠者及帮助者,这二者的叙事功能在好莱坞往往是弱于对手的存在。而在香港电影传统的渗透与影响下,则新变为与主人公一体两面的复合式主角构成。
其中,滥觞于粤语武侠片时代的师徒关系表现,经由新派武侠、功夫片、功夫喜剧的一路演进,已稳定成为香港武侠功夫片中至关重要的人物谱系,在体育电影中则进一步转化为教练员—运动员的二元结构。《激战》《一秒拳王》等影片一方面遵循体育电影叙事逻辑,通过教练形象完成身体规训、专业引领、精神传递的叙事功能;另一方面则因袭了功夫喜剧中师徒关系的喜剧化、现代性处理,甚至对教练的权威进行了解构——为师者或于精神上沉迷赌博、一蹶不振,或在肉体上罹患疾病、无力逐梦。由此,师徒间不再是引导—被引导的权力结构,而是相互替代、位置重置的复合关系。影片在琐细日常的生活实感中捕捞浓郁人情,又以共同梦想的实现牢牢扭合住人物命运。
而《 破风》《 点五步》《 夺冠》等作品则调用了由张彻导演武侠片开启、在黑帮警匪片中定型放大的 “双雄” 模式。《破风》中的仇铭和邱田、《点五步》中的阿龙和阿威,既是性格互补、惺惺相惜的同伴,又是抉择不同、命运交错的镜像。在《夺冠》中,更巧妙设置了陈忠和这个角色与郎平形成本土化/全球化的对照:性别对立、身份差异的两个人,由初出茅庐到各自挂帅,从同伴队友到竞争对手再至勠力合作,经由极具戏剧张力的人物关系巧妙结构起四十年间中国女排的时代传奇。
上述 “师徒/同伴” 的角色关系设定,调用香港电影传统资源,改写了好莱坞基于竞争的个人英雄主义表达,通过良师益友携手共促、自我超越的燃情叙事,找到了最为熨帖中国人情感结构的人物构造法,无疑也更符合“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 的现代奥林匹克精神。
(三)动作燃点的艺术性处理
燃情热血的受训蒙太奇段落、充满仪式感的终极一战……运动场面作为体育电影的符码和惯例,不仅是情节走向和人物命运的黏合剂,更是该类型的重要展现要素。如何艺术性地展现运动之美、营建令人激情澎湃的动作燃点是优秀体育电影要解决的核心性问题。因为体育电影并非实况转播或赛事录像,而是对体育活动中富有意义的动作再加工,这要求创作者必须在电影思维指导下把体育元素升华为艺术元素,彻底摆脱竞技现场时刻的束缚,删去冗余、攫取精华,既能穿透围绕一场赛事备战点滴的时空之维,又能定格在运动员奋力一搏时的坚定目光。
必须承认,“ 中国体育电影从新中国成立后,开始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运动员的思想历练上,对于体育运动本体的艺术呈现并不多”16,但香港地区的 “电影一向的强项不在叙事的深刻细致而在电影视听形式如动作、色彩、音响、节奏上的狂放、夸张、鲜活;笼统说是弱于文学性而强于电影感”。17长期武侠片、动作片的拍摄经验,使香港影人积累了高超的动作动感影像叙事技巧,他们以专业精神考衡不同运动项目的独特之处,不断尝试挑战体育运动视听表现的冲击力和感染力。

图3.电影《夺冠》剧照
在拳击题材中, 麦子善、 林超贤等人放大香港电影中建构性剪辑、升格镜头等技巧的表现力,对动作进行有效的压缩与延展,在动迅静定、俯仰结合中尽显身体对抗时速度、力度的爆发。拍摄赛车类运动时,刘伟强、麦兆辉等人除使用车载跟拍、快速剪辑、节奏调理等手法营造速度感,更运用大量航拍、摇拍 “诗意地表现赛道环境而将车手的内心空间外化”18,自在畅适间实现了快与慢的辩证。《夺冠》采用大画幅、高频帧实现观众对排球比赛的沉浸式观影体验,最多甚至同时动用13台摄影机以完成对排球 “本身的速度、力度和弧度,以及运动员之间的心理和行为博弈”19的精确捕捉。可以说,香港经验的加入,极大增强了中国体育电影在 “运动性”“体育感” 方面的表现力。
三、文化体认:港式人文理念的对接与香港精神的彰显
马丁· 斯科塞斯导演在拍摄《愤怒的公牛》(马丁·斯科塞斯,1980)时,曾将拳击描述为人生的寓言化呈现,而 “亦赛亦人生” 的体育电影历来通过赛场上的竞争反观人生:就像夺冠不是体育竞技的唯一目的,励志也不是体育电影的唯一母题,在自我超越中赢得尊严与价值、在自由之境中完成对生命的礼赞是现代体育电影叩问的共同主题。同时,出色的类型电影总在银幕上建构观众的集体梦想和认同想象,“是深层的人文精神,以及主流意识形态、主流社会愿望等种种元素和情感的交叉表达”。20必须看到,体育电影在凝聚人心、传递拼搏奋进正能量、鼓舞涤荡观众心灵方面,无疑具有天然的类型优势和不可替代的寓言价值。
近年来,香港导演将 “港味”美学的精髓——以个体关怀为主的港式人文理念嵌入大国思维,经由微宏叙事——“个人话语与宏大叙事相结合而实现的叙事范式变奏”实现了体育电影与 “新主流影片的‘整体类型化耦合’”21。其中,对个体生命与时代精神共振有敏锐体察的陈可辛导演,在《夺冠》中选择边缘性小人物——男性陪练和球队替补为核心角色,对观众熟谙的女排故事进行大刀阔斧的艺术加工,通过赛场高光时刻背后角色成长的心路历程,展现出既属于人物个体又属于当代中国的集体记忆。影片 “以日常化、人性化、细节化的表述策略弥合主流话语场域的内在裂隙,将主流价值融于个体体验以达成某种‘最大公约数’”22,在历史与当下的对话中询唤观众的民族自信与情感认同。可以说,《夺冠》在对接香港经验的基础上成就了更大的格局,实现了近年来中国体育电影 “见体育、见人物、见情怀” 的创作突破。
香港本土的体育电影也没有陷入始于小人物、终于小人物的狭小格局。无论是《柔道龙虎榜》中从人生谷底再爬起,与挚友相互感染、共同放飞红气球的司徒宝;《激战》中悟出 “怕,就输了一辈子” 而在拳台上爆发燃情斗志的落魄拳手;还是《点五步》中明了“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有勇气,去踏出这半步,尝试去改变” 的底层少年;抑或坚持 “上了船,我们就做一件事,跟着鼓声向前行”,尽显英雄本色的 “逆流大叔”……这些充满温度感的体育故事,为香港民众注入士气和斗志。影片中那些追逐梦想、永不言败的角色,正是充满生命力的港人情怀写照,是同舟共济、携手踏平崎岖的狮子山精神写照。
回首香港回归祖国的二十五载时光,那些经由长期岁月砥砺和激烈市场考验沉淀而成的创作基因,为中国电影创作注入新鲜活力,在两地影人勠力协作、不断调校下,不但完成了中国体育电影独具风格的类型规约,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市场化表达,更实现了与大众共情共鸣、提振社会正能量的文化聚合作用,中国体育电影的艺术探索与类型突破已初具规模和成效。“新时代是追梦者的时代。”23民众呼唤更具艺术成熟度、文化感染力的优秀体育电影作品,而更多与时代相映的中国体育故事、中国体育人物,等待两地影人在携手共进中深入挖掘、共同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