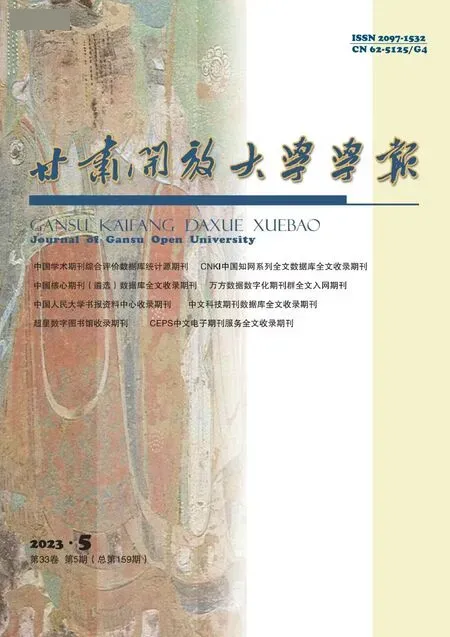从荒岛看人类与现代社会
——评孙频《我们骑鲸而去》
杨 朵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000)
纵观历史长河,人类以曲折的轨迹无限趋向文明,而在滚滚向前的文明巨浪中,发展的负面性使得缅怀历史成为人类永恒不变的主题。在孙频的中篇小说《我们骑鲸而去》中,“我”、老周、王文兰被置于封闭的荒岛之中,以现代人的身份回到几百万年前的文明之始。作者巧妙地将空间与人物的现代性并置,以此来展现旧时空和现代人之间产生的张力,进而讨论人性,以及人类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关系。
一、人类孤独的主题
荒岛文学是文学史上一大经典主题。岛屿作为一个特殊的空间环境,与小说人物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一方面,在西方文学史上,岛屿的出现具有偶然性。对于具有开拓精神的西方人来说,岛屿是土地扩张、产品储存的场所。岛屿的发现象征着人们对资本积累的追求以及对资本家冒险精神的赞扬。例如《鲁滨逊漂流记》中,鲁滨逊凭借顽强生命力在荒无人烟的小岛上进行生产活动,驯服奴隶,最后得以返回故乡,成为西方资产阶级的英雄人物。另一方面,由于岛屿在地理环境上的封闭性以及发展的落后性,岛屿被赋予孤独、荒凉的寓意。荒岛被浩瀚翻涌的海水包裹,自身像一座静止的监狱,独立于时间之外。在《我们骑鲸而去》中,作者以岛屿作为叙事空间,老周、“我”和王文兰三个不同性格的人物相继来到岛上。人物身上烙刻的现代文明的痕迹与文明始前的岛屿形成对立。但与传统的荒岛文学不同,作者虽然将人物放置在偏僻的岛屿之上,并没有完全将现代文明的产物杜绝在外。人物可以通过城市驶来的补给船获得淡水和粮食,他们无需像鲁滨逊一样与自然环境、物质需求作斗争。显然作者以荒岛作为小说环境,意在借用荒岛这样一片偏远、人迹罕至的场域来探讨人类孤独的精神世界。正如学者王春林所说:“孙频之所以要煞费苦心地把老周、王文兰以及身兼第一人称叙述者功能的‘我’也即杨老师,以一种‘孤悬’的方式放置到永生岛这样一个看起来极不起眼的封闭空间,正是为了充分地展开她对特定情境下人性状态的观察与思考。”[1]
小说中,岛屿的寓意随着视角的转变而前后变化。老周因才华横溢遭人嫉妒,失手杀人,逃到岛上。“我”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小科员,与老婆离婚后,“我”为了躲开人类,逃避与人打交道,主动要求到岛上守矿。杀死了家暴丈夫的王文兰,出狱后发现儿子车祸死亡,悲痛欲绝,受雇到岛上看护小洋楼。三个主人公共同代表着拥有黑暗过往,被社会排挤,欲追求诗意世界的社会边缘人。他们以处在现代社会的视角遥望岛屿时,岛屿是偏远而又独立的,像一个可以装载一切不适宜和错误事物的巨大容器,是边缘人类逃离现代社会的理想之所。作者在小说中化用了中国古代“桃花源”的典故,将岛屿变成一座海上桃花源。岛上“没有国家,没有战争,没有朝代更替,直接就从恐龙时代过渡到了现在”[2]2的历史状况与桃花源暗合。主人公老周是三人中第一位登岛者,他长期生存在岛上,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其生存状态与武陵人“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形成呼应。模拟桃花源来书写岛屿,说明岛屿承载着小说中三个人物的理想,是人物企图摆脱黑暗过去,摆脱现代社会生活的精神处所。显然,当人物以城市为中心时,岛屿即作为一个理想的彼岸出现。
但这个彼岸是主人公在现代社会受难后设想出来的场域,与现实的岛屿存在差距。当“我”以在岛上生活的视角反过来审视这座岛屿时,“我发现在这岛上最可怕的事情竟然是没有人可说话”[2]21。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将“时间流程中止”[3],“我”以第一人称的视角不断书写在这座没有四季的岛上闲逛时看到的椰林、榄仁树、橙花破布木,捡到的各种稀奇的贝壳、越南小孩的尸体、像女人头颅一样的椰子,等等。线性的时间跟随“我”的步伐和见闻被转化为具体可感的空间,“长成各种形状的时间正在那里走来走去地闲逛。”[2]1在叙述中,虽然小说的情节时间在不断地流逝,但人物内心的感受使得时间被分解成无数个零散的碎片,小说的叙述不再是推进情节发展,而是将有限时间无限延长,以细致片段的方式去呈现在岛上生活的细枝末节。时间的缓慢和行为无休止地重复增加了人物的空虚感、荒芜感,岛屿由桃花源变成了一座孤寂的牢笼。岛屿的荒僻象征着岛上生物的孤独,而四周围绕的海水则代表了人与人心灵间的城墙。在这岛上“我”自身也幻化成了一座漂浮的孤岛,岛屿和城市双重空间体验的对比,更衬托出了岛屿这一场域带给人类孤独的痛苦和危机感。最终,平静和孤独的自由带来的毛骨悚然使得“我”逃离人类的初衷消失殆尽,本能地产生了与其他人相依为命的感觉。
“我”情感的转变揭示了人类孤独的主题,人类本身就是一座孤岛,而对于长期处于社会生活中的人类来说,人群必是人类最终的归属,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附性是人类不可逃避的本质属性。
二、透视人性本质
岛屿作为一个封闭的地理环境,既是人类设想的远离人群的世外桃源,又是创造极端条件的人性炼狱场,是现实社会本身的缩影。按照小说人物对于岛屿的期待,岛屿将会是人类实现终极自由的理想空间。然而在故事的不断演进中,桃花源式的空间逐渐倒塌。在《桃花源记》中,武陵人通过辛勤劳动在桃花源中实现了世世代代的安居乐业,文章中记述了武陵人质朴的避世追求,却没有呈现在长期发展中桃花源的脆弱性。可以认为,《我们骑鲸而去》进一步向读者呈现了人类在桃花源生存状况的一种可能。小说中的三位主人公代表了外在力量对岛屿的侵入,他们自身携带的现代社会属性决定了他们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必定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
在荒岛的空间中,主人公无意识的外来理想以及人本质的属性被激发了出来。当主人公为了逃避人群中的扑朔迷离来到岛屿时,他们发现权力依然存在。在荒岛上,权力并不指由社会制度进化带来的社会地位的高低,而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由于社会行为的某种优势所带来的能够影响和控制他人的隐性权力。心理学研究者们从社会认知的角度,将权力看成一种心理状态,认为大多数人在生活中的某个时刻都能体验到权力,当人们体验到权力时,他们的社会认知、社会行为就会受到权力的影响。[4]
权力在三个人物身上来回流动,制约着人物间的关系。当岛上只有“我”和老周两个男士时,我们自然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平衡关系。而这种稳定的平衡在王文兰上岛后被彻底打破。三个人无形中构成了一个小型的人类社会。起初,主人公“我”和老周形成一个和谐整体,以“先到者”的身份殷勤地接待王文兰。随后,“我”和老周逐渐因为王文兰更亲近谁而表现出嫉妒心理,作为力量中心的王文兰显然也感觉到了三人间微妙的关系,权力在小说人物间悄然产生。王文兰上岛后产生了发展旅游业的想法,为了让“我”帮忙向朋友宣传小岛,她隔三差五过来帮“我”收拾房间。这时,“我”成为了王文兰依附的权力对象。但王文兰发现“我”在故意疏远她后,她又开始拉拢老周报复“我”。在三人的情感角逐中,“我”产生了对王文兰既厌恶,又渴望亲近的矛盾心理。最终,王文兰手握的权力促使“我”的行为超越自身意志,“我”不得不向王文兰示好表示屈服。
在一个集体中,各成员经过长期的磨合后会自然寻找到自己的位置。但当稳固的秩序由于外因或内因遭受破坏,各成员的位置受到威胁时,他们就会采取措施来维护自己的地位。小说中的三个人物虽然没有组成一个紧密的契约集体,缺乏强有力的制度也使他们无法形成统一的秩序,但基于人类本能的依附心理,三人无形中已经构成了一个松散的共同体。权力也依附于共同体在三个本为了逃避权力上岛的人物中繁衍出来。在权力的运作下,排挤、孤立的人际互动现象反复上演。心理学家将这种现象定义为社会排挤,即“个体没能得到家庭成员、同伴或某一社会团体的接纳,被排斥在这些关系之外,个体的归属需求受到阻碍的社会现象”[5]981-986。社会排挤将会对个体的情绪造成严重影响。当“我”被孤立在外时,“我”对老周带王文兰出海打鱼的行为感到愤怒进而演变为恐惧。“我”逐渐产生了幻觉,并每天给陌生人打电话,恳请对方不要挂电话。“我”的个体认知在被社会排挤中变异。反过来,社会排斥又将“导致人际关系的重构行为”[5]981-986,“我”因为害怕会发疯,更加殷勤主动地迎合王文兰和老周。小说中的三个人物经过多次人际情感的博弈最终形成某种具有约束力的交易关系,即个体通过满足他人利益来实现个人利益。在交易中,人际关系是三人交易行为的唯一目的,人际情感也因此成为了三人小型社会相互制衡的权力武器。
故事发生至此,已经完全背离主人公上岛的初衷,他们通过操纵自身潜在的权力去追求社会生活和致富梦。“我”最初为了逃避权力的羽翼来到这里,但最后却发现即使没有现代制度的介入,有人类的地方依然会产生权力。
三个人的孤岛遭际和变化揭示了人类渴望的桃花源世界即使在封闭的情况下仍然无法实现,潜藏在人性中的黑暗和对权力的渴望也并不会因为社会环境和制度的变化而消失,反而会在极端状态下被激发出来,人性的弱点是人类无法逃避的现实。
三、以桃花源对抗现代社会的悖论
从最初把荒岛作为建设桃花源的场域,到最后小说中的三个人物最终走向了不同的结局,揭示了现代人以桃花源对抗现代社会的失败。
小说中,作者设置“补给船”这一因素把现代文明的“福音”带到岛上,作者虽然没有大篇幅地介绍与岛屿相对的现代社会的状况,但现代文明却源源不断地通过船只传播、运送到了岛上。“补给船”的出现,从根本上否定了主人公可以通过鲁滨逊式的开发来实现物质自给自足的可能。后期因为寒潮,补给船延期到来,小说人物虽然还保持着面上的礼仪,但他们内心的交锋和状态变化,以及残忍地猎杀不知名的动物,更加证明了现代人对现代生产的依附性。此外,“我”和老周对香烟的瘾癖也展现了人类与现代文明、现代生产的不可分割。香烟是“我们”在原始的荒岛上对抗时间和孤独的丹药,当岛上的香烟全部抽完后,“我”和老周漫岛寻找地上的烟头,最后不得不抽叶子来聊以慰藉,但原始的植物并没有抽烟的感觉。
小说最后,三位主人公陷入与现代文明彻底割裂的绝境中。因为物质缺乏,“我们”面临着未知的恐惧,潜藏在人内心深处的黑暗跃跃欲试。最终,荒凉的恐惧感和游荡的食人欲望促使“我”提前结束与公司的两年合约,跟随终于到来的补给船回到城市。离开小岛后,“我没有再回去过一次,也避免打听关于它的任何信息”[2]157。“我”的决然离去彻底标志了“我”作为一个现代人企图以逃离的方式对抗现代社会的失败。岛屿的生活经历证明了回归是“我”必然的归属,而“我”所指向的则是全体人类。
主人公老周克制住了求生欲望,拒绝吃王文兰煮的无法辨认的肉。在表演完最后一场木偶戏后,他像长出鱼鳞的人类祖先重返大海一样,永远消失了。老周的形象指向了小说标题的“骑鲸”意象,“他身上既有中国古代隐士的高雅与淡泊,又有寻仙般的洒脱与自在,还有那种对赴死的通透与坚定”[6]。正如“我”在小说里所说,“王文兰与我更接近人类”,“老周其实更像那个树上的男爵”。[2]90“树上”代表了人类真正的心灵栖息之所,从城市到荒岛再到潜入大海隐逸正是老周寻找“树上生活”的过程,预示了老周和现代社会及人性变异的彻底割席。老周的隐逸就像“树上的男爵”一样,展现了其对人类无干扰、无限制状态的追求,对人类本质的追求。在现实主义背景下,老周这一人物揭示了作者对于风骨气质的追求,体现了作者对于深处繁复现代社会的人类的反思和忧虑。同时,老周的形象也反衬出了现代人类内心的空洞和思想性的丧失,警示人类,我们将会失去诗意世界。但从现实角度出发,老周最后以带有中国神仙隐逸趣味的方式突然在岛上消失,暗示了人类无法像作者想象的那样重返文明之史,即在现实世界中像老周一样完全否定现实存在,沉浸在虚幻的世界中去寻找诗意的栖居是无法实现的。
和“我”一样更像人类的王文兰最终选择留在岛上。她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在岛上发家致富的愿望支撑她独自留下。在岛上发展旅游业是王文兰的精神寄托,展示出她自身强大的精神内核以及抵御困难的能力,但小说也暗示了王文兰的留岛计划必然走向失败。首先,作者在小说中不断暗示王文兰的愿望天马行空。在不适宜的土地上种土豆和红薯,用海上漂流瓶来宣传小岛旅游,如愚公移山式的积攒礁石、盖石头旅馆等笨拙的行为都决定了王文兰发展旅游业的理想性和她持久留在岛上的不可靠性。其次,王文兰的行为姿态也说明了人类必须在他者中建立自身。王文兰产生建设小岛想法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向他人证明自己。她多次声称自己害怕别人的目光,实际上也体现了她对他者评价的在意。小说中两次提及王文兰的纸巾,她反复强调“这可是质量好的纸巾”,仿佛在他人肯定纸巾同时,她自身也会得到肯定。“他者是塑造稳定自我的根本途径”[7],对王文兰来说,获取他者的肯定是她汲取力量的源泉,因此她也必将存在于人类社会中才能不断确立自己。王文兰的选择代表了试图逃离现实世界去追求人类本质的坚持,但回归社会将会是人类最后的选择。
老周和王文兰皆隐射了人类对于自我价值的追求。但他们命运的梦幻性和不可靠性衬托出“我”回归现实社会、回归群体生活的必然性。孙频在采访中谈到:“我一直试图探讨的一个命题就是关于个体与时代的关系。个体与时代之间的复杂共生关系几乎构成了个体们创伤的源头。”[8]“我”选择逃离到回归的路径事实上就是孙频给出的答案,“我”的命运隐射了全体人类的命运。
四、结语
在荒岛文学《蝇王》中,为了逃避人类战争流落荒岛的孩子,最终被船只带回了正在发生原子战争的社会。《我们骑鲸而去》也呈现出了同样的命运路径。小说中的三人为了逃避现代社会主动奔向岛屿,最终“我”由岛屿回归到恐怖的现代社会,象征了人类终将从“树上的生活”回归现实存在的事实。
作者将人物引入设想的桃花源,却发现即使人类逃到荒岛之上,也无法摆脱激烈地自相鱼肉。岛屿无形中构成了一个小型社会,其所呈现的人类生存状态与相处状态就是人类社会的缩影,是现实社会的隐射。从构建桃花源到逆转式地解构桃花源,揭露岛屿与现实世界的共通性,展现了作者对于桃花源存在的质疑。作者在小说中打破人类桃花源的愿景,意在强调人类与现代社会的共生关系,逃离必然指向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