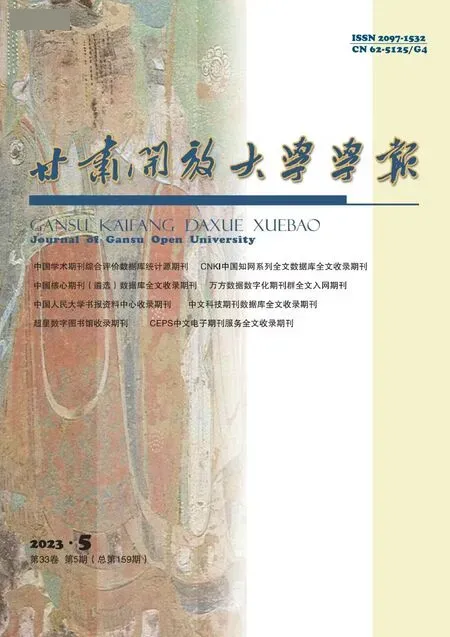欧阳修谪夷心迹变化及影响
宋 蕾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061)
仁宗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上书言事,遭到宰相吕夷简及其党羽的攻击,被贬饶州知州。朝中为其鸣不平者同时被贬,欧阳修愤然而作《与高司谏书》,触怒谏臣高若讷,被贬峡州夷陵令。五月底,欧阳修离开了汴京(今河南开封),顺水路南下,沿汴绝淮,泛大江,于十月底抵达夷陵(今湖北宜昌)。景祐四年(1037)十二月,欧阳修移光化军乾德县令(今湖北老河口),并于宝元元年(1038)三月正式离开夷陵境内,赴任乾德。欧阳修在夷时间仅约一年又三个月,但来夷前后的心态变化十分曲折,故对其初贬经历与达观心态的研究有必要从动态视角加以细察,以期尽可能地接近真实的欧公形象,理解其人格魅力得以名扬后世的内在逻辑。
一、初贬:欧阳修自罪意识的动态变化
史书对欧阳修贬夷陵有明显的誉欧倾向,并清晰记录了当时的舆论走向,如《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西京留守推官仙游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传于时。四贤指仲淹、靖、洙、修,不肖斥若讷也。”[1]欧阳修等人遭贬在士林中引起了广泛的同情,士人群体对高若讷极为不齿。再则,《宋史》中的欧阳修贬谪心态是“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2]10381,似乎欧阳修本人对流贬之事也是淡然自若,志气不减。至清代,袁枚在《谒长吏毕归而作诗》中谈起欧阳修初贬夷陵的心态曰:“欧公贬夷陵,欣然无不可。船载集贤书,梦摇金殿锁。偶参转运庭,伛偻趋而左。黯然神始伤,县令乃是我。”[3]42袁枚认为欧阳修初贬夷陵时“欣然无不可”,直到至荆南参与政务,才有官小而卑的黯然之情。
以上对欧阳修谪夷心态的记载多是一种欣然自若的总体概述,论断颇具一致性。陈湘琳在《欧阳修的文学与情感世界》[4]5中将这种现象阐释为欧阳修的两种形象:一种是作为政治家、经学家、史学家被拔高和褒扬,另一种是被主流文化形态所掩盖的“私人个体”。欧阳修谪夷事件的誉欧现象就是后一种情况,即史书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欧阳修作为“普通人”的情感表现。但如果深入考察欧阳修本人的相关作品,就会发现欧阳修初贬夷陵时在诗文中常以“罪人”自称,实无欣然之意。欧阳修的谪夷心理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需要对当时的贬谪制度、贬谪路途、交往情况及其思想状态进行深入分析,才可观照欧阳修谪夷经历的真实心态和具体影响,故对其初贬心态不宜概括论之。
首先,从宋代制度层面来看,欧阳修被贬夷陵是其仕途中的第一次重大挫折。欧阳修在仁宗天圣八年(1030)考取进士,先授西京留守推官,后改任馆阁校勘,直至被贬夷陵令。按照北宋前期的官制设计,入馆阁者,必须是进士出身,且“一经此职,遂为名流”[5],这说明欧阳修的政治出身极佳,位列清要,前途十分光明。贬谪制词中记载了欧阳修的官职信息:
敕镇南军节度掌书记、宣德郎、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馆阁校勘欧阳某:向以艺文,擢参雠校,固当宿业,以荷育材。近者范仲淹树党背公,鼓谗疑众,自干典宪,爰示降惩。尔托附有私,诋欺罔畏,妄形书牍,移责谏臣。恣陈讪上之言,显露朋奸之迹,致其奏述,备见狂邪。合置严科,用警偷俗。尚轸包荒之念,祗从贬秩之文。往字吾民,毋重前悔。可降授守峡州夷陵县令,替刘光裔,今年七月成资阙,散官如故,仍放谢辞。[6]2599
欧阳修遭到了降官出外的处罚,由京朝官贬至下县县令,且谪地偏远,贬途险恶,所以欧阳修受到的政治打击是比较大的。这也是他第一次在政治斗争中遭遇贬谪,自谓“天子以有罪而不忍诛,与之一邑”[6]995,意为获罪出外之臣,满怀对宦途险恶的戒惧和自省之心。
贬谪途中,欧阳修以罪人自居,并对被贬地夷陵展开了悲观的想象。景祐三年(1036)八月十一日,欧阳修一行抵江州(今江西九江),他在游琵琶亭时想到了同为谪臣的白居易,《琵琶亭》诗云“乐天曾谪此江边,已叹天涯涕泫然。今日始知予罪大,夷陵此去更三千”[6]801,哀叹自己的贬谪之路竟然比白居易还要遥远,内心颇为凄怆。此后,他还说道:“三峡倚岧峣,同迁地最遥。”[6]170与一同被贬的余靖和尹洙相比,贬地夷陵更为偏远。在两番对比中,欧阳修在途中多次悲叹谪地偏远,内心也变得更加凄惶。
九月十四日舟次建宁(今湖北石首),欧阳修收到了丁元珍的书信,在给丁氏的回信中他联想了郑瞻入鲁的悲惨经历,将其置于己身:
修之是行也,以谓夷陵之官相与语于府,吏相与语于家,民相与语于道,皆曰罪人来矣。凡夷陵之人莫不恶之,而不欲入其邦......幸至其所,则折身下首以事上官,吏人连呼姓名,喝出使拜,起则趋而走,设有大会,则坐之壁下,使与州校役人为等伍,得一食,未彻俎而先走出。上官遇之,喜怒诃诘,常敛手慄股以伺颜色,冀一语之温和不可得。[6]995
欧阳修虽为谪臣,但仍是夷陵县的亲民官,掌管着一县之民政。在此职权下,欧阳修却想象县民称自己为“罪人”,厌恶并排斥自己来到县邑境内,可见其悲戚与自伤。欧阳修的悲观想象一方面是对贬途及未来生活的焦虑和担忧,另一方面则是对贬官境遇的清醒认知。
且为政者之惩有罪也,若不鞭肤刑肉以痛切其身,则必择恶地而斥之,使其奔走颠踬窘苦,左山右壑,前虺虎而后蒺藜,动不逢偶吉而辄奇凶,其状可为闵笑。所以深困辱之者,欲其知自悔而改为善也,此亦为政者之仁也。故修得罪也,与之一邑,使载其老母寡妹,浮五千五百之江湖,冒大热而履深险,一有风波之厄,则叫号神明,以乞须臾之命。[6]995
他在给丁元珍的信中说道,官员有罪,如果没有遭受肉体的刑罚,那么一定会被贬到穷山恶水,在危险困厄的环境中使其自我悔恨和改正。欧阳修想象自己将遭遇各种折辱与困境,心中也早有“故修之来也,惟困辱之是期”的心理准备。加之此前又有“天子以迕意逐贤人”的犯上言论,故欧阳修初贬夷陵时内心惶恐不已,只能谦卑地屡言自幸。文曰:“故其受命也,始惧而后喜,自谓曰幸,而谓夷陵之不幸也。夫有罪而犹得邑,又抚安之曰无重前悔,是以自幸也。”他甚至表露出自悔自咎的倾向,谓“所以困辱之如此者,亦欲其能自悔咎而改为善也”[6]995。可以看出,欧阳修在此文中的自罪意识中还伴随着自悔改善之意,而这两种认识都建立在认同“为政者之仁”的基础上。所以,欧阳修作《回丁判官书》时,回信对象表面是丁元珍,实则还兼顾了皇帝及在朝掌权者,那么此信可能是一种有意为之的官方表态,或者表现出对现存政治运转规则的妥协。这也说明古代士人在绝对权力压迫下自我意识难免会产生扭曲和钝化。
但欧阳修诗文中表现出来的“罪人”态度值得再辨析一二,即欧阳修遭贬后的罪人心态到底是对皇权威势的屈服,还是对自己直言行为的自悔?欧阳修九月十四日在建宁作《回丁判官书》时,对此次贬谪还有些许惊惶,流露了示弱倾向,全然以罪臣自居。九月下旬,欧阳修留滞江宁十余日,参拜了荆湖北路转运使,此间所作的《与尹师鲁第一书》却已用平和的口吻谈及自己的处境,直言无惧无悔,还提出了对谪臣心态的代表性见解:
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戚戚之文。[6]997
欧阳修对前世谪臣抵达贬所后多作穷愁哀戚的文章,表示出不可取的态度,并告诫同时被贬的余靖和尹洙不要作戚戚之文,应当泰然处之,一改在前书中的自疑自悔态度。
两信间隔虽短,但欧阳修从自疑自悔到泰然处之的态度转变其实并不突兀。首先,从北宋前期的政治文化环境来说,庆历新政的核心人物范仲淹已经在仁宗前期的政坛崭露头角,在士大夫中间也享有盛名,彼时砥砺名节,敢于直言的社会风气已然初步成形。故欧阳修遭贬,于人无愧,于节无毁,被贬后不仅有苏舜钦、尹洙等人的支持和劝慰还有社会舆论的同情与维护,如蔡襄诗作的广泛流传以及峡州诸官的礼遇。其次,从现实的层面讲,欧阳修南下之途一路顺遂,沿线的险滩难路皆顺利通过,家中老小安然无恙,内心稍觉安慰,凄惶之意逐渐平缓。行至建宁县,夷陵府衙遣人来接应,“言文意勤,不徒不恶之,而又加以厚礼,出其意料之外,不胜甚喜”。说明之前的悲观想象并非现实,欧阳修对此充满了意外之喜,不再有前途未卜的焦灼。再次,欧阳修行至荆南,“昨日因参转运,作庭趋,始觉身是县令矣”。进入峡州境内后他开始介入官场运作,卑官庭趋的境遇也使他逐渐无暇沉浸在被贬的哀戚情绪中,转而积极面对现实,其理性务实的精神迥异于一般谪官。最后,从思想方面讲,欧阳修服膺儒家思想,追求“士志于道”的人格理想,有着积极的反思与自省能力,“路中来,颇有人以罪出不测见吊者,此皆不知修心也”[6]997。南下途中遇到的一些故旧亲友对其行为表示不解,这促使他对自己的行为和态度进行深度自省,故在给尹洙的书信中借由对世风沈默的批评,重申了不自疑的态度,强调自己“士有不死之义”的志向。所以,欧阳修态度的转变固然有诸多现实因素,但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内心对直道言事的无悔,但这种服法不“认罪”的精神状态,形成了一种身心错位的内在矛盾,使欧阳修时常在穷与达中感到无所适从。
总之,史书上欧阳修平和自若的贬谪心态并非一以贯之。他在抵达夷陵前就有比较复杂的心理活动,其贬谪心态的变化在诗文中体现得更加细腻与真实。从面对制词罪幸交织的惶恐,到荆江途中的悲观想象,再到荆南后的冷静自省。欧阳修这一情感态度的变化过程,既伴随着对皇权威势的体认,还有对士人志道的坚守。
二、西陵长官:欧阳修对罪人身份的自赎与治愈
景祐三年(1036)十月,欧阳修抵达夷陵境内。正如上文所述,抵达夷陵前,欧阳修经过了一轮反思,从全民共弃的悲观想象中冷静下来,理性接受了现实,但心情和身份转变仍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因此其“罪人”心态也有了新的特点。
首先是对交游的书写,融洽的人际关系抚慰了欧阳修落寞的心灵。景祐三年(1036)十月二十六日,欧阳修抵达了夷陵,并受到上官朱庆基及同僚的同情与礼遇。朱公与欧阳修相识于汴京,为照顾旧友,特地为欧阳修盖至喜堂,还“日相劳慰”。在朱公的帮助下,欧阳修在夷陵正式安顿下来。除了上官朱公外,欧阳修在夷期间最重要的知交就是丁宝臣。宝臣字元珍,时任峡州推官。欧阳修在夷陵期间,与丁元珍共游山水胜迹、古刹禅院,以疏解心中闲愁。他们在冬日共游龙兴寺、东山寺,欧阳修作有《龙兴寺小饮吴表元珍》,诗曰:“一樽万事皆毫末,蜾蠃螟蛉岂足云。”[6]172两人在寺中互推杯盏,小饮怡情,疏旷不已。除游寺赏景外,欧阳修还常与元珍一同探讨夷陵的风候习俗,分享自己“荆楚先贤多胜迹,不辞携酒问邻翁”[6]174的悠闲生活,甚至雪后初霁,新开棋轩,种了两株楠木也要与丁元珍絮叨一二,足见他们来往之密切。同为异地迁客,丁元珍与欧阳修有着深刻的情感共鸣,他的陪伴也极大地安慰了欧阳修远谪夷陵产生的寂寞和失落。此外,欧阳修还与处士何参,推官朱处仁相处甚密,还与慕名求学的荆南乐秀才讲论文道关系,给谢伯初写诗集序文,可见其在夷的人际关系甚为融洽。值得玩味的是,至喜堂建成后,欧阳修再言谪罪时,心境已经明显不同。其在《夷陵县至喜堂记》中写道:“夫罪戾之人,宜弃恶地,处穷险,使其憔悴忧思,而知自悔咎。今乃赖朱公而得善地,以偷宴安,顽然使忘其有罪之忧,是皆异其所以来之意。”[6]563他颇为促狭地谈起了自己的贬谪经历,表达了从有罪困辱到顽然忘罪的欢喜之意。
其次是对夷陵山水的描摹与吟咏,夷陵的奇山异水纾解了欧阳修的满腹忧思。欧阳修沿水路一直南下,浪小路平,至峡州奇山异水接踵而来,令欧阳修称道不已。他在《黄杨树子赋并序》中以物寓志,托物言情:“夷陵山谷间多黄杨树子,江行过绝险处,时时从舟中望见之,郁郁山际,有可爱之色。”[6]253进入夷陵江面上后,欧阳修发现此地多黄杨树,它们在绝壁穷僻处独立生长,郁郁苍苍,枝叶繁茂,见此景不禁称道“负劲节以谁赏,抱孤心而谁识”,借此抒发自己在险恶的官场上不改初衷的意志。夷陵的奇山异水,秀美风景使欧阳修在闲愁中度过了相对美好的时光,他还写下了著名的“夷陵九咏”,即《三游洞》《下牢溪》《虾蟆碚》《黄牛峡祠》《松门》《下牢津》《龙溪》《劳停驿》《黄溪夜泊》。览胜中的欧阳修暂时摆脱了罪人的惶恐与忧思,反而通过夷陵风物的坚劲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意志和立场。景祐四年(1037)三月,欧阳修曾赴许昌娶亲,归夷途中写道:“闻说夷陵人为愁,共言迁客不堪游。崎岖几日山行倦,却喜坡头见峡州。”[6]169此时欧阳修已能用轻松的笔调写出归夷之喜,殊无谪官的窘迫之态,可见其心态变化之大。夜泊黄溪时,他又写道“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6]168,已是处之泰然,逆境生乐的旷达性情。
再次是欧阳修努力通过坚守政治理想实现对罪臣心态的自我救赎。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对夷陵风土人情的关注。作为夷陵亲民官,欧阳修在诗文中提及夷陵落后的民风颇有不满之处:“楚俗岁时多杂鬼,蛮乡言语不通华。”[6]175楚地与中原文化的交流还相对有限,在偏远的夷陵还留存着楚地古时候的巫风文化,百姓多不通文字,实在难以沟通。其二,勤勉政务,无不躬亲。在《与尹师鲁第二书》中,欧阳修提到了在夷的公务情况,“夷陵虽小县,然争讼甚多,而田契不明。僻远之地,县吏朴鲠,官书无簿籍,吏曹不识文字,凡百制度,非如官府一一自新齐整,无不躬亲”[6]999-1000,据《宋史》记载:
方贬夷陵时,无以自遣,因取旧案反覆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于是仰天叹曰:“以荒远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尔,遇事不敢忽也。学者求见,所与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凡历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故所至民便之。[2]10381
可见,欧阳修虽是贬官之任,但仍然负责地履行着职事官的职责。吏曹不识文字,不通制度,他便亲自办理,纠正各种冤假错案。他力倡宽简的政治原则,教导士人以政事为己任,造福于民,做到了身在其位,以谋其职。这使欧阳修超越了古代卑臣谋食的庸俗境界,真正实践了儒家士人以民为本的政治理想。
由欧阳修贬夷期间的交游、山水和政事书写可知,欧阳修已从罪人身份中解脱出来,逐渐适应了西陵长官的身份,并在精神上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纾解和宽慰。但不可忽视的是欧阳修心中的寂寞与失落之意从未消失。
初至夷陵,欧阳修就有了思归之意,曾写诗云:“时节同荆俗,民风载楚谣。俚歌成调笑,摖鬼聚喧嚣。得罪宜投裔,包羞分折腰。光阴催晏岁,牢落惨惊飙。白发新年出,朱颜异域销。县楼朝见虎,官舍夜闻鸮。寄信无秋雁,思归望斗杓。须知千里梦,长绕洛川桥。”[6]170夷陵地僻,风俗怪异,欧阳修身为外来迁客,颇难适应风土习俗,只能借诗歌聊以抒情。再想到自己与知交亲友相隔天涯,音信茫茫,而往事历历在目,却不知相见何期,思归之意愈加强烈,故常在诗中流露出寂寞之意,甚至在而立之年就生出了华发之叹,所谓“西陵长官头已白,憔悴穷愁愧相识”[6]736。时节气候的变化也加深了欧阳修的寂寞情绪,他曾写诗云:“夷陵寂寞千山里,地远气偏时节异。”[6]11此时欧阳修的诗文中也多有衰翁、病翁之语,如“时扫浓阴北窗下,一枰闲且伴衰翁”[6]173,又如“山城寂寞少嘉客,喜见琼枝慰病翁”[6]171。再如名篇《戏答元珍》曰:“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夜闻啼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曾是洛阳划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6]173此诗以“天涯”比夷陵之僻,颔联虽写物华生气勃勃,但末二联又不可避免地露出几分郁气,此诗情感可谓委婉顿挫,欧阳修欲平愁绪却不能的纠结与努力尽付诗中。
闲逸的生活、诗酒的欢娱和山水的奇美始终无法使欧阳修的心灵得到真正解脱,这些调适方式只能帮助他摆脱罪人身份的阴影,完成“西陵长官”这一新的身份认同,而实质上并不能达到此心淡然的超脱之境,所以欧阳修贬夷期间的“达观”可能仅仅是一种间歇性的情绪治愈。但要注意的是,这种治愈仍是欧阳修主观努力的结果,即欧阳修善于借助现实环境中的积极因素,用理性的态度去调适感性的彷徨与失落,为自己的存在寻求价值,这种思维方式也深刻影响着他此后的处世态度。
三、思夷:欧阳修对贬夷经历的反省与超越
景祐四年(1037)十二月,欧阳修移光化军乾德县令,宝元元年(1038)三月正式离开夷陵境内,赴任乾德。此后,他在人生的各个阶段对夷陵的山水、风俗及生活都有不同程度的回忆。欧阳修在夷期间时常在寂寞与自解中沉潜,而离夷后,思夷逐渐变成欧阳修仕宦风浪中的精神浮木。
离夷后,欧阳修在怀夷中进入了思山忆水的悟道境界。赴任乾德不久,欧阳修就在《离峡州后回寄元珍表臣》中说道:“经年迁谪厌荆蛮,惟有江山兴未阑。”[6]176欧阳修虽然对夷陵落后的风俗多有不满,但十分留恋当地的山光水色。此时欧阳修追忆夷陵山水之乐,实际上是在表达贬谪风波后的释怀和坦然,虽然还未回到朝中,但其心态已经趋向稳定与平和。宝元元年(1038),欧阳修在乾德任内写的《与梅圣俞四十六通》(七)中道:“修昨在夷陵,郡将故人,幕席皆前名,县有江山之胜,虽在天涯,聊可自乐。”[6]2447欧阳修在释怀的基础上还构建了更加积极的贬谪回忆录,并点出了实现超越心态的指南,即山水之乐是治愈贬谪伤痛的良药,纵在天涯之远,亦不妨有自娱取乐的达观心态。宝元二年(1039年)冬,在《送琴僧知白》中他再次回忆起贬夷生涯,“二年迁谪寓三峡,江流无底山侵天。登临探赏久不厌,每欲图画存于前”[6]746。两年贬谪生活,欧阳修在游山乐水中逐渐忘却了罪臣之身,主动寻求山水之乐,吟咏其美,陶冶情怀,探索如何解开自己的心灵枷锁。可见,离夷后,欧阳修通过对夷陵山水览胜的回忆逐渐完成了对人生经历的思索,将山水之乐与体道之思合二为一,以胜景幽赏之乐充实着自己的精神世界。如果说贬夷期间的山水吟咏尚是欧阳修排遣寂寞的一种方式,那么离夷后的山水之思就掺杂了对志道的寄托和对人生境界的追求。
欧阳修对穷达之遇和苦乐心境的辩证思索也体现着贬夷经历对他思想的深刻影响。庆历五年(1045)春欧阳修权知成德军事(今河北正定)。二月韩琦、范仲淹、富弼等相继罢官外出,欧阳修上疏辩诬未果,萌生退隐之心。他在给薛夫人的寄诗中写道“却思夷陵囚,其乐何可述。”[6]32在《班班林间鸠寄内》中欧阳修对谪夷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回忆和反省,“一身但得贬,群口息啾唧。公朝贤彦众,避路当揣质。苟能因谪去,引分思藏密。还尔禽鸟性,樊笼免惊怵。子意其谓何,吾谋今已必”[6]32。此年欧阳修因“张甥案”落龙图阁直学士,降知制诰,出知滁州。在《滁州谢上表》中欧阳修道:“若臣身不黜,则攻者不休,苟令谗巧之愈多,是速倾危于不保。必欲为臣明辩,莫若付于狱官;必欲措臣少安,莫若置之闲处。使其脱风波而远去,避陷阱之危机。虽臣善自为谋,所欲不过如此。”[6]1321可见,再次被贬的欧阳修已经将贬谪作为保全自身,脱离风波的方法,而不再视其为一种屈辱的惩处。更难得的是,欧阳修虽有明哲保身和归隐之意,但他始终不忘士大夫的责任。嘉祐年间欧阳修在《与薛少卿二十通》(九)中再次审视了自己的贬夷心态,书云:“某向在夷陵、乾德,每以民事便为销日之乐。苟能如此,殊无谪官之意也。”[6]2507这种造福于民,与民为乐的思想与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的忧乐观念显然是一以贯之。欧阳修这种进一步“扬弃悲哀”[7]的宋人性格特质深刻影响了宋代谪臣的心态与处世,亦为后世称道不已。
欧阳修在《有美堂记》中明确认识到达者之乐难得,而穷者更易有取诸山水的愉悦之赏,曰:“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潜之士、穷愁放逐之臣之所乐也。”[6]585嘉祐五年(1060)夏秋间,欧阳修在《奉达原甫见过宠示之作》中写道:“吾生少贱足忧患,忆昔有罪初南迁。飞帆洞庭入白浪,堕泪三峡听流泉。援琴写得入此曲,聊以自慰穷山间。中间永阳亦如此,醉卧幽谷听潺湲。自从还朝恋荣禄,不觉鬓发俱凋残。”[6]125此时欧阳修几经升贬,非议缠身,虽官至翰林学士,入值禁中,却仍然难忘三峡山水的幽美。他还与还朝后的纷繁生活作了比较,更加怀念在夷游景弹琴的雅趣生活,加之身体衰病,不禁起了鬓发凋残之叹。熙宁二年(1069),欧阳修六十三岁,出知青州,筑宅于颍,致仕之意愈强,谓“老年世味益薄”。他在《书琴阮记后》中透彻阐释了穷达之乐的差别,正是经透世事的肺腑真知,“官愈高,琴愈贵,而意愈不乐。在夷陵时,青山绿水,日在目前,无复俗累,琴虽不佳,意则萧然自释。及做舍人、学士,日奔走于尘土中,声利扰扰盈前,无复清思,琴虽佳,意则昏杂,何由有乐?乃知在人不在器,若有以自适,无弦可也”[6]2575。以弹琴为例,欧阳修进一步阐明了谪臣的穷途之乐易得,而身处高位后自在心境难得,且多尘俗负累的拘束之感。而欧阳修借夷陵山水抱怨声利之扰时,我们似乎也能品尝出几分甜蜜的烦恼和无奈的喟叹,但不管如何夷陵山水在这种对比中也变得更加脱俗了。
以上对忧乐之念的辩证思考表现出欧阳修对谪夷经历的反省到了一个更高的思想境界,由平和地接受贬谪,到理性思考荣辱境遇对个体生命的意义,欧阳修在忆夷中自觉反思着在纷繁尘世中逐渐迷失的自我意识。不可否认的是,欧阳修晚年的忆夷诗文明显有美化过往之嫌,虽然可能遮蔽了当时的真实情态,但这种积极的回忆建构正体现了欧阳修笑对苦难与挫折的人生智慧,可以说初贬夷陵对欧阳修心态的影响是深远而持久的。
四、先行者:贬谪谱系中的欧阳修及其影响
欧阳修在宋代贬谪谱系中没有苏、黄醒目,其贬谪经历也比不上元祐文人艰难深刻,但对北宋超越型贬谪文人的心态有一定的引领作用。尚永亮和钱建状在探讨贬谪文化在北宋的演进时就提到:“至于欧阳修之数次遭贬,也一定程度地展示出漠视人生困境的旷达情怀。其被贬夷陵后作诗有云:‘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颇能从一己之悲愁中超拔出来,将贬谪视为因祸得福的机缘。这样一种心态,上承白居易,下启苏东坡,而与多数唐人大不一样了。事实上,正是因为宋代贬谪文人先行者在人生精神上的这种奠基,元祐时期的苏轼、黄庭坚诸人才得以发扬蹈厉,将面对人生困境的旷达进一步发展定型为一种内涵更丰富的超越意识。”[8]具体而言,欧阳修进一步探索了文人贬谪后的超越路径,一边继以山水之乐,生活之趣来消解忧愁苦闷,一边却是对政事人生毫不懈怠,极为理性和务实。欧阳修的可贵在于他善于自解,且擅长反思,有一定的主体意识,故能主动酿造一种平和心境来面对现实,接受挫折,他对贬夷经历的书写与回忆即是如此。陈湘琳也谈到宋代文人对谪居心态的消解与调适[4]135,不应当从王禹偁开始,事实上是欧阳修先以务实的理性和平易的精神来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为宋代贬谪心态的整体变化找到了基调,此论不假。然而毕竟是先行者,欧阳修贬谪心态在超越事实上还未达到苏轼贬儋时的超脱境界,醉翁仍时常在愁与乐中沉潜,理性与现实错位带来的退隐回避思想似乎更加强烈,故其文学风格虽得平易风神,却难言出苏轼“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9]5130的轻快澄明。
此外,从地域视野出发也能显示欧阳修贬谪心态的特殊性与价值影响。苏轼曾作《夷陵县欧阳永叔至喜堂》,诗云:“谁知有文伯,远谪自王都。人去年年改,堂倾岁岁扶。追思犹咎吕,感叹亦怜朱。”[9]111此言有为欧公不平之意,其后又有“故老问行客,长官今白须”的问答,显出一片温厚和谐,可见主官欧阳修在夷陵的民心和威望犹存,也透露出了苏轼对欧阳修贬谪时仍能与民为乐的敬服之情。黄艳《宋代三峡诗研究》中也注意到“欧阳修是宋代三峡贬谪文化发展流变中的关键性人物,他使三峡贬谪文化的基调由激愤不平、消极哀怨转变为平和沉稳、积极乐观”[10]。其实这一变化不独在宋,明清人也多得欧阳修之沾溉,张邦奇《夷陵山行至九湾绝粮》云:“路险仍遭雨,人疲又绝粮。山花空的历,我马自玄黄。草屋家家破,秋田处处伤。昔年羁宦者,青史著欧阳。”[11]诗人在人生困厄,旅途艰辛之际,至夷陵思及欧阳修,总能在困境中获得一些情感共鸣和精神力量。清代光绪年间的李稷勋在《夷陵岁晏行寄赠陈学士韬庵前辈并柬损庵左丞》中云:“去年珂马喧京洛,春风凄咽东华钥。今年闲对夷陵花,岁晏天寒意萧索。夷陵城郭连江湄,欧九当年此咏诗。青苔遍踏下牢渡,元白苏黄各一时。我来苦被浮名误,山川文藻今非故。转石时牵瀼口船,堑山尽斫峡州树。”[12]诗人去年尚在京洛繁华之处,如今却只能闲对夷陵花,其心态与欧公当时颇有相似之处,正是汲取了欧阳修、苏轼等人以山水自娱的人生态度,才令诗人自觉发出“我来苦被浮名误,山川文藻今非故”的感想。可见欧阳修的人生态度对贬谪文人确是一种救赎,历代贬谪官吏路过旧址时心绪便格外不同。欧阳修之后的夷陵虽然仍是艰苦的贬所,但其境况与欧阳修当时面临的窘境与荒芜已有很大不同,而最大的不同就是欧阳修的人生经历能够给予谪官们些许安慰。诗人们在追慕文宗遗风,履迹旧址中,领悟其旷达处世的人生态度,并引为异代知音,聊以慰藉不平心绪。
贬夷经历对欧阳修而言意义极大,其心迹书写随其人生经历的变化而不断深化,体现了欧阳修可贵的自省精神。所谓“庐陵事业起夷陵”,夷陵作为欧阳修平易文风的成熟地,与民为乐思想的萌发地,也是欧阳修挺立士大夫人格的一次主观尝试。首先,欧阳修贬夷心迹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对贬谪的思考深入到了上位者的动机与士人志道的坚守之中,自觉在思想层面进行反思和超越,这使得士人在穷僻贬谪之地,仍有一片修行己道的灵台方寸山。从谪夷时的窘迫,到谪滁忆夷时的旷达,欧阳修完成了由衰翁、病翁向醉翁的形象转变与自我塑造。其次,欧阳修贬夷心态的变化也体现在其平易畅达的文学风格之中,即穷贬则不必悲伤作戚戚之语,显达也不必欢喜有轻浮之辞,并以至喜亭、至喜堂为中心留下了极具代表性的诗文作品。至此,欧阳修与史书中“志气自若”的形象似乎别无二致,但须注意到史书中的贬谪记载和诗文中的贬谪心迹书写,一种是结果论断,一种是过程呈现。惟有深入后者才能理解欧阳修情感与思想的变化曲线,还原出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欧公形象。诗文中的心迹书写对史书记载也是一种印证,惟有两者合一,才可能出现文学史上人所共称的“文章道德宗师”。再次,欧阳修乐观平易的精神对宋代以来的贬谪文人心态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也赋予了夷陵山水以浓厚的人文气息,产生了一定的文化影响力,这也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