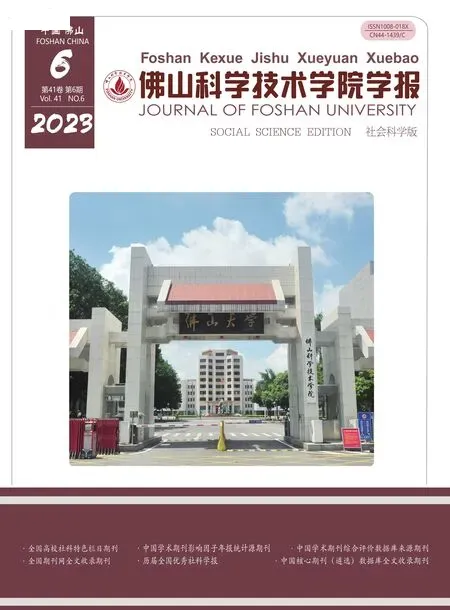董仲舒孝论新探
——以《孝经》为线索
于 水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学院,北京 100872)
从整体上厘清并分析《春秋繁露》中与“孝”关联的文句,可见其基本围绕《孝经》展开。既有对董仲舒孝论的探讨往往集中于以天道观为中心进行呈现,侧重以董仲舒天人观念来谈,也即“以天论孝”。[1]这样的论述无疑是准确和精当的,但很容易导致在具体文本解读过程中对《孝经》与《春秋》以及董仲舒孝论之间内在关联的忽视,①似乎董仲舒是为引而引,为“孝”而“孝”,结果便是对董仲舒基于《孝经》所发挥孝论的关注不足。[2]如果转换角度,以《孝经》为线索,从文本出发,找寻董仲舒孝论基于《孝经》的发扬之处,自然可以更全面地诠释董仲舒的孝思想。此外,孝论还是董仲舒天人观念落实于国家统治构想的关键环节,因此无论是讨论其哲学思想中的天人观还是政治观,都需要重视董仲舒的孝论,并关注《孝经》与之关联的紧密。
一、董仲舒孝论与《孝经》
《孝经》在儒家经典文献中最早以“经”为名,[3]76是关联“孝”的重要儒家典籍。关于《孝经》的作者与具体成书年代,历来众说纷纭,但可以明确汉代已有确定的《孝经》文本,并在国家统治与伦理教化的层面都发挥着巨大作用:汉代提倡孝治,统治者尤其重视《孝经》,皇帝谥号基本带有“孝”字。汉文帝时首次设立《孝经》博士,[4]120至武帝即被罢,原因绝非其落后于时代,反倒是“受经与不受经者皆诵习之,不宜限于博士而罢之者也”,[5]178这就是说,《孝经》在汉武帝时的普及程度已经相当之广,甚至无需专设博士来传诵学习。董仲舒作为西汉最重要的哲学家与今文经学家,其思想与学说又属汉武帝时最受重视,对当时国家统治与政策导向产生较大影响。由此可简单推测董仲舒孝论与《孝经》的相关性,对他的经典著作做梳理便更加可以验证这一猜想:《春秋繁露》两次明确提到并引用《孝经》,分别为《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篇(“《孝经》曰:‘事父孝,故事天明’”)和《五行对》篇(“《孝经》曰:‘夫孝,天之经,地之义’”)。又如《为人者天》篇虽未明言《孝经》,却直引其中原句“先之以博爱”“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等,并且《深察名号》篇从天子至庶民之孝的描述也与《孝经》从《天子章》至《庶人章》比较类同,可以认为是《孝经》内容的改写。此外,董仲舒著名的《天人三策》同样援引《孝经·圣治章》“天地之性人为贵”一句展开具体论述。由此可知,董仲舒不但对《孝经》非常熟悉,其关于“孝”的表述与展开也和《孝经》有着紧密的联系。
更进一步来看,《孝经》之“孝”不单单指向家庭生活中父母子女的爱敬之孝情与孝行,还意味着政治生活中促使家国和谐的孝治。这其实正与董仲舒的思想相契合,也是他多次引述、改写《孝经》的原因所在。从其文本来看,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孝接天人。天有四时五相对应五行,父生子、父养子便如木生火,火生土等一样自然,地义顺承天经,以风雨等表现四时五相;其二,孝以安国。君王均是天之子,传位于其子以及不同朝代的更替,都是对孝的顺应;先王以孝治国,君主应在目、耳、心等方面形成榜样以达成教化。
二、孝接天人
董仲舒孝论最鲜明的特点就是确证天命在人身的赋予而表现为孝,明确人道与天道的直接对应,前者是对后者的顺应和外化表现。这些表述在《孝经》中也有着清晰体现,经过分析可见董仲舒孝论与其承继关系:在《孝经》的整体论述中,《开宗明谊章》开门见山,指出孝的重要意义为“至德要道”,它不但是人诸多品德的根本,还是治理国家的最好方法。每个人生来即有父母,这是身处现世生活最为确定的一点。故家庭因素是国家中规范个人行为的起点,并且应当是最重要的、自上而下贯彻的、无一例外的衡量标准。想要达成这样的目的,孝一方面不是虚无缥缈的神秘谕令,另一方面也不是生硬的法律条文,而是有始有终的切实规范。在其之下,人人依孝行事,个体的行为就必须考虑其背后的家庭与宗族,《天子章》至《庶人章》便对此进行具体说明。《三才章》承此并展开后续论述:一方面,它再次概括孝的重要性,孝不但是“至德要道”,还是“天经地义民行”,人们循孝而行,就是承顺天意,彰显地利;另一方面,其之后的各章便是孝在政治上的具体展开,如总体而言的“孝治”,和以周公为代表的、更进一层的“圣治”等。
董仲舒以《三才章》所论孝乃“天经地义”为其论述起点:
河间献王问温城董君曰:“《孝经》曰‘夫孝,天之经,地之义。’何谓也?”
对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木为春。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长之;父之所长,其子养之;父之所养,其子成之。诸父所为,其子皆奉承而续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尽为人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观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经也。此之谓也。”
王曰:“善哉。天经既得闻之矣,愿闻地之义。”
对曰:“地出云为雨,起气为风。风雨者,地之所为。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于天。命若从天气者,故曰天风天雨也,莫曰地风地雨也。勤劳在地,名一归于天,非至有义,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谓大忠矣……忠臣之义,孝子之行……此谓孝者地之义也。”[6]314-316
河间献王为刘德,是汉景帝次子,他对儒学典籍的收集与整理有着不小贡献,今文本《孝经》也是经他之手进入朝堂,可推知他对这些经典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因此当他向董仲舒提问,得到的回答自然也不是泛泛之谈,而有着深刻的理论内涵。董仲舒首先论讲“天经”与“孝”的关联,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渐次相生,对应于四时,木即春,火即夏,土即季夏,金即秋,水即冬。五行的顺次传递,就像春夏秋冬的运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一样自然。人在天地间生活,自然也遵循着这种规律,生者为父,被生者为子,父生子长,父长子养,父养子成,其实都是在表述人子对人父的顺承,儿子需要像四时五行的必然传绪一般,不轻易违背父亲的意愿,继承其父的志业乃至推之光大,父传子继,这就是“孝为天经”的含义,这些解释与《孝经》此章的内容基本是相合的。至于“孝为地义”,董仲舒则采纳阴阳尊卑之说进行发挥,天阳地阴,天尊地卑,因此发生在大地的如风、雨等自然现象,其根源在于有天,地只是承接天意并表现出来,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都是下事上,就像地事天一样,所以说“孝为地义”。显然,董仲舒在这里对孝的内涵进行拓展,在他看来,孝之所以具备“天经地义”的广大内涵,原因不仅在于它是人生来即具与父母之间的自然感情,还在于它是政治秩序构建的基本准则,人子顺应其父为孝,人臣顺应其君为忠。与此类似的表述在《孝经》中同样也存在,概括而言即“移孝作忠”。《孝经·士章》载:“故以孝事君则忠”,强调士人可以借助事父之孝来形成其在政治生活中的行为规范,从而获得相应的俸禄与爵位来更好地侍奉父母与显扬家族。董仲舒通过阴阳尊卑之说将这层含义蕴涵于对此句的解释之中,由此可见他基于《孝经》的创造性发挥,而在《立元神》篇他的描述就更加详细和具体:
何谓本?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礼,不可一无也。
无孝悌则亡其所以生,无衣食则亡其所以养,无礼乐,则亡其所以成也。三者皆亡,则民如麋鹿,各从其欲,家自为俗。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虽有城郭,名曰虚邑。[6]168-169
天、地、人相互连通,是维系整个世界万物的根本。“天生之以孝悌”,也即“孝”为“天经”,地顺应“天经”,孕育万物,是其有义。人受二者滋养,通过礼乐来表现自己对“天经地义”的承接,才能够成人。三者缺一不可,并且人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如果人不行孝悌,那便无法认识到人能够得到生命的原因:人因天赋其生命于父母而得生;不以衣食供养,保全生命的延续,那便是对“地义”的辜负;而如果没有以礼乐对人的行为进行约束和规范,整个社会和国家就没有秩序的构建,会陷入混乱。缺乏对天地人三本的认知,人与其他动物也就没有什么区别,做事没有具体根据,子不从父令,臣不从君令,家国也就只是虚名。因天而行孝,因地而养身,因人而推行礼乐,这就是董仲舒在《孝经》之“孝为天经地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挥。
三、孝以安国
董仲舒直引《孝经》中的《三才章》与《感应章》,两章的关联性本身就比较强,都是赋予“孝”以神秘色彩的抽象表达,不过后者的面向更加广阔,在前者抽象的天人、父子、君臣相接续的表述之外更加关注具体现实政治中孝对于国家统治的重要作用。《感应章》讲明王以孝事父母,使得天明地察,能够感化天地,自然可以感化民众,也就是说这样的做法顺应天经地义,因此可以达成整个国家的上下和谐。首先便从董仲舒于此的引述论起:
尧舜何缘而得擅移天下哉?《孝经》之语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天与父,同礼也。今父有以重予子,子不敢擅予他人,人心皆然。则王者亦天之子也,天以天下予尧舜,尧舜受命于天而王天下,犹子安敢擅以所重受于天者予他人也。天有不以予尧舜渐夺之,故明为子道,则尧舜之不私传天下而擅移位也,无所疑也。儒者以汤武为至圣大贤也,以为全道究义尽美者,故列之尧舜,谓之圣王,如法则之。[6]219-220
董仲舒以一个设问开端,尧舜是上古贤王,同时也是孝子的代表,为什么他们可以将天下给予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他人呢?这是不孝吗?至于汤武,儒者也认为他们也是圣王,但他们却选择将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父亲将自己的最重要的天下托付于儿子,儿子自然不敢有懈怠,谨慎地保有天下并且不会擅自将之给予他人,这显然更契合对“孝”的顺应。董仲舒的说法则对尧舜、汤武之举都进行周圆的解释,“天”将天下给予尧舜,尧舜承接天命为天子,不敢轻易地给予他人,而当为父之“天”决定不将天下给予尧舜,尧舜不传位于自己的儿子也同样是承顺天命。因此,君王不但是上一任君王的儿子,还是天之子,天下无论是被给予君王之子或是他人之子,都是天意,都是合乎孝的。
董仲舒此说无疑有着较强的现实关怀,也就是说,他论及尧舜、汤武不只是要说明其王位变革与传绪的合理之处,还指向当世汉代帝王之间父子传承的合法性。君王作为天子,无论由于主观还是客观原因有没有将王位传于子,都可以认为这是天命的不同表现,因而如此解释不但可以从理论上较好地回答诸如传位、立太子等敏感的政治问题,同时也留有足够的解释空间和回旋余地。并且从另一方面来看,董仲舒的说法也很好地契合儒家传统之说。例如《孟子》载万章提问,是尧将天下给予舜吗?孟子回答不是,天子不能将天下给予他人,是“天”予天下于舜,“天”虽不言,但会以具体的行为和事实来展示,尧不过是天命的执行者。“天”将天下给予贤人而贤者主政,给予君王之子即其子为王。两说可谓相称,不过董仲舒进一步将“天”与君王以孝进行关联,将之等同于父子关系。“天”作为不言无象的存在,由此便具有清晰的人格神意味。此外,通过如祭祀中的具体事项进一步加强君王与“天”之关联,经由对君王的行为规范的约束而形成天下人的模范,“孝”之为国家根本的意义还在于每一任君王都是天之子,都承接着天命,既要保全“天”所赋予的天下土地与人民,还要时刻谨守相应的行为规范,不超出界限以防惹怒“天”,否则会被回收“天子之位”,君王如果不能形成国家的典范,不但是政治的不善,而且是伦理的不孝。这也可以说是《孝经》内容的体现,例如《孝经》在《天子章》至《庶民章》对分属五个不同阶层的天下人之孝分别做出阐释:天子至尊至高,他的一言一行都受到全天下人的关注,因此除开对于最亲近父母表现足够的爱敬之外,也自然不敢对天下其他人的父母有非礼之举,由此才能够作为天下人的模范而推行德教;诸侯身处高位,只有端正态度,约束举止,保证承继而来的社稷的稳固,促使民众相合才算是尽孝;卿大夫则需要遵循先王所制定的法言法行,在朝堂上表现得合理得体,以此来保有用于家族祭祀的宗庙,使之长久留名为孝;士属于天子、诸侯、卿大夫家族之外的臣子,走入政治生活,以家庭中事父之孝为参考,便能在工作中做到尽职尽责,由此获得一定的政治地位与俸禄来奉养自己的父母与光耀自己的家族;庶人需要做到基本的顺应天时地利,保全其身以恭敬地奉养父母。因此概括而言,虽然不同群体的孝行有着较大的区别,但其核心均指向家族的存续乃至显扬。董仲舒的解释与此大体相类:
故号为天子者,宜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号为诸侯者,宜谨视所候奉之天子也。号为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礼义,使善大于匹夫之义,足以化也。士者,事也;民者,瞑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从上而已。[6]286-287
君王为天子,自然以天为父,侍奉天就要竭尽其孝道,诸侯就应当以天子为参照物,谨慎地效仿其所作所为,虽言君臣之道,其实仍讲尽孝。卿大夫则需要努力培养自己的忠信品德,反复修习礼仪,达到能够感化民众的水准。士人即是从事之官,只需要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侍奉上位者即可。由此可见,董仲舒基本依循《孝经》来建构家国之孝,自天子至庶人形成整体安排。因此,董仲舒以“孝”为国之本还体现在他对君主的榜样与教化作用的强调,这同样是《孝经》的基本主张:
孝弟者,所以安百姓也……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故曰:“先之以博爱”,教以仁也;“难得者,君子不贵”,教以养也;“虽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弟也”。教化之功不大乎?
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故君民者,贵孝弟而好礼义……故曰:“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此之谓也。衣服容貌者,所以说目也;声音应对者,所以说耳也;好恶去就者,所以说心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则目说矣;言理应对逊,则耳说矣;好仁厚而恶浅薄,就善人而远僻鄙,则心说矣。故曰:“行思可乐,容止可观。”[6]319-320
君王以孝悌来安抚百姓,所谓圣人的治道,自然不是以严酷的威严压倒民众,而是通过道德教化来获得人民的信任。“先之以博爱”,就是说天子能够对天下人有着普遍的关爱,以此才能教“仁”;“难得者,君子不贵”则是说虽然以严厉的刑罚和苛政使得民众在表面上屈服,但真正的贤君对此不以为意,而是相反,通过自己行孝示之众人而推展孝治,由此可知何以养民;即便天子亦有尊有先,指向“孝”与“梯”的具体彰显,例如汉代所推行“三老五更”制度,天子需要以事父之礼对待“三老”,以事兄之礼对待“五更”。[7]由此足见教化的功效之大。董仲舒还以心体为喻,君为民之心,民为君之体,君主喜好孝悌、推行礼义,民众自然也会跟从效仿,因此先王才知晓“孝”的教化作用进而推行孝治,这具体表现为衣服容貌的端庄得体、交流应答的从容不虚、自心底对仁厚品德的喜爱以及对恶习的排斥。为了家族的延续与显扬,上位者尤其君王需要对自己在外表、言行等各方面展示榜样和示范作用,民众心悦诚服,自然可以达成整体国家的和睦与繁荣,孝能够安邦定国的作用便显现得更加清晰。
四、小结
从总体上说,董仲舒孝论的形成与展开与《孝经》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通过发掘其中的关键语句并互相参酌可以呈现得更加清晰:一方面,董仲舒以“孝”为“天经地义”,从抽象层面赋予孝以至高地位,强调行孝即顺应“天经地义”,孝为天人相接与沟通的枢纽;另一方面他也在现实政治中确立孝对于国家的根本作用,身处政治生活的不同群体都有着相应的行为规范,从对家族维护、延续乃至显扬的角度出发,因之遵守便可以促成家国的和谐与安稳。董仲舒孝论是汉代《孝经》学繁荣及帝王推尚孝治的集中体现,并且经由他的整合与发挥,孝为政治层面教化的作用更加凸显,作为伦理观念也更加深入人心,对汉代乃至后世孝文化的发展与广播有很大贡献。
注释:
①汉唐学者基本一致认定孔子因至晚年政治抱负仍无处施展,因此作《孝经》为后世立法,以《孝经》为学习和钻研其他经典的入门阶梯。并且《孝经》与《春秋》的关系尤为密切,例如《孝经纬》即载:“孔子云:‘欲观我褒贬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伦之行,在《孝经》。’”就是说《春秋》主要记载孔子其时诸侯的种种行为以及孔子对他们的看法,《孝经》则是在现实基础上针对理想政治状态下的人伦构建,两书的主要目的都在于讲明治国之道,为后世做参考,汉代统治者即由此提倡孝治。
——从明代朱鸿《孝经》类编著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