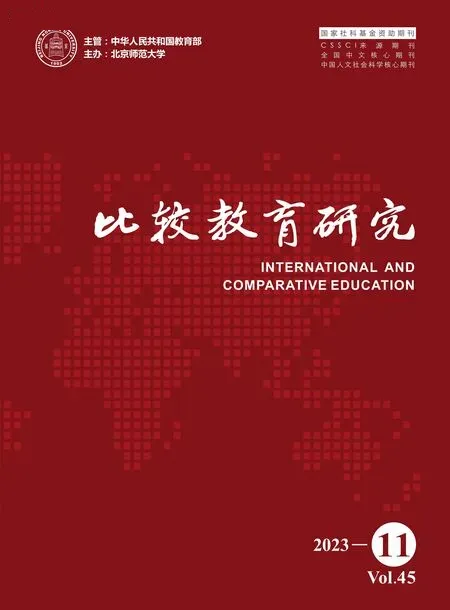《去学校化社会》50年:重新发现伊利奇的教育思想内核
徐芳健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湖北武汉 430079)
一、问题提出
《去学校化社会》(Dеsсhooling Soсiеtу)一书于1971 年问世,是美国当代学者伊万·伊利奇(Ivаn Illiсh)最具代表性、最负国际影响的著作。该书出版后,引起多方面的强烈反应,伊利奇被冠以“神话”“先知”“不切实际的思想家”“煽风点火的人”等名号。尽管受到的评价毁誉参半,伊利奇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却始终是无法回避的。因而,他的“去学校化社会”思想在短暂地被主流教育研究界抛弃后,不断地迎来复苏。特别是在《去学校化社会》出版50年后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今天,全球大规模的线上学习、“停课不停学”的教育变局使得“去学校化社会”的观念重新进入我们的视野。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与伊利奇已经相隔甚远,但这种理论的确当性却在当下重新蓬勃生发。
回溯过往,继伊利奇出版《去学校化社会》之后,皮韦托(Didiеr Рivеtеаu)发表了一篇名为《伊利奇:学校的仇敌,还是学校系统的仇敌?》(Illiсh: Еnеmу of Sсhools or Sсhool Sуstеms?)的文章,对伊利奇的思想作了基本的阐释和澄清。[1]此后,围绕伊利奇的介绍与争论不绝于耳。例如,迈克尔·阿普尔(Michael Apple)将伊利奇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传统进行比较,并将伊利奇的理论看作是“口号系统”的一种。[2]杰里·布朗(Jerry Brown)将伊利奇描述为“极为稀少的一类人,博学、清醒而又敏感”[3]。一些了解伊利奇的学者还在《对于伊利奇的挑战》(Тhе Сhаllеngеs of Ivаn Illiсh: а Сollесtivе Rеflесtion)论文集中对其所有著作主题都进行了讨论,涉及伊利奇生活和思想的背景及其关于教育、神学、技术和社会的观点,其中还包括伊利奇以前未发表的论文。[4]除此之外,网络上还出现了专门研究伊利奇思想的期刊《伊利奇国际研究》(The International Journаl of Illiсh Studiеs),关于其教育思想研究的文献更是不断涌现,不可胜数。
反观国内,伊利奇《去学校化社会》最早的中文译本是由吴康宁翻译、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于1994 年出版,之后于2017 年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发行汉英双语版。国内详细论述这一思想的专著极为少见,只有一些介绍性、评论性文章散见于著作之中,如赵祥麟主编的《外国教育家评传》,单中惠、杨汉麟主编的《西方教育学名著提要》,张人杰主编的《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修订版)》等。这些著作都对伊利奇的生平、去学校化社会思想及影响作了或繁或简的分析,大多都倾向于辩证地看待其人其书,从正反两方面对其思想进行评价。相较于著作介绍的理论性,期刊论文则凸显了该思想的实践性意义。例如,石鸥、刘丽群指出非学校化思想绝非无稽之谈,反映了一定社会现实,揭示了现代教育制度发展的某些趋势。[5]郑金洲、吕洪波认为,尽管“学校消亡论”在理论与实践上存在问题,但促进了我们对学校教育职能及隐蔽课程等问题的认识。[6]项贤明提出,伊利奇出于人道关怀而对学校教育制度异化所进行的激进而深刻的批判是我们面向未来建构新教育的前提和基础,对当代世界教育改革仍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7]还有一些学者立足具体的教育实践,从伊利奇的教育思想中汲取了关于当代成人教育、终身教育、现代远程教育和学习型社会等方面的启示。
相对来说,由于视角局限及翻译缺失的问题,国内学者对伊利奇教育思想研究的资料来源十分狭窄,几乎都集中在伊利奇的早期作品,甚至单纯依赖《去学校化社会》这一本教育著作来进行解读。尽管这一著作是其教育思想的系统性成果,但视野的狭窄必然带来认识上的问题。其实,当伊利奇将《去学校化社会》书稿交到出版商手中的那一刻起,他对于其中教育观点的论述便变得越来越不满意。他另外的重要著作,如《觉醒的庆典:呼唤制度革命》(Сеlеbrаtion of Аwаrеnеss: а Саll for Institutionаl Rеvolution)、《欢乐的工具》(Tools for Сonviviаlitу)、《能源与公平》(Energy and Equity)等,以及其他的教育文章、教育演讲和谈话都深刻地潜藏着其教育观点的内在脉络与思想核心。因而,本文想要丰富对伊利奇教育思想研究的文献基础,探寻其“去学校化社会”的内在假设与真实指向,在波澜壮阔的教育发展历史中重新发现并理解伊利奇教育思想中层层包裹的内核。
二、去学校化社会的背后:其人,其思
伊万·伊利奇自始至终就不是一个标准的知识分子,他的受教育经历与问题阐释方式都是独特的。人们无法从社会批评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教育学家、神学家等类别中的某一个去认识他,因为他思考问题的方式不是单一的,社会、历史、玄思的视角都体现在其“去学校化社会”等教育思想之中。在某种意义上,伊利奇还是一个爱追根究底的激进分子。他质疑现代生活的前提,并追溯许多制度上的过度行为。与此同时,在他激进质疑的态度背后,还隐藏着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与价值关怀。在其著作中,伊利奇努力地在我们现代世界观的确定性中开辟裂缝,他质疑学校、医院、技术、经济增长和无限的能源。[8]即使在去世之后,他也深深地扰乱了现代性的追随者。
(一)伊利奇的教育思想背景
伊利奇在一次谈话中直接明确地否定了学校对于自身需求的满足作用。他自述道:“我是在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情况下长大的。……是的,我上学,但只是一点点。比如,在8岁时,我突然决定要学习塞尔维亚语,以便为考试做准备,并可能进入南斯拉夫的一所学校。所以我从一位在外交学院任教的教授那里学到了这门语言。我从来不把学校当回事,实际上,我学到的一切都发生在校外。因此,当1956年我突然发现自己是波多黎各庞塞市天主教大学(the Саtholiс Univеrsitу in Рonсе, Рuеrto Riсo)的副校长,一年后成为政府教育委员会的成员,负责管理从大学到小学的一切事务时,我不禁问自己,这是什么教育?我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件事情。”[9]回顾伊利奇的教育生涯,正是在波多黎各,作为管理岛上整个教育机构的董事会成员,他通过对学校工作的全面了解和观察研究,注意到学校通过垄断教育,并将其定价设在大多数人承受范围之外,从而挫败了它们表面上旨在实现的目标——机会平等。他得出的结论是,波多黎各的义务教育构成了“结构性的不公正”。他看到“学校的愿望集中在海市蜃楼上……法律已经要求孩子们接受超过国家负担能力的教育。更糟糕的是,人们也学会了责怪自己没有实现不可能的事情”[10]。在接下来的15年里,伊利奇完善了他对学校教育的分析,并扩大了研究范围。20世纪60年代末,他出版了《拉丁美洲学校教育的无用性》(Тhе Futilitу of Sсhooling in Lаtin Аmеriса),在1971年出版了他的重磅著作《去学校化社会》。
而在《去学校化社会》正待付梓之际,在他呼吁为了改善教育而解散学校时,伊利奇马上注意到这是其错误所在。他开始担心,教育性教会的瓦解会导致不同形式教育的狂热复兴,使世界变成一个普遍的教室、一个全球的校舍。更重要的问题似乎变成了——“为什么这么多人,甚至是对学校教育的强烈批评者会对教育上瘾,就像对毒品上瘾一样?”[11]随后,伊利奇更清楚地意识到教育功能已经从学校转移到了社会,现代社会将越来越多地建立其他形式的强制性学习。这种强制性学习的形成不是通过法律,而是通过其他伎俩,比如让人们相信他们是从电视上学到一些东西,或者强迫人们参加在职培训,或者让人们支付巨额资金来学习如何玩游戏等。这种“终身学习”和“学习需要”的说法已经超越学校维度,彻底污染了社会,使其散发着教育的“恶臭”。[12]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伊利奇的好奇心和思考重心开始集中在“教育需求”这一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上。此时,他不再接受把某种教育需求看成是历史赋予的人性之说法,而是将注意力从学校转向教育,从教育的过程转向教育的方向,开始理解教育是生产手段稀缺假设下发生的学习。与此同时,他开始注意到,教育仪式反映、强化,并实际上创造了在匮乏条件下追求学习价值的信念。他逐渐认识到,这种信仰和仪式的安排甚至在取消学校教育、免费教育或家庭教育的规则下依然可以轻易生存和蓬勃发展。
(二)与教育相互交织的核心议题
正如前文所述,只从某一个角度去剖析伊利奇提出的深刻洞见是误入歧途。同样地,对于“去学校化社会”等教育思想的阐述是与不同方面的问题紧密交织的,这是伊利奇看待复杂性教育的一贯思路。综观伊利奇的著述,从教育、医学、经济发展到文化史和应用伦理学,他在不同的领域反复挑战官方智慧的确定性,其提出的重要问题的核心在关键之处有所重叠,可以将其称为基本的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伦理学和神学等问题。[13]
第一,社会学问题是伊利奇向学校和现代医学等机构提出的挑战。在这里,关键概念是彻底的垄断和反生产力,他声称社会制度很容易成为意识形态和自我辩护的寻求。第二个问题可以称之为“历史性的问题”。伊利奇认为,历史问题应该以生活实践为基础,倾向于考察历史的“断裂性”。如“教育人的历史”必须与“教育的历史”区分开来。第三,在与前两个问题交叠处出现了一个哲学人类学问题。伊利奇坚决反对“非历史性人类”(аhistoriсаl humаn being)的观点,因为真正存在的是生活在特定时代和地点的“具体化的现实之人”。他拒绝将人类服务制度化以满足人类的需要,倾向于探索人类感官的具体经验。哲学人类学很容易融入第四个问题,即伦理学。在这里,伊利奇提出了关于自主、友谊和希望的主张。他指出,这些“基本善”(fundаmеntаl goods)正受到人为的侵蚀,而这些却是我们最后的归途。最后,还有一个神学问题。伊利奇所强调的如宗教、神话、信仰、仪式等观点和概念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意味和启发性质。
(三)伊利奇的学术思想态度:“人道的激进主义”
埃里希·弗洛姆(Еriсh Fromm)在《觉醒的庆典:呼唤制度革命》一书的序言中,描述了他眼中的同道伊利奇的思想核心——“人道的激进主义”(humаnist rаdiсаlism)。弗洛姆将其概括为“怀疑一切”的格言,特别是对那些人人共享、承担常识公理角色的意识形态概念的怀疑。这种怀疑是一种有所准备并有能力进行的批判性质疑。而这一激进质疑只有当一个人不把自身所处社会的概念,甚至整个历史时期的概念视为理所当然才有可能产生。但这一揭露和发现问题的怀疑并不一定意味着否定,因为它接受辩证法,理解对立的展开过程,并以否定和肯定的新的综合为目标。其立足于“人是根本”(thе root is mаn)的非实证主义、非描述性的意义,即从一个过程而非一件事物的角度来看待“人”的潜力。因此,总的来说,“激进主义主要不是指一套特定的思想,而是指一种态度,或者可以说是一种方法……人道的激进主义是一种激进的质疑,其指导思想是对人之本性的动态洞察,以及对人的成长和全面发展的关注”[14]。
而弗洛姆所说的这一“人道的激进主义”构成了他和伊利奇共同的思想内核。这种批判的态度赋予了“去学校化社会”思想以独特而深邃的视角,而其人道主义的倾向则体现出其终极的价值关怀。[15]二者结合形成了伊利奇学术思想的根本态度。
三、去学校化社会:必要的选择?
在明了伊利奇的人生经历与思想基础后,我们便可以直接转向伊利奇的教育批判对象——“学校化社会”,思索这一去除学校化的努力是否是一项必要的选择,我们今天又该如何对此作出新的判断与行动。
在伊利奇所处的时代,挑战作为一个系统而存在的学校是很艰难的,因为人们已经太习惯学校了。“我们的工业类别倾向于将结果定义为专门机构和仪器的产品……比奈(Аlfrеd Binet)将智力定义为其测试所测出的分数。那么,为什么不把教育想象成学校的产物呢?一旦这个标签被接受,未受学校教育的‘教育’就会给人一种虚假、不合法、未经认证的印象”[16]。在伊利奇看来,学校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所谓的“特权的制度支柱”。与此同时,它也是一些人社会流动的主要力量。尽管如此,追逐学校教育意义的行动在真正的学习、真正的创造力和真正的民主方面付出了什么代价?以这种方式使自己永久化的社会最终要付出什么代价?我们又能提出怎样的教育替代方案?对此,伊利奇从教育的宏观到微观层面逐步进行了他的批判性质疑。
(一)“价值制度化”的文本还原
在宏观层面上,借助于“人道的激进主义”这面透视镜,伊利奇自认为找到了现代社会一切邪恶和痛苦的根源,即“价值的制度化”(institutionаlizаtion of vаluеs)。[17]这一“价值的制度化”造就了人与其所创造的机构之间的某种异化关系。也就是说,人创造机构,并赋予其价值,最终使机构成了价值的化身,而人却丧失了自身价值。就学校而言,问题则在于——人通过把自己的学习托付给学校,赋予其教育的价值,但最终却使人自身丧失了自学的能力。
在《去学校化社会》中,伊利奇认为“学校化”是一个工业时代制度的“范式”。在某种程度上,学校教育建立并维持着保护和维持其他机构的规范和行为模式,因此对学校教育的分析成为分析家庭、国家和医学等其他制度的“范式”。因此,去学校化应该在两个方面进行:不仅要去除学校化的教育,而且还要去除学校化的社会。
更进一步地而言,伊利奇利用“制度光谱”(institutionаl sресtrum)的概念将制度光谱两端划分为两种根本对立的制度:最左端的制度比较温和,提供沟通合作网络,以供服务对象自行利用的理想的互惠性制度,最右端的制度是在现代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并赋予现代社会以意义,主要表现为强行看管,或者是有选择地提供服务的操纵性制度。他认为“最为阴险的”学校位于右端,只能为某种产品服务,是虚假的公用事业,表面上平等地面向所有人开放,但实际上只有那些有条件的人才能享受学校教育。同时,学校依赖于诸种“神话”保持与工业社会的联系,通过宣传“专业技能”的信念创造了激进的垄断,限制了人主动为自己做事和主动自我定义的能力,模糊了通过自我定义的行动来实现个人意义的生活与被动的期望及毫无乐趣的消费之间的区别。
尽管如此,伊利奇仍乐观地认为当代社会向右的转向并非不可避免。他试图通过“学习网络”(learning webs)的例子来证明左端的选择至少是可能的。他指出,存在一些不依赖于操纵或营销的有效的教育机构,社会上的学习需求可以通过以下四种网络来满足:学习辅助工具、技能交换、同伴配对与生活指南。在此基础上,他还借用“厄庇米修斯”(Ерimеthеаn,又译“埃庇米修斯”)的神话阐明了他的伦理指导原则:最好的生活包含自我决定的自由活动,在社会范围内追求自我定义的目标和意义。
(二)教育/学校教育,教育/学习的辩证法
在中观层面上,伊利奇基于历史及玄思的视角指出教育与学校教育、教育与学习之间的辩证关系。他发现,在“教育”这个术语进入通俗用语之前,学习中心就已经存在了。“在以前,我们自主阅读经典或法律,我们也没有受过终身教育。但到了17世纪初,一种新的共识开始出现:人生来对社会无能为力,除非他接受‘教育’,否则他将一直如此。教育开始意味着生命能力的反面,必须为所有人的利益而生产,并以看得见的恩典的方式传授给他们”[18]。伊利奇进一步指出,学校教育和教育是相互联系的,就像教会和宗教,仪式和神话的关系一样。仪式创造并维持着神话,神话通过仪式产生了永久存在的课程。“教育”作为一个包罗万象的社会辩护范畴的名称,是我们在基督教神学文化以外找不到其他特定类比的一个概念,通过学校教育过程产生的教育使学校有别于其他时代存在的其他学习机构。
由此,学校通过将学习重新定义为“教育”来垄断学习。在校外学习的人仍然是官方上的“未受教育者”。具体而言,学校的垄断地位是通过对“未受教育者”的歧视,通过将书籍和实验室集中在学校,以及将大量公共资金限制在从普通学校毕业的人身上而建立的。因此,与法律强制人们上学相比,强制消费学校所定义的“教育”更有效。更微妙的是,机构通过削减社会想象力来强加其普遍垄断,人们开始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做自己的事”,觉得需要“拥有”或“获得”一些东西。这种从主动世界观到被动世界观的转变很好地反映在语言上:人们与其说是“想学习”,不如说是觉得“需要教育”[19]。显然,当注意力集中在学校教育上时,我们很容易从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上分心,即如何看待学习。
(三)“隐性课程”祛魅
承上所述,伊利奇提醒我们,要看清我们面临的选择,首先必须区分学习和学校教育。学校中隐藏的结构必然传达的信息是只有通过学校教育,个人才能为成年后的社会做好准备,不在学校教授的东西没有什么价值,便不值得知道。
更进一步,伊利奇将其称之为“隐性课程”(hiddеn сurriсulum),因为它构成了学校系统不可改变的框架,有形课程的所有变化都是在这个框架内进行的。学校里隐藏的课程总是一样的,它要求所有一定年龄的儿童在认证教师的授权下,以大约30人为一组,每年一起花费约500或1000或更多小时去接受教育。只要该机构声称有权界定哪些活动是合法的“教育”,无论课程设计是为了教授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天主教、社会主义还是解放的原则,都不重要。[20]
基于社会与经济的视角,伊利奇尖锐地指出,隐性课程的利害之处在于它使学生们认识到,通过分级的消费过程在学校获得的教育是有价值的,个人在社会上获得的成功程度取决于他消耗的学习数量。隐性课程将“从一项活动中学习”转化为一种商品,并由学校垄断市场。我们现在给这种商品起的名字是“教育”,这是一种可量化的累积产出,是一所名为学校的专业设计机构的成果,其价值可以通过将一个过程(隐性课程)应用到学生身上持续的时间和成本来衡量。进一步说,一个人接受的教育越多,他获得的“知识存量”就越多,他在知识资本家阶层中的地位就越高。因此,隐藏的课程既定义和衡量了教育是什么,也衡量了它赋予消费者的生产力水平,它为工作和相应的特权之间日益增长的相关性提供了理由。[21]
整体来看,伊利奇对学校教育的批评是辩证的,不仅强调了当前状况的问题,而且还提供了可能是什么的另一种模式。在他眼中,学校是一个社会的启蒙仪式,而这个社会的导向是:一个消费越来越多隐形和昂贵服务的社会;一个依赖世界普遍标准的社会;一个强调大规模测评和长期规划的社会;一个不断将新需求转化为对新消费的具体需求的社会。[22]通过对社会发展的研判,伊利奇断言:学校正处于危机之中,就读这些学校的人也是如此,前者是政治机构的危机,后者是政治态度的危机。学校已经失去了对教育合法性的无可争议的主张。我们必须作出选择,是让人们接受更有效的教育,以适应日益高效的社会,还是选择一个新社会,并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建立学习机构以及相关的自由保障。[23]
对于伊利奇提出的“去学校化社会”,我们还可以根据其推进的社会目标和实现手段进行评估。[24]伊利奇称取消学校教育是一个“政治目标”,但随后没有指出任何合理的政治行动步骤。我们不禁怀疑,“学习网络”是否可以成为让社会脱离学校教育的一种手段,成为一种“左倾”的快乐选择的工具?伊利奇的想法到底是一个富有成效的新方向,还是一条死胡同?毕竟,他只提供了关于左翼欢乐机构的暗示,没有“左倾”快乐社会的具体例子,而这可能会要求“一周全是周末”或“终生退休”的逻辑状态。尽管如此,伊利奇重新聚焦于社会中的教育讨论,非常清楚地表明了教育政策问题的利害关系,并释放了大量被认为理所当然的假设所束缚的能量。“去学校化社会”现在可能已经过时了,但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当代词汇来表达其依然领先的见解,它可能会作为新时代到来的想法而重新焕发生机。
四、去学校化社会之后,该走向何方?
前述的问题,甚至毋须我们回答,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伊利奇自己便承认,他开始认识到他最初所提的“去学校化社会”策略的徒劳。他的问题入手点——社会批评很快被历史考古学和哀叹所取代。考虑到这一变化,与其说伊利奇是一个社会批评家、哲学家或预言家,不如说他更像是一个在我们的高科技城市呼喊着承认技术科学进步及其迷人的知识论和政治刺激所造成的破坏的激进分子。[25]在其后续的社会思索中,在其引发的教育变革中,我们应拨开层层迷雾,踏上一条他所描绘的自由与解放的教育理想之路。
(一)伊利奇的教育思想转向
实际上,在出版《去学校化社会》之后,伊利奇还撰写了《去学校化之后,是什么?》(Аftеr Dеsсhooling, Whаt?)、《囚禁于全球化课堂》(Imрrisonеd in thе Globаl Сlаssroom)、《镜中过往:演讲和讲话 1978-1990》(In The Мirror of thе Раst: Lесturеs аnd Аddrеssеs 1978-1990)等更深入也更激进的教育著作。他逐渐开始认识到,去学校化要求我们认识到教育事业本身的非法和宗教性质,教育的傲慢在于试图使人成为一种社会存在。因此,在提出“去学校化社会”之后,伊利奇不仅开始质疑学校教育,而且开始质疑教育本身的理念。他呼吁对“教育人”(天生需要教育的人类物种)而非教育的历史和起源重新进行研究,他从历史和经济的角度将现代教育的概念定义为“稀缺性假设下的学习”,即学习的手段总体上是稀缺的,而这一稀缺性假设导致人们创建社会机制试图确保他人学习某些东西。经过一番考察,伊利奇悲观地认为这样的干预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帮助的,但它们很快就会变得在规模和强度上越来越大,以至于把手段变成了目的,最终导致其目的受挫。
继历史的角度之后,伊利奇还以玄思的方式为我们提供除了关于教育稀缺假设之外的可能选择。他给出的答案是,“信任和信仰大自然的善良、正义。也有人会说,是上帝的善良”[26]伊利奇对前稀缺的“希望”(hope)概念和后稀缺的“期望”(expectation)概念进行了区分。他论及,希望意味着相信大自然的善良,而期望意味着依赖于由人计划和控制的结果;希望集中在一个我们等待礼物的人身上,期望则从可预测的过程中得到满足,这个过程将产生我们有权要求的东西。[27]“如果在这个摇摇欲坠、腐朽不堪的社会中还有什么希望的话,那么就是通过旧意义上的严格友谊实践,在犹太教或修道院的意义上,在完全支持另一个人的意义上”[28]。基于此,伊利奇保持了对当代社会行动的怀疑,希望通过追溯到“好心的撒玛利亚人的寓言”(thе раrаblе of thе Good Sаmаritаn),重新发现友谊的古老深刻意义。在他看来,自我对他人的全部意义、给予和奉献即是他人赠予我的礼物,友谊则意味着朋友之间充满善意、自我克制、彼此关联的支持。
然而,我们不免会怀疑这样的撒玛利亚人行为究竟是一种常态,还是例外。但在这里,伊利奇想要提醒人们必须小心对待的是——不要屈服于工程精神的自大幻想,即认为一个人可以将社会塑造成一个给定的目标,无论这个目标看起来多么有吸引力。否则,人人就有可能成为一名“教育者”,也就是一名塑造人的人。“那我该怎么做?我尽我所能成为一个好朋友,试着把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放在我的心里,成为一个真正的邻居,并相信学习是在人类的生命中进行的。自然,教育的状态将是:爱一个孩子(或任何年龄的人),不是按照我的期望塑造他或她,而是对那个人抱有希望和信任,深深地看着他或她的眼睛,全神贯注地倾听她或他的声音,找出那个人是谁,然后接受那个人是谁”[29]。
(二)需要警惕的教育改革:“自上而下”的道路
西方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的教育改革实践,在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伊利奇对于最初所提“去学校化社会”设想的担忧。现在,学校已经变得太容易成为大家攻击的目标了,当前的危机使攻击学校变得很容易。毕竟,学校是保守和僵化的,它们确实产生了从众和冲突,它们确实歧视穷人,接近特权阶层。于是乎,取笑学校、抨击这头曾经“神圣的奶牛”(sacred cow)已成为一种时尚。[30]
人们对伊利奇和取消学校教育的兴趣的复苏,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取消学校教育对世界各地寻求发展后发展、去殖民化、土著教育以及社会运动的吸引力。由于这些人中的许多人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被边缘化,可以称其为一项“自下而上地去学校化”运动。然而,当前重新发现取消学校教育吸引力的不仅仅是激进分子,在过去10年里,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一种类似的现象,可以称之为“自上而下地去学校化”运动。[31]在这种现象中,来自更中间和右翼立场的经济和政治精英也开始接受将学校作为一种制度批评,并推动摆脱对扩大正规教育的重视,转而支持替代性的学习和发展模式。这个由精英领导的项目很少直接提到伊利奇或“去学校化”这个词,并在意识形态上与伊利奇和“自下而上地去学校化”运动的激进议程背道而驰。尽管这些批评者提出的一系列替代方案,包括个性化学习、在家上学、非制度化和开放的学习网络等非常类似于伊利奇的方案,但这些取消学校教育的意图和做法是蕴含危险的,它们通常集中在教育政策和实践的三个关键领域:质疑将普及高等教育作为合法的政策目标;推动取消专业、管理和技术劳动力的学校教育;事实上放弃普及义务教育。[32]
而这一运动的兴起需要置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变化的更广泛背景下考察。一方面,上述议程中的去学校化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新自由主义、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教育政策改革模式推动的,在这种模式下,教育的核心目的被缩小为服务于市场的需求;另一方面,这一做法将进一步模糊社会教育制度对什么可能是重要的,以及如果放弃对这一制度的承诺可能会失去什么的判断,尤其是对于许多低收入群体、种族和民族地区而言。因为他们缺少更好的、替代类型的社会机构来取代当地学校。[33]因此,当教育完全基于实践、经验或背景时,这些学习往往是困难、危险和不负责任的。
正如伊利奇在20 世纪70 年代所警告的那样,如果不同时否认这样一种观点,即知识更有价值是因为它来自经过认证的套餐,并且是从由专业监护人控制的神话知识中获得的,那么对学校制作的复杂课程套餐的诋毁将是一场徒劳的胜利。只有实际参与才构成有社会价值的学习,即学习者参与学习过程的每个阶段,不仅包括自由选择要学什么和如何学习,而且还包括每个学习者自由决定自己生活和学习的理由。进一步说,除非我们保证工作能力是就业、晋升或获得工具的唯一可接受的标准,从而不仅取消学校,而且取消所有的仪式筛选,否则去学校化就意味着用撒旦驱逐魔鬼。[34]
(三)自由与解放:重新走上教育的美丽风险之旅
正如埃弗雷特·赖默(Еvеrеtt Rеimеr)所说,“人们为了理解社会而受学校教育,为创造或再创造社会而受教育”[35]。寻求学校制度本身的根本替代办法必须建立在明确的政治要求上: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建立学习机构以及相关的教育自由保障,这或许意味着法律保护、政治纲领和制度安排建设等与现今普通学校相反原则的落实。如果没有立法全面禁止任何基于事先入学的歧视,禁止将税收资金的控制权从社会转移到个人手中,那么就不能取消学校。[36]然而,即使是这些行动也不能保证教育自由,除非它们伴随着对每个人在学校面前的独立性的积极认识以及衡量具体、现实的人的恰当目的和方式。[37]
具体而言,只要教和学仍然是神圣而非世俗、封闭而非开放、压制而非解放的活动,去学校化的诉求就只会将责任转移到另一套更无形的机构。因而,去学校化教育必须是教与学的民主化,必须包括将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的控制权归还给人们。要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负有对自身进行“去学校化”的责任,且只有我们才拥有为之所需的力量。因此,必须保证学习者的自由,而不是向社会保证他将获得什么知识。无论谁冒着教别人的风险,他都必须对结果负责,就像学生暴露在老师影响下一样,教育必须承担起帮助他人成长为独一无二的义务。
在一份圣经式的宣言中,伊利奇深情地号召我们每个人携起手来,一起创造一个新世界。在那里,充满着自由选择的工作和愉快的交往,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可以欢庆我们的潜能——并且发现一条通向更富人性的世界道路”[38]。这便是伊利奇为我们所描绘的欢乐社会的未来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