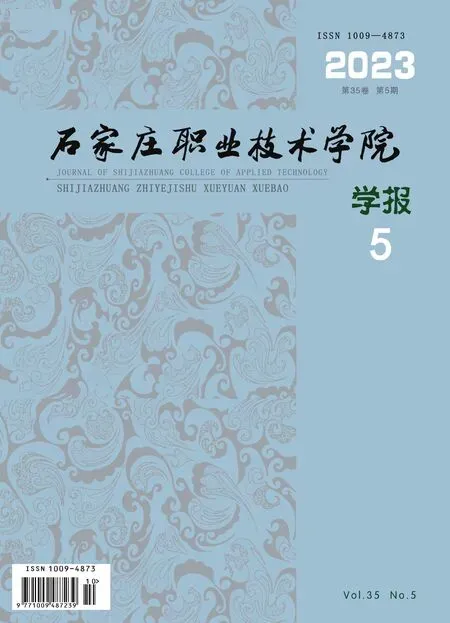城市文化空间的认同与建构
——评城市组诗《石家庄长歌》的艺术创新
宋 菲, 赵素忍
(河北经贸大学 文化与传播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61)
《石家庄长歌》是女诗人田耘2019年底出版的一部城市组诗,被称为“中国第一部城市史诗”。面对长达三十万年的时间跨度,田耘对石家庄相关历史素材进行了较为合理的划分、取舍及组合。她将石家庄的历史浓缩为“起”“承”“转”“合”四个部分,分别对应“古代石家庄”“近现代石家庄”(除解放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石家庄”和“建国后的石家庄”四个历史时期,通过系列组诗唤起了人们对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记忆。
用诗歌这一艺术形式去展现历史,并非当下诗歌创作的主流,而用诗歌去呈现一座城市、一个地域长达三十万年的历史,更是鲜见。可以说,田耘的创作尚处试验阶段,几无创作经验可循。而用诗歌记录与传承历史在当下是一件具有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事情。本文以《石家庄长歌》为例,重点对历史题材诗歌创作的艺术创新进行一些探讨。
一、以多元化、开放性视角完成对历史的再现
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的魅力,在于时人与后人的不断碰撞,并由此产生差异化的解读,这种差异化解读在文学创作领域则更为突显。如何看待、处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成败。延续既有史实的描述,难免流于平庸,而完全捣空或戏说历史则无法立足严肃文坛。发掘新的史料,进行有新意的艺术创作,是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有效路径。今天,人们对历史的探寻已经不再是追究它的绝对真实,海登·怀特曾说:“只要采取叙事的方式进行历史书写,就必然会把原型神话和情节化结构带入叙事之中。”[1]历史是开放的,历史人物也可以是多侧面的。以《石家庄长歌》中的《石家庄汉朝那些事·刘邦篇》为例:
我要在/史籍的缝隙中抽丝剥茧,复原一个/高鼻梁、圆眉骨,长着/漂亮胡须的凡人刘邦/复原他的疲惫。登基八年/异姓王的反叛,按下葫芦起了瓢/龙床龙椅从未焐热过/一到东垣,御驾亲征韩王信/二到东垣,御驾亲征阳夏侯陈豨/复原他的豪爽。东垣城头的骂声/在滹沱河南岸回荡了一个多月/开城投降后,曾在一片骂声中/选择沉默的将士发现,迎接他们的/不是死亡,竟是自由/复原他的仗义。赵王张敖花甲之年的/相爷贯高及十几个门客为主人出气/刺杀刘邦事败,宁可灭九族/也要断发锁脖、装作家奴跟随主人/只为等待一个辩白的机会/几千道鞭痕、满身被铁条烧焦的皮肉/下面仍然保留的十几颗忠心,到底/带给刘邦多少震撼,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十几颗忠心/后来在相国或郡守的位置上/继续为大汉王朝发光发热/甚至还荫及后世子孙/也别忘复原他的负心:/《汉书·淮南厉王传》有载/详址已湮没于东古城某处的/赵美人墓里,千年的哀怨依然未散[2]10-11
刘邦作为汉代开国皇帝,正史、野史中关于他的大事件已为人熟知,对这样的人物进行再创造并非易事。田耘通过搜集、整合东垣历史长河中有关刘邦的记载,勾连起一代帝王与一座城市的历史渊源。田耘笔下的刘邦是这样的:他长着漂亮胡须,身为帝王有着他的疲惫,面对战俘有着他的豪爽仗义,而他对真定赵美人的负心让美人的哀怨千年未消……田耘力图“复原”一个有血有肉、有情也无情的刘邦,身为帝王他既有多疑、狠心的一面,也有疲惫、仁义的一面。东垣地域的刘邦记忆被集中呈现:刘邦亲征东垣平叛,返程过赵,张敖献赵美人,贯高等谋反张敖蒙冤,赵美人生下儿子(刘邦幼子刘长)含恨自尽、葬于真定,贯高等门客凛然受刑澄清谋反始末,张敖被放、门客名声远播。在这一系列历史事件背后,疲惫、仁义、多疑、负心的圆形人物刘邦呈现在读者面前,赵王、贯高、赵美人这些配角也相继登场,在不长的诗篇里串联起了相关历史事件。
田耘还善于从历史人物身上找到自己独特的切入点,她在《石家庄汉朝那些事·刘秀篇》中为我们展示了一个隐忍的刘秀:
那个低三下四表示效忠,请求持节/巡行河北的西汉宗室后裔、粮商刘秀/在草包刘玄面前,隐藏了内心/熊熊燃烧的火焰。星夜兼程北渡黄河/是为亡兄复仇,更是为了自保[2]12
这首诗以刘秀的隐忍为切入点,描写了刘秀起兵时期的艰难,为获得地方势力支持,娶真定王刘杨外甥女郭圣通为妻,婚礼上的藁城宫灯映照出的却是多方势力各怀心思,预示着二人的婚姻难以善终。
二、用蒙太奇式的镜头转换呈现历史
蒙太奇原为建筑学术语,意为构成、装配,后进入电影领域表示镜头的组接。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蒙太奇,“一是作为一种具体的剪辑技巧和技法;二是作为一种结构手段和艺术技巧;三是作为一种思维方法,贯穿于电影创作始终。”[3]不同镜头间的组接即为蒙太奇,但其意义不止于剪辑技巧,蒙太奇的使用对于电影的艺术表现至关重要。而在某种程度上,电影镜头的变化、组接与诗歌创作中的时空转换有异曲同工之妙。田耘在创作某些历史题材诗歌时,跨时段多个场景的转化犹如电影画面的蒙太奇衔接,增强了诗歌的画面感、感染力。
我们以《石家庄长歌》中描写辛亥革命烈士的长诗《吴禄贞,或石家庄1911》为例,看作者如何用蒙太奇式的镜头组接进行城市空间的历史转换及对烈士吴禄贞的缅怀:
长安公园西北角的空气,永远凝结在/1911年深秋凌晨一点半/一个头颅神秘消失于石家庄的空气中/一场兵分三路蓄势待发的起义/本应成为辛亥革命的句号/却在无物之阵中败下阵来/被侍卫长用于花街柳巷的/二万两酬银,为身上的污渍蒙羞/为参与改写了中国近代史蒙羞[2]34
全诗从石家庄长安公园西北角的吴禄贞墓起笔,首先成功地把今天与事件所发生的1911年进行了时空置换,让读者骤然感受到了1911年的深秋隐藏着一场撼动旧中国的雷霆风暴。其次,把发生在石家庄的一场革命活动与辛亥革命的大背景进行了镜头融合,类似蒙太奇手法中的淡、切,交待了时代背景及此次革命活动的悲剧结局。
囚犯说服了审讯官,学生说服了老师/吴禄贞和张之洞的对话中/到底藏着多少惊雷和闪电/才会让1901年武汉街头的人们/惊讶地注视着一个被委以重任的囚犯:/湖北武备学堂会办吴禄贞/请允许百年后的我/在想象中为这段对话附上插图——/“时局图”上虎视眈眈的熊、虎、蛤蟆、/鹰、太阳,抬不起头来的“东亚病夫”/卑躬屈膝的清廷统治者[2]34-35
该诗第二节开始对吴禄贞的事迹进行追忆,此节把镜头拉到了1901年,一个囚犯(吴禄贞)说服了老师、审讯官(张之洞),而后被委以重任。之后作者再次跳转画面,1901年武汉街头的镜头牵引出的,是面对20世纪初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一场“新”与“旧”的大较量。那些“熊、虎、蛤蟆、鹰、太阳”与“抬不起头来的东亚病夫”出现在一张图上,呈现出令国人心痛无比的民族危亡情景。
1898年,站在熙来攘往的东芝、第一银行、/王子造纸、日本电信电话公司门口/却怀揣一颗焦急之心,望向东海的/那个中国留学生,隔着120年/我仍然能听到,他胸中起伏的波涛/“励志会”与“兴中会”的距离/只有东京到横滨的三十公里/吴禄贞和孙中山,两颗干净的心灵/从此再也没有距离/1903年一颗“投身中央,伺隙而动”的心/早已装下沉甸甸的三民主义/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痛苦,是与虎谋皮/却要对虎强颜欢笑[2]35-36
第三节时间再次向后倒推,1898年在日本留学的吴禄贞,站在代表日本先进技术、发达经济的公司、银行门口的镜头快速切换,让我们看到一位爱国忧民青年的一颗拳拳赤子之心。后吴禄贞创立“励志会”,与孙中山会面后加入“兴中会”,完成了对吴禄贞留日期间革命活动的勾勒。在本节最后,时间拉回到1903年,黄兴劝吴禄贞潜伏于清廷北京练兵处伺机而动,与虎谋皮、强颜欢笑的画面历历在目。
凌晨一点半。冰冷的子弹和匕首/在一个秋夜里埋头批阅文件的人面前/在一个心里唯独没有自己的人面前/是否曾有过片刻的摇摆。军大衣上/仍然闪烁的八角双龙宝星和死不瞑目/瞪大的双眼,是否曾让一颗猥琐的心/有过片刻的颤栗。当一个头颅从/一具仍然冒着热气的躯体离开/当那具躯体被曾经的知己何遂抱着/石家庄到太原的铁轨上/载不动的,是鲜血和眼泪/石家庄到太原的空气中/凝固住的,是呜咽的秋声/何遂手中那柄极度悲愤绝望的短剑/使脖颈流下的血,与知己脖颈的血/早已融为了一体[2]36-37
最后是吴禄贞遇害场面的特写镜头描写,英雄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遗憾、刺客心中的颤栗、革命战斗的残酷与曲折,在特写镜头中得以升华。“极大部分景都只是为了使观众容易看清楚、看明白故事才采用的。唯有特写镜头(还有近景,从心理学看,两者是相同的)和全景,它们一般都具有一种明确的心理的内容,而不仅仅是在起描写作用。”[4]全诗终结于烈士牺牲这一惨烈的特写镜头,血腥残酷的视觉冲击给读者带来了强烈的心灵震撼,中国近现代史上革命先烈前仆后继,多少仁人志士流血牺牲,吴禄贞是一个缩影,这是一首对辛亥革命烈士的礼赞之歌。吴禄贞血洒石家庄这一历史事件被田耘用诗歌的形式呈现出来,让更多的读者,特别是年轻人知道了石家庄长安公园一角的墓碑来历,继而主动去了解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用诗歌的形式唤醒历史文化记忆。
三、运用意象、比喻增强叙事现场感
诗歌不同于其他文学体裁的一个特点就是用更精简的篇幅,更精炼的语言,更加丰富的想象和集中的意象去抒情、叙事。历史题材的诗歌创作,如何增强现场感,如何拉近读者与历史之间的距离,使读者产生共情乃至共鸣是创作者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田耘善于运用多种诗歌表现技巧去营造现场感,增强读者对历史背景、氛围、人物的感受力。
《在井陉口》中,田耘似乎让我们隔着纸张闻到了井陉古驿道上秦始皇腐尸的味道:
秦皇尸车上,鲍鱼和腐尸的味道还在/秘不发丧的赵高,将大秦帝国/由顶点推向深渊的那团阴云还在[2]16
“那团阴云”的制造者——只手遮天的赵高,为了让胡亥登上帝位故意隐瞒秦始皇在河北的死讯,辒辌车里被有意塞进的鲍鱼和腐尸的味道共在,两千多年前在井陉秦皇古驿道上演的这一幕历史大剧被田耘用一系列意象再现出来,今人读来仍触目惊心。
在《真定,真定》中,田耘让我们对安史之乱中那座血流成河的正定城感同身受:
白麻纸本上流淌的,不是268个字/是炙热的泪,是一泻千里的岩浆/没有笔,没有墨,唯有一腔悲愤/如熔金出冶,遍地流走/一篇反复涂改34字,奋笔疾书的祭文/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变成/万人膜拜的“天下第二行书”/就让“祭侄文稿”中,颜真卿/墨迹未干的千年悲愤,复原那个/内缺粮草、外无援军的真定城/复原史思明屠刀下横尸塞路、/血流成河的真定城中,几百颗/宁肯被砍,也绝不低下的头颅/复原未及成为国之栋梁,便已/身首分离的侄儿颜季明/复原安禄山手中那条冒着热气的舌头、/舌尖上颜真卿兄弟颜杲卿仍未止歇的/“叛国造反,涂炭黎民”的骂声/复原颜杲卿幼孙颜诞、侄儿颜诩、/幼子颜询、长史袁履谦散落一地的手足、/割下的肉、刮净的骨头[2]18
“炙热的泪”“一泻千里的岩浆”“熔金出冶,遍地流走”,这一系列意象,连缀出的不仅是颜真卿“祭侄文稿”这一“天下第二行书”,更是颜真卿兄弟颜杲卿等人舍生取义、壮怀激烈的报国之志,“冒着热气的舌头”“散落一地的手足、割下的肉、刮净的骨头”这些惨绝人寰的镜头就是作者对刽子手的无声控诉,作者试图还原历史现场的真实感,进而完成对英雄的礼赞。
在《石门情报站》中田耘把机智勇敢的地下党员比喻成演技高超的演员:
“殷志杰”进入石门法院街4号军统/虎口拔牙的方式/是沿着一条线顺藤摸瓜/收买机械零件的天津人刘文贵/大兴纱厂机修车间主任张志华、/华北饭庄的一场饭局、保证书/是这条线上的点/对付背上的芒刺、藏在暗处的/无数双眼睛的最好方式/是在殷志杰的角色设定里/再随机加上无数场好戏/是成为最佳男主角、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殷明飞婶子的葬礼上/那个身穿重孝、痛哭流涕/守灵7天的侄儿,谁能想到/他此时修炼的不是“悲伤课”/而是“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2]57
作者以轻喜剧的手法去处理红色题材诗歌,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机智果敢,举重若轻地将刀尖上行走、随时会踩到地雷的地下工作者呈现在读者面前。
四、其他叙事技巧的灵活运用
(一)“起”得精彩,“收”得意外
“三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地点、人物、事件,变成相及/只需要一个名字:张耳”(《云盘山古墓、刘邦与背水之战》),这样的开篇,以简练的语言迅速切入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内核,是什么样的风马牛不相及的地点、人物、事件与张耳相及?一下抓住了读者的好奇心,主人公张耳起伏的人生命运便是线索。而“背水之战”便成了张耳和陈余这对本来“相与为刎颈交”的好友命运的分水岭,一个大富大贵,一个兵败身亡。这首诗的结尾“只身南逃、被斩杀于汦水的/白面将军陈余想没想过/害了他的,不是命运/而是一颗嫉妒心”,全诗结束于对历史人物命运的剖析。诗中作者还通过大量细节描写为我们讲述了一个耳目一新的“背水之战”,“起”和“收”都别出新意,凸显了一种历史理性。
(二)虚实结合,以实映虚
虚实相生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大特点,是古代意境理论的核心内涵之一,虚往往由实诱发,虚写部分看不见摸不着,却能让读者从字里行间体味到某种难以言说的境界。实则指客观世界中存在的、被写进诗中的实象、实事和实境。之所以称为“虚实相生”,就是指二者相互渗透、相互转化,达到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的境界,具有开拓诗歌意境,引发读者审美想象的重要意义。田耘的诗歌创作,继承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优秀传统,她的诗中经常采用虚实结合的手法以增强艺术效果。
“1947年11月12日11时的正太饭店/当一杆红旗与一个国家的命运坐标/牢固地插在一个点上”(《石家庄记忆》)中,“一杆红旗”是实,“一个国家的命运坐标”是虚。“当正太铁路线上的第一块晋煤/用十年的时间穿越屈辱的中国近代史”(《石家庄记忆》)中,“第一块晋煤”是实,“屈辱的中国近代史”是虚。
“跨过太行山,一路向西/在石太铁路线上,怀揣一副‘正太铁路’/扑克牌的人,是一个怀揣百年心事的人/取自1913年法国人照片的54张牌上/那些趾高气扬的洋人监工、太原府城门前/与洋人合影的畏手畏脚的清廷官员、/沟渠旁的工人、牵驴的农民,倒映出一部/黑白的中国近代史”(《在石太铁路线上》)中,“正太铁路扑克牌”是实,“百年心事”是虚,洋人监工、清廷官员、工人、农民是实,“黑白的中国近代史”是虚。
这两首诗中,“实”的部分增强了历史真实感,“虚”的部分则以小见大、以虚映实交待了大时代背景,相比一味地宏大叙事,这样的历史代入是亲切的、自然的,也是具有说服力的。
我们再来看一首《永生堂药铺的故事》:
站在兴凯路儿童活动中心北门/向南望,是游人如织、鸟语花香/向北望,是71年前的花园饭店/71年前的悲怆/刮西南风时,市中医院的中药味/就会往东北方向飘/一直飘到不远处的北后街/飘到71年前的/永生堂药铺[2]61
其中今天的“儿童活动中心”是实,“71年前的悲怆”是虚,今天“市中医院的中药味”是实,“71年前的永生堂药铺”是虚。“实”是今日石家庄人熟悉的地点、场景,“虚”是71年前地下工作者利用行医之便获取情报、运送军需物资和药品,舍身取义的烈士事迹,现实与历史在诗中碰撞,一座城市繁荣发展的背后有着无数先烈的斗争与牺牲,一座城市的红色基因理应薪火相传。
(三)第一人称“我”的融入
《石家庄长歌》以叙事为主,田耘的叙事并非零度叙事,在她的叙事中历史事件经作者内化后再次显现时,已悄悄植入了作者的情感。在某些诗中作者全篇或穿插使用了第一人称“我”,而第一人称叙事给读者以亲历感,这种叙事视角的优点是便于作者直接抒情,也能使读者产生一种真实、亲切的感觉,提供一种可以共鸣的视角,容易拉近与读者的距离。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虚拟的/故事发生地暖水屯,等于/涿鹿温泉屯加石家庄宋村/这是家住石家庄南二环/宋村旁的我,抚摸这本书的手/时常有暖流传来的原因之一[2]87
在《石家庄宋村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首诗中,通过家住宋村旁的“我”手上的“暖流”,传递出对新中国土地改革的歌颂。诗中第一人称“我”的使用是诗人主体情感表达的一种方式,身为石家庄人的诗人田耘曾明确表示,她创作《石家庄长歌》的动机,是想让石家庄人认识、熟悉并爱上自己的城市,也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上石家庄这座城市,更想为丰富这座城市的地域文化,激荡起一座城市的人文精神贡献绵薄之力。
历史和地方志是相对客观、冰冷的,然而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却能够让逝去的历史和人物重新鲜活、丰满起来,可以填补历史书籍和简单的历史数据留下的空白,用文艺的形式更好地去记录、传承历史。《石家庄长歌》系列组诗刻画和记录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历史人物与重大历史事件,作者用丰沛的情感赋予诗歌独特的节奏和律动。这样的尝试与探索,创新性地运用诗歌这一艺术创作方式对石家庄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进行了寻根探源式的回溯,增强了读者对这座城市的文化认同,也为城市文化空间的建构增添了厚重的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