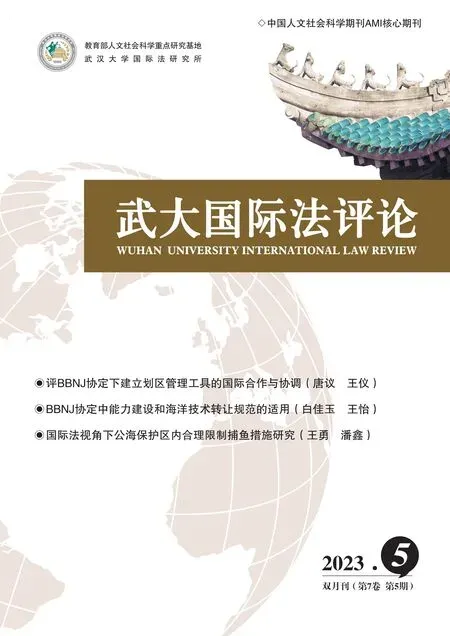《BBNJ协定》争端解决机制评析:自愿、强制抑或另一视角?
林兆然
一、问题的提出
2023 年6 月20 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以下称《协定》)正式案文终获通过,开启了海洋法的一个新纪元。
争端解决机制是《协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争端解决条款的设计也是《协定》谈判的争议焦点之一。从2022 年6 月《协定案文草案进一步修改稿》起,案文中就存在“强制派”(强调沿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留甚至扩张以强制仲裁为代表的强制性法律争端解决机制)和“自愿派”(主张重新设计争端解决条款,以尊重自愿原则的谈判和调解为核心)的两大对立主张。①See UN,A/CONF.232/2022/9,1 June 2022.《协定》通过前,一些观点赞扬该协定草案较完整地沿用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称《公约》)的强制争端解决程序;另一些声音则对这种做法表示保留和异议。在这一“路线之争”的视角下,分析《协定》与其他条约有关条款的异同,可以基本把握《协定》的变与不变。不过,《协定》的新规定和新情况也对旧有“强制vs自愿”的争端解决视角形成了新的挑战。
目前,针对《协定》争端解决机制已有少量研究,时间集中于《协定》正式通过前,内容主要是根据《公约》等条约的设计预测或建议《协定》条文的拟定,①See e.g. Eduardo Jimenez Pineda,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of the Future Third UNCLOS Implementation Agreement on Biodiversity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BBNJ):A Preliminary Analysis, 9 Peace&Security-Paix et Sécurité Internationales,Euro-Mediterran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 (2021); Yubing Shi,Settlement of Disputes in a BBNJ Agreement: Options Analysis, 122 Marine Policy 104(2020).或是介绍《协定》谈判的进展情况。②参见施余兵:《国家管辖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谈判的挑战与中国方案——以海洋命运共同体为研究视角》,《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2 年第1 期;施余兵:《一步之遥:国家管辖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谈判分歧与前景展望》,《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3年第1期。对于《协定》通过后其争端解决机制在海洋法体系中可能产生的影响,目前鲜有系统的研究。本文对《协定》争端解决条款进行逐条分析,重点研究《协定》的争端解决程序(第60 条)、咨询意见制度和防止争端制度。本文试图回答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在“强制性—自愿性”对抗性视角下,如何理解《协定》对争端解决机制的发展;二是是否可以超越“强制性—自愿性”的框架来理解《协定》的新贡献和新可能。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提出中国更好处理相关争端的策略。
二、从《鱼类种群协定》到《协定》的争端解决程序
《协定》第60 条“争端解决程序”是争端解决机制谈判中最具争议的一条。该条10 款案文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即《协定》缔约方争端解决程序的一般适用(前7 款)以及不妨害和不影响条款(后3 款)。既有研究分析了《协定》与《公约》的关联,但对第60 条内部条款的关系,及其与《协定》其他条款、其他海洋条约和现有海洋法司法仲裁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少有涉及。
1995 年《鱼类种群协定》的争端解决条款将《公约》下的强制争端解决机制推向深入,而《协定》相关条款则对前者进行了高度借鉴甚或直接移植。《协定》第60 条强调强制争端解决程序,特别是强制仲裁的核心地位,从而在更大程度上排斥了其他更侧重自愿的争端解决方式。有外国学者指出,对强制争端解决程序的保留是《协定》争端解决机制设计最重要的成果:“最重要的是,《协定》继续允许强制争端解决,因此,根据该协定确定管辖权范围的任务仍将留给法院和法庭”。③Lan Ngoc Nguyen, Danae Georgoula &Alex Oude Elferink, Dispute Settlement Under the BBNJ Agreement: Accepting Part XV of the UNCLOS with a Twist, EJIL: Talk!, https://www.ejiltalk.org/dispute-settlement-under-the-bbnj-agreement-accepting-part-xv-of-the-unclos-with-a-twist/, visited on May 15 2023.这可能代表了大多数“强制派”支持者的心声。①对于认为强制争端解决对《公约》运作和海洋法秩序的形成至关重要的观点,参见Rozemarijn J. Roland Holst, Reflections on the Governance Function of Compulsory Dispute Settlement in the Legal Order for the Ocean,38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 1(2023)。
(一)争端解决程序的一般适用
1.《协定》与《鱼类种群协定》的异同
《协定》第60条前7款的规定高度借鉴《鱼类种群协定》第30条前4款的规定,但两者间也存在一定差异,其中部分差异对强制争端解决程序而言有重要意义。
首先,二者都整体援引了《公约》第十五部分,但方式有很大不同。《鱼类种群协定》对《公约》的缔约国和非缔约国在同一条款中进行同等处理,以“比照适用”(mutatis mutandis)的用语对《公约》第十五部分进行援引式并入(referential incorporation);②See Nigel Bankes,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Dispute Settlement Bodies of the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With Respect to Other Treaties, 52 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 364 (2021). 另外,《鱼类种群协定》第4 条“本协定与《公约》之间的关系”还规定:“本协定应参照《公约》的内容并以符合《公约》的方式予以解释和适用”。而《协定》则将涉及《公约》非缔约国的争端单独设条款处理,并分别使用了两个不同于“比照使用”的用语。
其次,《鱼类种群协定》在更大程度上扩展了《公约》第十五部分的适用范围。《鱼类种群协定》第30 条第2 款将《公约》第十五部分比照适用于与该协定相关的分区域、区域和全球渔业协定的一切解释和适用争端,无论其缔约国是否《公约》缔约国。这种扩大适用既溯及已缔结的有关协定,也含括未来可能达成的有关协定。《协定》则没有类似规定。
最后,《鱼类种群协定》专门规定了关于争端解决的非常广泛的可适用法律,而《协定》中不存在这样的条款。对于《鱼类种群协定》下的争端,可适用的法律除《公约》第293 条所规定的以外,还包括“任何有关分区域、区域和全球渔业协定的有关规定”和“养护和管理海洋生物资源方面的公认标准”。③因此,在《协定》生效后,《鱼类种群协定》的可适用法应包括《协定》,因《协定》可作为“养护和管理海洋生物资源方面的公认标准”;而反之,则不一定。
由此可见,尽管大量移植了《鱼类种群协定》争端解决机制的条文内容,《协定》强制争端解决机制在非《公约》缔约国适用、属事适用范围、可适用法等方面皆秉持较为保守谨慎的态度。
2.《协定》第60条前2款的适用问题
《协定》第60 条第3 款至第7 款围绕《公约》第287 条和第298 条,分别针对《公约》缔约国和非缔约国进行了较为清晰的规定。上文已经提及,第60条第1款和第2款的规定与《鱼类种群协定》有重要区别,值得特别关注。
《协定》第60 条第1 款规定:“应按照(in accordance with)《公约》第十五部分规定的争端解决条款,解决关于本协定解释或适用的争端。”第2 款规定:“为解决涉及非《公约》缔约方的本协定缔约方的争端之目的,《公约》第十五部分和附件五、六、七和八的规定应被视作纳入(replicated)本协定。”①事实上,使用“replicated”表达“纳入”其他条约条款的含义,在现代国际条约的实践中并不常见。“replicated”经常指向的是特定的项目、实践或物件的复制。例见Project Grant Agreement between The Kingdom of Morocco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Job Training for Women,No.18625,1170 UNTS 180(1980).值得注意的是,直到2022 年《协定》草案第五稿,案文仍未区别对待两类国家,而是规定:“应根据有关本协定解释或适用的争端任何当事方的请求,提交争端以便按照《公约》第十五部分规定的争端解决程序作出有约束力的决定,无论争端当事方是否也是《公约》缔约方。”②UN,A/CONF.232/2023/2,2 December 2022,p.38.
而在第五稿之前,对应规定中的用语则是“比照适用”(mutatis mutandis)。施余兵教授指出:“中方表明了‘比照适用’这一表述存在的含义不确定性以及相关国际裁判实践的缺乏。随后,大会主席……删除了‘比照适用’这一术语。”③施余兵:《一步之遥:国家管辖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谈判分歧与前景展望》,《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3年第1期,第47页。“比照适用”条款在一些与《公约》相关的国际条约的争端解决机制中常有出现。例如,《鱼类种群协定》第30 条第1 款和第2 款规定了两类对《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比照适用”。还有一些条约则“比照适用”了《鱼类种群协定》的争端解决机制,例如2000 年《西部与中部太平洋高度洄游鱼类养护与管理公约》第31 条、2009 年《南太平洋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公约》(以下称《南太公约》)第34条第2款、2012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公约》第19 条和2018 年《预防中北冰洋不管制公海渔业协定》第7 条。不过,截至目前,这些争端解决条款都没有被其缔约国援引过,也没有在国际司法实践中得到检验。
如果说“按照”条款是一种参考规则(rules of reference),是有机地援引外部规则的嵌入机制(built-in mechanism),④See Ke Song, Liberal or Constrained? Judicial Incorporations of Other Ru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UNCLO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Genuine Link Test”, 13 Journal of East Asia and International Law 166(2020).“纳入”条款则代表一种更机械的复制与挪用。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3款丙项,在同时是《公约》缔约国的《协定》缔约国之间,对于《协定》第60条第1款具体适用问题的解释,整个《公约》都属于“适用于当事国间关系之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协定》的解释可以引入更庞大的规则体系。而对涉及《公约》非缔约方的争端,则不存在这种情况。因此,相比于“比照适用”,当前的条款可能将更好地保护非《公约》缔约国的有关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土耳其、美国等国的关切。①See UNGA Document:Textual Proposals Submitted by Delegations by 25 July 2022,for Consideration at the Fifth Session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on an International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the Conference),in Response to the Invitation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Conference in Her Note of 1 June 2022(A/CONF.232/2022/5),Article-by-Article Compilation,A/CONF.232/2022/INF.5,1 August 2022.
3.《协定》第60条下的强制管辖权
无论是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还是《公约》附件七下的仲裁庭,其有关管辖权实际上都直接源于《公约》第288 条。根据该条第2 款的规定,法院或法庭的强制性管辖权要件至少包括以下三点:一是所依据的国际协定与《公约》的目的相关;二是程序的提出符合该国际协定本身的规定;三是争端源于对该国际协定的解释或适用。就《协定》而言,判断是否具有管辖权的关键在于判断第二点是否成立,这主要又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满足《协定》第九部分其他条款规定的条件或限制,主要是第58 条、第59 条以及第60 条第8 款至第10 款的各类规定;另一方面,就《公约》而言,应符合《公约》第十五部分第一节的一般规定,且不属于第三节规定的限制和例外。
对国际海洋法法庭来说,强制管辖权条件的满足可能更为容易。《国际海洋法法庭规约》第21 条规定:“法庭的管辖权包括按照本公约向其提交的一切争端和申请,以及将管辖权授予法庭的任何其他国际协定中具体事项的一切申请。”根据该规定,该法庭的管辖权可以延伸到其他国际协定中规定的任何事项(matters),而不仅是关于条约解释和适用的争端。该法庭如被选为争端解决法庭,则有可能处理一般被认为是《公约》和《协定》范围以外的法律事项,如一般国际法问题。②See Responsibilities and Obligations of States Sponsoring Persons and Entities with Respect to Activities in the Area,Case No.17,ITLOS Reports,2011,p.56.
即使抛开国际海洋法法庭的独特规定,《公约》属事管辖权在实践中的扩张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现象,而这类实践无疑又会对《协定》争端解决机制的理解产生影响。以《公约》第293 条“适用法律”的实践为例,尽管原则上,适用的法律属于实体法律问题,不能用于扩张管辖权,③See Peter Tzeng, Jurisdiction and Applicable Law under UNCLOS, 126 Yale Law Journal 260(2016).但位于《公约》第十五部分的该条由于规定可以适用“其他与本公约不相抵触的国际法规则”,在实践中已屡次成为事实上扩张属事管辖权的法律依据。④参见廖雪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项下法庭与仲裁庭属事管辖权的扩张》,《环球法律评论》2022年第6期,第180-182页。由于《协定》本身并未对适用的法律进行任何规定,在启动强制争端解决程序时,关于适用的法律的问题将完全根据《公约》确定。国际海洋法法庭法官特雷弗斯(Treves)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适用的法律不应包括整个《公约》的条款,而只是直接关于涉案协定争端的条款。①See Tullio Treves, A System for Law of the Sea Dispute Settlement, in David Freestone, Richard Barnes&David Ong(eds.),The Law of the Sea:Progress and Prospects 428(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然而,这种相关性的判断仍属于法院或法庭的裁量范围。更激进的立场可能认为,适用的法律包括争端所涉协定的条款、整个《公约》、其他与《公约》不相抵触的国际法规则。②See Tullio Treves, A System for Law of the Sea Dispute Settlement, in David Freestone, Richard Barnes & David Ong (eds.), The Law of the Sea: Progress and Prospects 427-42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当前,《协定》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定很可能进一步鼓励这种扩权行为。
(二)例外与限制:不妨害和不影响条款
《协定》第60 条第8 款至第10 款分别从三个方面着手对强制争端解决程序起到了“限制阀”的作用。
1.其他法律文书或框架下争端解决程序的影响
《协定》第60 条第8 款规定:“本条的各项规定应不妨害作为相关法律文书或框架参与方或相关全球、区域、次区域或领域机构成员的缔约方,就这些文书和框架的解释或适用所同意的争端解决程序。”它可能意味着“相关法律文书或框架下的争端解决程序不受《协定》相关争端解决程序所得结果的影响”③Lan Ngoc Nguyen, Danae Georgoula &Alex Oude Elferink, Dispute Settlement under the BBNJ Agreement: Accepting Part XV of the UNCLOS with a Twist, EJIL: Talk!, https://www.ejiltalk.org/dispute-settlement-under-the-bbnj-agreement-accepting-part-xv-of-the-unclos-with-a-twist/, visited on May 15 2023.。相比于《鱼类种群协定》第30 条第2 款,《协定》的这款“不妨害”规定,理论上对其他相关的组织、机构和安排等给予了足够的尊重,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国家自愿选择原则。
然而,《协定》第60 条第8 款所规定的“不妨害”只针对“争端解决程序”。这种“争端解决”可能是相当狭义的,甚至可能不包括第56 条“防止争端”的方式和手段。参考《公约》第281 条第1 款规定的管辖排除协议,这类争端解决的协议通常也需要满足很严格的标准,才能排除《公约》下争端解决机制的管辖权。④See Hayley Roberts, Identifying“Exclusionary Agreements”: Agreement Type as a Procedural Limitation in UNCLOS Dispute Settlement,52 Ocean Development&International Law 113-142(2021).因此,第8 款所指的“争端解决”可能不会尊重其他形式的争端管控和处理,例如“不解决争端”(non-settlement of disputes)的安排。⑤关于“不解决争端”的安排,可参见Peter Tzeng,The Peaceful Non-Settlement of Disputes:Article 4 of CMATS in Timor-Leste v Australia,18 Melbourn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72(2017).关于“不解决争端”的形式,另可参见黄瑶:《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和平搁置争端》,《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第118-124页。在2018 年东帝汶提起的与澳大利亚的涉海洋划界强制调解案中,国际条约的管辖权排除效力并未得到认可。东帝汶与澳大利亚曾经签订了搁置和冻结争议、不提交强制争端解决措施的协定,澳大利亚因此主张东帝汶无权将争端提交强制调解,①See Timor Sea Conciliation (Timor-Leste v.Australia), Decision on Australia’s Objection to Competence,19 September 2016,PCA Case No.2016-10,pp.3-4,paras.15,17.但调解委员会却在其管辖权的裁定意见中认为,《公约》只尊重其他“解决争端”的方式,而不是“不解决争端”的方式。②参见杨文澜:《〈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强制调解第一案——“东帝汶与澳大利亚强制调解案”述评》,《国际法研究》2018年第3期,第56-59页。换言之,即使有关机构和安排中规定了有法律约束力的搁置争端条款,也可能无法影响未来《公约》和《协定》下强制争端解决程序的进行。
2.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争端的排除
《协定》第60 条第9 款规定:“本协定中的任何规定均不得解释为授予某一法院或法庭对关于或必然涉及同时审议国家管辖范围以内区域法律地位的任何争端的管辖权,或对关于本协定缔约方对大陆或岛屿陆地领土的主权或其他权利或有关主张的任何争端的管辖权,前提是本款的任何规定均不得解释为限制某一法院或法庭根据《公约》第十五部分第二节享有的管辖权。”对比之前草案的内容,③参见《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就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拟订的协定案文草案进一步刷新稿》,A/CONF.232/2023/2,2022年12月2日。该款一方面增加了排除特定争端管辖权的规定,另一方面又加入了不限制管辖权的“前提”。
比较明确的是,《协定》第60 条第9 款排除了与大陆或岛屿领土权利相关争端的管辖权,包括附带性的管辖权,以应对《公约》强制争端解决机制下法院或法庭扩张有关管辖权的现象。④扩大现象可以分为“争端与《公约》条款的不当联结”“对《公约》外部事项的管辖”和“对《公约》外部规范的适用”三大维度,参见廖雪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项下法庭与仲裁庭属事管辖权的扩张》,《环球法律评论》2022年第6期,第180-182页。此处主要涉及的是第二类。2023年3月4日通过的《协定》草案将“任何未决争端”改为“任何争端”。近年来,国际司法或仲裁机构可能会激进地认定某些争端已经得到解决或不存在,以排除管辖权上的障碍。例如,国际海洋法法庭在2021 年毛里求斯与马尔代夫海洋划界案的管辖权裁决中指出,毛里求斯与英国之间关于查戈斯群岛的领土主权争议,已经被国际法院审理的查戈斯群岛咨询案所解决,因而不会妨碍其管辖权。⑤See Dispute concerning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Mauritius and Maldives in the Indian Ocean(Mauritius/Maldives),ITLOS,Preliminary Objections,Judgment of 28 January 2021,pp.72-73,para.246.这种处理方式引起了不少的批评。⑥例见高健军:《谁解决了查戈斯群岛的主权争端?——“毛里求斯与马尔代夫海洋划界案”初步反对主张判决评析》,《国际法研究》2021年第5期。不过,一个“已决争端”是否法律上的“争端”?如果法院或法庭认为某两国间争端已被解决,那么两国之间的法律状况是不存在争端,还是存在一个“已决争端”?实践中,答案可能更倾向于前者。因此,将“未决”删去是否足以遏制这类管辖权扩张的倾向,犹未可知。
“国家管辖范围以内区域法律地位”也类似地排除了大多数对海洋空间的管辖权及其主张的管辖权。然而,这一部分必然与“限制某一法院或法庭根据《公约》第十五部分第二节享有的管辖权”的前提相关。如何解读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强制争端解决程序适用的一个关键点。
3.一条特殊的限制条款:第60条第10款
第60 条第10 款规定:“为避免疑义,不得以本协定的任何规定为依据,提出或否认对陆地或海洋区域的任何主权、主权权利或管辖权主张,包括与此有关的任何争端。”该款规定最早出现在2023 年3 月4 日通过的《协定》草案,是最后一刻加入的条款,其内容主要来自一些拉美国家的条款提案。
从条文上看,第60 条第10 款并不仅仅旨在规定争端解决事项,而是更类似于《协定》的一条基本原则。它出现在当前第60 条最后一款位置,很可能是匆忙完成谈判的结果。比起第60 条第9 款,第10 款无论是用语还是句式结构都更接近于《协定》其他部分的一些规定,比如,“一般规定”部分的第6 条“不妨害”规定和关于划区管理工具适用范围的第18条规定。
在原则性条款中,《协定》一般强调的是不影响“任何主权、主权权利或管辖权主张”。但在争端解决条款中,此前草案的多个版本强调的都是“大陆或岛屿陆地领土的主权或其他权利或有关主张”。在这种规定下,一些独立主张的海域权利无法被包括进去。①例如,历史性权利和历史性所有权是否属于一种依赖于陆地存在的海洋权利,目前并未有定论。See Clive R.Symmons,Historic Waters and Historic Rights in the Law of the Sea:A Modern Reappraisal 102-103(Brill/Nijhoff 2019).从这个角度上看,在争端解决部分加入第10 款可能是无奈但必要之举。
总而言之,从基本设计上看,《协定》在强制性争端解决程序上的立场确实承继了《公约》和《鱼类种群协定》。以自愿性和调解为主的方案虽未占上风,但也对强制性争端解决程序施加了一定限制。不过,这些限制条款仍然为管辖权的扩张留下了相当的解释空间。仅从这一角度看,《协定》确实仍是“强制派”的胜利。
尽管在理论上讲,《协定》争端解决机制存在着被滥用的可能,但现实中这种情形却并不一定会发生。截至目前,直接或间接、全部或部分适用《公约》争端解决条款的海洋条约为数众多,但最终通过强制性程序处理有关争端的实践则寥寥无几。而且,《协定》本身更具科学性和政策性,大量问题需要由专门机构或专家委员会处理,国家对传统争端解决模式的运用意愿也会降低。《鱼类种群协定》以及相关渔业组织条约的实践就是很好的例子。
当前,在渔业养护和管理问题上,相比于传统的诉讼和仲裁,国家可能更倾向于运用“软性”但覆盖面更广的程序,比如咨询意见或国际组织内的特殊争端处理程序,后者包括防止争端程序。
三、《协定》咨询意见制度的影响:强制管辖权的“再扩张”?
国际性司法机构行使咨询管辖权是近年的理论和实践热点,在国际海洋法法庭尤为如此。小岛屿国家委员会最近在该法庭提起的咨询意见案更是引发了激烈争论。在国际海洋法法庭是否拥有咨询管辖权,以及该法庭能在咨询意见中发表什么内容这两大问题上,学者们的意见产生了重大分歧。①See Richard Barnes, An Advisory Opinion on Climate Change Oblig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A Realistic Prospect?, 53 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 180 (2022); Alina Miron, COSIS Request for an Advisory Opinion:A Poisoned Apple for the ITLOS?, 38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 1 (2023); Monica Feria-Tinta, On the Request for an Advisory Opinion on Climate Change under UNCLO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14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391 (2023); Benoit Mayer, International Advisory Proceedings on Climate Change, 44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1(2023).《协定》专门规定了向国际海洋法法庭全庭提请咨询意见,这在普遍性多边条约中尚属首次。从当前趋势看,这一程序越来越从经过多方合意的机制演变为一种实质上的强制司法机制。因此,《协定》这一规定似乎对强制管辖权进行了某种“再扩张”。这一情况对国际海洋法法庭以及各国的立场都可能产生重要影响。
《协定》第47 条“缔约方会议”第7 款规定了咨询意见制度。该条款被《协定》草案第五稿从争端解决部分中移出,被安排在“体制安排”部分,凸显了缔约方大会的职能。根据该条第5 款的规定,缔约方大会请求提供咨询意见,应经过协商一致,或在无法达成协商一致的情况下,采取2/3 多数决的方式作出决定。虽然存在以紧急事项的形式绕过正常的缔约方大会决策程序的可能,但在实践中,上述规定已经足以构成对滥用咨询意见制度的限制。
(一)国际海洋法法庭的态度
第47 条产生的问题可能更多在《协定》之外。尽管有上述限制,国际海洋法法庭仍有较大空间去扩张其审议的事项。根据《国际海洋法法庭规约》第21 条(也可能涉及第22 条),其咨询管辖权可能涉及《协定》“具体规定的一切申请”;而且,根据《国际海洋法法庭规约》第23 条,国际海洋法法庭将适用《公约》第293 条,即包括《公约》整体和其他与《公约》不冲突的国际法规则。易言之,《协定》下缔约方大会提出的请求范围可能是非常有限的,但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实际审议却有可能超出这些范围。
根据《国际海洋法法庭规则》第138 条第1 款,国际海洋法法庭全庭行使咨询管辖权只需要一项与《公约》目的相关的国际协定,且该协定赋予实体向国际海洋法法庭就某一法律问题请求咨询意见的权力。在当前已向国际海洋法法庭全庭提请咨询意见的两次实践中,作为提出方的西非次区域渔业委员会只有7 个成员国,而小岛屿国家委员会则仅由安提瓜和巴布达、图瓦卢两个国家成立(目前仅有6 个成员国)。《协定》显然完全满足这两项要求,而国际海洋法法庭也倾向于接受更广泛的咨询案来源。
(二)《协定》缔约方的可能应对方式
对于国家而言,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各国自身对国际海洋法法庭全庭咨询管辖权的态度问题。国际海洋法法庭全庭的咨询管辖权由于缺乏明确的《公约》和《国际海洋法法庭规约》条文基础,仍然存在较大争议。不少国家都对这种咨询管辖权持反对态度。①对此,中国一贯明确表示反对。See Request for an Advisory Opinion Submitted by the Sub-Regional Fisheries Commission (SRFC) (Request for Advisory Opinion Submitted to the Tribunal), ITLOS,Written State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6 November 2013; Request for an Advisory Opinion Submitted by the Commission of Small Island States on Climate Change and International Law (Request for Advisory Opinion Submitted to the Tribunal), ITLOS, Written State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5 June 2023.美国、英国、法国、爱尔兰、西班牙、阿根廷等国也均表达过反对。
《协定》是第一份明确赋予国际海洋法法庭全庭咨询管辖权的普遍性条约,在理论和实践上,对这类管辖权作出了一次重要背书。由于《协定》不允许保留,各国如批准或加入《协定》,也必然需要接受这一条款。这可能对反对这类管辖权的国家立场产生一定的冲击。
因此,一个可能的情况是,在批准或加入《协定》时,国家会借此机会表明对国际海洋法法庭全庭咨询管辖权的态度。例如,在国家声明中表明:该协定是经过广泛的国家合意、就特定海洋事项规定的特例,不能被视为对这种咨询管辖权的一般性认可。一国批准或加入《协定》,并不代表同意国际海洋法法庭接受咨询管辖请求的“低门槛”做法。有关国家可以相反的思路提出主张,即《协定》的这一规定恰恰说明:这种管辖权应该且只能基于权限明确、世界各国普遍参与且与《公约》密切联系的国际条约的授权,而不应通过国际海洋法法庭内部文件进行一揽子授权;这种咨询管辖权也应该严格在《协定》规定的条件下行使,尤其是不能以任何形式触及领土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主张和争端。
《协定》关于咨询意见的规定确实为国家采用一种变相的强制性争端解决方式提供了可能,国际海洋法法庭也很可能会积极利用这种状况进一步扩大其管辖权。不过,对这种管辖权持反对意见的国家也可能借此进一步主张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咨询管辖权应受条约条文的严格限制。《协定》对整个咨询意见制度乃至海洋法争端解决机制产生的影响仍有待观察。
四、理解《协定》争端解决机制的另一个视角:防止争端制度
《协定》参照《鱼类种群协定》规定了争端处理的特殊方式,主要包括第56 条“防止争端”和第59 条“技术性争端”。尽管海洋法中的防止争端制度至少可以追溯到20 年前,对这一制度的法律分析却相对有限。一些研究从争端解决角度注意到了防止争端作为一种准法律手段的潜力。①See Andrew Serdy,Implementing Art.28 of the UN Fish Stocks Agreement:The First Review of a Conservation Measure in the South Pacific Regional Fisheries Management Organisation,47 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 1 (2016); Rosemary Rayfuse, Settling Disputes in Regional Fisheries Management Organisations: Dealing with Objections, in H. R. Fabri, et al. (eds.),A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s: Dispute Resolution in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Watercourses and the Law of the Sea 240-276(Brill 2020),etc.大部分研究仅关注传统的国际诉讼和仲裁,倾向于将“防止争端”视为一种国际组织和机构内部的执行政策问题,却忽略了其作为一种替代性或平行性争端处理手段的重要功能。在对《协定》争端解决机制的讨论中,这一部分也常被轻视。分析这一制度规定的细节,可以为我们带来对《协定》争端解决机制理解的另一个视角,摆脱“强制性—自愿性”的简单二元对立思维。
(一)防止争端与技术性争端解决
《协定》第56 条规定:“缔约方应开展合作,以防止发生争端”,但未对“防止争端”(prevention of disputes)②《鱼类种群协定》中表述为“预防争端”。为理解和阅读便利,本文将有关表述统一为《协定》所用的“防止争端”。进行界定。相比之下,《鱼类种群协定》第28 条有着更明确的规定:“为此目的,各国应在分区域和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内议定迅速有效的作出决定程序,并应视需要加强现有的作出决定的程序。”这一规定当然并非对“防止争端”的穷尽性描述。“防止争端”和“解决争端”之间的界限并不明确。③有学者认为,《鱼类种群协定》第28 条中的“防止争端”与争端解决机制应该明确区分。See Andrew Serdy,Implementing Article 28 of the UN Fish Stocks Agreement:The First Review of a Conservation Measure in the South Pacific Regional Fisheries Management Organisation, 47 Ocean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Law 1(2016).另有一些观点则对此不作严格的区分。《鱼类种群协定》第29 条和《协定》第59 条都规定,如涉及技术性争端,缔约方可设立特设专家小组,在不诉诸有约束力的争端解决程序的情况下迅速解决争端。虽然这两条都使用了“解决争端”用语,但其根本目的在于避免细节性和技术性的争端上升为法律争端,尽量在组织机构内完成这些争端的处理。而且,许多技术性争端往往是关于标准的设置或具体数额的分配,涉及多个国家乃至所有缔约国,很难被归类为传统国际法意义上的“争端”。因此,这些机制在严格意义上可能更接近于“防止争端”。
(二)作为防止争端手段的决策机制
对《协定》而言,除了第59 条外还存在何种防止争端的法律机制?《鱼类种群协定》第28 条提供了重要参考。虽然《协定》不应干预分区域和区域渔业管理组织,但反过来,《协定》缔约方完全可以积极利用这类组织的机制,防止关于《协定》争端的发生。《协定》多次提及与各层次不同机构的关系,不仅是明确“不妨害”的关系,也是提出互相协调的要求。因此,各国在相关组织机构中以有效的程序防止争端的产生,应是《协定》认可乃至鼓励的做法。
1.《协定》中现有的决策程序
《鱼类种群协定》第28 条提到的“迅速有效的作出决定程序”及其加强,涉及运作良好的决策程序。对于技术性较强的事务,决策程序需要兼顾时效性和公平性,在国家自愿和国际公共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协定》在划区管理工具和环境影响评价部分规定了专门的决策条款,但只在关于划区管理工具的第23 条规定了机构性的决策程序。该条主要包括两大部分:决定的通过和生效;对决定的反对(objection,又可译为“异议”)及其后续处理。鉴于本文关注争端解决机制,此处只讨论更为相关的对决定的反对问题。
《协定》第23 条的规定与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的决策机制是高度类似的。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或安排最核心的职权职责是通过渔业养护与管理决定或决议,对渔业的配额、捕捞时间、工具使用等问题进行规定。在决定生效后,基于对国家自愿的尊重,一般允许国家提出反对,以拒绝接受关于渔业养护与管理决议的约束。然而,如果国家提出反对的权利不受限制,养护与管理决定的实际效果可能会受到负面的影响。因此,对反对的提出通常存在各项条件和限制,具体分为以下几类:①参见林兆然:《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的异议审查机制——南太平洋区域渔业管理组织两起捕鱼配额异议案述评》,《国际法研究》2019年第3期,第45页。只有提出反对的时间限制;需要反对国说明反对理由,并提出等效性措施;需要反对国提出条约规定的反对理由,并提出等效性措施。《协定》采取了其中较严格的限制。首先,《协定》规定了三项理由,分别是决定与《公约》不符、对反对方存在形式或事实上的歧视,以及反对方确实无力遵守,并要求“反对应以下列一项或多项理由为依据”。其次,反对方应在不违反《公约》的情况下,“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采取与其所反对的决定具有同等效果的替代措施或办法,并且不应采取损害其所反对的决定有效性的措施或行动”。最后,《协定》要求反对方就其替代措施等后续行为进行定期报告,并且对反对的续展作出了规定。
2.《协定》决策程序的可能完善方向
《协定》的规定在借鉴现有实践的基础上,在国家主权和国际公共利益之间取得了一定的平衡。然而,从决策程序还肩负防止争端任务的角度来看,它可能还存在有待完善之处。《协定》只要求反对国定期提交报告,而没有给其他缔约国以及缔约方大会以充分表达意见的渠道,减少了多方参与对话从而纾解分歧的可能性,有可能引发更多的争端。在这方面,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的实践可能可以提供不少值得借鉴的经验。例如,一些区域渔业管理组织规定了对反对进行专门审议的机制。例如,在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中,经反对国提出请求,可以组成审查专家组对反对及其针对的决定进行审议;①See Convention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Highly Migratory Fish Stocks in the Western and Central Pacific Ocean,Art. 20, https://www.wcpfc.int/doc/convention-conservation-and-management-highly-migratory-fish-stocks-western-and-central-pacific,visited on 15 March 2023.在西北大西洋渔业组织中,反对国同样可以提请审议,但如果其不提起审查请求,该组织则可以自行决定是否组成有关专家组进行审议;②See Convention on Cooperation in the Northwest Atlantic Fisheries,Art. 14, https://www.nafo.int/Portals/0/PDFs/key-publications/NAFOConvention.pdf,visited on 15 March 2023.南太平洋区域渔业管理组织(以下称“南太渔业组织”)对这种审议机制的支持最为明显,其规定,当一国在期限内对决定提出反对后,审议专家组的程序就自动启动。③See Convention on the Conservationand Management of High Seas Fishery Resources in the South Pacific Ocean,Art. 17 (2), https://www.sprfmo.int/assets/Basic-Documents/Convention-and-Final-Act/SPRFMO-Convention-2023-update-12May2023.pdf,visited on 15 July 2023.南太渔业组织也是唯一进行过这一机制实践的组织,截至目前已有三个审议案例。南太渔业组织专家组的审查内容可以分为程序部分和实体部分,以及反对国提出的替代性措施是否与原决定等效。综合以上审查结果,审查专家组将根据不同情况作出有拘束力的裁决与建议。该审议程序的一大特点是南太渔业组织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和委员会本身都有权提交备忘录(书面环节)并在庭审上(口头环节)对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发表意见,且应得到专家组的考虑。这一机制兼具争端解决和防止争端的功能,不仅起到了缓和各成员国分歧的作用,还充当了类似于“司法审查”的功能。考虑到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和机构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这些组织也需要特定机制的监督。在这种大背景下,有关渔业组织的实践不仅提供了一种更高效、经济的替代性争端处理方式,还强化了各成员国的参与以及与国际组织间的互动。如果这类机制无法解决问题,它也可以为传统的争端解决程序做好铺垫和准备。①参见林兆然:《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的异议审查机制——南太平洋区域渔业管理组织两起捕鱼配额异议案述评》,《国际法研究》2019年第3期,第61页。
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实践中的一些经验可能值得参考,以助力完善《协定》项下的机构制度。这些制度设计也可能惠及未来相关组织机构的设立。这些经验可能包括:其一,在高度专业化和技术化的问题上,坚持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避免治理问题形式化、政治化;其二,在监督国家的同时,加强对组织和机构的监督和问责,特别是应该避免将组织运作的问题包装为国家间的争端。对争端的解决也好,防止也罢,对争端的认知和处理既不应“反专业化”,试图用法律方式解决所有问题,也不能盲目地维护“专家之治”(technocracy),使其免于公平性和正当性的检验。
总而言之,防止争端制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并非“强制性—自愿性”二元对立的视角,它作为一种结合了法律性和技术性的替代性措施,在多方面存在良好的制度潜力。借助《协定》的实施,这一制度值得进一步的实践发展和理论深化。
五、结语:我们如何迎接《协定》的争端解决机制?
随着《协定》案文的通过,世界可能即将迎来一个全球海洋治理的新纪元。这种新景象同样出现在争端解决机制中。《协定》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公约》和《鱼类种群协定》的争端解决机制,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是海洋法下强制争端解决的一次“新胜利”。这一结果可能并不符合不少国家强调独立性和自愿性的意愿。鉴于上文的分析,我们应当认识到,仅运用“强制性—自愿性”的二元视角去理解《协定》是不够的。
对我国而言,《协定》争端解决机制的未来运行可能存在两大重要愿景:一是切实高效地解决具体矛盾;二是避免各种形式的滥诉行为。这两个目标相互独立,但又紧密联系。同时,这也对我们提出了如下方面的问题:
首先,如何拟定批准或加入《协定》时的一般性声明。其中可能涉及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第一,《协定》不适用于南海断续线内区域,不能用于解决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有关主张和争端,也不能以任何形式赋予任何法庭以司法或仲裁的管辖权;第二,《协定》的争端解决机制不应影响其他国际文书和机制中关于争端处理的规定和安排,而不仅是狭义的“争端解决”,不应忽略和越过国家间达成合意的其他争端处理方式;第三,表明对国际海洋法法庭全庭咨询管辖权的态度,《协定》不能被视为对其咨询管辖权的一般性认可。中国批准条约并不代表同意国际海洋法法庭接受咨询管辖请求的“低门槛”做法,反而是重申这种管辖权应该基于权限明确、世界各国普遍参与且与《公约》密切的相关文件的授权。这种咨询管辖权也应该严格在《协定》规定的条件下行使,不能以任何形式触及领土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主张和争端。
其次,是否考虑在《协定》中声明选择的争端解决程序。在加入《公约》时,我国并未声明接受哪类争端解决程序,在《公约》规定下,这被视为默认接受附件七仲裁为争端解决方法。如果在加入《协定》时不另作声明,我国将继续面临相同的不利局面。由于沉默不能被视为拒绝任何一种争端解决程序,进行战略性的选择可能更有助于把握主动权。《公约》缔约国可以作出与《公约》不同的争端解决程序选择声明,单独适用于《协定》的问题。因此,可以考虑在《协定》中选择相对更权威、公正和谨慎的国际法院,体现我遵守国际法、维护国际法律秩序的努力,也避免继续表现出默认选择《公约》附件七仲裁的态度。
最后,是否积极推动建设防止争端机制。要革新理论和实践的体系,就不应仅在争端解决问题上采取单纯的防御姿态,而应积极探索更合理务实的做法。因此,我们可能需要把更多精力放到对防止争端机制的解释、建设和运用上。《协定》第23条的规定是防止争端制度的重要部分,但目前其规定还相对简单,需要后续进一步完善。例如,可以借鉴特定专家组审议机制,既避免诉诸传统上耗时费力的司法和仲裁程序,同时又能比较有效地处理全球海洋治理中的争议。可以考虑积极推动防止争端和技术性争端解决机制的有效联动,在后续工作中推进和完善这些机制的具体建设,把握话语权上的主动,以求建立高效、公平、科学的替代性机制,既避免不必要甚至恶意的诉讼,也可切实促进争端的最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