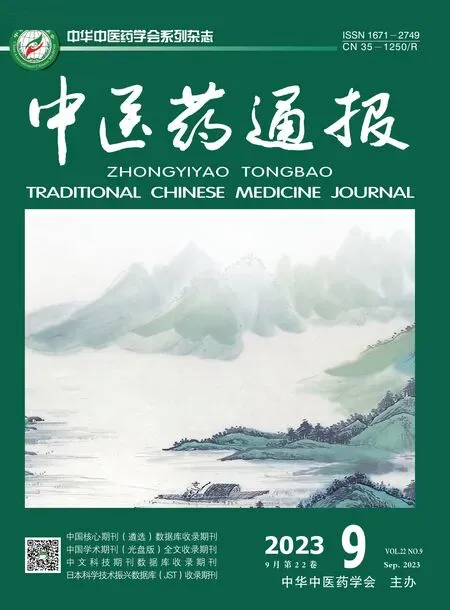黄芩汤证治初探※
方艺伟 丘余良
黄芩汤出自《伤寒论》,由黄芩、芍药、炙甘草、大枣四味药物组成,原文记载:“太阳与少阳合病,自下利者,与黄芩汤,若呕者,黄芩加半夏、生姜汤主之。”其论述十分精简。后世医家依此发挥,演变出许多治痢之方,如张洁古的芍药汤、朱丹溪的黄芩芍药汤等,清代汪昂则称本方为“万世治痢之祖”。笔者认为,黄芩汤临床应用范围并非局限于此,如田氏[1]通过对黄芩汤类方的古代文献进行总结,认为其可用于发热性疾病、下利、便秘、衄血、吐血、便血、尿血、诸痛证、黄疸、痘疹疮痈、眼科疾病、妇科经、带、胎、产及儿科多种疾病的治疗。因原文对黄芩汤论述极少,历代对其认识仍未统一,故本方之主治病机、配伍要点、临床应用等仍有待进一步挖掘。
笔者通过比较小柴胡汤与黄芩汤在出入升降、寒热虚实方面的不同之处,以研究黄芩汤的组方意义;并通过分析“合病”的内涵及其与黄芩汤的内在联系,探讨黄芩汤的六经定位及证治特点,试从中找到黄芩汤之本意;同时,结合相关临床医案进行阐述,以求提高临床辨证的准确性与灵活性。笔者学识有限、临床经验不足,不正之处望不吝批评指正。
1 少阳非皆小柴胡,胆热火郁黄芩汤
1.1 枢机不利,出入有别《说文解字》曰:“枢,户枢也。”户枢指转轴[2],取类比象枢之功能如门之转轴,沟通、维系着事物的运动,正如《管子·水地》中“其枢在水”注释为“枢,主运转者也”,而“少阳为枢”于《素问·阴阳离合论》首次被提及,原文曰:“三阳之离合也,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三阴之离合也,太阴为开,厥阴为阖,少阴为枢。”少阳因不在表亦不在里,其居表里之间而为“枢”,张景岳则认为:“少阳为枢,谓阳气在表里之间,可出可入,如枢机也。”因其“可出可入”,故欲调少阳枢机,须知有“出”“入”之别。
偏于出之不得者,当和转而升散,此小柴胡汤所适之证。小柴胡汤以八两柴胡为君药,助枢机和转而升散调达,正如柯韵伯于小柴胡汤解中所言:“柴胡感一阳之气而生,故能直入少阳,引清气上升而行春令,为治寒热往来之第一品药。少阳表邪不解,必需之。”虽方中亦有苦寒清降之黄芩,但其并非方中主药,如原文之加减法提到“若腹中痛者”“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皆去黄芩,由此可知黄芩是为枢机不利,郁而不伸,气郁化热而设,故可随证去之,此正如柯韵伯[3]所言:“本方七味中,半夏、黄芩俱在可去之例,惟不去柴胡、甘草。当知寒热往来,全赖柴胡解外、甘草和中。”
偏于入之不能者,当和转而降收,当与黄芩汤为宜。证属枢机不能和转而降收之人,多见火盛之象,如口苦、咽干、目眩、舌红苔黄、脉弦数等症,犹如天地有春夏而无秋冬,火行天地之间,于人体而言则是火邪内盛之象。
1.2 不离八纲,寒热虚实柯韵伯[3]言:“言往来寒热有三义:少阳自受寒邪,阳气衰少……一也;若太阳受寒,过五六日,阳气始衰……二也;风为阳邪,少阳为风脏,一中于风便往来寒热,不必五六日而始见,三也。”此即言小柴胡汤治疗因正气不支、血弱气尽,风寒之邪入侵少阳,枢机凝滞之证。而黄芩汤较之小柴胡汤,既无大补元气之人参,亦无辛温苦燥之半夏与辛温散寒之生姜,而以苦寒之黄芩与酸寒之白芍为主药,故其乃偏于治实证、热证,正如《伤寒论》第333条所言:“伤寒脉迟六七日,而反与黄芩汤彻其热,脉迟为寒,今与黄芩汤,复除其热,腹中应冷,当不能食,今反能食,此名除中,必死。”由此可见,黄芩汤确为彻其热邪而设定,此即寒热之辨。
纵观小柴胡汤、黄芩汤之药物组成,小柴胡汤含柴胡、生姜、半夏等辛散之品,其偏于透邪外出,再合以人参,故偏升散且燥又能益气。《长沙药解》曰:“人参气质淳厚,直走黄庭,而补中气。中气健运,则升降复其原职,清浊归其本位,上下之呕泄皆止,心腹之痞胀俱消。”小柴胡汤入人参而补中气,中气健则气机之升降出入调和,配柴胡则助其和解而升散达邪。黄芩汤以黄芩为君药,又配有酸寒之芍药,可清泻胆火、养阴和营,故偏降收而润又能养阴,如郑钦安于《医理真传》所言:“芍药甘草汤一方,乃苦甘化阴之方也……苦与甘合,足以调周身之血……凡属苦甘、酸甘之品,皆可以化阴。”故黄芩汤入芍药可助其和解而降收之,益其津液而熄火邪。因此笔者认为,小柴胡汤偏升散温燥之功而适用于气虚者,黄芩汤偏降收凉润之功而适用于津亏者。
1.3 验案举例杨某,女,48 岁,2019 年5 月6 日初诊。主诉:心烦易怒3 天。患者近日心烦易怒,伴情绪低落难以控制,多思多虑,口苦,口干,头晕,自觉浑身酸痛,项强,不欲饮食,恶心欲吐,难以入睡,寐时梦多,小便黄,大便不畅。舌质红,苔黄少津,脉弦数。中医诊断:郁证,辨为少阳火郁,津液不足证。处方予黄芩汤加减,药用:黄芩12 g,白芍10 g,炙甘草3 g,大枣10 g,生姜3片。3剂,水煎服,每日1剂,早晚饭后分服。
服用至第二剂,情绪即较前稳定,其余诸症亦较前缓解,尔后以调和肝脾之方善后。
按 《伤寒论》言:“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此案患者虽见心烦喜呕、口干、口苦、头晕等众多柴胡汤证,但笔者认为其非小柴胡汤所宜。因患者出现舌红苔黄而少津,脉象亦成弦数等阴津亏虚,内有郁热之象,乃胆火上炎,津液不足,少阳枢机不利所致,而小柴胡汤偏辛散温燥,投之恐伤阴液而煽火邪,应是黄芩汤所适。且患者虽有身体酸痛、项强等太阳病表现,但实非表证,因少阳为枢,枢机不利可波及太阳经之气化,营卫运行不畅,故有此表现。少阳火盛而逆,枢机不能和转而降收,胆热迫胃,胃气不降,故见纳少而恶心欲吐;其难以入睡,寐时梦多,亦是枢机不利,阳不入阴,火邪扰心之象。综上,当予黄芩汤为宜,恰中少阳火盛而逆,枢机不利的病机。方中以黄芩为君,可清少阳邪热、散其郁火;再取白芍酸寒益阴和营;炙甘草、大枣扶助中焦以助气血生化之源;生姜配大枣调和营卫且能止呕。诸药合用,共奏清解郁热,和降少阳之功。
2 太阳少阳合病义,一方两经勿小觑
2.1 师言合病,妙在机变关于“合病”,目前医家多认为是两经同时感病,但是张仲景所举的四种合病,在原文中无一处记载两经或三经症状并见,也未见其运用方药兼解多经。以方测证,此虽称合病但并非两经或三经同时受病,而是指一经为主同时又影响它经从而出现相应症状。六经辨证亦是对人体生理、病理变化的划分,故其内在必然离不开脏腑经络的普遍联系,因此,六经之间必然有着如同脏腑生克制化、经络循环一般的关联。其中值得推敲的是,当出现多经的证候表现时,是否需要同时处理多经病?从原文中合病的施治即可知医圣张仲景的本意并非如此。太阳阳明合病治在太阳,太阳少阳合病治在少阳,少阳阳明合病治在阳明,三阳合病治在阳明,故黄芩汤于六经中应归属于少阳病之证治。
如临证中遇风寒感冒的患者,症见畏冷、咳嗽,伴见纳少、便秘及心烦、胸闷等不适,无须在散寒宣肺的基础上佐以治疗心、脾之药,因风寒外束可同时引起三脏问题,即一因多果。风寒束表,肺失宣肃,肺与大肠相表里,故可导致大肠传导失职而便秘;正气趋外抗邪,中焦脾胃气血相对不足,故见纳少;而心烦、胸闷亦可由肺气不宣,气机不畅所致。此类患者若无相应的心脾病变之舌脉等表现,则可予散寒解表宣肺之品,待肺气开宣,水精四布,其余诸症可随之而解,此类情况不胜枚举。倘若临证中见症治症,则有失辨证论治之精神,难于圆机活法,故“合病”之义应是医圣张仲景举例强调应抓住疾病病机的主要矛盾,不可泛泛而治。
因此可以认为,合病并非真的合而为病,正如刘氏[4]所认为的,《伤寒论》之合病实则病在一经,或虽有多经症状,而病机却在一经,一经的症状取决于另一经的病机。故黄芩汤亦是病在少阳,而见两经之症候。
2.2 黄芩苦寒,亦可宣通或疑黄芩本是苦寒清热之品,若未配柴胡何来和解之功?如《本草害利》所言“柴胡退热不及黄芩,柴胡苦以发之,散火之标,黄芩寒以胜热,折火之本”,认为黄芩直折其火。殊不知《黄帝内经》言:“故无不出入,无不升降。化有小大,期有近远。”一味黄芩非单纯清降之品,亦有其升降出入之理。《伤寒杂病论》中小柴胡汤类方7 首,除四逆散外,均含柴胡与黄芩,说明黄芩与少阳病有直接的关系。《医学衷中参西录》曰:“又善入肝胆清热,治少阳寒热往来(大小柴胡汤皆用之)。兼能调气,无论何脏腑,其气郁而作热者,皆能宣通之。又善清躯壳之热,凡热之伏藏于经络散漫于腠理者,皆能消除之。”张氏之说证明黄芩入肝胆而治疗少阳病证,又以其能“调气”治疗“气郁而作热”,说明其清降中又有升散之力,可达腠理而清伏热,故言“皆能宣通之”,此正应少阳枢调气机升降出入之能。而张锡纯于《医学衷中参西录》所引用的李时珍医案则进一步说明黄芩入少阳而治热证,原文曰:“黄芩治少腹绞痛,《名医别录》原明载之,由此可见古人审药之精非后人所能及也。然必因热气所迫致少腹绞痛者始可用,非可概以之治腹痛也。”因少腹乃肝胆经所过,黄芩可治少腹绞痛,即黄芩入肝胆、少阳之佐证,故黄元御于《长沙药解》直言:“味苦,气寒,入足少阳胆、足厥阴肝经。清相火而断下利,泻甲木而止上呕,除少阳之痞热,退厥阴之郁蒸。”
或疑黄芩虽清降中又有宣通之力,但较之麻黄、桂枝温通宣散之性仍是天壤之别,何以能胜任太阳少阳合病?此因黄芩本非为太阳中风、太阳伤寒而设。黄芩汤所治之太阳少阳合病乃基于少阳火盛、枢机不利进而影响它经的病证,枢机不利而开阖失常,波及太阳之“开”则见恶寒、身痛等不适,波及阳明之“阖”而见干呕、下利、腹痛。正如现代医学所说的各类感染发生时常可出现畏冷、身痛甚至寒战等表现,但此并非皆散寒解表之法所能胜任,当审证求因随证施治。不解表而“表”自解,故知“太阳少阳合病”中的“太阳病”乃症候似太阳病,非真正意义上的太阳伤寒或太阳中风,此亦正如《辅行诀》所言,是黄芩汤清透热邪,和解少阳之佐证,其曰:“小阴旦汤(即黄芩汤加生姜)治天行,身热、汗出、头目痛,腹中痛,干呕,下利者。”
2.3 验案举例方某,男,24 岁,2018 年3 月10 日就诊。主诉:腹痛2天。患者无明显诱因出现阵发性脐周腹痛2 天,伴恶心,不欲饮食,口苦,两侧头痛,头晕,全身酸痛,项背强,腰痛,关节痛,自觉发热,恶寒,无汗,小便黄,大便调,但自觉排便比往常通畅,舌质红苔黄腻中等厚度,六脉濡数稍弦。自觉发热恶寒、项背强等症状随着腹痛、恶心等症状的出现而出现。中医诊断:腹痛,辨为少阳湿热,枢机不利证。处方予黄芩汤,药用:黄芩12 g,白芍10 g,炙甘草3 g,大枣10 g。3剂,水煎服,每日1剂,早晚饭后分服。
服用3剂后诸症皆去,稍觉身倦,嘱节饮食、适寒温,数日后身倦自复。
按 此案起初考虑外感湿热、表里同病,但疑点在于为何会出现明显的太阳经之发热恶寒、项强、关节痛、腰痛表现,且这些症状是伴随着腹痛、恶心的出现而出现,是否需要表里双解?笔者反复斟酌,忽悟此乃太阳少阳合病的黄芩汤证。所谓少阳喜呕,加之见口苦、头晕等少阳提纲证的表现,此应是少阳病。少阳湿热内盛,枢机不利,开阖失常,导致表气不和,里气不畅。表气不和而发为恶寒发热、头项僵痛、身痛;里气不畅,少阳胆热内迫肠道,故有腹痛、恶心、纳少等症,虽无下利之症,但排便较前通畅已具下利之势,其依然是典型的太阳与少阳合病,故直用黄芩汤原方。
患者自诉药后少时突然腰痛如折,待约15 min后腰痛豁然自解,全身微微汗出,其余诸症也随之逐渐缓解。由此可知黄芩汤治太阳少阳合病不假,此案虽见两经之症候,但未见脉浮、苔白等太阳病之舌脉,且诸多太阳病症候是随腹痛、恶心等症而变化的,足见病机关键不在太阳而在少阳,其太阳病症候之增减变化亦类似少阳病之寒热往来,因枢机不利,阳气郁滞于中,不达表而见表证,内迫于里而见里证,待阳气郁极而伸展,诸证遂缓,此亦不离少阳病之意。
3 总结
《素问·方盛衰论》曰:“是以切阴不得阳,诊消亡;得阳不得阴,守学不湛。知左不知右,知右不知左,知上不知下,知先不知后,故治不久。知丑知善,知病知不病,知高知下,知坐知起,知行知止,用之有纪,诊道乃具,万世不殆。”诊法如此,而辨证立法、处方用药亦是如此。本文以阴阳对立统一的视角分析小柴胡汤与黄芩汤的关系,和解中偏升散、温燥、补气的小柴胡汤属阳法,和解中偏降收、凉润、益阴的黄芩汤属阴法,由此观之,少阳病之证治非皆柴胡汤类方所能胜任,亦非“和法”一词所能涵盖。而所谓“和法”,奠基于《黄帝内经》《伤寒论》时代,又经后世医家不断实践并丰富理论。细析之,“和法”或着眼于局部,偏指治疗手段,如和解少阳等法;或着眼于整体,偏指治疗目的,即运用补虚泻实、调和阴阳使不和者和之,如协调脏腑功能、调和阴阳等法。临床医生倘若笼统理解“和法”的内涵,常使临床辨证模糊化而皆投以寒热虚实并治,终使处方用药针对性下降。本文以《伤寒论》合病的内涵及黄芩汤治疗太阳少阳合病为切入点,研究《伤寒杂病论》中抓主要矛盾的辨治精神与“和法”的内涵,提高临床辨治的准确性。总之,进一步研究黄芩汤可拓展其临床应用范围,亦有利于对六经辨证系统的研究,终为提高临床疗效提供理论参考。一隅之见,望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