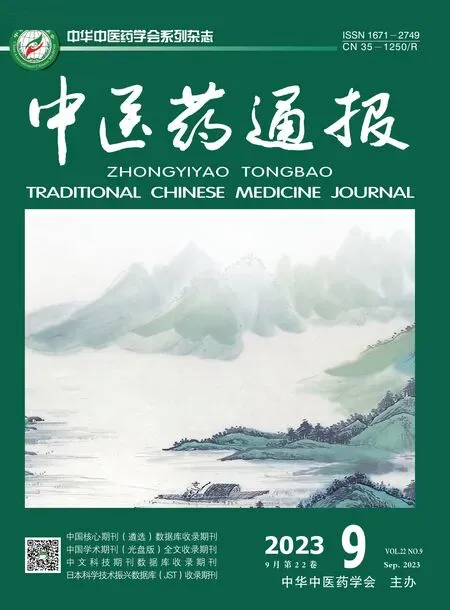论虫类药在络病治疗中的应用※
陈吉全 陈瑞祺
中医络病学说肇始于《黄帝内经》,张仲景之《伤寒杂病论》首次提出“脉络”一说,创设一系列治疗络病的方药,其中虫类药的运用别具特色。叶天士将中医络病学说系统化,使络病学说日趋完善[1]。叶天士常用的通络方法有虫类通络、藤类通络、辛香通络等[1],其中虫类通络法为当代许多中医名家所喜爱,广泛应用于临床各科疾病[2-8]。虫类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虫类药是动物类药的别称;狭义的虫类药主要指《本草纲目·虫部》所列举的药物,包括卵生类之(僵)蚕、露蜂房、(全)蝎、水蛭,化生类之蝉(蜕)、䗪虫,湿生类之蜈蚣、蚯蚓等,为现代科学分类中的昆虫类药物,以及部分环节动物、爬行类动物等。叶天士指出,治疗客于经络数十年之风湿“须以搜剔动药”,“藉虫蚁血中搜逐,以攻通邪结”,因此叶天士所指通络虫类药主要为虫蚁类药物,属于狭义虫类药的范畴,本文亦主要讨论狭义虫类药。
现代中医名家一般只是根据虫类药的性味特点来选用虫类药物治疗络病,认为虫类药具有搜剔之性,能通达络脉[2-8]。但是,络脉有气络和血络之别[9-10],其中气络通行宗气等气[10]。对于如何根据气络、血络及诸气特点选用虫类药,目前尚未见相关报道。因此,笔者基于中医经络学说,认为狭义“经络之气[11]”是指“神气”[12],经络应包括3 种类型的通道:主要运行营卫的经络,单独运行卫气的经络和单独运行神气的经络。其中,主要运行营卫的络脉可称为血络;单独运行卫气与神气的络脉可分别称为卫气之络(可简称为“卫络”)与神气之络(可简称为“神络”)[13],二者属于气络。在此基础上,笔者对部分常用虫类药在络病治疗中的应用规律进行探讨,现介绍如下,以飨读者。
1 络病分型治疗
络病发生的一种情况是急性病、暴发病发病不久即邪客于络,发生络病;另一种情况是叶天士所谓“久病入络”,即疾病迁延不愈,发展到一定阶段,形成络病。络病总病机无外乎痰湿、瘀血、湿热等内生邪气及邪毒等稽留于络脉或久病络虚,使络脉气血运行、津液输布、信息传导失常,并影响到全身。笔者认为,络脉疾病包括血气之络病、卫气之络病和神气之络病,治疗需根据病机特点选择用药。
1.1 血气之络病关于营气的运行通道,《灵枢·决气》曰“壅遏营气,令无所避,是谓脉”;《素问·脉要精微论》又云“夫脉者,血之府也”;《素问·痿论》中“心主身之血脉”一语又提出“血脉”的概念,故《黄帝内经》认为,血脉为营气运行的道路。《黄帝内经》认为脉有清浊之分:血气在心肺得自然界清气温养,为清脉;血气到达脏腑组织,经过络脉微循环,清气转化为浊气,为浊脉。血络在清脉、浊脉的转化中起关键作用。血络可类比为毛细血管(包括微动脉、微静脉等)。此外,《灵枢·营卫生会》认为,营行脉中,卫行脉外,营卫并行,现代医学中,血液中的白细胞具有免疫功能,与卫气的功能相似;血浆及红细胞运输营养与氧气,与营气的功能相似。二者共同组成血液,通过血脉周流于全身,可作为营卫并行的佐证,因此血脉、血络为营卫并行的道路。
血络是并行之营卫输布贯通的枢纽,其细微广泛,分布全身,是清脉浊脉转化,津液出入,濡养全身及独行卫气、神气的关键,一旦邪客血络则易使营卫运行和津液输布失常,主要发生络脉阻滞[14](甚或瘀阻)、络脉拘急[15]和络脉空虚[14]等病理变化。络脉阻滞是络中邪气阻滞气血运行,以瘀血为主者,症状以瘀阻部位针刺样疼痛为主;络脉拘急者亦多有牵引疼痛、热胀疼痛等症状;络脉空虚者或可见患病部位颜色苍白,或感知觉功能减退等神气失养症状。
临床治疗上可以用虫类药协助通络。对于虫类药的使用,叶天士认为“飞者升,走者降,有血者入血,无血者行气,灵动迅速,以搜剔络中混处之邪”;吴鞠通曰“以食血之虫,飞者走络中气分,走者走络中血分,可谓无微不入,无坚不破”。叶天士、吴鞠通认为虫类药在功效上有升降气机和入血入气的差异,故络脉阻滞以瘀血为主者重在运用入血分之虫类药(如土鳖虫、水蛭等)以活血化瘀,通络达血,方用大黄䗪虫丸、抵当汤等;络脉拘急(绌急)因寒者,治宜温通经络,方如桂枝汤、四逆汤等;络脉拘急因血热者,治宜凉血化瘀,药如丹皮、赤芍等;络虚失养者,治宜养血通络,方如当归四逆汤等。此外,络脉空虚者,因气虚推动无力,故多夹瘀;络脉拘急因寒者,因寒主凝滞,则络脉收引绌急,故多夹瘀,络脉拘急因热者,因瘀热常常互结,亦多夹瘀;所以,络脉空虚与络脉拘急者,可在养血补络,温通经络或凉血化瘀的同时,酌情加用入血络虫类药。血气之络病常见于冠心病、慢性肾小球肾炎、肾病综合征、顽痹、糖尿病并发症等。
1.2 卫气之络病至于卫气的运行通道,综合《黄帝内经》相关条文可知,卫气循行除前述营卫并行外,还有2 种方式[16]:卫气独行,如“昼日行于阳二十五周,夜行于阴二十五周”(现代医学所说的淋巴细胞及其他免疫物质独行于淋巴管中,可参考之);卫气散行,如“卫气者,出其悍气之慓疾,而先行于四末、分肉、皮肤之间,而不休者也”(现代医学认为白细胞可以在微静脉处通过变形运动,渗出脉外而散行,可参考之)。卫气的3种循行方式互相结合,互相转化。营卫并行周流全身,但周流中,并行之部分卫气可在络脉处出于经脉而散行;并行营卫的一部分卫气,可在络脉处进入卫气独行通道转为独行(现代医学认为白细胞可以在淋巴结中高内皮微静脉处从血液循环进入淋巴循环,可参考之);散行之卫气及其余气通过络脉可转为独行(现代医学认为白细胞可以通过毛细淋巴管回到淋巴循环,可参考之),独行者可在心肺大会时转为并行之营卫,故卫气亦有自己单独运行的通道。卫气通过经络升降出入,周流不息,贯穿全身脏腑筋膜、四肢百骸。
卫气之络疾病主要包括卫气之络郁阻、卫虚失荣两类。邪在卫气之络,卫气郁阻者,邪气盛,邪正相争剧烈则发高热;卫气之络不通,护卫神气无力,神气轻微受到邪气干扰则发痒。治疗时,宜选用性质轻清飞升,入卫气之络,具有宣风泄热,通达卫气之功的一类虫类药,如蝉蜕、僵蚕等来通络达卫,痒甚可加通达神气之虫类药,方用消风散、升降散及现代名方乌蛇驱风汤等。卫虚失荣者,开阖失常则汗多;温煦不足则肢冷;抗邪无力则易外感。治疗宜用调和营卫、温经通络、益气通络等法,方用桂枝汤类、玉屏风散等。
1.3 神气之络病神气包括主司感觉、运动、思维之气和调控脏腑功能之气等。脑为元神之府,为全身神气之总汇,五神之四神(神、魂、意、志)、情感、思维、感觉、动觉及寤寐、生长、生殖等脏腑功能的终极调控均由脑统摄。督脉与脑相通,为脑之使,总督全身阳脉,在布散传达神气功能之外,还主司五神之魄(无意识动作)及部分脏腑调控之神气,故神气中枢在脑和督脉。此外,任脉主全身阴脉,在传达神气方面亦起重要作用。人体内外刺激经神气感应后上传至脑和督脉,经脑中神明反应之后通过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布散动觉或调控脏腑之神气于全身。
至于神气的运行通道,《黄帝内经》未明示,然而由五神及脏腑调控反应快捷可知,神气清灵,传导迅疾,非《黄帝内经》所云营卫昼夜运行于阴阳达50 周可比,故神气亦应有自己单独运行的通道。结合现代医学,神经可被视为神气运行的通道。再考虑《黄帝内经》中“血藏神”及“脉舍神”之语,神气的运行通道应与血脉并行。神气通过络脉接受血脉濡养,又通过络脉向肌肉组织等效应器布散神气,不同经脉间神气通过络脉彼此联系。现代医学认为神经可以通过神经末梢或神经突触等布散、接受神经冲动等,可参考之。神气需通过经脉、络脉(神气之络)进行传导,并与血络及其他脏腑官窍、肌肉组织相联系,其中,与血络相通则可以接受营血津液的濡养,与其他脏腑官窍、肌肉组织相连则可以接受和布散感觉、动觉之气。
神气之络疾病多是由血络虚滞、神气失养,以及神气之络瘀滞、神气不通或神气之络受损所致,多出现感觉、动觉、脏腑功能及思维异常或失能,如麻木、运动不能、言语謇涩、疼痛等,其机理在于:邪入神气之络或神气失养,感觉之气不能上传,则麻木;动觉之气不能下达,则运动不能;调控脏腑功能之气不能正常下达,则脏腑功能失常;神气之络受损则疼痛。神气之络疾病常见于中风后遗症、面神经麻痹、重症肌无力等。邪在神气之络者,宜选用相对重浊沉降,偏入神气之络,具有搜风剔络,通达神气之功的一类虫类药[13],如全蝎、蜈蚣、地龙等入络搜邪,通达神气,方如止痉散、补阳还五汤等。血络瘀滞者通行之,病久神气失养,重在养血安神,可佐少量通达血络之虫类药以通畅营血、濡养神气。
2 虫类药的综合运用
经络的3 种通道之间相互渗透、灌注,通道之间通过络脉进行广泛的气血津液、能量与信息的交换,通道之间还可以直接贯通,如《灵枢·营卫生会》认为,夜半子时卫气与营血“大会”于手太阴肺经。这3 种通道在功能上相互支持,运行以通为顺,尤以络脉通畅为要。血络通,脏腑肢体及卫气、神气则得到营血的濡养。气络中,卫气之络通,卫气到达全身脏腑官窍,发挥其温分肉、肥腠理、司开阖、抗御邪气的作用,温养护卫营气与神气诸气,并实现与营气、散行方式之卫气的会合交流[13];神气之络通,神气升降出入,入可将四肢百骸、脏腑等信息上传于督脉与脑,出可将脑反应后的信息散布全身,发挥其主司感觉、运动,调控全身脏腑、四肢百骸及全身营卫、元气、宗气诸气,主司语言情感思维等功能[12]。因此络病治疗往往需要综合运用虫类药来进行。
虫类药的综合运用存在2 种情况。 一种是因络脉之间紧密联系,治疗时兼用少量入另一种络脉之药,有助于疾病康复。如神气之络疾病的治疗,因血脉对神气具濡养作用,加用少量通达血络药,可通畅营血、濡养神气。又如血络疾病的治疗,因神气对脏腑与血脉功能具调控作用,加用少量通达神气之络药,有助于血络所在脏腑与血脉功能恢复。再如治疗心络瘀阻的通心络胶囊中含土鳖虫、水蛭等入血络的药物,并合用全蝎、蜈蚣等入神气之络的药物。
另一种情况是因邪气在络脉之间可以传变,可见络病合病、并病的情形,因此有时需要综合应用虫类药,如邪气可由卫气之络波及神气之络或由卫气之络直犯神气之络。邪气波及神气之络者,轻者使用蝉蜕、僵蚕等宣通卫气之络之虫类药以清宣卫气之络之风热,重者合用全蝎、蜈蚣等入神气之络的虫类药。邪气直犯神气之络,症见牙关紧闭、角弓反张者,可选用五虎追风散;血络邪气外出卫气之络,如中风患者头面烘热,可加用僵蚕等;血络与神气之络疾病同病者,如顽痹,常常同时使用入神气之络的虫类药(如:全蝎、蜈蚣)与入血络的虫类药(如:土鳖虫),方如朱良春创制的益肾蠲痹丸。
3 验案举隅
张某,男,46岁,2015年8月24日初诊。主诉:颈部瘙痒、成片扁平红色丘疹2年。2013年患者因工作紧张、饮食失调,多食辛辣、香辛食物及肉类而发病,发病之初自觉颈部阵发性剧痒,夜晚尤甚,搔抓及摩擦后皮肤逐渐出现绿豆大小的成片扁平红色丘疹,圆形或多角形,有光泽。现症见:扁平红色丘疹密集成片,皮嵴明显增厚,皮肤苔藓样变,皮色淡红,有明显抓痕及血痂,间有1~2 个大约1 cm×1 cm 的高耸化脓疔疮,按压流出黄色脓液,舌红,苔白腻,脉滑数。中医诊断:牛皮癣,辨为湿热邪气蕴阻肌肤,卫气之络瘀滞证。治法:宣风泄热,除湿通痹,通络达卫。处方予仙方活命饮加减,药用:防风10 g,金银花30 g,皂角刺10 g,天花粉15 g,浙贝母15 g,白芷10 g,当归10 g,陈皮10 g,赤芍10 g,蝉蜕10 g,僵蚕10 g,乳香3 g,没药3 g。6 剂,每日1 剂,水煎400 mL,早晚分服。
2015年8月30日二诊:化脓疔疮已平,微红,与周边丘疹无异,仍然夜间瘙痒难忍。证属湿热邪气夹风蕴阻肌肤,神气之络受扰。治宜宣风泄热,除湿通痹,通络达神。处方予乌蛇驱风汤加减,药用:黄芩10 g,乌梢蛇10 g,黄连10 g,金银花15 g,薏苡仁30 g,连翘10 g,蝉蜕10 g,僵蚕10 g,荆芥10 g(后下),羌活10 g。以此方加减治疗半年,红色丘疹消失,皮肤颜色稍白,皮损基本修复。
按 神气调控卫气、营气,患者工作紧张,神气郁滞于脑,失去对卫气的调控,卫气开阖失司,又因饮食失调,蕴生湿热,风湿热邪郁阻肌肤不得外发,故颈部瘙痒,出现成片扁平红色丘疹,邪气波及神气之络,故瘙痒难忍。一诊时,方用仙方活命饮宣散风热,活血通经,解毒消痈,佐以蝉蜕、僵蚕入卫气之络宣散风热。二诊时,方中黄芩、黄连、连翘、羌活、荆芥宣散风热、清热燥湿;金银花、薏苡仁解毒祛湿;虫类药的使用则在一诊方蝉蜕、僵蚕入卫气之络基础上加用乌梢蛇入神气之络搜邪,通达神气,故获良效。
4 讨论
虫类通络法首创于《伤寒论》,张仲景将其用于血气之络病的治疗,由于古代没有提出血络、气络观念,故以通络概之。叶天士提出虫类药有入气、入血之分,将虫类药广泛用于血络与气络病治疗,虫类药理论初步形成。现代医家吴以岭[9]、邱幸凡[10]等明确提出络脉有气络与血络之分,血络运行营血,气络运行诸气,为虫类药分型论治络病打开途径。笔者在此基础上,认为经络学说是中医藏象学说发展的产物,《黄帝内经》指出脉为血(营卫)之府,则神经、淋巴管可以认为是神气、卫气之府,中医经络是对至少神经、血管、淋巴管三种类型通道的综合的象反映,因此,将气络进一步分为卫气之络与神气之络。根据虫类药的性味特点、功效、归经,笔者进一步认为常用虫类药有偏入神气之络、卫气之络、血络之分,或通络达神,或通络达卫,或通络达血(营卫),临床需根据病机特点选用或综合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