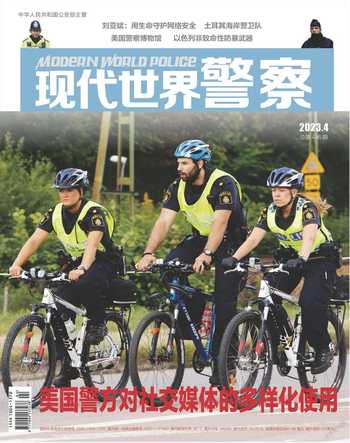纽约绿卡警察(下)
卢克·沃特斯(美)



四、路易玛事件
尽管我们平时很忙,但反扒反诈中队毕竟隶属于特勤队,随时被快速反应组召入执行防暴任务。艾伯纳·路易玛事件演变为游行暴力,我就全程参与,该事件一度成为全世界的头条新闻。
1997年8月9日晚上,30岁的海地移民路易玛在布鲁克林一家同性恋夜总会里玩,突然里面有人打架,他和其他人一起扯架。不久警察赶到了现场。在抓捕过程中,有人袭警,警察贾斯汀·沃尔普被人打了一拳。沃尔普认为是路易玛打的,于是逮捕了他,并在返回第70局的路上对他进行殴打,并实施了性侵犯,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沃尔普后来表示,这些伤都是被捕前同性恋粗暴性交造成的。
起初,我不太相信这些是真的,后来有关方面证实了路易玛确实被警察侵犯。消息传出后,人们怒不可遏,数千人走上街头,穿过布鲁克林大桥,威胁要攻击警察,攻击市政府。
纽约市所有受过训练的警察都被动员起来,戴防暴头盔,持防暴警棍和一个小型防弹盾牌。当我站在队伍里准备迎接袭击时,发现抗议者和我一样,脸上充满了恐惧,因为抗议活动已经失控,大家分不清你我,不少的暴徒尖叫着冲向我们,疯狂地扔东西砸我们。
见此情景,我立即弹开伸缩警棍准备反击。一名中尉马上对我咆哮:“收起来!让他们发泄一下!他们有权利这么做。”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越来越多的抗议者加入,数不清的石头、水瓶、木棒向我们飞来。后来我们接到命令,将游行队伍强行挤回大桥,控制局面。随着其他支援力量的投入,我们最终获得了控制权。
整个过程惊心动魄,我从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路易玛后来起诉了市政府和警察局。1999年12月14日,纽约布鲁克林法院判处警官贾斯汀·沃尔普(29岁)有期徒刑30年,其他三名警察同伴被开除;市政府赔偿原告870万美元。
这起案件就发生在我身边,这些警察都是我的同事,着实更新了我的认知,原来干警察这么危险。
五、缉毒署
不知不觉已经毕业6年了,我想离开巡逻车,我的朋友都升职了,尼克已经成为缉毒特工。我也写了申请,要求调往缉毒大队工作,并如愿以偿。
我参加了北曼哈顿倡议组织(NMI)举办的为期三周的毒品知识培训班。导师教我们如何识别不同的毒品、如何卧底、如何钓鱼执法等。这个速成班对我帮助很大。
在执法过程中,有很多东西可以救你的命,其中之一就是要听领导的话。
2000年初的一天早上,我们经过戴克曼和第十大道的拐角处,科尔曼中士满意地说:“这五个小时你们应该很轻松。”
缉毒现场小组共有八人,由基斯·科尔曼中士带队。他的长相、头发和声音就像动画片《辛普森家族》里面的小丑“库斯提”,尖酸刻薄。
在一间公寓外,“小丑”中士发现一个20岁左右的男子坐在门廊上抽着自制卷烟,一支粗大的、掏空的雪茄,里面可以填充大麻、海洛因甚至是PCP(天使烟尘),也可以是一枚小型手榴弹,随时会爆炸。
通常,当警察接近一名吸毒嫌疑人时,后者会逃跑,但这厮竟然不管不顾,沉浸在烟雾之中,怡然自得,有点像诗人。
走近后才发现原来是个瘫痪者,看来这个叫丹尼尔·罗德里格斯的家伙没有什么威胁,我顿时放松警惕。
“中士,要不我们就放了他,意义不大。”我低声道。
“不行呀,今天我们的数据很低。他是吸毒者,带回去取个材料先凑数,然后再说。”
“库斯提”小丑真是个无情的家伙。
我把丹尼尔抱到车上,并搜查他身上是否带有违禁品和武器,履行程序。他一直很配合,满脸笑容。同事把轮椅放在他的身边。
“嘿!把轮椅放在后备厢里。轮椅搜查了吗?”“小丑”中士提醒道。
我把轮椅拿出来,仔细搜查,突然发现在轮椅座板的背面夹着一把手枪,.25口径半自动袖珍手枪,顿时吓出一身冷汗。
丹尼尔吸食了大量的毒品,渐渐地开始发作,越来越有侵略性。感谢“小丑”中士提醒了我们,否则丹尼尔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拔枪向我们射击,后果不堪设想,说不定我就报销了。
“你们这些家伙就是不听我的话,我一直告诉你们,街头没有规则,全靠我们谨慎小心,千万不能相信这些犯罪分子。”中士怒道。
回到警察局,我们指控残疾人丹尼尔吸食毒品和非法持有武器,后者在纽约市是一项重罪。不久之后,法官裁定丹尼尔非法持有枪支的罪名不成立,因为我搜查轮椅之前没有申请搜查令。
法律就是法律,有时候很没意思。
我们的总部位于107街,办公室是一座不高的建筑,一边是篮球场,另一边是繁忙的大道。当地人都知道这里是处理停车罚单的场所,但是如果知道密碼,电梯就会把你带到高层,我们的缉毒办。
我们中队有两名卧底,埃迪·拉莫斯和罗伯·张。卧底是一项压力大、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经验很重要。由于我的爱尔兰肤色苍白,独特的口音意味着永远不能做卧底。就在这一天,罗伯·张扮演“大叔”,就是买家,而拉莫斯扮“幽灵”,也就是跟踪搭档,暗中保护,发生枪击时,第一个冲上去支援,同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他们会经常换岗,角色互换。
在街上,我们和他们俩从不交流,尽一切可能回避,因为毒贩非常谨慎,耳目众多。
我在停车场埋伏,等待两名卧底的消息。突然,接收器传来拉莫斯的声音。
“伙计们,目标出现,110街,雷克萨斯车。”
“现在是十点零四分,穿防弹衣,出发。”“小丑”中士下令。
几分钟后我们就包围了这辆车,并从司机身上搜到了毒品。卧底警察如果知道吸贩毒者隐藏毒品或者枪支的地方,他会给我们暗示。他在和毒贩交谈时会说“你的裤子挺有特色的”。那就意味着有东西藏在裤子里。窃听器会把他们的对话传过来。
每天我们需要抓捕五个对象才能达到加班的指标,有额外的加班补助,说来说去都是为了钱,为了绿色的美元。街头缉毒工作不太稳定,一般来说抓五个不是大问题,曾经有一天我们抓了12个。但是抓捕之后的法律文书工作非常烦琐。
我发现,在毒品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你是白人、黑人还是西班牙裔,白领还是失业,这都无关紧要,只要你吸毒,后果都是一样的。没人能把航空公司的空姐和兼职妓女区分开来。一旦吸毒,空姐也可能成为兼职妓女,吸毒后都会崩溃,牙齿一颗一颗地掉下来,瘦骨嶙峋。
一天上午,只有我和“小丑”中士有兴趣加班,于是我们搭对前往河滨大道巡逻。在西146街的拐角处,有四名西班牙裔男性走成一条直线,相距十来米。
“中士,这些人有些不对头。”
“哦,那我们去看看这些家伙。”中士在开车。
在我们的枪口下,四个人很老实。不料这次是大鱼,缴获了一把9毫米手枪,还有小袋可卡因,大约1.1公斤,市场价高达十万美元,当然其准确市价还得取决于里面是否混杂了粉笔、糖和其他稀释剂。
成绩斐然,我们大喜过望,但助理检察官却反应平平,好像忘记了我和他其实是一边的。
“伙计们,我仔细研究了抓捕的细节。你们没有合理的理由对这些人进行拦截和搜查,他们的律师会说你们侵犯了他们的宪法权利。所以,这不好起诉。”
我据理力争,无奈人微言轻。这不是第一次对检察官办公室的疏失感到失望,也不是最后一次。
六、往事蹉跎
在缉毒署工作四年后,由于我的业绩突出,被调往第42警局刑事侦探队。该警局位于南布朗克斯中心,是纽约州最疯狂、治安最糟糕的地区之一。不管怎么说,也算是重用吧。
缉毒队工作期间,在“小丑”中士带领下,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肯定,街头吸贩毒现象明显减少。可是,在我们陆续升职离开以后,继任者却把毒品送还吸毒者的手上和肺里,给吸贩毒者开“绿灯”,赚“绿色”的美元。
我在缉毒队工作四年间,先后有九名同事被抓。
在缉毒队的时候,我和苏珊结婚了,还有了女儿塔拉,住在布鲁斯特,离市中心一个小时的车程。如今调到42局,离家就远了。
一天早上,我翻阅《纽约每日新闻》,有个标题“毒品丑闻中的警察”,插图是一名警察手拿一沓美元。内容是一名警察因抢劫和贩卖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可卡因而被捕。这个人是缉毒队的阿巴杰·迪亚兹,我曾经和他打过交道,非常积极的人。
联邦调查局估计,阿巴杰·迪亚兹及其同伙在布朗克斯、皇后区和上曼哈顿缴获了750公斤可卡因和400万美元现金。
新闻媒体说,即使每年付给每个警察一百万美元,腐败仍然存在,低收入和腐败是密不可分的,但不是必然因素。
1993年,当我进入警察学院时,一个新警的基本工资加上加班费,每年大约是五千美元,虽然不富裕,但还不至于要靠绑架、谋杀或勒索来贴补。15年后,收入上升了,两万多一点,但性价比却陡然下降,正如一名因拉皮条被捕的警察说的那样,一年两万美元不可能在纽约生活下去。
所以这个城市里有很多戴着警徽的罪犯。
七、命案追踪
我42岁时调查了警务生涯中第一个重大案件,而且是发生在“9·11”恐怖事件维稳期间,至今令人难忘,因为受害者就在我面前死亡。
2001年10月13日,911指挥中心转来报警称,一名男子在东163街和3大道拐角处被人砍伤腿部。我和同事火速赶到现场,找到了受害者,22岁的西班牙裔黑人男子威廉·马拉德。他坐在地上,双手掐住大腿,大腿流血不止。
我蹲下来与受害者交谈,他认识刺伤他的那个人,但说不出名字。医务人员也到了,进行急救。血流越来越大,止不住。他脸色苍白,没有精力和我说话。在送往医院的途中,马拉德因流血过多不治身亡。一起袭击案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变成了凶杀案。
我们迅即开展调查,得知有个叫菲利普的年轻人和死者马拉德发生争执,菲利普比马拉德个子小一半,但是他心狠手辣,拔出一把刀,猛刺马拉德,刺中了股动脉。
我们找到了菲利普的家里,他是多米尼加共和国裔,继母很不喜欢他。继母告诉我们,菲利普逃去多米尼加了。
我多次与菲利浦通电话,劝他回来自首,还曾两次给他寄机票,但都没起作用。引渡的手续和过程非常繁杂,而且多米尼加也有可能拒绝。
此案明显是一级过失杀人,而非谋杀。由于嫌犯拒不归案,在他缺席的情况下,我们根据州法律指控他二级谋杀罪,交由法院来决定。最终,控辩双方达成协议,菲利普的律师接受了七年的刑期。
我主办的第一个命案就悬而未决,很是不爽。我发誓一定要将此人捉拿归案,于是做了很多基础工作。三年后,菲利普继母告诉我他回来了,在波士顿一个建筑工地打黑工,还给了我他的手机号码。当时的技术尚不能手机定位,无法确定其准确位置。
2004年11月23日上午10点30分,一个阳光明媚、异常温暖的上午,多切斯特社區一栋旧房子正在翻修,很多穿着牛仔裤的工人在劳作。
我拨通了菲利普的手机号码,有一个年轻人停下锤子,掏出手机接听。不错,这个人和照片上的人很相似,就是他。波士顿警察蜂拥而上,把他包围。
“嘿,伙计,你还好吗?”我率先打破沉默,虽未谋面,但声音非常熟悉。
“一般,谢谢你的惦记,你就是卢克警官呀。”
菲利普很平静,毕竟面对五把手枪。他朝我苦笑了一下,举起了双手。
八、最后一案
有时,找到罪犯只需要现代技术和警察,但有时候却需要动用很多资源。我从未想象过,有案子要花两年时间,三个警察局、三个联邦机构、一艘豪华巡洋舰、一架直升机、一架私人飞机和数百万美元才找出案犯。这也是我在纽约警察局的最后一案。
2009年11月26日下午8点,国家橄榄球联盟有一场令人瞩目的比赛,比赛双方是巨人队与主队丹佛野马队。
在布朗克斯的克雷斯顿大街上,一辆黑色的本田雅阁停在服装店的旁边,司机在观看电视转播。比赛开始后,巨人队的31号高速发动,长驱直入,比赛进入关键时刻,人们屏息以待。突然,从本田车上跳下一人,30岁上下的拉美裔黑人男子,拔出手枪,对着那些挡在他面前看电视的人连续扣动扳机,人群惨叫连连,哄然四散。整个过程不到十秒钟,歹徒乘车逃离,三人当场死亡。
难道是因为挡住他看电视,一怒之下开枪杀人?
我不相信这个说法。经过调查发现,枪击前不久,莱维特(外号“史努比”)曾经出现在该本田车附近,那时球迷们正在高声齐唱国歌。莱维特是该区的头号毒枭,也是“克雷斯顿船员”的帮主,正在与其他毒贩争夺该区的毒品市场,被杀的三个人都属于敌对帮。
这明显是黑帮火并,蓄意谋杀。
凶手很快被确认为赫克托尔·加西亚,身高1.8米,26岁,来自波多黎各,因贩毒刚从联邦监狱释放,最近被提升为克雷斯顿船员帮的中尉,被称为“麻烦终结者”,该帮每年的营业额约为1亿美元。
二十小时后,杀手加西亚又找到了目标,正在等红绿灯的罗纳尔多·佩雷斯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连中三枪。
由于前一次杀人案的原因,街头加强了巡逻。一辆巡逻车听见枪响后,迅即追了上去,灯光闪烁,警报鸣叫,开始了一场高速追逐,在布朗克斯区持续了数公里,吓得路人尖叫避让。威斯彻斯特警察局有名警察试图阻拦,差点被撞。由于在闹市区,为了安全起见,警方放弃了追逐。
“卢克,你接手这个案件怎么样?你有丰富的追捕经验,想办法把这个杀人恶魔加西亚抓起来。”奥图尔中尉递给我一沓案卷,“我们组建一个专案组,你来负责,如果联邦调查局有兴趣也可以参加,他们有人有钱。”
得到上级领导的器重让我倍感兴奋,欣然领命。
我打电话给纽约南区助理检察官杰西卡·马塞拉。她坚定、专注、勤奋,除非她相信自己会赢,否则她就不考虑提起诉讼。
在听我介绍了案情后,她表示可以接受这个案件,并且提前介入。这让我省心不少。
莱维特的毒品是通过波多黎各运来的,该团伙的大多数成员在那里有着密切的亲属联系,是南美卡特尔毒品集团进入美国大陆的重要渠道。这意味着美国烟草火器与爆炸物管理局、缉毒署以及联邦调查局都有兴趣介入。
2010年5月10日,在纽约警局工作17年了,我终于有了个头衔:联合作战专案组组长。
联邦调查局有资金、人力和技术;我有一个线人,来自莱维特的组织内部。
他是一名假释犯,我们称他为“小小”,是莱维特帮的老成员,但他一贯反对暴力。
我和“小小”进行了无数次面谈,从第一次见面开始,我就感觉他很可靠,不是穷凶极恶的暴徒。我迅即申请把他注册为线人。注册线人可以从特情经费中获得报酬,有的一周高达一千美元,免税的。他们的身份是绝对保密的,绝不能透露其姓名,甚至也不能告诉法官。
该帮的主要活动基地是克雷斯顿大街2600号,我们偷拍了每个进出的人,然后通过人像比对,搜集其档案资料。
据“小小”反映,房东在楼道里安装了摄像头,录像数据传送到安全公司,然后发送到用户的电脑上。于是,我们联系安全公司,让他们在发送数据给房东的同时,也给我们传一份。这样,黑帮在走廊上的活动等于是现场直播。
莱维特的毒品帝国以克雷斯顿大道为中心,但他的另一个落脚点在八公里外的克拉伦斯大道上有一间公寓,我们也安装了窃听器。
2010年11月21日,听见里面断断续续谈到大量毒品的事,我带领几名特警队员悄悄地来到公寓,敲开了门。里面有两名帮派成员,马上被我们控制。搜查时在鞋盒里面找到了27.6万美元现金,一捆一捆的,旁边还有一个点钞机。据毒贩交代,这是他们一天的收入,他们说平均每天收入25万美元左右,一年9000万美元,这足以让他们铤而走险。
2011年5月20日,卧底说有人将在时代广场周围交易,我和同事埋伏在广场,但一直没有找到嫌疑对象。突然,我看见有个人提着一个手提箱,一点都不像游客那样东张西望、拍照什么的,而且这个手提箱看起来非常重。我上前亮出证件,提出要看看他的箱子。他慌慌张张,看我们几个人围住他,不得不打开箱子,里面竟然有35公斤可卡因,装在塑料包里,市场价约150万美元。贩毒者叫理查德·冈萨雷斯,系莱维特帮成员。
第二天,《纽约邮报》以大幅标题“大时代广场突袭”报道了此案,把我写成了英雄人物。
我一直在追寻杀人犯赫克托尔·加西亚,将其抓捕归案不仅可以彰显法律的尊严,同时还可以据此突破克雷斯顿船员帮,搜集证据。
有一天,有人告诉我他可能在布朗克斯区,一个小开发区的私人海滨公寓,就在纽约州立大学海事学院旁边的半岛上。这也是莱维特财产之一,主要是为了洗钱。
我们躲在渔政局的中型豪华渔船上,上面有相机、望远镜和其他监控设备。接下来的几天几夜,我们轮流用长焦镜头观察,希望能看见加西亚,但毫无结果,上下颠簸的轮船让我们焦躁不安。五天后,我们不得不放弃。
不久,有人说加西亚和妻子及孩子住在波士顿,我们很快找了过去。加西亚的妻子说丈夫一个多月没有露过面,她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由于没有搜查令,我别无选择,只有留下手机号码,叫她保持联系。接着,对他妻子的手机号码进行了监听。
长时间的追踪没有进展,专案组成员颇感烦躁。我提出采用“打草惊蛇”的办法,方法是在大街小巷张贴通缉令,对举报加西亚准确行踪的人奖励2000美元。此举肯定是抓不到他的,但可以惊动他的朋友,或许有人会打电话告诉加西亚,警方正在悬赏缉拿,叫他小心点。这些朋友不知道手机已经被警方监听,从而泄露加西亚的行踪。
专案组同意了我的计划。于是我和同事在街上四处张贴通缉令,其他同事则在监听重点人员的手机。突然,我看见一位30岁左右的短黑发女人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跟着我们,手里拿着手机,看着我們的一举一动。我恍然大悟,原来黑帮也一直在跟踪我,对我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
她装着不注意我,我也装着不注意她,警匪默契。
联邦调查局的人迅即实施反跟踪,很快查明这个女人是莱维特的女朋友卡丽娜,是帮里的重要成员。
我朝她走去,面带微笑,尽量显得随意。
“你好,小姐,你看看这个传单,我们正在找照片上的这个人。”
“好的,警官先生,我可以多拿几张吗?说不定能认出这个男孩。”
“没问题,想拿多少都可以,谢谢你的协助。”
说完,卡丽娜把海报夹在胳膊下走开,拐过角,她迫不及待地掏出手机拨打。
一小时后,我的手机响了。如果我的预感是对的,那么意味着休息时间没有了。
“卢克,你这个爱尔兰人真幸运,祝贺你成功了,聪明的绿卡警察!”联邦调查局的李武罗兴奋地说,“那女孩打电话给莱维特,莱维特马上联系上了加西亚。伙计,准备好行李,我们要去加勒比海了。”
窃听结果揭示了接听电话的位置在波多黎各自治邦卡罗来纳城加莱街。
第二天,我们花了一天时间申请相关的文书,获得了允许在飞机上携带手枪等特权。让我惊讶不已的是重案组的成员竟然携带了MP5冲锋枪。
我不由得笑道:“伙计,火力够猛的,如果其他乘客看见我们的武器,会吓得不敢登机的。”
我们来到卡罗来纳城的头一天,5月21日凌晨三点,卡罗来纳城每个角落都站有警察,警灯闪烁,向当地黑帮表明警察已经准备好火力射击。联邦调查局刚刚完成了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警察腐败案调查,在波多黎各多地进行了突袭抓捕,89名警察和多名惩戒官员被捕。波多黎各每年发生1000起谋杀案,帮派林立。
这纯粹是巧合,不是我们计划的一部分。
在圣胡安市和卡罗来纳城,我们不相信任何人,在这里度过的几个晚上都是睁着眼睛睡觉。任何泄密都会导致加西亚丢弃手机,逃之夭夭。如果这次再逃脱,那不知道哪一年才能抓住他,不知道有多少人被他害。
波多黎各岛上多是半乡村的山区,信号基站比较少,手机信号弱,不能确认手机准确位置。随着时间的推移,参战人员的耐心在减退,挫折感上升,所有的目光都转向了我。我提出向军方求援,他们的定位设备好。
刚刚从墨西哥访问回国的美国上将蒂姆·卡拉汉接到我们的请求后,同意派人协助。军方技术人员背着一个便携式信号跟踪器,悄悄在街上探测,但依然找不出准确位置。如果我们开一辆大型的信号中转车辆四处溜达,那很快会被发现,搞不好就是前功尽弃。没办法,我们尝试使用直升机和船只靠岸追踪加西亚的手机信号,但依然微弱,没法定位。
就在我们束手无策的时候,卡拉汉上将大怒,下令出动军用飞机,飞到悬疑区域上空,收集加西亚的手机信号。
我们地面人员做好了充分准备,参战人员和配备的武器足够在中美洲小国发动一次政变。
军用飞机飞过我们的头顶,我们静默以待。卡拉汉站在队伍的前面,犹如指挥千军万马,突然,他大臂一挥。
“找到了!飞行员发来了坐标,出发!”
四处埋伏的警察蜂拥而出,冲向一栋建筑物。突然,有人跌跌撞撞地从后门蹿出来,向山上跑去。二十多名特警紧跟其后,大声喝叫。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那个逃跑的人就被抓住了。我上前一看,就是赫克托尔·加西亚,在纽约枪杀四人的凶手,恶贯满盈,逃亡539天后终于被捕。
在当地警察局,我对加西亚进行了简短的审讯。他很担心妻子和孩子,我答应把他的妻子和孩子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但是他必须要配合警方。他心知必死无疑,如今只关心家人,对莱维特没有多少忠心,答应配合我们。
2011年7月13日早晨6时,纽约警察局刑警、缉毒警、重案组、特警,以及联邦调查局、烟草火器与爆炸物管理局等联合开展行动,实施集中抓捕。充分考虑了目标可能会反抗,因为许多人面临着终身监禁会绝地反击。
克雷斯顿大街2600号被包围,附近的屋顶上安排了狙击手,警用直升机在头顶盘旋,地面配备了装甲式盾牌。
莱维特·费尔南迪尼一直是布朗克斯街头最残忍、最恐怖的人之一,但不代表他愚蠢。看见警方如此阵势,他选择了直接投降。
盘踞在纽约市中心的大毒贩黑帮终于被剿灭。这是我警务生涯中办理的最大的案件,也是促使我退休的案件。
参与主办此案的地区检察官艾达和我从来没有发生过冲突,当然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观点差异,最近她嫁给了凶杀案组的同事吉米·麦克斯洛,不久吉米升职,升为二级侦探,意味着更高的薪水和地位。有人说本来是考察提拔我的,因为最近几年我的业绩比较突出,特别是在打黑除恶工作中得到了军警政各界人士的好评。如此“被忽视”让我非常愤怒,但也不感到惊奇。执法工作向来就是政治的一部分,纽约警察局也不例外。
生活本就不公平,人生不可能完美。有人告诉我,下一个升职的是我,我一笑了之。
当初入警时,充满着幻想;离开警坛时,不应该有吹嘘。对我来说,背景中没有温馨的音乐,只是曾经的酸甜苦辣。
这个时候我想起了30年前,最好的朋友保罗·赫尔利带我来纽约,至今历历在目,现今他依然在酒吧营生。
我毅然提交了退休申请。
【作者简介】卢克·沃特斯,Luke Waters,美国紐约警察,爱尔兰移民,2016年退休,现今和妻子及三个孩子住在卡万县。
【译者简介】刘长煌,江西省上饶市万年县公安局教育训练大队长,曾作为联合国维和民事警察赴利比里亚、东帝汶等国三次维和,先后三次获得联合国和平勋章。
(责任编辑:冯苗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