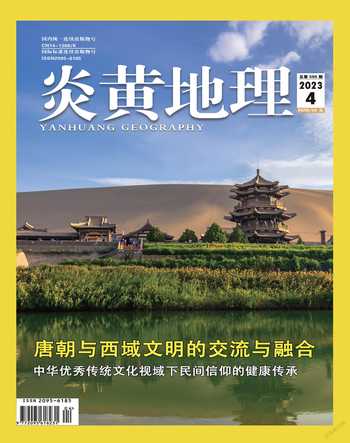秦汉土地所有制问题商榷
刘子谦

秦汉土地所有制是秦汉经济史研究的热点话题。支持土地国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学者从国家授田、国家对编户民的支配等方面进行论证;支持土地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学者则举出地主置私产的证据,并质疑国家所授土地的来源。秦汉时期的土地所有制应被视为一种变化中的历史进程。国有土地与私有土地长期共存,在经过激烈斗争之后,土地国有制之下的土地逐渐变为土地私有制、尤其是大土地私有制所有。
我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性质的问题是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的“五朵金花”之一,其中对秦汉土地所有制的争论尤为激烈。在20世纪50至60年代,以侯外庐为代表的学者主张,秦汉虽存在着一定的私有土地,但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土地国有制,代表作有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李埏《论我国的“封建的土地国有制”》等。另一派学者认为秦汉占主导地位的是土地私有制,代表作有张传玺《两汉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等。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秦汉时代的土地主要形态是国有和私有并存的,代表作有朱绍侯《秦汉时代土地制度与生产关系》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该问题又有新的论述,赵俪生、姚澄宇、黄展岳等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试呈现这场争论中双方的论点,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待后之览者在该问题的探索上做出更大贡献。
关于秦汉土地所有制问题的争论
新中国成立以后,关于我国古代土地所有制性质问题的争论,是由侯外庐先生于1954年发表的《中國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引发的。秦汉土地所有制是这次争论的焦点:该时期的土地制度是以土地国有制为主,还是土地私有制为主,抑或是哪种混合的模式?
侯外庐先生在文章中指出,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土地所有制,是以土地国有制为主的。他使用“皇族土地所有制”作为该种所有制的名称,皇帝是最高阶层的地主,这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于中国封建社会”。尽管事实上存在大量地主私人土地和土地兼并,但中国并没有承认土地私有的法权概念。他认为,中国古代这种土地制度模式就是马克思所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原来的氏族公社发展为土地国有制,其本质是氏族贵族所有制,也就是中国历史实际中的“家国一体”;这有别于在旧的公社破坏后以家族为单位分种小块土地的西方古典制度。
侯外庐的说法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一经发出,立即引来学界的热烈讨论。支持侯外庐的固然很多,但更多学者持相反的观点,认为中国(秦汉)封建社会应是土地私有制的社会。大量的文献表明农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交易土地,这已经符合土地私有制的特征。他们还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社会描述的是印度等国的情况,与中国并不相关,反对侯外庐的生搬硬套。这种不愿意接受落后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中国古代实际的情绪,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大论战中就出现了。最为要紧的是,如果按照土地国有说,那么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变成国家与农民的矛盾,而非地主和农民的矛盾了。
秦汉时期的土地国有制
认为秦汉时期土地国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学者,大多选择从授田制度出发看待土地问题。黄展岳通过分析云梦秦简发现,传统观点所认为的秦国通过商鞅变法废除井田制、确立土地私有制的说法,无法从出土的秦简中反映出来。尽管传世文献中有关于土地交易的记述,但秦简中的大量记载反映的是国家授田的措施,并且是国家以法律形式责成地方官负责的,可见有大量土地还掌握在国家手中。李埏认为,战国时期从井田制向郡县制的转换,实质是国家将原本分封给功臣贵胄的土地转颁给农民,农民接受了国家的授田,仿佛成了国家佃农的形态。臧知非认为,战国诸子特别重视“百亩之田”“五亩之宅”,就是在强调国人、野人转化成国家编户民之后君主向他们颁田制产的重要性,李悝的“尽地力之教”以授田百亩为前提即是一个例证。另外,他反对许多学者主张的“名田制”,即把土地登记在册即能合法占有的说法。他认为,名田即是颁田,是按照社会等级授予编户民田宅等物。以上论述证明土地国有制的思路都是一致的,即国家给编户颁田这一行为,证明了在当时,土地国有制是主要的土地所有形态。
国家不仅有能力颁田,还对授予后或民间买卖后的土地拥有处置权。甚至土地的所有权也并不在编户,土地授予后虽鲜有收回,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放弃了对土地的所有权。汉代有打击私人占田(“田宅逾制”),还有假民公田、赋民公田的做法,以及强令豪强之家迁徙到西北守陵、亦即官府主导下的大规模移民,都表示国家拥有对土地的最终处分权和对编户民的人身支配权。《资本论》指出,土地所有权的前提是某一些私人独占着地体的一部分,把它当作他们私人意志的专有领域,排斥一切其他的人去支配它。很显然,这个权力不属于秦汉时期的大小地主,而只属于国家。
国家对编户民的强力控制,为土地国有制打上了注脚。国家授田并非为了便利民生,而是为了更好地控制农民,更严密的“五家为伍”代替了以前的“九夫为井”“十夫为沟”。再加上以功劳、爵位“行田宅”,即授田,土地和人口全部隶属于国家,此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语才有了实际的社会意义。
赞成土地国有制的学者一般都延续了侯外庐的研究框架,但也有对其理论展开批评的。李埏认为侯外庐提出的“皇族土地所有制”是值得商榷的,皇帝的产业和国家的产业应该分开,作为政府官员的大司农与作为皇帝私属的少府之间就有界限。君主一方面是国家的代表,另一方面又是土地的占有者,具有双重性,因此侯外庐的“皇族土地所有制”应该改成“土地国有制”之类的表述。臧知非也指出侯外庐学说的另一个薄弱环节,即在隶农问题上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没有具体揭示国家力量如何导致奴隶向隶农转变。
秦汉时期的土地私有制
在侯外庐撰文之后,土地私有制一派在学界中获得了更大的共情。以张传玺为代表的支持该观点的学者,首先将手中掌握的能够证明秦汉时期存在自由土地买卖的文献作为依据。两汉时期土地“买卖由己”,甚至出现《后汉书》中记载的“标卖田宅”。买卖双方订立的契约被社会认可,在当时被称作“丹书铁券”,往往要一剖两半分藏两家。可见即使没有法律上的认定,在民间也早已有了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共识。在当时阻止土地买卖也是不可能的事,以至王莽颁布了不允许民间买卖田产的“王田”之法后引起巨大的反弹,隗嚣就以此为借口传檄起兵。
从传世史作中即可发现,秦汉时各阶层都加入了置地行列。两汉时期商人地主开始大量出现,他们纷纷加入了兼并者的行列,以至萧何请求开放宫苑空地时,刘邦还怀疑他是受商人贿赂而为之请愿。官僚自战国后期就开始在“食厚禄”之外寻求置私田,到了汉初官僚兼并已经是普遍的社会现象,甚至萧何也不例外。厚俸供养的贵族也寻求置私田,汉哀帝收效甚微的“限田令”就是以此为背景的。最后,连侯外庐认为的全国土地所有者——皇帝也加入了置私产的行列。如果皇帝或皇族是全国土地的所有者,那么怎样解释皇帝置私田的现象呢?张传玺认为这宣告了土地国有制的瓦解。但如前文所说,这种论断也是和侯外庐一样,没有看到土地国有制和皇族土地所有制的差别,皇帝的身份理应具有“二重性”。
关于土地国有制论者提出的授田问题,他们也做出回应。战国、秦汉时期供国家分配的大量的所谓国有土地,其实绝大多数是战乱之后的无主荒地,汉代在“假民公田”“假郡国贫民田”中租让的就是这种荒地;性质相仿的还有从罪犯处所没收的官田。但这些土地并不能代表土地国有制在全国占支配地位,更何况农民在接受这些授田之后,在剧烈的土地兼并浪潮中很容易就被地主买了去,皇帝还喜欢把大量国有土地赏赐给贵族、亲信,遭遇天灾人祸或不堪繁重赋役的贫民也很难不把自己的那一小块地卖出去。因此即便有大量国家授田的行为,也不能保证这些田地在一段时间后仍由统治者支配。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秦汉时期地主与佃农之间存在濃厚的宗族色彩,此即公社制度的残余,因此不能被认为是一种私有制形态。对此,土地私有制的支持者回应道,这是地主用长幼尊卑之序来控制农民,用亲睦和振恤等手段麻痹人心,这只是地主土地所有制下封建族权获得进一步发展的表现,和公社有着本质区别。
用这一点来否定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主导地位是站不住脚的。就像土地国有制的继承者批判侯外庐的观点一样,土地私有制的继承者们也对这一派的中心人物张传玺的许多观点提出了反思。姚澄宇认为,张传玺所说的皇帝置私田,即土地国有制崩溃、土地私有制完全确立的说法是无法成立的,因为在皇帝置私田后,汉代依然有“假民公田”和边境屯田,这些难道不是国有土地吗?针对张传玺提出的山林川泽买卖也标志着土地所有制彻底崩溃,姚澄宇指出山林川泽实际上就不是国有土地,而是皇帝私产,不能与土地国有制挂钩。
发展中的土地所有制
秦汉时期大量土地买卖和兼并的证据,诚然属于私有制的内容,但我们不能将其按照市场经济的思路来理解。诚如臧知非所言,我们不能“纯粹立足于经济关系看历史问题”“买卖关系是社会关系的组成部分,买卖行为的发生既决定于买卖双方的意愿,也决定于社会关系的制约”。由于沉重的赋役,农民往往在国家(特别是下层胥吏)的盘剥下倾家荡产,不得不将土地转移到大土地所有者手中。此时国家承认私人土地交易,一定程度上是在法律层面对这种剥削做了认可。这样的私有制是不彻底的,但仍应属于私有制的范畴。
在秦汉时期,国有土地与这种不充分私有制下的私有土地应当是长期共存的,学者们争论的只是哪种土地所有制占据主导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从运动的视角看待这个问题。赵俪生通过比对传世文献资料,认为汉代国有土地的数量是非常庞大的——当商品经济尚未达到活跃期,田土制度一般比较稳定,国有土地应当是大量存在的。但同时土地私有制也合法化了,在私有制要求其逐步深化的历史进程中,必然持续不断地冲击国有土地,“亚细亚”式的生产方式就在这种撞击下不断减弱。
我们可以将秦汉时期的土地所有制看作一种变化中的历史进程,一种运动中的消长过程。朱绍侯在文章中呈现了两汉时期土地国有制与私有制的斗争。在汉初七十年的休养生息中,土地私有制也渐渐壮大,迎来了第一次土地兼并潮。汉武帝通过迁徙富豪、禁止商人名田等措施短暂地遏制了兼并,但昭宣之后兼并浪潮又起,官僚、地主、商人更是紧密地结为一体。到了西汉末,土地和奴婢兼并现象已相当严重,汉哀帝本欲采纳师丹的限田限奴之议,但在朝臣的阻挠下宣告失败。王莽制定禁止买卖土地奴婢的王田私属制以打击兼并,三年后迫于压力又不得不取消。光武时实行度田以抑兼并,却导致“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最终只能黯然改弦易辙。此后直至汉朝灭亡,当权者都几乎没有再提出限田限奴的政策。历次斗争的结果是私有制日渐占据上风,终于成为土地国有制无法抗衡的对手。
赵俪生更将此过程抽象成模型。根据他的发现,秦汉时期的土地国有制、大土地私有制和小土地私有制(后两者有着迥乎不同的身份)三者是互相影响的。国有制土地通过被占田、假田、赐田等渠道进入私有制土地中;大土地私有制的土地通过强制性的移民或政治打击(如算缗),小土地私有制的土地通过抛荒等方式又进入国家手中;小土地私有制土地又因为天灾人祸等各种原因不得不自卖或负债,土地又归大土地私有制所有。如此不断运转,总的趋势是大土地私有制越来越强大,土地国有制和小土地所有制支配下的土地不断收缩。从秦末的“民前或相聚保山泽”、汉初的“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发展到西汉末年与农民武装势均力敌、东汉初年用武装反抗迫使刘秀放弃检核田地的地步。
参考文献
[1]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规律商兑之一[J].历史研究,1954(01):17-32.
[2]臧知非,周国林,耿元骊,等.唯物史观视阈下的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变迁[J].中国社会科学,2020(01):153-203+207-208.
[3]黄展岳.云梦秦律简论[J].考古学报,1980(01):1-28.
[4]李埏.论我国的“封建的土地国有制”[J].历史研究,1956(08):47-69.
[5]张传玺.两汉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J].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61(03):11-20.
[6]姚澄宇.论秦汉土地所有制形式[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04):50-53.
[7]赵俪生.试论两汉的土地所有制和社会经济结构[J].文史哲,1982(05):21-30.
[8]朱绍侯.秦汉时代土地制度与生产关系[J].开封师范学院学报,1960(01):116-141.
——秦汉时期“伏日”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