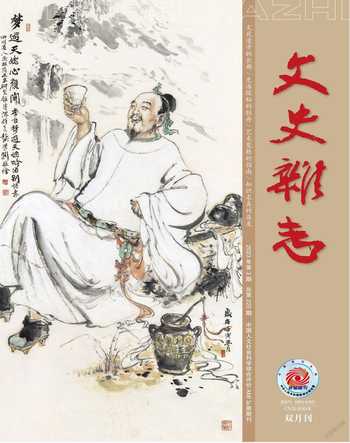《成都得名研究》的学术价值刍议
谢天开
摘 要:李殿元教授的新著《成都得名研究》提出,“成都”的名称所表达的意思就是“在统一全国战略中走向成功之都”。作为学术争鸣,其开放性与批判性可视为成都的“天问”。作者用心用力完成的这部著述,可以为今天及未来成都的发展提供借鉴,委实具有社会人文价值。
关键词:探析之书;争鸣之书;今日之书
李殿元教授的《成都得名研究》,一经巴蜀书社推出(2022年),便得到学界与社会的首肯点赞。学者屈小强说:“该书学理上的创造性与学术上的冲击力是毋庸置喙的。”
学者邓经武评:“李殿元先生关于‘成都’的研究成果,以一人之力连续推出十多篇论文,从方方面面详细阐述他关于‘成都’得名的观点。”
李殿元教授为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长期以来致力于巴蜀文化研究。《成都得名研究》是他的最新学术成果。
探析之书,学术价值
“成都”得名的系列研究及其这本书,始于一个偶然。李殿元教授在从事巴蜀文化研究时,发现“成都”的“成”字在现代汉语工具书如《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均只有六画,而在《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古代典籍中却必须七画才能查到。那么多出来的那一画是什么原因呢?学术始于问题意识与批判意识。原来,古代的“成”字是由“丁”与“戈”组成的,带有明显的军事意味,而在《辞源》等有关古汉字的词典中,关于“成”字的释意就有武力征服、停战和解、调和调解,等等。
关于“成”字带有明显军事意味的偶然发现,让李殿元教授一下子就将“成都”得名的研究与秦统一全国的战略部署联系起来,于是一发而不可收拾地开始了成都得名的学术勾稽之旅:从2014年在《成都大学学报》发表《论秦征服古蜀与“成都”得名》一文开始,再论、三论、四论、五论、六论、七论、八论、九论、十论等一系列关于“成都得名研究”的论文纷纷出台,从各个方面去论证“成都”的得名来源于秦统一全国的战略部署。他经过长达七八年的探析,在2022年完成本著的总括性论文《成都:在统一全国战略中走向成功之都——“成都”得名系列研究之最后结论》。结论指出,“成都”这个名称所显示出来的军事意味,与秦统一全国的战略意图非常吻合;它所包含的意思就是“在统一全国战略中走向成功之都”。这应该就是“成都”之名的来源及其涵义。
作者之所以得出“成都”意谓“统一全国战略由此走向成功之都”的结论,是缘于以下几个基本观点:宋人关于“成都”得名的解释不可信;秦灭蜀以前没有成都城;文献与考古证明战国后期才有“成都”;古籍中的古蜀地名均为中原文字;秦的统一战略与“成都”得名有关;成都在秦统一后便强势崛起。
从古到今的学界关于成都得名的讨论,或以《史记》的记述为基础;或以《山海经》的记述为支撑;或以《华阳国志》的记述为材料;稍近的讨论又扩及考古学、文字学等等。而李殿元教授认为“研究‘成都’得名绕不开秦文化”。因此,他的成都得名的学术勾稽之旅,始终是将成都得名问题看为历史记忆的社会文化存在。其在历时性上,是紧紧围绕秦陇文化与巴蜀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展开的;在共时性上,是从秦陇文化与巴蜀文化的历史维度、社会维度与文化维度三个交叉点上进行探析与去蔽的。
由此,可以看到作为学者的李殿元教授的探析“成都得名研究”的过程,洵为一个不断修正与调整的过程,亦是一个研究视域不断扩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李殿元教授一方面钻进故纸堆燃犀烛照,一方面观察最新考古成果而纵目古今,最终独辟蹊径,直击肯綮,得出了自己的学术观点。
争鸣之书,文献价值
作为争鸣之书,《成都得名研究》其开放性与批判性可看作为成都的“天问”。
《成都得名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学术争鸣,它是典型的争鸣之书。从“序”开始,至“正编”“附编”,到后记,都充满了学术批判与问题争鸣。
关于“成都”得名,长期以来,学者们就众说纷纭,各有解读。李殿元教授在本书中,不仅围绕“成都”之名的来源及其涵义是“在统一全国战略中走向成功之都”进行论证,更重要的是,对“成都”之名所涉及的许多问题都敢于直面讨论。例如提出最早对“成都”释名的是李昉的《太平御览》而不是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征服古蜀是秦对统一全国战略的首先一步;成都、新都、广都为“三都”的时间是在三国时期而不是古蜀国时期;古蜀国的“蜀”字是他称而非自称;“成都”得名是在张仪修成都城之后;等等。这些观点虽为一家之言,却因其讨论采用三重证据法,即传世文献(历史典籍)、田野调查(包括文物考古)、口传资料(口述史)相结合,辅以语言学、文字学、比较学的功夫,对成都上下数千年的相关历史记载、文化事件、社会问题予以整饬剖判,条分缕析,并将它们置于人类文明长河以及中华文明“满天星斗”多元大格局(包括大变动、大演进)中进行观察、审视,从而使其论证依据充分,张弛有度,要言不烦,一语中的;行文则具有条理性、逻辑性、科学性;观点虽别出机杼,却大体在理。
李殿元教授正是这样于百家争鸣与百花齐放中,从各个方面展开自己发散性学术思路的。他以一人之力持续撰写出十多篇论文,对于成都得名进行追踪性的研究而成果斐然。亦如学者屈小强先生所评论:“李殿元的研究是站在前人肩膀之上的,却又是以自己的方式来解构‘成都之问’的三重扃锁的。”
关于“成都”得名的来历,本身就极富争议性。作为学者的李殿元教授,他宁可将《成都得名研究》原本的专著“委屈”为“编著”,也要增加“附编”,从而将所有成都得名研究具有影响性的论述,如任乃强、李金彝、王家祐、温少峰、徐中舒、谭继和、孙华、徐学书、钱玉趾、贾雯鹤等学者的论文全部收录于该书。这样做的意义特别值得肯定,正如李殿元教授所说:“‘成都’得名研究,学术界暂时可能尚难以统一认识。那么,将关于‘成都’得名研究的文章汇于一处,说明我们这代人对这个问题进行过非常认真的研究,虽暂时没有统一意见,却为后人留下了一份详尽的研究资料,这也是我们对这个研究的贡献。”
今日之书,社会价值
地名不仅代表命名对象的空间位置,指明它的类型,而且还常常反映当地的自然地理或人文地理特征。地名虽然属于历史地理学,但从文化学的角度上看,地名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既有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又具有相对稳定性,保留了较多的历史信息,积淀有深厚的文化。因此地名既为空间的生成,亦为时间的生成,而且在每一時代又不断积淀、扩缩、解构与重构其内涵与外延。它属于一种文化性的社会历史记忆。
成都(包括所在的成都平原)的神奇,因有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的存在;成都的非常,是由于它开启了南方丝绸之路;成都的富有,是因缘于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修筑,让成都平原取代关中平原而成为“天府之国”、唐代成为“南京”、宋代作为发明纸币的“交子”之城,时谓“扬一益二”,为中国农耕时代最为发达的工商业城市之一。继往开来,当今成都的昌盛,是因成都得天时地利人和之缘而为中国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科技中心、文创中心、对外交流中心与综合交通枢纽中心。
我们可以将《成都得名研究》视为关于成都的历史文化记忆的知识文本。它涉及成都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包括神话传说、民俗风情、方言俗语、考古、文字、移民、族群聚落以及城市规划等等。从资政与参政的角度,我们亦可据此探本溯源,了解成都从何而来;还可以借鉴历史文化,明析其对今天成都发展的种种影响。
我们可以将《成都得名研究》视为关于成都文化的历史文化记忆的勘误文本。因为李昉、乐史等人最早对“成都”的释名,虽然是错误的,影响却非常大,至今一些学者乃至政府文件,仍然在沿用,这并不利于成都未来的建设与发展。而李殿元教授则得出了“成都”这个名称的含义:在统一全国战略中走向成功之都。其不仅追溯成都历史文化的形成与演变,还回应了今天的成都社会文化的定位与发展问题,并瞭望明天成都文化的远景。在这一意义上,李殿元教授的《成都得名研究》既是探析成都文化的昨日之书,亦为展望成都文化的今日之书,委实具有较高的社会人文价值。
作者:知名书评者,成都锦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