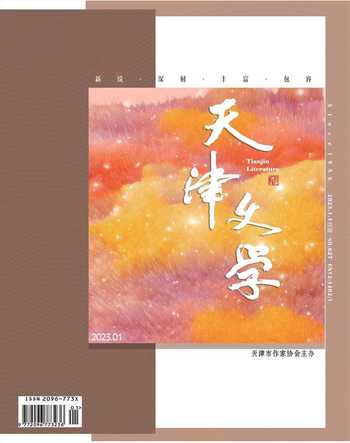祖屋
王淑彦
1
“唐宋亲情会”微信群里,四哥发布了一条信息,引起了一场舌战。
四哥说:“老家的祖屋年久失修,耳房房顶落架了,门窗也掉了。正屋房檐脱落,朝阳的坡屋顶子上的椽子腐朽了,塌了两个大窟窿。请家人们出出主意,该怎样处置老房子?”信息发出的时间是下午五点,晚饭后,群里热闹起来。
“唐宋亲情会”是由大外甥建起来的,名字也是他起的。他喜欢唐诗宋词,想让这一大家子过上诗一般的生活;也听说老家的村庄建于唐末宋初,就随意起了这么个名字。进群的是我们兄弟姐妹和子孙们,三代三十四人,时常聊聊老家、祖屋、祖院、祖辈、父辈和现在,很温馨,也很浪漫。说到祖屋要坍塌了,大家反应各不相同。
第一个发言的是大姐,她是老师,说话很有条理,也挺直白,免不了得罪人。“祖屋咋就塌得这么快呢?上次去不是还好着呢吗?咋说塌就塌了呢?再说,祖上家业怎能断在我们手上?不能丢,这还用讨论吗?翻修!实在木料不能用了,重盖,一定要把房子建起来。那可是祖祖辈辈几代人的心血啊,咋能塌掉不管?咱们不怕丢人吗?”七十四岁的大姐,现退休,在廊坊居住,她感叹着。
“大姑,重盖谁去住啊?你又不在家,我们这一代人都在外地工作,城里有房也都不在家,盖上也是闲着,闲家物,没用。”一个侄子表态了。
二姐说:“叶落还归根呢!出嫁的闺女总想回娘家看看,谁也不希望娘家房倒屋塌。再说了,那里不是还有大家共同的念想嘛!我同意重建,那木料拆了也用不上,都酥了。”
“我亲爱的姑姑们,为了个念想,投那么多资金翻盖,不值得。在那么高的大台台上盖房,成本高不说,连个车也进不去。从东边走,得从斜坡上走上去,拐两次弯儿,从大街上走进家里。咱那王家胡同是按推进平板车的宽度设计的,也开不进汽车啊。家家都有车了,总不能不开车吧!”一个侄子论述着。
“姥姥家的房子别看矮,但暖和,我还想躺在炕上数星星呢。你们要是翻盖啊,算我一份,我也出钱。”一个外甥女陈述着。
“能躺在炕上数星星,那也能在炕上望月亮吧?多惬意啊!盖吧盖吧,浪漫的生活。对了,听我妈说,还能在房顶上看长城,还能听到大山的回声,多美啊!那是城里人向往的营地啊!”外孙女想象着、描绘着。其实,那就是我们小时候的真实生活。
“想象很浪漫,现实很残酷。那处祖屋矮矮的,上百年了,拆下来的材料是不能用了,要盖就得买新的。谁出钱盖呀?盖了又归谁呀?你们要回家,可以住家里另外两套房子,我爸妈两人,也不用住那么多房子,他们还等着你们回去做伴呢!我说姑姑们、伯伯们,别操心了,卖了得了。”又有侄子表态了。
大哥没有儿女,住在养老院,他只用手机打电话,不会玩手机,他是看不到群里对话的。三哥也于一九九八年因车祸去世了,留下两个侄子,都在外地,没有发言。
二哥不再沉默了,发表着自己的观点:“卖掉是不好办到的,因为那是祖上传下来的房子。我们哥儿几个分家时,只把母亲和我们几个盖的新房子分了,祖屋是作为家中公产保留下来的。分家的时候,我在唐山,妯娌们议论为什么不分祖屋,这几年我好像越来越明白了母亲的意思。那个地方不能卖,那是祖上留下的根,是大家共同的精神家园啊!”
母亲于一九九〇年的农历六月十三去世,从那时起,祖屋再没住过人。母亲去世后的第一年,那座温馨的小院冒出来一棵棵洋槐树苗,经四哥修剪留下来二十多棵。三十多年过去,那些洋槐树长到了二十多米高,双手一搂,都快抱不住了。每年五六月份,满院黄白色的一嘟噜一嘟噜的槐花,钻出浓密的长卵形树叶,散发出清新的、淡淡的芬芳。每每在这个时候回到院中,浑身都被槐香浸染着,直达心底。好像母亲伸开双臂,拥抱着我们;又好像在母亲的怀里,闻到了母亲身上奶香的味道。
每到槐花盛开的时候,我们兄弟姐妹常会不约而同地聚在那里,有时带着孩子,有时带着媳妇儿、老公,在那里相聚是最快乐的事情。回忆过去,重温往事,有说有笑。大家神奇地发现,那些树不是树,而是母亲的化身。槐树摇曳的“沙沙”声,分明是母亲的叮咛与嘱托;槐花甜甜的清香,分明是投进母亲怀抱闻到的奶香,更像是母亲端来的饭香;槐树下习习的清风,分明是母亲的抚摸与亲吻。
“奶奶家的槐花开了吗?今年开得艳吗?门口那盘石碾还在吧?房后那棵杏树还结杏儿吧?那杏儿金黄金黄的,特别甜,至今我也忘不了那味道。”远在美国工作的侄子,抽空发来一条信息。
“我想回去看姥姥家了。姥姥最喜欢我,还教过我《黄河大合唱》呢!要盖房,我出一份。”一个外甥表达着自己的心情。
随后,孩子们发来一张张照片。有的在耳房前拽着门环,一个红衣少女的形象;有的在石碾上盤腿而坐,一个淘气大男孩儿的留影;有的是登着梯子,拿着篮子,上房取红薯干、取柿子的样子。还有几张孩子们的合影,他们用槐花编出一个个美丽的花环,套在脖子上,槐香萦绕着他们……
二哥发来一张全家福,还调侃了一句:“你们看照片里没有谁?她去哪里淘气了?”我知道二哥在点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在报社工作的二舅,给全家拍合影的时候,我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呢。在祖屋正门前,围着父母的哥哥姐姐们高兴的样子,一直让我羡慕。
四哥说,那些槐树已经砍掉了。因为邻居们说那里长期不住人,常有野猫聚集,晚上的叫声、黑天里的流窜让他们害怕。再加上树木越长越高,遮蔽了邻居家的房屋,房子不见太阳,房子上的木料发霉了,总是从瓦下掉土坷垃,瓦片也快掉下来了,他们要求伐掉那些洋槐树。四哥顺从地听了他们的要求,找人伐掉了,槐树钱顶了伐树的工钱。槐树没卖到钱,白白伐走了。只是伐树的时候,由于槐树太高,把房子也砸坏了。大家一直在心中的疑问,加速祖屋坍塌的原因,好像找到了。
“唐宋亲情会”群里顿时无语了,出奇地寂静。
一大段沉默后,是大姐、二哥、二姐、三姐和孩子们发来的一个个流泪的表情。继而,又发来一串串问号和省略号。
2
算起来,祖屋该有一百三四十岁了。我们的祖籍在白洋淀边上,算是一个小小殷实之家。先人们从山西大槐树迁移到一个叫西向阳村的高岗上,靠着勤劳置办了田产,盖上了瓦房。可两次鸦片战争后,政局混乱,列强入侵,再加上不是旱就是涝的自然灾害,家境渐渐衰落。
有一年水灾,白洋淀一片汪洋,淹掉了土地,淹没了房屋。高祖王会香带着名叫“江、河、湖、海”的曾祖四家人,溯源向西北方向逃荒,来到了拒马河的发源地涞源。他们先在杜村落脚,安下家来之后,住了一二十年,留下了大曾祖父江和三曾祖父湖;后来,这两家成了杜村的名门望族,后人曾当过县法院院长。高祖又带着二曾祖父河和我的曾祖父海两家,继续向东行进二十五公里,来到了拒马河北岸悬崖峭壁的高台上。与卢姓、颜姓、马姓、李姓、张姓、林姓等融为一体,在名叫辛庄的村里,建起了王家胡同。
老王家以织席、耍叉会、办音乐会、做生意、贩牲口为业。三里五乡的,没有不知道他们的。遇有红事、白事,他们会拿上音乐会的家什——笙、管、笛、箫、云锣、唢呐、二胡、长短号子等乐器,打场奏乐,说唱助兴。每遇节庆日,他们也会办场音乐会,送给乡亲们乐和乐和。乡亲们求着帮忙修补炕席的时候,他们会拿着席刀、席篾儿走家串户,为乡亲们修修补补。这些活儿从不收费,既搭工,又搭料,因此赢得了乡亲们的认可。虽是外来户,可没有外乡人的感觉。
村里的人们大多也是外地聚集过来的。卢姓来自涿州卢家场村,古时称范阳郡,是东汉政治家卢植的后裔。颜姓来自山东,是颜回的后裔;也有人说来自博野,是颜元的后裔。马姓来源于西北或是蒙古草原。这个村庄据说从唐末宋初开始有人定居,宋辽战争后,“檀渊之盟”把此地归属了辽国管辖。一代代繁衍生息,渐渐兴盛起来。民风既有农耕文明的儒雅,又有草原文明的彪悍。而白洋淀搬来的王家,既有文的音乐家风,又有武的耍叉弄枪,还有实实在在的持家本领,村里的人们都很喜欢老王家的人。
老王家盖房的时候惊动了乡邻。在那高台之上的一个中心位置,东西向盖起了十五间大北房。
房子盖好了,在村里虽不是最高的,但也是高房子之一。高祖上过私塾,教育孩子们很有办法。曾祖父胸怀宽广,也很讲究,房子绝不能超出邻居房子的高度,那样会压住人家,妨碍人家,会影响和气,一切都以和为贵,以邻为友。
后来的日子还算顺利,曾祖父给我的爷爷们都娶了媳妇。我的祖父为老大,叫王殿秀,住在最东头的院落,娶了个卢氏的奶奶,高祖、曾祖父最满意。他们说,卢氏家风好,卢氏女子懂事理,王家要发达了。后来,我的父亲、伯父、叔父们相继来到了祖屋里,可惜没有一个姑姑,表亲就少了些。
3
高祖为躲过水灾、八国联军侵略的外患,选择了留在山里的高台上,建屋定居,繁衍生息,然而却没能躲过日本人的“烧光、杀光、抢光”的魔爪。
“九一八事变”后,大伯父被国民党抓壮丁,背硫酸时烧死了。年轻的二伯父去保定参加了抗日救亡的队伍,成了一名共产党员。三伯父参加了八路军。老王家又有了一个特殊的名字——“抗属”,“抗属”真让老王家“火”了几把。
那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父亲接到组织上命令,让他组织村里的民兵埋伏在闫庄子的山坳里,负责配合八路军歼灭从易县进犯涞源的日本鬼子。那天,父亲给奶奶说,日本鬼子要攻打县城了,劝奶奶和乡亲们一起躲进山沟里。奶奶还有些舍不得这房子,说:“不看着哪行啊?日本人能拿我们老婆子怎么样?”祖父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他好像知道了父亲“要出去干事儿”的意思,就嘱咐说:“放心去吧,家里有我呢。”父亲辞别二老,随队伍出发了。
战斗进行得很激烈,凭借地形和熟悉的环境,军民打了个大胜仗,鬼子们被打死打伤二百多人。清理战场的时候,父亲望了一眼自己的村庄,熊熊的火焰冲向天空,一股烧焦的味道飘了过来。“不好,逃跑的鬼子又去咱们村里祸害去了。”他们穿过玉米地,蹚过拒马河,从南沃头的河底攀岩爬上村里。从村西最高的山梁望去,王家胡同的房子上蹿着火龙,直上云端。
“队长,先从你们家灭火吧?”
“不行!先救颜家,后救我家!”
“队长,怕来不及了!”
“别啰嗦,这是命令!”
那时候的父亲身体结实,一米七八的大个子也就一百二三十斤,身体轻盈,再加上常年做叉会会长,功夫让人称道。十来公斤的钢叉,在他手上好像一根竹竿那样轻,在头上、腰中、裆下舞动着,边舞边唱。钢叉所到之处,呼呼生风,扇动着树上的叶子一片片飘落下来。月牙形的钢叉颈上挂着银白色的套环,旋转起来好像寺院里塔铃的交响。在这熊熊大火面前,父亲和他的队友们挥舞着扫把猛烈抽打,扫把着火了,浇上些水;扫把烧没了,再抽出一把荆条,在房梁上、梯子上抽打着火苗。他们与火龙较量着。救下几处房子后,父亲最后来到家中,房上的椽子、檩条都烧落架了,木料发出“嘎巴嘎巴”的声响。他的队友们抽打着零星的火苗,父亲发现了蜷缩在西墙根儿下的祖父、祖母,他们相拥在一起,目光中带着痛苦,带着仇恨,带着希望。那一刻,所有的力量都压在了父亲身上。
“你们没走啊,吓坏了吧?”父亲问双手一直在发抖的祖父、祖母。
打量之后,父亲说:“还好,没伤着你们吧?身体没伤就好。别急,我再把房子盖起来。”不知是吓走了魂儿,还是吓破了胆,两位老人满脸灰色,表情木讷,听到父亲的话后,才失声痛哭起来。
战争环境下,没那么多讲究,房子能住就不错了。再次上梁的时候,父亲找来木匠,把烧焦的柱子顶端锯掉,露出新木茬儿;又把烧煳的大杔、上梁、中梁刮去煳面,安上椽子、檩条,再覆上青瓦,就重新盖好了新房,只是比隔壁三祖父家的矮了一些。
祖父和父亲经常挨三祖父的数落,责怪他们做抗属。房子被烧了,祖父、祖母有时候也会责怪父亲:“不老老实实做生意,总往外跑,做什么?还有老二老三去干什么了,不回家,回家就赶上跟鬼子打仗。你们兄弟几个在做什么?”父亲笑而不答,被问急了就说:“你们的儿子们在做大事、光荣的事,在打日本鬼子!”说到这儿,二老会反问父亲:“你们能打日本鬼子?狠狠地揍他们!要给咱们家报仇!”父亲咧嘴笑了。
老家房子第一次被烧时,母亲还在水桥沟种地,喂姥爷跑脚的红棕色骡子、深灰色马。母亲成为党员后,父亲紧追着母亲,母亲却不知道父亲打过游击。听说父亲先救别人的房子,让自家房子落了架,母亲才真的动了心。后来,母亲成了祖屋的主人,也是住的时间最长的一位。
没想到,母亲成为祖屋主人的一年后,祖屋又一次面临灭顶之灾。
我们的村庄四面环山,东侧、北侧、西侧都是绵延起伏的山峦。南山离村庄有两公里的路,南山脚下是闫庄子村。一条蜿蜒的拒马河从西向东缓缓流淌,两岸的冲积扇上,祖辈们辛勤耕耘,已培植出肥沃的土地。
北部群山中,盘旋的长城犹如一条巨龙,保护着这里的山川、土地和人民,但它却未能保护住群山里的宝藏。日本人在北山开了石棉矿,抓民夫运石棉,修公路,打石棉矿石。新婚不久的父亲、母亲接到上级通知,要想办法切断交通,不能让宝藏糟蹋在日本人手里。
在祖屋的炕上,听着从拒马河传来的水声,父母心里极不平静。一辆辆运石棉的日本汽车的喘息声,刺痛了他们的心。这里是中国的国土,是中国人民的家园,日本鬼子是什么东西,竟敢在我们这里撒野。望着窗前的明月,父亲母亲躺在炕上,合计着破路的计划。他们想到了一句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们的责任就是切断日本鬼子的运输线,保住我们的石棉矿。
村里民兵来到了长城岭的马路上。从山上滚下一块块巨石,用铁锹挖出一道道壕沟。当鬼子发现的时候,长城岭上的山路已被破坏了两公里多。父亲和他的队友们完成了一次巨大的使命,快速返回主村的路上,被站岗放哨的鬼子发现了。可恶的鬼子对无辜的祖屋,放了第二把大火。
父亲、母亲又一次重复着救火的路子。先救他人的房子,当回到自己家里时,房顶子又一次脱落下来。再次盖上房顶,进屋住的时候,房子又降低了高度。
祖屋第三次着火,是因为给抗日民主政府和八路军运送公粮被日本鬼子发现。父亲告诉母亲,抗日民主政府的同志和前线的战士在吃臭椿树叶、山桃树叶充饥,战斗力急剧下降。上级通知,要把坚壁在后沟子的公粮送出去。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任务。而那个时候,日本鬼子正穷凶极恶地进村扫荡,稍有不慎,就会暴露;稍有疏忽,就会全军覆没。还是在祖屋那盘热乎乎的炕上,父亲、母亲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用给祖父祖母准备的棺材板,将公粮送出去。送出去之后,日本鬼子对祖屋点了第三把火。第三次修好入住时,房子更矮了。不久,大哥出生,长到了一米八的大个子,进门总被提醒:“注意,别碰着头。”
4
一九四九年后,日子平稳了,父亲母亲告别了“头掖在裤腰上”的日子,战斗中凝聚的爱一下子爆发出来。我们兄弟姐妹们相继出生在祖屋里,过着“屋矮声高”的热闹生活。
记得兄妹八人常坐在热乎乎的炕上,脚对着脚猛劲儿地对着踩,谁的脚先歪了谁就会输,谁输了谁唱歌。我最小,也想显摆显摆,故意被踩歪了,站在炕上,高声唱起来。把熟悉的歌唱完,哥哥、姐姐们再教首新的。那段时间,物质上说不上富裕,可精神上是轻松愉快的。
父亲去世得早,可我并不缺爱。在那个低矮的祖屋里,我得到了大家的爱护,好像父亲就在身边。
母亲把三个哥哥送到了部队,虽然很想念他们,可别人问起想不想孩子的时候,她嘴上总是说:“不想,他们保家卫国去了,去搞建设去了,有什么好想的?”可每当有人问她这些问题后,她总会嘱咐我给哥哥们写封信,告诉家里的情况,嘱咐他们在部队建功立业。那一封封饱含母爱的家书,都是从祖屋发出的。我从小就成了母亲的秘书,办公地点就在祖屋。
有一年,一组工程兵进村铺设光缆,住在我家。清澈的拒马河水流淌着,战士们挖好导流渠后,挖沟铺设光缆。正在铺设线路的时候,导流渠冲开了一个口子。眼看就要前功尽弃,战士拉起手,坐在决口位置,用身体挡住了决口。在高处观看的母亲急忙回到家中,把正屋腾出来,把住在东屋的战士们的被褥抱进了正屋;还烧了满满一锅热水,另一锅煮了半锅姜汤送到了工地。战士们回到家中,高一米八的大个子低头走进正屋,用热水洗脸泡脚时,母亲的眼泪像串珠一样流淌。
我们的孩子们都愿意上姥姥、奶奶家。在姥姥、奶奶的炕上,做游戏、听故事、听小喇叭,心里美极了。祖屋很矮,可我们的心很敞亮,像长了翅膀,飞得很高很高。
一大家子人赶上了好时代,有在全国各地工作的、上大学的,还有留学国外的。村里人夸我们有出息,请教母亲咋管孩子,母亲常说:“没有别的,听党话、跟党走,走不错的。”
家里人陆陆续续外出工作或远嫁他乡,孩子们也在城里成家立业,村里只留下四哥和四嫂。母亲在世时,盖了两处大院,房子是够住的。那处老院一直保持着第三次重盖的样子。后来,村里给补助,让修缮一下,可我们怕父母和祖辈们“找不到家”,一直没有翻盖。
祖屋面临坍塌,由四哥代全家申请,经村两委同意,我们兄弟姐妹们集资翻盖了新房。
新房是由二哥主持盖的。拆祖屋时,二哥摆了个方桌,烧上三炷高香,对着祖屋深深鞠躬:“列祖列宗在上,今天我们这些后人们要拆除老宅,盖新房了。请你们也住住新时代的房子,有排水,有空调,有电灯,还有云数据呢!不管你们在哪里,相信你们一定会看到美好的新生活的。”二哥对祖辈们说着心里话。他还转告列祖列宗,他和我去白洋淀寻过根了,那里的老宅子一直有人看守,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翻盖做了大队部,老家的亲人们一直盼着有人回去。
祖屋拆除的过程让人心酸。我们发现祖屋用的木料很凑合,特别是山墙的三角形横梁是烧断的,搭在山墙上,根本起不到固定平衡作用,想起来都后怕,一旦出现松动,中梁就会砸下来,后果不堪设想。特别是那些年,大哥作为生产队的计分员,每天晚上祖屋里都坐满了人。也许是好心有好报吧,祖屋一直呵护着我们。
新房盖好了,跟邻居的一样高,一样宽敞、透亮。盖了正屋和东屋,西侧是平平整整一面墙,请画家给创作了一幅《寻源图》:一队人身带席刀、唢呐,肩挑担子,孩子们坐在担子两端的筐里;他们身后是一片汪洋,前方是绵延起伏的群山,山上是古老的长城、烽火台。
令人想不到的是,新房盖好后,院中央竟又长出几棵新洋槐树苗。四哥拍下新洋槐树苗,发在了“唐宋亲情会”群里,并留言:“明年槐树就要开花了。”后经我们兄弟姐妹们讨论决定:“一、大家集资盖房的明细记录放在新房的收藏室里,作为家庭文物予以保管;二、新房仍是公产,每个人都有居住权,原产权属于兄弟姐妹八人;三、每年选出一个院长,负责排班入住;四、每个人都要在新房记录本上续写新祖屋居住的故事;五、每年中秋节和槐树开花的时候,是全家大聚会的日子,平时的小聚自由组合。”
最后一条信息是大姐发布的:“请家人们把老祖屋的物件、照片收集存放在新祖屋里。每个人都要写‘我和祖屋的故事以及每年的进步与变化,也一并存放进去。”
责任编辑:杨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