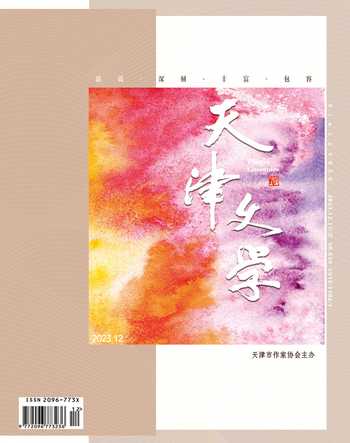小河归来
老家坐落在一条小河边,河里的水常年泛着银白色的光,两岸杂树环绕,旁逸斜出的弯柳和翘立的直杉比较常见。冬天时树枝秃顶,河岸像一幅如烟的水墨画,其他季节林叶丰茂,呈现斑斓的水彩模样。特别是晚霞铺满河面,一群白鸥成群结队路过,一条鱼“扑腾”跃出水面时,那情景格外明艳动人。
沿着河坝走出去,是一条东西向的公路,约四十里。公路西头是我们的小镇,小镇有小学和中学,有简短的集市,小镇窝在长江怀里,需坐船才能去到远方。公路东头是邻居小镇,热闹得很,理发店、服装店、文具店、小吃店等各自一条街。从这个小镇继续南行,就能到市里,但需坐蓝色大巴士。我读高中以前,没有出过这两个小镇。有时会望着巴士屁股发呆,畅想它们的去处。
我读书的小学就在河对面,放学后我们都是走河边回家。在河边有时可以捡到大鸭蛋,有时可以捡到河蚌,有时还可以摘些紫桑葚、野葡萄。我和小伙伴们夏天不用穿鞋,在追逐打闹中我们就轻松地度过了童年。
初中后,我的天地从河中心转到了镇上。儿时的许多伙伴辍学,镇上的中学相比乡下小学多了许多考试,我不由得收敛了玩性,变得内向起来。初二,还不到穿裙子的季节,我已经踩上了凉鞋。清晰记得,它被丢在商店外面只卖三块钱,所以我选择了它。褐色的,有点挤脚,我却一点也不在意,为脚指头能透气而感到高兴。
那时我也有了辍学的念头。虽然成绩说得过去,可是在同学眼中,我被看成一个性格孤僻的人。她们谈论明星八卦,我完全一头雾水。她们喊跳舞我不去,喊买零食我不去,我像钉子一样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慢慢地她们不再叫我了。
大概那时候,我开始领受到物质贫穷带给人的羞辱感。有时我会最后一个跑进食堂,打两毛钱的米饭,要一点黄瓜盐水拌饭,而大多数时候是嚼五毛钱的干脆面。对于女孩子戴的各种发饰,比如粉粉的彩带啦,心形发卡啦,等等,我也不再感兴趣。夜里看着窗外的月亮,我常常希望自己去远方。
而且我还差着学费。总以为学费是老师和家长之间的事,没想到有一天戴眼镜的班主任特意找我说明学费的事。他开口的一刹那,我迅速低下了头,脸上不自觉地烧了起来,感觉唯一支持自己的老师也不存在了。或许,那个年龄的女孩,经不起一丁点与尊严有关的挫折。
酝酿了一段时间,我开始关注打工和创业的故事,还特意写了一个打工女孩帮老板生意兴隆的剧本。老师阅后什么也没意识到,只说叙述得不错,打了个A。
一天一天地挨过,课桌越来越乱,我总是漫不经心地把书扔进桌肚,下次要用就埋头找半天。如果有谁翻开我的桌肚,应该能感受到里面的“疾风骤雨”。终于在一次晚自习后,同学们走光了,教室里黑了下来,我背起书包离开了学校。我朝镇子尽头走去,那里是长江,江上有船,坐上船,就可以去远方。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江对面是另一个县,所以其实到不了多远。但那天,我还是穿着三块钱买的挤脚凉鞋,硬拖着脚掌,乘路灯的微光,一步一步挨到了江边。心里的酸涩让我忘记黑暗大墙,一点点微光就给了我前行的方向。
翻过一座矮堤,终于走到江边,我却犹豫起来。江水漆黑黑的,江边隐隐约约有一只船在忙碌,我站在灯光下,船上的人就看见了我,朝我喊话:“坐船吗?”我说:“等一会儿。”我手上并没有钱。江边有个小屋,可能是在江边干活的人家。透过白色的破塑料窗,我看到一个老婆婆,她拿着针线在缝着什么,同时跟一个老爷爷说话。我很想进去坐坐,找她借一点过河钱。但我到底有没有敲门进去,老婆婆有没有对我说什么,我有没有开口借钱,这些全不记得了。我大概是敲门了的,老婆婆大概问了声“谁”,但我没应声。在窗外看着那对老夫妻彼此细心干着手上的活,心里慢慢涌上一点暖意。当船家催促说:“船要走了。”我说:“您先走吧!”
我站在那里,前方一片黑暗,只有身边小屋露出的灯光,从黄变白,越来越亮,逐渐变成一个擦不掉的印记。我应该站了好久,腿都麻了,最后决定回家。从江边穿过小镇,跨过公路再回到河边的老家,平时骑车都要半个小时,所以我终于走到家门口时,已经过了午夜。路上静悄悄的,什么也没有遇见,阿猫阿狗都没叫一声,我忍着脚痛,像划船的船夫漂过黑夜。
我轻轻喊了一声,怕惊醒邻居们。父母房间的灯立马亮起,父亲出来开了门,像知道我要回来似的。似乎我不是半夜偷跑回家,而是早约定好的,他一直在等我。我还在为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而忐忑不安,父亲竟然什么也没问。后来他说,他确实是感到很疑惑的,怎么回来那么晚,又不是周末?但想着太晚了,第二天再说。他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我就又离开了家。
是的,回到家没有被问起原因,这让我心里又多了一些怅惘。我脱下鞋,在灯下审视自己的脚,已经起了不下三个脚泡。我有些疼惜自己,想着或许明天与父母谈一谈。但第二天,当我起床时,他们已经下地干活了。我失望极了,长期以来濒于崩溃的心情又拉开一个口子。我决定不等了,便朝另一个镇走去,能走多远走多远。
那时候有一首歌很流行,叫《橄榄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轻流的小溪,为了宽阔的草原,流浪远方,流浪。”这首歌把“流浪远方”带到了我心里,我时常想着它所蕴含的美好。
现在想来,一个镇能有多大呢?步行离家出走,能走到哪里呢?我想着到一家店里打工,安顿下来,但一切都得靠运气。去往邻居小镇时,碰到村里几个熟人,他们问我往哪里去,我故作镇定地说有事。走到邻居小镇后正不知方向地乱撞时,看到一位漂亮阿姨坐在店门口,她太像我的有珍姨了,我不禁停步看了看她,她恰好回头,脱口而出:“青青吧?”我立即向她奔去。原来表姐在这儿开理发店,有珍姨过来帮忙。
有珍姨家在南边另一个镇,她突然出现在隔壁小镇,这是我没料到的。多年后,我上大三时,有珍姨病逝。她不到五十就去世,我追忆她坐在门口召唤我的场景时,只觉得那一刻她就像一个发光的天使。
莉姐那时十六岁,皮肤散着白皙柔嫩的光,充满弹性。她的眼睫毛很密,眼睛和有珍姨一样又黑又亮,下巴上还有一颗痣,越发显得妩媚。她招了个学徒工秀儿,秀儿苗条可爱,这个理发店因此很招男孩子青睐。
“青青,你怎么到这里来了?”有珍姨问我。
“我不想上学了。”我说。
“我很少坐在外面。我要是不回头,你不就走过去了?”
“可能吧。”
“成绩这么好,不上学多可惜。你看你莉姐,给人洗头理发,不辛苦吗?”
“是啊,你爸妈知道你到这里了吗?”莉姐问。
“我没跟他们讲。”我低头说。
因为我表现得有抵触情绪,有珍姨就让我先玩几天。而我打的小算盘是,找机会借一点钱,继续去远方,或许找一个餐馆打工。这样,我就在理发店玩,门店后面有房间和厨房,我可以住下来。我翻着些娱乐杂志,顺便看着那些顾客进进出出。
我发现有个平头青年老来找秀儿洗头,还爱吹口哨,就说:“他喜欢你咧。”
“我才不喜欢他呢,我喜欢谢霆锋。”她这么一说,我就想起女同学们也谈起过谢霆锋。八分头、喇叭裤,眼睛和嘴角洋溢着微笑,一副酷酷的样子。
秀儿十五岁,一头微黄的马尾,穿紫色短袖衫、黑色阔腿裤、高跟凉鞋。她的五官特别柔和,脸上有一些绒毛,洋溢着欢笑。她知道客人喜欢她,也知道师傅莉姐喜欢她,因此总是那么快活。
我从来没有那样的快乐,我几乎立即领悟这差距在哪里。
“洗头要看手。”莉姐说,“细长、灵活,才是巧手。”
我看了看自己的手指,又短又粗,再看秀儿,她的小手在顾客头上翻飞,像一对轻盈的燕子。
我的心里有了忧愁,不知道这双手以后能做什么。
店里还有另一位青年老出现,瘦长英俊。有珍姨不在眼前时,我看见他和莉姐亲密搂抱。有一回有珍姨问我:“他们是不是一起到楼上去了?”我不好说什么,就说他们挺般配的呀。有珍姨的脸耷拉下来:“小孩子懂什么!”原来这青年是门店老板的儿子,他和莉姐恋爱,但有珍姨看不上他。我忘了他的名字,就叫他俊哥吧!
有一次又聊起不想读书的话题,俊哥说了很重要的话:“如果你能活到八十岁,你十三岁不读书了,那你以后的人生都要被你不读书限制,你能做什么呢?我有个朋友不读书了,只能去开拖拉机。”我数学不错,做完俊哥这个算术题立即让我后悔。我心里开始动摇,要不要回学校去?
可是自己跑出来的,又这么回去,实在太憋屈了。我嘴上就继续强硬:“你也没读书了呀!”
俊哥爽朗一笑:“所以我现在愁得很。你莉姐这么漂亮,我能不能娶到很难说。”我那时以为他们都长得好,俊哥家庭还可以,有珍姨没有理由反对。可事实是,他们的恋爱遭受双方家庭的阻拦,即使后来结婚并有了孩子,最终还是分开了。
就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父亲出现了。没有人通知他我在莉姐这里。他说,班主任找到家后说明情况,他就开始放下农活四处找我。他骑着车,把所有能想到的地方都找了一遍,还问了人,有人说朝这边来了,最后决定来莉姐这里碰碰运气。他说我应该不知道莉姐的地方,能在这里看到我也很意外。
我心里涌起一股热流,多么感激父亲及时出现。我已经不好意思在莉姐这里继续待下去了,但也不好意思自己走回去。父亲来了,他没有任何指责的话,只说:“回去啦!”我就拿起书包坐上了他的后座。
我本想告诉父亲自己在学校所有的委屈,但还是忍住了。毕竟,在他的心中,我赢得过满墙奖状,是走到哪里老师夸到哪里的孩子。但父亲并不知道,小时候同学们总以我为中心,如今他们选优秀学生,会故意不选我。可是,我什么也没说。正如,父亲自己的委屈,也从来没对我说过。
父亲骑着车,风轻轻地吹过我们。他突然说:“你吃不吃小笼包?”我很少撒娇,这时候就高兴地说:“吃。”
父亲就停好车,到早餐店买了一袋小笼包,递给我。我给他一个,他不吃。我就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慢慢咬,像咬一袋糖。小笼包吃起来并没有闻着香,但我还是一脸幸福的样子。
回到学校后,我照常学习,心里却明白自己已不再一样。
暑假补课期间,我一回家就往小河跑,河流无声地召唤着我。我拿出家里的洗澡盆,轻轻地躺在上面,随水飘荡,还拿起一本文学书翻看,想象在死海里漂着浮着的样子。恰好有邻居看见了,赞扬说:“青青好爱读书哟,在水里都拿着一本书。”
我是爱读书的孩子吗?在现实中屡次碰壁时,我确实每每只能通过阅读来寻找出路。而每次回家,只要看到清亮的小河,心头就莫名地涌上一种安慰。
去年五月,在现实中打滚、疲惫不堪的我回到家乡,却看到河流正赤裸胸口,大片大片的河滩露出棕黄色的皮肤,有沙漠的质感,河水瘦成一条小沟在河心苟延残喘。从来没想过,会见到小河干涸见底的一面。走在河滩上,仿佛踏在一个爱人的心口上,有说不出的痛。放眼望去,矮草蓄势,成群的白鹭围在水沟边,仿佛在祭奠将要消失的河流。不久,河滩上的草叶疯长,高如密林,难以下脚,其旷其荒,令人唏嘘不已。
儿时在清水中嬉戏的记忆变得虚幻起来。小河大概是累了,费心养育村庄,却遭遇大旱。这些年,不在小河身边的我,仿佛一头被困住的小鹿,总想奋力奔进丛林,躲在芳草里呼吸。有一个声音说:“你要到对面的树林里去,可以,交出你头顶的犄角。”我不答应,于是被打倒,犄角被割去。我伤心地逃跑,此后一直顶着残缺的犄角苟活。我的整个青春,几乎被投进一所牢狱。
每当血液里的痛发作,真想用一把小刀把它们引出来。当我把烟和打火机放到抽屉时,又突然想起那个深夜,父亲像知道我要回来似的,立即起来为我开门。那一点点柔情,帮助我慢慢平息蓄积的愤怒和失望,得以重新面对生活。
让我没想到的是,今年六月回家,小河里竟然又“灌满”了盈盈的河水!它度过了整整一年的干涸岁月。那些无人打理的野草高得钻出了水面,留下曾经荒芜的印记。我问父亲,父亲说:“长江放水,河就活了。”
长江同样干旱,但为了搭救一条濒死的河流,它舍身放了水。
这种奄奄一息的挣扎,我在高考时、就业时屡次经历过。曾以为自己将死,但又慢慢活过来了。
记得十二年前,生命的链条突然断开,我把自己锁在不到十平方米的出租屋里。近半年时间,不与过去的朋友联系,每天泡在政治、英语、中外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书籍中。睡觉前一边泡脚一边看文学作品。书背不进去了就抄笔记,把知识点一一刻进脑海里。那是一段无声的时光,只有窗外的绿藤陪伴我。
但那段岁月毕竟有了收获,有了后来的南京求学,又有了回乡就业看小河的机会。十多年后,我还敢这么来一次吗?
河流的生命充满了弹性,我见证了它的盈枯。人也一样,或堕低谷期,或逢高光时刻。遇到低谷,再像儿时那样背起书包逃学吗?显然,逃是逃不掉的,或许可以来一段旅行,这旅行,或用脚步丈量,或用文字丈量。
一颗心到底可以碎成多少瓣?又可以愈合多少次?在书本搭建的世界里,充满了文字考试。而文字考试,比起烈阳炙烤、冷风扑面,确实来得温和一些。有机会,我还是想在小河的怀抱里躺一躺,听一听它干涸时的心声与它复活后的感悟。
逃学那一年遇到的莉姐,后来南下广东重新组建了家庭。那是另一个奋斗的故事。我因此知道,故乡的河流,流过那么多荆棘,铺陈那么多风景,已经融进了我们的性格。只要有大海,有长江,小河就会归来,继续映照天空。
泥北,原名毕文清,南京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语文教师。曾在《三峡文学》发表小说《白云深处》。
责任编辑:艾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