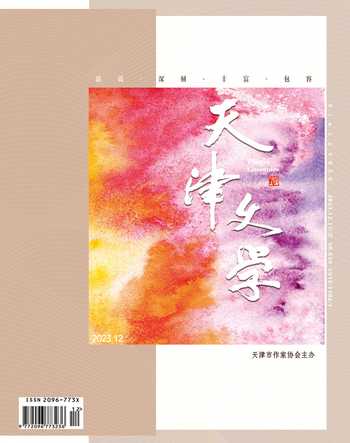那些年,我被斜视的人生
李霞
1
2009年4月,我从那所东经121度线穿过的常住人口不到300万的小城光荣毕业。
定语用到“光荣”两个字,是因为从毕业那天开始,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个人档案和简历中学历学位那一栏将标注为硕士研究生。如果不看学校,不念出身,那个门面至少还能像模像样装在兜儿里唬人一段时日。
那场令人生厌的春雪就那样不合时宜地在一个离别的季节呼啸而来。
清明刚过,谷雨未至,东北的干冷四月天还是挺让人记忆犹新的。在异乡求学两年半,我已经饱受那个小城“一年刮两次风,一次风刮半年”妖魔气候的摧残。未承想,临了,还得留些皴和冻伤在那张半青不黄的脸上,以证明我曾经来过。
那一次,应该是我人生最后一次随着绿皮火车慢慢爬了。
那一天,仗着夕阳的余光,临着刀子嘴豆腐心的东北风,我们一行五人踏上开往济南的列车,结伴去寻找人生中下一个停靠。
直到参加完毕业后的第一场考试,看到考场内外为找份糊口的工作而赶考的茫茫人群,我才真正理解了十多年前初中地理课本上对于咱们这个东方文明古国的定义——人口众多,到底是怎样一个概念。
整整一个月工夫,我来来回回奔波于济南的大街小巷和各所学府临时搭建的各式考场。多少年过去了,对于那一个个不堪回首的考试结果,我至今记忆犹新。银行入职考试我参加了一堆,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的选拔考试,最终都止步初试。唯一的差别是,前者成绩差一分,后者则是大比分落败。
再后来,我和80后们一样,还参加了各种级别的公务员考试、事业单位考试,结果无一例外都以失败而告终。在多种尝试未果之下,我不得不提前打道回府,回到鲁西北平原生我养我的小县城。
回家后没几天,你就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一种心酸叫有苦难言。
刚开始的日子还算痛快,每天雷打不动吃了睡,睡了吃,美其名曰是再也不用上学后的放纵。白天,串串亲戚,走走同学;晚上,看看电视,聊聊手机。没过几天,那句经常挂到嘴边的俗语就摆上台面:好日子到头儿了。没有终于的企盼,只有提前的落寞。
好歹得找个事情做做,至少向生你的爹妈证明你不是酒囊饭袋。接下来的一个月,我把大学里学完的八册英语课本翻过来倒过去温习好几遍。后来,又把从学校扛回来的那台陪了我好几年的二手电脑拆了装,装了拆。直到,有一天,我把机箱里每一个芯片的型号都记得滚瓜烂熟,再也无事可做;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日子真的过得不叫日子了。
后来,不论七大姑八大姨来我们家串门还是父亲母亲同事来我们家做客,都会问同一个问题——你们家闺女研究生毕业,找工作了吗?开始,我还礼貌性地应付两句。几次过后,那个千篇一律的问题摇身一变成了另外一副嘴脸——你们家闺女研究生毕业,找到工作了吗?虽然一字之差,但是在我听来却有质的区别。前者的意思是:如果还没找工作,应该尽早打算了,是善意的提醒;后者的意思是:还研究生毕业呢,找了那么长时间工作,怎么还没个结果,半是好奇,半是讽刺。
再后来,我开始尝试一种新的处理方式:躲。有一段时日,一听到屋门响,我条件反射似的躲进弟弟之前住过的小屋子,打开播放器,翻出磁带,戴上耳机,装作什么也听不到。慢慢我发现,掩耳盗铃有时候还是挺管用的。就这样,一个月又混过去了。
转眼间已经到了7月份,爹再也沉不住气,开始通过各种关系给我张罗工作。那曾经是我最不想提及的一段人生,我把它准确地定义为八个字——没脸没皮,生不如死。
那些天,我们全家都病了。我口腔生了疮,原因不言自明;我妈上了火,因为每天接收来自各方的唾沫星子和难听口舌;我爸苦了脸,因为每天都在求人,每天都在打探消息,每天着急又不能催,每天睡觉前都有一个响声在耳边响起叫作没有结果。
最终,时针分针转了多少圈以后转到了2009年那个枣花飘香的9月。最终,改变我命运的那场面试机会还是来了,在我毕业在家赋闲3个月零20天之后。
那一天,在多少年之后,我和父亲再次踏上开往天津的大巴去寻找我人生的下一个可能。从此,我再也没有离开过这座海滨城市。
突然想起来,还有一段伟大的“光荣历史”需要交代一下,就是在那个小县城,我的故乡,我还瞒着所有人参加了一个县财政局事业单位的入职考试。那是那一年下来,我唯一初试通过的一个考试,行测和申论两科总成绩位列榜首。最后要面试了,需要盖章走手续什么的,瞒不住了,实在没办法,我告诉了爹。他思量再三,还是让我放弃那个让我下半辈子留在他身边过活的唯一一次机会。
2
后来,听同一个公司的同事描述给我听我才知道,原来那一年,我第一次踏进单位大门的热闹场面,造成的是那种土豪效应。其实,那就是父亲所谓的朋友的朋友推荐的天津一个互联网公司的面试机会,职位是程序员。在以学历说事儿的那几年,我能够有幸获得这个机会仅仅是因为我比正常大学毕业的孩子略高一头的那顶硕士帽子。
去那个之前一直被我和同学们定义为一线城市的直辖市之前,母亲硬要陪我去逛商场,说去买一身能让外人看得过去的职业装。对于老太太那一套早就过时的外貌理论,我实在是没什么兴趣。我告诉自己的亲妈,我就是个没有级别的村儿里人,没必要愣顶上个大帽子穿金戴银去装门面。她固执惯了,不听我那一套,硬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连推带搡,把我拉出了我们家的大门。
不一会儿,我们来到了商贸街街面上最红火的金猴鞋店前。我至今仍记得那句传遍大江南北耳熟能详的广告语——穿金猴皮鞋,走金光大道。进店门之前我明知故问,不是说买衬衣西裤吗,来鞋店干吗?老太太义正辞严地回答我,上身下身都穿新的,鞋总不能穿一双旧的出去丢人吧?
在试了不下10双鞋之后,终于找到了一双相对比较舒服的。在我再三要求下,老太太最终帮我挑了一双实根皮鞋,至少没有镂空,不会崴脚。价格就不用说了,不到1000块,要是让我那个爸知道了,估计好几宿都睡不着觉。
出了鞋店大门,老太太又提溜我去了全县城最大的服装商场。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我们母女两个人提了四大兜子服装鞋帽,就这样高高兴兴回了家。
没错,就是个面试机会而已,可是一下子花了一堆人民币不说,还要呼啦呼啦去一堆人。父亲,父亲朋友的朋友,父亲朋友的朋友的司机,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位行业内人士,外加一个应该被重点介绍的我。要是最后没有啥结果,我都不知道怎么回来和在家痴痴等待的那个亲娘交差。临走那天,老太太一直把我送到家属院大门口。我看着她远去的背影,眼里开始慢慢湿润。那么多年,她从来不会说句我爱你啥的,每次分别也不会来一个假模假式的拥抱仪式,她最擅长的就是让我睡得好,吃得香,饿不着,冻不着,还有就是不缺钱花。世界上,有一个人,把我从小到大所有穿过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没有一个泥点子,每次拿出来,都像新买的一样,那个人,就是我的亲妈。
转天,我到了天津,进了那栋即将决定我命运的三层写字楼。
对于那场外人看来声势浩大的入场仪式,我是没有发言权的。本该唱主角的我,在那个时间的那个地点,就像小区门口的一条等人施舍的流浪狗,只能低着头嗅嗅气味,寻找方向。
不知道在那个陌生的大厅沙发上如坐针毡地待了多久,最终,一个体型丰满的女生穿着锃亮的高跟鞋,“吧嗒吧嗒”来到我身边。她弯腰把计算机专业的考卷和一支笔递给我,指点我在一个工位就近坐下,告诉我考试时间是一个小时。
看到那张卷子,我顿时有些发蒙。因为来之前说的是面试,没想到,还得“外甥打灯笼——照旧”答卷子。来之前,我唯一做过的功课就是从网上查了一些关于面试互联网公司的“独家秘笈”,根本没牵扯任何计算机专业课课本知识。那场突如其来的笔试,就像那双没有预兆的金猴皮鞋,叽里咕噜突然闯入我27岁的莽撞人生。
没办法,赶鸭子上架,我只能尽量搜索脑子里关于研究生两年半学的那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计算机专业知识。至今我还记得卷子上的题目大概涉及Sql语句、Html还有一些简单的编程基础问答和程序算法。题目不算多,但是做起来却没有那么容易。研究生顾名思义,就是为研究而生。在那所二流工科院校读研的日子,我大都被导师忽悠着做课题或者帮他打杂去了,哪有心思去学什么计算机理论,本科四年混的那一筐专业课知识早就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还给老师了。
交卷的时间不知不觉到了,从来不知道时分秒可以长那么多只脚跑那么快。我难为情地站起来,把那张已经被我划得密密麻麻的考卷递给主考官。后来上班后才知道,他是我的项目经理。他简单问了我之前在学校的项目经历,我也尽量往大了去说。我们俩四只脚站着聊了大概有10分钟的样子,最后一个问题是问我英语好不好。听到那个问题,我终于长舒了一口气,一本正经地告诉他,我的英语水平是CET6,全班第一。还好,那场决定我命运的考试和谈话就这样结束了。他告诉我,完事儿,可以打道回府,回家等消息,他有我电话。就这样,我们一干人等,在一个多小时以后,声势浩大离开了那个后来承载我十年光阴的地方。
等待通知等待审判的日子似乎比之前躲来躲去的日子还要难受,有过之而无不及。不知道浑浑噩噩过了多少天后,我接到了来自公司人力资源部的一通电话。那一刻,我正在家里沙发上发呆,想接下来剩余那半天的时分秒要怎么算计。
听到我可以去上班那几个字从电话那头传过来的时候,我没有过多的兴奋表情。唯一的念想就是,我终于可以松口气了——离开家去一个听不见唠叨听不见闲言碎语的地方,开始另一段生活。
对于多少年前那个外人看来非常不错的结果,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表情去回应。只知道,那通电话过后,我身边所有的人包括我最亲近的人,立刻,马上,换了另外一副喜笑颜开的面孔。唯一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依旧保持平常心的,似乎只有那个本真的我。
3
研究生实习期是4个月,每个月固定工资2000块。敲下这些字的当下突然意识到,13年后的今天,我的工资水平似乎又回到了当初。不对,确切地说,税后到手的那少得可怜的人民币数额离实习期还差个零头。关于工资的这个话题,在21世纪的现在说起来似乎是个天大的笑话,用我亲爹的话说,连个环卫工人都不如。世界是有轮回的,可是,没想到那个圈圆到我身上,周期只有短短10年光阴。
四个月的时间,确切地说是120天。去掉每个月4天的休息日,还剩104天,按照1天10个小时的工作量,为了顺利成为那时候看来万人追捧的国企正式员工,我整整努力了最少1040小时,只多不少。现在看来,那个时候尚且年轻的我,努力起来还是挺疯狂的。那个时候,公司规模没有那么大,我们程序研发小组只有4个人。1个项目经理,2个程序员,我是刚来的第4号人物,暂时看来只能是打杂的最好人选。
之前3个人的标配中,2个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毕业,一男一女,男生是项目经理,硕士研究生;另外一个,女生,本科。剩下的那一个,中国地质大学毕业,男生,本科,脑子聪明得让我每每大开眼界。之前的人员配备,一律是地理信息系统专业。我是第4号人选,计算机专业出身,成了唯一的一个杂牌专业。外行人一听计算机专业女生,大脑里想来想去都觉得不可思议;回归现实,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清楚。实践证明,我对自己的预判还是蛮准确的。
尽管我拼死拼活整整努力了100多天,最后也通过了实习期考核。但是,那个所谓的结果并没有那么让人喜笑颜开,守得云开见月明。因为,4个月的时间让我认识到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论智力,我是4个人中最低的那一个;论资历,我是最浅的那一个,我和项目经理同一年毕业,他比我早来3个多月;论年龄,我是最大的那一个,比我们项目经理还大了整整1个月;论出身,我的学校和专业是最拿不出手的那一个。如果硬要找一个优势出来,那只能是吃苦耐劳。但是就算这点山东人身上最普遍的品质,落到互联网公司,也只能是掩人耳目:转正那天,部门经理明明白白告诉我,你的表现在这里只能是勉强及格,因为先天资质不够。现在缺人,留下以观后效。
我就这么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留了下来。不是因为我有多出色,多优秀,只是因为时势造英雄。
最终,促成我转正的那一个砝码还是试卷。不同的是,进公司的时候,答的是纸质考题,而成为正式员工,需要在电脑上编程序。那似乎是我平生第一次通过电脑程序去确认自己在世界上的存在。6道考题,从最基本的程序认知,到最后的实际工作论证。虽然之前的那100多天我真的费脑子去琢磨,认认真真去过了,但是当我看到那张似乎专门是为了考我而出的电子试卷的时候,我真的开始怀疑人生了。
答卷,最终在两个小时后哆哆嗦嗦地提交到了项目经理手里。我起身站在他身后,看到他郑重其事坐到我工位上,一只手迅速在我的那个勉强能够称为程序的英文代码上点来点去,一副表情凝重的样子。
当我写下关于那四个月的文字种种,我第一次发现,原来,我肚子里有那么多的话可以说,可以琐碎,可以唠叨。无非是那些话当时说出来可以用来嚼舌根,也可以用来面对那个不敢正视的自己。现在看来,只能是更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理清这么多年下来一个女程序员的因果定数。也许,这就是我应该有的人生。
接下来的一顿填表入职手续仅仅是个手续而已。我一笔一划填完了那些表,签完了那些字,当一切就绪的时候,一阵风似的离开了人力资源办公室。从此,我成了那个互联网公司的第108号员工,软件部门同一战壕的第12个兵。
那天晚上,我如约给我那个在老家等待喜讯的老父亲打了电话。那头,他和母亲已经准时等候在手机旁边,只等我按响那个熟悉的电话号码。他们很兴奋,兴奋得就差昭告全世界。只有我,平静得不能再平静。具体以后有多少坑多少洼虽然暂时脑子里还想不清楚,但是其中的艰难程度,那时我已有了心理准备。
4
转正后,当我被正式介绍给部门其他一干人等的时候,我才真正认清楚另外一个不争的现实——我的学校,放到那里,真的是拿不出手,杂牌中的杂牌。那感觉,就像小时候,在一堆人里,只有你不是班干部。有时候,你会想如果有一天能够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该有多好。更多时候,你会说服自己,不要想了,那只是一个不可能成为现实的梦境。
之所以这么说是来到这里之后才明白,校友这个词在21世纪的互联网公司有多么的流行、吃香和重要。900多年前,唐宋八大家里面,宋代的六位文人除欧阳修本人外的五位都是他的学生,分别是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和王安石。虽然过了差点儿一个世纪,剩下的那几位同僚没有那么多的同门在同一个坑里过活,但是同一个母校这个事情是必须被摆上台面的一个事情。
想不到时至今日,门第概念还是那么重要。这个道理,从我踏上济南那片热土前投递第一份简历找工作的时候就认识到了。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面对现实:那一张张天花乱坠的看似公平的网络招聘启事背后,大都挂上了准入门槛,一个叫985,另外一个叫211。这时候,你才明白,你的学校,你之前的履历,摆到台面上,只能叫作不伦不类。既不属于A,也不属于B。当那个大圆被抠去了两个小一号半径的圆圈后,剩下的那部分,到底究竟哪个点会是收留你的落脚点,大都是靠运气。看似那么大一张饼,切来切去,能够属于你的,只有很小很小一块,这就是二流学校的不争事实。就算是学校的顶级专业,也于事无补,因为那个大的前提已经决定了你以后的道路,必定不是那么好走。而这个不争的事实,到了你找到工作看似人生暂时有了着落的那天,还是会一次又一次加深你的不安和痛苦。那种境地,既不是你一时半会儿能明白的,也不是除了你之外的其他人可以感同身受的。
和你所谓的同事混熟了之后你才会明白,校友两个字造成的最直接后果是人分出了“堆儿”。这里的“堆儿”,不是指菜市场里没人稀罕的陈白菜烂帮子,而是上等人找上等人的非法定条款,可以叫作现象,更确切一点描述,叫作定律。那个不成文的规矩最适用的地方就是吃饭喝酒等中国人情社会里各种常见的应酬场面。
每当有部门聚餐,你会发现,你永远是那张饭桌上最不合时宜的存在。说到武汉大学学校的樱花节,你只能在想象中闻闻味道;提到武汉大学学子传统的娱乐项目“杀人游戏”,那么一大桌子人都可以参加的扑克游戏,只有你一个人在看了半天后还不明就里。赢了,你就是个陪衬;输了,你只能是那个被人嘲笑的罪魁祸首。
现在,我仍然记得多少年后我和老公的那次纵深谈话,最后结论的前置状语一个是“如果”,一个是“因为”。如果时光倒退20年,我们会付出之前双倍的努力、双倍的勤奋去迎接那场决定人一生命运的高考。因为时过境迁后,我们才发现,高考是目前活了大半辈子的我们参加过的最公平的一场考试,没有之一。在没有如果的当下,我们只能用片片破碎的心去面对那一个个已经不可更改的现实——十年河东,十年河西。那么多年过后,有的同学高分考上了部队院校,现在在如花不惑的年纪已经顺利躺平过上高薪退休的生活,有的同学上了985院校,毕业时找工作可以“挑三拣四”,有的同学利用学校出身的优势过了独木桥考上了朝九晚五的公务员,过上了“有钱有权”相夫教子的生活,唯独剩下一个你,还在所谓的一线城市拿着二线城市的薪水过着三线城市的生活,这就叫作不堪忍受之重。
一个人这样,叫作承受痛苦;两口子这样叫必须认命。
5
小时候,我是来过天津的。那个最初的渊源是因为母亲生下我的那一刻起,我的一只眼睛带有先天性的视力缺陷,左眼远视散光捎带眼球轻度倾斜。
关于那个先天性的缺陷,关于那个偶尔都会斜着眼睛看人的故事,我真的面对了很久很久。小时候,被大朋友小朋友嘲笑的场景偶尔都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间点蹦出脑海。直到有一天,父亲痛定思痛,利用寒暑假时间,带我跑遍了济南和天津大大小小的医院,最后找到了一位特别靠谱的眼科大夫做了个小型手术后,那个因为视力原因造成的心理阴影才有所缓解。谁承想,多少年后,在单位碰到的那个人,又一次让我陷入痛苦的回忆和纠结中去。
那是转正后的一个傍晚,一个部门的人都在加班。正在我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部门经理不知什么时候悄悄走到了我身后。
不知不觉已经伏案敲代码敲了很久,身心有些疲累,想站起来抻抻胳膊抻抻腿。猛然间回头,看到了那道读不出温度的目光。我心里忽地一愣,当时糊里糊涂地说了句什么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一个人呆呆地站在那里,像做错事情的小孩儿等待家长审判一样。他冷不丁冒出一句:“怎么这么大反应?我就是走到这儿了,顺便看看这么些天,你都忙了些啥?你又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有什么好怕的?”至于后面的一堆话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只觉得瞬间血液倒流脑子嗡嗡直响,一直到他离开我的工位回到他自己的办公桌。
从此,我和那个叫作部门经理的人就结下了所谓的梁子。那么多年,我其实一直想问清楚说清楚当年那个都不算是误会的误会。但是,时间久了,有些事情,你越想忘记,就越往你心里钻,直到最后,成为一块心病,一块烂肉。想割割不掉,想忘记又忘不了。
后来,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瞎寻思,也许我第一天来到这方宝地考试的那天,他就一直在某个角落盯着我,只是我没有发现而已。也许,从来到这儿的第一天开始,他就知道我是别人介绍来的,至少那个名牌大学很容易得到的考试机会以我之前的资历和条件,是够不到他执掌的那个部门的最低门槛的。
以后在他手底下干活的每一分每一秒,不管什么情况,我都活得不知所以。对的时候,他总能吹毛求疵挑出毛病来;错的时候,更不用说,更是东南西北,哪个方向的风吹得都不对。那些年,我最发怵的时候就是年底考核和年初谈薪资待遇的时候。
国企嘛,每年年底都有考核。那么多年,我没有拿到过一次优秀员工,就算我手底下的小弟都变成别人眼中的高徒了,我却还是那个最差的老师。
每年不管大考小考,明面上,在那个人眼里,我总是专业最差的那一个。每年那个决定来年收成的考核结果,倒数几名都会留一个位置给我。别人过年,总是拿着奖金和优秀证书高高兴兴回家去,只有我战战兢兢不知道是否有来年,不知道开班第一天,会不会被部门主管约谈。就算幸运逃过一劫,在那场声势浩大皆大欢喜的调薪涨级运动中,只有我,每次坐到部门主管办公桌对面,来之前总觉得有一万个理由让他给我涨薪。来之后,每次都被对面的周扒皮问得哑口无言,扫兴而归。
那么多年,我曾经想过各种各样的办法去改变那个不堪入目、不想提及的现状。一开始,你还会用所谓的公平和不公平去衡量整个事件,后来,当你慢慢发现无论你多努力去面对未来,有些东西始终还是改变不了的时候,你会坦然很多。开始那几年,我还煞有介事地和同事们讨论一下那个冠冕堂皇的考核结果。后来,你慢慢发现,过了某个时间点,那个你很在乎的东西在别人看来已经没有意义,只有你一个人还在抱着它,痛苦着,挣扎着,忍受着,煎熬着。
眨眼间,那些年就这么浑浑噩噩地过去了。现在想来,最奇怪的事情是,不论每次处于何种境地,我都从来没想过打退堂鼓,没想过破罐子破摔,或者辞职换一个新东家。
后来,一个关系还不错的同事某天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了一句:“姐姐,我坐在你侧面,总觉得你在偷偷瞄我,你有感觉吗?”那天,我猛然间意识到,我小时候下意识的眼球转动角度不到位造成的影响这么多年一直都在。我也第一次明白了,许多年前我和部门经理之间造成的那么多年的那个隔阂,那个我至今都拿不起放不下的梗,原来只是一场误会而已。而这个误会,说起来好听,实际上并不美丽。
那天下班后,我一个人走出公司,来到园区,坐到柳树旁边的秋千上,心里想了很多很多。那些年,那个人,那个所谓的领导先入为主的成见已经深深刺痛了我的心肺。也许是我把他看得太重了。从根儿上说,他和我一样只是个普通人。他只是有个部门经理的头衔挂在那里,天天端着架子过活而已。你可以私下把他想成纸老虎,容嬷嬷也可以。可以是可以,可是当他第一次在你心里变戏法的时候,你已经把他整成了一座雄伟的砖头垒的万里长城竖在心口。想换一个人设给他,你还得先拆再建。
当有一天,曾经困扰你的种种已经有条件可以不困扰你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活的方向并不会有所调整和改变。因为那么多时分秒跑过之后,等你终于想明白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之前该发生改变的早已经变了,剩下那些顽固不化的东西,该存在的还是没有理由地存在着。曾经你觉得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那个人,已经不知不觉中把自己对你的态度潜移默化地转嫁到别人身上。明面上他是走了,实际上,他之前某个时间点某个场合不知所以的一句话,一个动作,一汪眼神,已经留下了太多太多的“后遗症”,而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已经注定了接下来你要走的路。
这就是,那些年,曾经,我被斜视的人生。
责任编辑:杨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