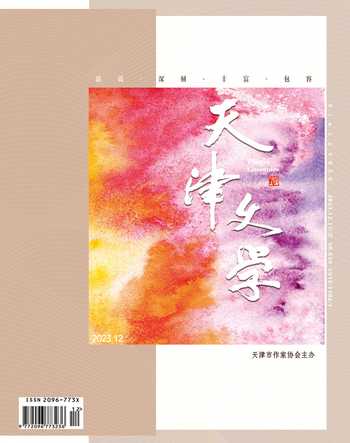虚实的辩证与联结的可能
1
《天桥美人》从开始便致力于将“天桥”“美人”处理为“虚实”相关的隐喻。一方面,“天桥”“美人”几乎是不可见的,藏身于首尾两端的情节线索之中,顶多是公司1908室或803室的一幅挂画,目之所及,即使觉得吊诡,也一闪而过,来不及细究;另一方面,在小说中,赵志明又不断强调它们各自的幽灵属性,令读者始终为此悬心,无法完全放弃对这一帧画面的斟酌。这构成了小说中最重要的张力。赵志明以特有的耐心首先为读者勾勒出这幅埃舍尔风格的画面:“特大暴雨那天……宽长的车身被卡在步行阶梯到天桥路面的转角处……就像一只大海龟好不容易从海里爬到一块凌空礁石上……照片左下角的一位女子来。她没有打伞,冒雨疾行的背影被定格在天桥远端……即使身后有一辆车差一点飞越天桥,她却全然没有被身后的巨大动静吸引,毫无缓下脚步或者转身瞧个究竟的迹象……”这一景观如同忽然到访的,意义不明的寓言,撕开了这家刚刚成立的教辅公司的一角。
一个看似外部的事件,如何在叙事的行进中,不断嵌入故事现实的肌理,以至于一家本该有所作为的公司,转瞬间溃散离析?答案是,一切源自虚实的辩证。从某种程度上说,《天桥美人》的独特美学,正建立在从实到虚,再由虚入实的逻辑过程。暴雨、冲上天桥的轿车、绝尘而去的不打伞女人,作为启动事件的元叙事存在。它是网络热议的图片,也是叙事者肇所亲见的场面;是现实,也因为具有某种超现实的视觉冲击,伴随强烈的虚幻感。最为关键的是,由于画面的信息要素不全,它同时为虚构与叙事留下了余地。在“实—虚—实”的链条中,“虚”是核心引擎,它充当了现实中“天桥”的作用。小说中的“虚”,正是作为教辅材料编辑部主任的肇,对这一景观进行的虚构和想象。在他的假想中,暴雨中的轿车和女人有了关联,由于轿车的主人与女人发生争执,女人离去,从而上演了轿车追逐,直至偶入天桥的荒诞场景。赵志明最富想象力的设置,便在于肇的虚构,在小说的推演行进中,逐渐幻化为现实:轿车的主人是教辅公司的经理,女人则是他的情妇。这番虚构随后被有心人利用,成为撬动现实的杠杆。这一虚实辩证法,极像画家徐累一幅名为《霓石》的巨幅作品,彩虹本是虚幻之光,但在画家笔下,它却由灵石构造,虚实相生,一时间也虚实难辨。这正是《天桥美人》所试图达到的美学效果。
2
当然,《天桥美人》所构置的虚实辩证并不仅仅是一种美学。当我们试图追溯小说发生的时间,我们将发现,赵志明敏锐地将其锚定在21世纪之初——互联网兴起不久的时刻。无论他是否有意这样做,这篇小说都因此具有了某种追寻“前史”的意味。21世纪的驳杂,很大程度上来自互联网时代开启后虚拟网络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入侵现实的状况,“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一场旷日持久的虚实辩证从而真正开始。彼时,这场辩证还没有热搜时代议题的多样性与复杂度,话题间的缠绕也未过分至无法厘清的地步。它似乎更具有一种朴素、单纯的面目。因此,当我们以此为观测装置,会更为清楚地意识到虚实交错的运动轨迹。
起码有两个人物昭示了互联网时代以来虚实杂糅的显著特征。其一是叙述者肇,如上文所述,他是“实—虚—实”逻辑链条的关键一环。尤其在由实向虚的动态过程中,是他率先制造了一次虚构。当肇作为普通旁观者,参与想象与重构“天桥”“轿车”“美女”的叙事时,已天然进入了互联网与现实所重新搭建的网格中。他面对实像做出的虚构,第一次将虚拟与现实的边界打破。换句话说,就算他并未实际参与网络对该事件的想象性重构,但仍间接进入了该运行流程之中。回头看主人公肇的名字,我们会理解赵志明的用意,肇是引发、创始之意,它的惯用词组是“肇事”“肇始”。主人公肇正是在无意识中,以“虚”构参与并引发了现“实”的震荡,是名副其实的肇始‘事者。而小说中另外一个关键人物,陆总的司机柳哥,继肇混淆虚实边界之后,对虚实进行了别有用心的“剪裁”,相比较肇象征普罗大众,柳更像是背后实际操弄虚实之人。他知道陆总“金屋藏娇”以及在北京开设教辅公司的真实目的,知晓其背后仰仗的是其妻子的势力,同时,他洞察了肇的推测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他利用几方的信息差,通过告密与示忠,实现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柳的意图非常明确,既然他始终要做陆总的司机,那么保全陆总的现实利益,就能保全其自身。因而,陆总的情妇,以及在北京开设的教辅公司,显然构成了其生存的主要威胁。赵志明写柳“笑面虎”的形象出神入化,他的恶并非大奸大恶,而是属于互联网时代之恶,他以一种吊诡的方式,通过操弄虚实,操弄了一个群体的聚合与离散。这一躲在暗处的,看似毫无相关的人,成为介入事件最深的一个。这正是当代互联网时代的悬疑之处,你永远无法设想那个隐匿在虚拟身份背后的“真身”。
3
“我难免会想起当年的同事,他们都比我年轻,大多刚毕业,风华正茂,对未来充满憧憬,却马上迎来铩羽。我们在一起共事的时间太短,不足一年,才刚刚熟悉却又各奔东西。我忍不住想,为什么会这样?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在他们中间,本来应该缔结友谊,经常聚餐;应该萌生爱情,男欢女爱,所在多有,在所难免。”在这篇小说的创作谈中,赵志明提到写作这篇小说的一点初衷,它似乎来自一种叹惋和遗憾:这样一群伙伴,本应缔结一些深厚的关系,却什么也没有发生。如同小说里最重要的隐喻“桥”,本应象征联结,但实际上意味着某种情感的失落与中断。
《天桥美人》中,赵志明少有地写作了一个关系较为隔膜、疏远的群体,他们之间缺乏“联结”,不存在深刻的交往。部分原因在于,小说发生的环境被设置为公司/住所混杂的地带,这也造成了某种集体生活与私人生活不分的情况。但也许更重要的是,21世纪以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模式,随着互联网的进展而完全改变了,由此造就的新的一代正逐渐抛弃传统的交际与情感范式,他们最显著的特征是沉默。因此,所谓“桥”的隐喻,与其说是“联结”,不如说是在暗示人与人之间的“间距”。小说中一再出现的场景,是员工们各自站在窗口,望向窗外的天桥,他们以此观察自己的上司、自己的同事。也就是说,一种真实的,面对面的理解已然消逝,人与人的关系,被更替为近似人与天桥的关系,即“看”与“被看”、窥视与臆测的关系。
以这样的方式重新理解天桥之后,我们会发现为何《天桥美人》的叙述人称显现出一种“错位”。第一人称叙事本应具有强烈的情感共鸣,“我”强烈地参与事件,并为读者提供切肤的见解与感受。但在这篇小说中,“我”的叙事却退化为一种近似第三人称的旁观者视角,“我”更多时候只是被动地观看,无法参与其中。事件仿佛一道道门,把“我”隔绝在外。他者在“我”眼中的化身,是卢云鹏和陆总情妇的形象,他们两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致力于成为不存在之人——在房间里竭尽所能消除自己存在的痕迹与气息。这些都极具互联网时代的症候。
在这样的情感关系中,“我”显然无法与他者产生更为强烈的关联,“我”所能做的,只是作为侦探,搜索他者存在的蛛丝马迹。因此,这种叙事人称的“错位”,可以看作是赵志明偏执的努力,他以小说家强大的意志与爱,去试图弥合人与人之间已然产生的间距,为原本无事发生的离散,寻找一个可信赖的原因。
我相信,这是他对读者的慰藉,也是对自己的。
高翔,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文学研究、评论见于《当代文坛》《扬子江文学评论》《当代》《十月》等。
责任编辑:崔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