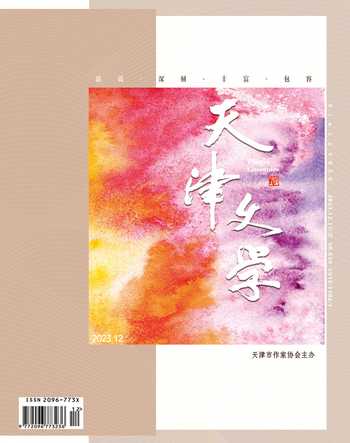天桥之上,自成风景(创作谈)
赵志明
记得以前上海电视台有个栏目,叫《诗与画》。年幼的我经常看,惜乎画的欣赏没有入门,诗歌的爱好却发轫于此。印象最深的是卞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彼时,我自然不知道苏轼评论王维的诗画——“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更不能领悟到诗与画的“量子纠缠”。我只是懵懂有感,《断章》很美,构景简单,好像也没有什么小学语文老师每每要强调的高妙的中心思想喷涌出来。我觉得它就像一片掐头去尾的残梦,记住了,就很难忘,记不起的,再怎么刨挖都徒劳无功。
因为这层记忆,我对桥格外有感。在南方水乡生活的二十多年,我以为《断章》中的桥便是架在水上的长虹,像马致远的“小桥”、杜牧之的“廿四桥”、郑克柔的“板桥”等等;等到了北方,在北京看到如此多的过街天桥,又觉得《断章》里的桥是旱桥,一桥飞架东西南北,其下大道通衢,车水马龙,络绎不绝,傍晚到入夜这段时间的下班晚高峰,堵车三五里,汽车尾灯通红,成为京师一大特色,只是不免对赶路人心生同情,料想他们绝没有看风景的心情,和装饰梦境的雅意。
初到北京的几年,我住在柳芳地铁站旁边的新天第。那是一座商住两用楼,西边是东土城路,北边是柳芳北街。我站在北窗前,柳芳北街的那座过街天桥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得便于此,早晨上班前、中午休息时、傍晚下班后,这三段我专属的“望痴眼”时间,便主要用来看天桥,看天桥上的行人,看天桥下的车辆。
然后,便是“汽车冲上天桥”的事件在网上发酵,成为热搜。当然,那时候网络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热搜”“热度”还没有专门用于测绘网络热议事件。我以为这正是我等候已久的,不是风景,也不是梦境,而是小说的灵感。于是,我写下“天桥上”三个字,作为备用的小说名。
一晃又是多年过去,我早已搬离柳芳。偶尔坐车经过七圣路、西坝河路、柳芳北街、东土城路,看到新天第、天桥、西坝河,记忆被触动,我难免会想起当年的同事,他们都比我年轻,那时大多刚毕业,风华正茂,对未来充满憧憬,却马上迎来铩羽。我们在一起共事的时间太短,不足一年,才刚刚熟悉却又各奔东西。我忍不住想,为什么会这样?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在他们中间,本来应该缔结友谊,经常聚餐;应该萌生爱情,男欢女爱,所在多有,在所难免。
在记忆中,我又站到新天第的办公室里,凭北窗而望,那座天桥依旧在,上班下班时间段,天桥上人流涌动;其余时间段,天桥上断断续续有人经过。我在看风景——一道虚构的风景线。有人在装饰我的梦——小说中的人物。
小说家蒋一谈有一次分享他的创作经验:把灵感像种子一样埋在土里,静等种子发芽,破土而出,长成应有的样子。我觉得《天桥上》已经破土,遂把小说成形的构思描述给他,求教于他。他建议说:“小说名不妨改成《天桥美人》。天桥为实,美人为虚;天桥犹如现实,美人犹如理想;天桥就是风景,美人好比梦境。”
蒋师之说,醍醐灌顶。不经意间,我当年手培的种子已长成植株。其是否自成风景,能否装点梦境,作者本人已无从置喙,端赖读者诸君评判。
责任编辑:崔健
——论《贝多芬:阿多诺音乐哲学的遗稿断章》的未竞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