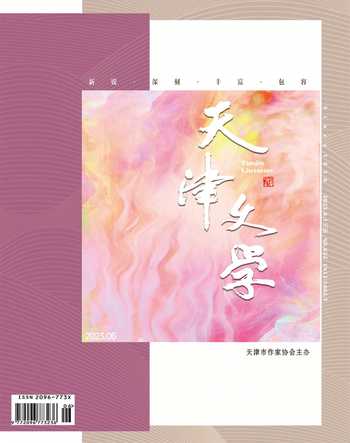新鲜的生活与新鲜的力量
在我们的《改稿会启动和实施方案》中,编辑部提出了45岁以下占比50%的要求,可见我们对于挖掘年轻新人新作的决心,这一限定也使得我们在两个区作协报送上来的作品中看到了一些可喜的成果,尤其是西青区报送的小说与诗歌作品、河北区报送的诗歌作品中,年轻作者占了大多数,其创作潜力不可小觑,这的确是本次改稿会的一大亮点。另外,我们也看到了在平时投稿中所熟悉的作者,这一次报送了自己的新作,也得到了编辑部一致的肯定。我们依据“文学性、探索性、开拓性”等等要求对于来稿进行评判与衡量,从而确定了最终入选改稿会的名单。总体来说,稿件的质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但也发现在工作之中一直以来会面对的一般性问题,也出现了一些个人尚需提升与改进的地方。在接下来一对一的改稿中,作者可以听到编辑对于这些作品的具体指导意见。
下面开始正式的改稿环节。郑皓文的小说一共报送了两篇——《腥汤》与《山火》。郑皓文年龄虽小,16岁,但是作品却显出了超越年龄的成熟气质。郑皓文的小说有一种诗意,由种种神秘的意象“金鱼”“棺材”“血红的女人”或者是充满神秘感的叙事场景“族长的死”“围观的人群”“随时响起的尖叫声”构成。题目《腥汤》就可以看到小说意识与味道是非常浓的,信息量大,一个“腥”字就有了小说张力。但是小说的问题也比较明显:
首先是语言问题。短篇小说要有力度,同时也要清晰表达。郑皓文的语感很好,小说的文学味道足,比如“父亲把鱼包起来烤,用筷子一块块捅进肚子里”这个描述就很有趣味也很生动,但年轻作者容易陷入对文字表达的迷恋之中,形成一种文学腔或学生腔。语言本身应是为小说服务的,在写作过程中应该有意识避免对自己文字的过分强调而显得油滑。郑皓文的语言也是因为过分强调这种文学感觉,有时候是刻意为之,反而给人一种生涩的感觉,将简单的问题叙述得复杂化了,在阅读上会给人形成一定的障碍,这个还需要多加训练,尽量避免陷入对文字的顾影自怜。
其次是情节推动问题。郑皓文的语言是截断式的,一节一节的,情节也是跳跃的,幻灯片似的。应该通过情节连贯性的叙述训练,加强小说叙事连贯性的表达。现在故事或者说是一个小说念头的转化还是碎片式的,不够完整。
第三是视角的转化问题。比如《腥汤》的第三段,前面还在说父亲伸展身体,后面又要以主人公章化为主视点作为叙述。要注意在一个段落中或者章节里尽量避免视角不停转化,会给读者一种混乱的阅读体验。
最后说说小说的主题。郑皓文的小说其实呈现了一个逐渐迷离和疯狂的现场,最后血腥味非常浓。作者其实呈现出的是一种具有先锋意识的写作风格,主题并不明确,当然也可以认为是一种成长母题,这一母题在青年写作中身上并不鲜见,他们逐渐成长,开始有意识地反抗长久以来在成长中父权的压制,于是在文本中以各种隐喻的方式呈现一种撕裂的反抗。但这样貌似具有隐喻性的写作虽可作为阶段写作的成果,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求学并步入社会,作者应该更深入生活现场,透过现在看似深奥与深刻的“寓言”看到生活的真实面貌,改变二元的思考方式,切实了解生活本身的面貌,使真正的生活成为笔下的主要对象。当然对于这个年龄且呈现出这样写作风格的作者来说这样的要求还太早了也太高了,但是我相信随着作者阅历不断丰富,若他依然保持着对待文学创作的热情,一定会写出更多令我们感到惊喜的作品。
郑皓文另一篇小说《山火》,语言非常轻松洒脱,这是我非常喜欢的。比如小说开始两人对话,在节奏的把控上就很节制和有分寸。“我给你开开灯,给你发个电报。她笑了几声……”这个对话和人物动作之间的空隙穿插很自然,对于成熟的写作者都是比较难得的。还有“她说,你把语音挂了,我给你录一段。不会啊这么明显。”这样生活气息浓郁的对话,与《腥汤》对比就轻松自然很多,这两个作品不知道哪一个写得更早一点,但《山火》显出一种更放松的写作状态。不过,《山火》存在与《腥汤》相同的问题,就是作者有时候会忽然停顿下来描写某个场景或者心情,可能是作者本人兴之所至吧。但兴致不能作为一个完整作品的写作标准,写完作品需要反复修改,与小说本身无关的细节描写再精彩也要学会放弃。
这篇小说依然是一个充满着实验色彩的先锋小说,郑皓文试图在小说之中再创造一个故事,是关于小说的小说,我们会称之为“元小说”。在小说里郑皓文提到了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阿莱夫》,我估计作者也读了很多这位阿根廷小说家的具有独特空间意识和思维路径的小说,显然在他自己的小说里也采用了一种先锋小说叙事策略。但我们深究这个故事,除了它叙述方式的独特性——故事中套着故事,与一个名为“幽灵”的人进行思想对话,故事中引用典故等之外,其核心情感依然是青春题材的。这个现象很有趣,就是作者本身的生活经验就这么多,但他开始接触到西方的现代派作品,于是他借用了这样一种形式来写自己的生活。这样的写作方式当然是被允许的,也是很多人刚开始写作时会采用的方式,但其实也是曲折的甚至是徒劳的,其实就是没有必要。作者目前只是看到了西方先锋作品形式的新鲜,却没有看到形式本身是要与内容相联系的,现在呢,被割裂了。我在这篇小说里只看到了叙述本身,没有看到更多的东西,这是遗憾的地方。西方现代派的形式也依然是要为内容服务的,比如说普鲁斯特的意识流写法,现在很多写作新人还在模仿,但是学一个形式看似是容易的,却没有意识到这一文学叙述形式其实是普鲁斯特在表达他自己对于时空的特殊认知,而不是单纯的一个散漫的形式再将自己的任何东西装进去。以上是我对郑皓文小说的看法与建议,总的来说,郑皓文是一个非常有天分与潜力的写作者,我相信,如果他未来还有写作的愿望,一定会有更成熟的作品出现,这是一定的。
下面我来谈一谈吴春笑的创作。《驴伙计》是一个篇幅比较短的小说,但是可以看出作者丰富的写作经验和成熟的写作技巧,我认为这也是年轻作者们应该学习的。作品非常完整,结构很工整,详略得当,实际上是一篇几乎没有修改余地的作品,但也是因为这样,这篇作品才有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故事没有大的波澜与起伏,功能落脚在抒情上,它显得更像一篇散文,而不是小说。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应该是可以将一个在日常生活中业已熟知的主题焕发出生机的,是要找到平凡主题中新的叙事角度的,当然,这是很不容易的,但这正是一个作家得以脱颖而出的根本原因。短篇小说应该是唤醒读者沉睡的坏死的日常经验,它面向的是人类精神性的考察。我说了这么多,并不是说不能写像《驴伙计》这样主题的作品,而是我们要找到文中所讲述的人与动物情感密切连接的新的叙事可能,现有的这个故事并没有超越我对生活的一般的认知经验,它是可被预期的,也就没有那么高的审美价值了。
另一篇小说《老高的瓜田》,其实也有相同的问题,但仍可以看出吴春笑本身的创作实力,没有短板,也没有硬伤,起承转合处理得严丝合缝,高低起伏也都是精心设计过的,呈现一个完整故事的能力是具备的,但欠缺的是更吸引人的素材和进入素材的新颖视角。平铺直叙地将一个故事讲完是容易的,但没有真正打动人的点,于是再有力的表现、再坚实的地基,可能也淹没在一个相对平庸的故事构造里,这是让人遗憾的。我给吴春笑的建议与前面年轻人的意见相反:他们需要收着写,吴春笑需要放开了写,大胆地写,疯狂地写,跳出自己固有的写作思路与方法,将一个故事推向一种极致,或许能够呈现一种全新的写作面貌。
接下来我来说说孟宪华的稿件。孟宪华是《天津文学》的老作者了。这次改稿会孟宪华送审了两个作品,一个诗歌、一个散文,我放在一起说说感受。首先,散文《中秋,情满故乡》开头的诗歌“摇着轮椅,画出一个大大的圆”“母亲是我的故乡,我是母亲的月亮”等都是很有诗意的,这是孟宪华诗歌功底的一个呈现,但进入到散文的正文,问题出现了——孟宪华的散文更像被是她稀释过的诗歌。诗歌的抒情性在语句与语句中间连接自有的一种情感的节奏、韵律,但她的散文空有情感的语句,成了一个空壳,情感无法附着,显得轻薄没有说服力。我们一直都说散文是“形散神不散”,但显然孟宪华这篇散文神也散了她想在这篇散文中表达一种家乡的新变,这种姿态和意识是向上的,应该予以鼓励,但没有寻找到一些可供依附的日常意象来进行描写,空泛的感情表达是碎片化的,空喊口号,也没有独特的令人耳目一新的表达。近几年编辑部常会收到一些写景抒情的散文,散文以家乡风物或是亲情回忆为主,在这些散文中,尚可发表的是一些在语言表达或者内容上还算有些趣味、看头或者是有独特经验的。“真实表达”只能作为散文写作最一般性的要求,相较于小说,散文貌似写作门槛低了一些,但其实,这一文体对于写作者自身的情感与文化底蕴的要求更高,写出一篇与众不同的散文需要穿透人生经验,直抵精神和灵魂的深处,在没有戏剧冲突(当然也可以有戏剧冲突)的文字中间,我们要看到一种全新的表达、新的认知,这就要求散文写作者,不能仅将目光停留在生活的表层描写生活中可触及的东西,更要试图去挖掘那些不可触及的、深邃的、尚未为人所知的认知。写散文不能偷懒,写景抒情只要有一定文字基础都能做到,但怎样脱颖而出,怎样写出不一样的情感,这是需要我们反复去思索的。很多散文作品写得太老实了,本本分分,无功无过,这反而才是最大的问题。在这次改稿会收集上来的作品中,也几乎都是这样的问题,写景散文写得像景点的说明文字,这其实恰恰说明了在散文写作中,我们欠缺智性的思考与生活的沉淀。散文的主题可以有很多,生活的种种都可以进入散文写作,它考验我们的思考力与鉴别能力,考验我们对生活本身的转译能力和驾驭能力,需要阅历,更需要仔细的观察,许多作者都与经验有着丰富的写作经验,欠缺的反而是写作能力与经验之外的更深入的思考与大胆的尝试。
孟宪华的诗歌《打卡魏氏庄园》我认为比散文要好。在孟宪华的诗句里,其实总能发现一些闪光的句子:“当人烟和时光已经离去建筑还在说话”“今日,我要省略一场雪赶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雾霾前再把庄园的每个角落审视一遍找到那熟悉又陌生的笑声”。但是,问题也很明显,题目和诗句都有一种不稳定的感觉,俗与雅并存,不协调。比如题目中“打卡”这个词很当代和随意,但是诗歌本身的风格却典雅的,题目拉低了整体的阅读感受。比如《第二次踏进魏氏庄园》中“庄园的故事高悬成门口的红灯笼照亮我们的背影。是在告诉我们大起有大落还是财与才哪个重要”也是这个问题,前半句与后半句有落差之感,诗歌语言要凝练更要讲究。《生活在魏氏庄园的紫藤》中这一句“多好啊,能在一起生活下去”,这种口语式的写法就好一些,虽然仍然浅白,但是显得自然。写作诗歌应该好好打磨与凝练字句,所以写作过程要紧张起来,要“绷”起来,也就是写作的时候要肌肉紧张,不要过于松弛,不然会给人漫不经心的感受。这一组诗歌我认为思路是好的,从不同角度写了一个地方给你的感受。《天津文学》曾经发表过女诗人安琪的一组写文物的诗歌《文物记》,从取材的思路上有相似的地方。但相比孟宪华可以更深入素材内部,而不是简单地将物与情联系起来,要把这个地点作为一个支点,撬动更多的灵感,而不是就事论事,和你的散文创作一样,不要太依赖切身的某些感受,要充分发挥想象力,要让诗句飞翔起来。再回头看看我认为写得灵动的诗句,就明白其中的缘由了。
河北区报送的庞骏是一位年轻作者,其诗作很冷峻、尖锐,诗歌有画面感,也有叙事,有自己的风格。他的诗歌有智性的书写,显然是有文学专门训练的,比如开头就写:“将叙事进行下去已经毫无意义了”,这首先就否定了叙事的可能,那么他的诗歌就没有叙事了吗?不仅没有还相当丰富,“他倚着黑暗中的一面墙,手指像蛇一样一圈圈缠在打火机上,我敲了敲他的手指,火熄了”这显然都是叙事。我认为这是一个诗人应具备的也是可以保留的,但庞骏的问题出在,他掌握了大量的或抽象或智性的语词,他过于信赖这些语词了,诗歌中出现这些语词,会对他的诗歌的深度与独特性造成破坏——“不安”“不祥”“神像”“灵魂”“欲望”还有各种神话中的典故等等。庞骏在国外求学,应该会读到很多西方的诗歌作品,于是他的诗歌里有翻译腔,也会使用很多抽象的高级的词语,这些词语本身就带有很多精神性的含义,但这些含义限制了他的诗歌表达。如果用自己的母语写作,就要重新梳理自己的语言表达系统,用母语体系去训练思维方式,回到自己的语境中来,翻译腔容易让诗歌显得有格调,但同时也会使诗歌空洞。要学会降低自己的身份,现在作品中的高级感都是词语赋予的,不是诗歌本身的,要忘掉自己强大的知识背景,重新审视自己的表达,学习自己的母语,这是我对你的建议。
这次改稿会,令我非常惊喜的是看到区作协报送的小作者们的诗歌作品,清新、纯净、灵动。一方面是孩子们还处在成长阶段,没有过多受到外界各种声音的干扰,另一方面也看到了区作协在文学新人培养上的良苦用心。我简单地点评一下小作者们的作品:一个是付婧翚的两首诗歌,充满诗意的想象,这肯定是写诗歌最需要也是最基本的素质。她的诗歌并没有追求刻意的押韵,但在韵律和节奏上却有着天然的语感,这可能是本身的天分带来的。“斜阳下的傍晚真好心宁静得像一座小岛”,这样的诗句令我的心也宁静了。付婧翚的语言是很质朴没有雕琢的,也因此显得很高级,但不同于成人写作时要刻意追求一种质朴,但她的作品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首《晚风》用了重复的写法,第一句“傍晚的风很柔很轻”这句话重复了三遍,当然不是不可以,但诗歌重复的写法显得像歌词,诗意的浓度会降低,尽量减少这种重复性的手法。第二首《桂花香》,前五句都可以,保持着质朴的特色,但是像“萦绕”“芬芳”“春耕 夏耘 秋收 冬藏”这些词语要尽量避免多次使用,《晚风》这首里面也有,这些本身就带有感情色彩的词语使用得过多会落入一种范式的浅俗,拉低诗歌的格调,在作者这个年龄,学着尽量用自己的语言去描绘你眼中的世界。
杨顗诺的三首诗歌,因为年龄比付婧翚大,一下就看出她思考问题的深度了。第一首《我是什么》更像是一个小小少年不断确认自己的身份、在世界上的位置的宣言,我认为其作为诗歌的价值因此就立住了。再看其中的“我认为”“他们觉得”“你觉得”“有人说”“也有人说”“而我更希望自己是”等等,这种不断的视角转化相当精彩,也让人耳目一新,尤其最后作者反而不愿意成为世俗生活中所认定的成功者,其实也反映这一代少年对于成人世界所谓的那套成功学的抵制与反抗。《耳朵》很容易就让人想到了杨顗诺在这个年龄所要面对的成长问题,《气味》则是她对于世界认知的一种个人视角——通过气味来辨识。这两首诗,一首是通过听觉,一首是通过视觉,这是一个诗歌创作者迈向成熟所应对世界敏锐感知的表征,她都做到了。如果要对她提出建议的话,我认为是多读书,打开视野,真正去感受世界,不断历练,如果写作的动力能够一直持续下去的话,生活的历练会给她更多的素材与方法,她也会慢慢解锁更多诗歌写作的有趣的技巧、题材和情感表达,我对她的写作还是充满期待的。
于树漫的诗歌,或许需要从另一个视角去审视,就是儿童的视角。但是,用于树漫的诗歌与前两位小作者的诗歌作对比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不同之处,作为一名成人写作者无法再回归到最原始的童真状态,成人的想象是嫁接在刻意压低的成人视角上的了。做个比喻,有点像家长和自己的孩子沟通时,刻意用那种孩子的声音说话,这是这组诗歌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它显得有点过于压低自己了,不自然了。比如《稻草人》:“稻草人,像个大哥哥……”这个像一个家长的口吻;《含羞草》里面的“你好啊你好啊”就是一个成年人在模仿小孩子说话;《天上的雪》“落啊落落啊落”这种重复的呓语,都显得有点过于稚嫩了。与前面提到的一样也要在诗歌中避免去刻意重复同一句话。于树漫是一个很成熟的儿童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但我认为当下的儿童文学创作需要一种勇气,就是要提高难度,前面我们看到了14岁的孩子已经可以写出这么成熟的诗歌,我们的成人儿童文学创作者也应该放开自己的手脚。孩子们现在起点很高,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可能早就需要更为深邃的知识与认知补充了。如果从非儿童文学编辑的角度来给这组童诗提意见的话,我认为还应该更松弛,更开阔,更有深度。不应拘泥于儿童视角,不要刻意去营造那种稚嫩的氛围,比如《孤独的云》,我认为这是一首很好的诗歌,但不一定非要以童诗的视角去看待它。
责任编辑:崔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