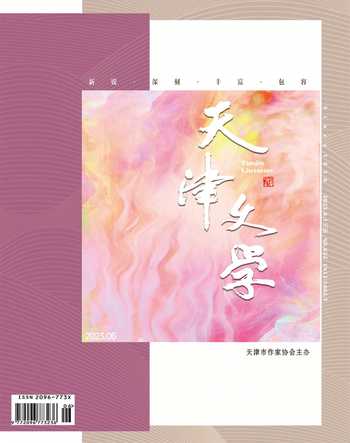私人讲述或记忆同构
一、《秋游》:叛逆的辩证法
如果我们足够坦率,那么必然不可回避一个现实的问题——儿童文学在整个文学场中处于边缘。当然这并不仅限于华语文坛,在世界范围内亦复如是。无论是学界的单独讨论抑或是作为“百花园”中的一个“可爱而调皮”的存在,甚至对于儿童文学受众年龄的严肃讨论,都证明着儿童文学界而今的“独立闭环”已经形成。但如果把这个“闭环”只看成是行业与学界的单纯壁垒,那未免太过天真。事实上,这种文学闭环,其显影出的是成人世界对儿童的“区域限定”,是对成长着的人无形的粗暴“划分”,难道这不能算是一个值得深度讨论的命题吗?
叛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关键词。应对这种文体的“叛逆”,儿童文学界迫切需要意识到这是一种有益的驱动与文体(文化)自觉的有效催生。如果作家不以轻视为忤,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就具备了坚守儿童本位的立场,如果以文学的形式来实施对偏见乃至“约定俗成”的“叛逆的反攻”,则是完成了儿童文学的复杂指涉。就如同新时期几乎全部新锐作家都取用儿童视角一样,“叛逆的反攻”因视角的去遮蔽化而更加抵达,由此走向对人性、社会乃至历史的深度反思。当儿童文学作家不再局限于讲述儿童、关怀儿童、为儿童发声,而是在上述基础之上以儿童视角和立场去反映更为广阔的时代症候,那便是以叛逆之道达文学之用。在这个角度上,叛逆是一个充满了辩证的关键词,关乎文学更关乎人文。
能够不以“叛逆”为忤,又敢于去“叛逆”的儿童文学作品才是真正的佳作,而其难度远在于成人文学之上,毕竟这是在“特殊文学门类”之下的创作,却要辐射全部年龄段的读者,给出更加绵长而深刻的省思,这种举重若轻,言简义丰,对作家提出了更苛刻的要求。
而这种举重若轻的观照之感,在彭学军的短篇小说《秋游》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小说聚焦于乡村的一所小学校,是俗套得不能再俗套的新手老师应对难缠学生的“古老”故事。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当下的儿童文学创作现场,能够坚守书写严肃日常的作家已经少之又少,这种回归传统的写作实际上是一种“向后的进发”。果然,我们在故事中看到了儿童与成人的相互破壁,看到了清浅的叙事所编织的意蕴之网,这构成了小说宝贵的张力。
小说的双重推动在于偶发事件与心理嬗变。小说的开篇便是亚亭的难眠,由于同事杨老师的妈妈生病需要到县里照顾,亚亭必须承担起独自一人管理学校的责任,这种突如其来的偶发事件,造成了主人公内心的焦灼,焦灼的中心是孩子们的午饭,梦中那一个个被磕出来的小鸡,以一种糅化在合理情节中的儿童性剖开了这种焦灼之重。而现实的困境则完全成为梦境的投射,在孩子们的期待中,面由不够到过剩,主人公的慌张无措与不断变换的“问题现场”,成功推动了小说走向高潮。我们由此读到了一个经典的“谈判现场”:
终于,在佘敏的“威逼利诱”下,那半盆面分掉了。
可是很快,亚亭就知道了,那半盆面不是白吃的。
……
“大家都说老师煮的面好吃,蛋汤鲜,臊子香。”佘敏先说这个。
“大家说,肖老师人真好!如果下午不上课……”佘敏顿了一下。
亚亭听了好笑:“下午不上课就是人好?不上课你们想干什么?疯玩?”
“秋游。”佘敏说完,眼睛亮闪闪地盯着她。
这是带有明显儿童特质的对话,智性与灵动彰显着小说具备儿童性真正的内核。此时,“定海神针”杨老师的偶然离去,成为孩子们提出诉求的有利契机,而那半盆剩下的面则成为把握契机的筹码。作家以一种对智性的敏锐把握,完成了儿童文学最珍贵的要素——描写对象的平等性。当叙述者将自身成人的身份完全抽离,这种近乎“零度叙事”的讲述,让儿童文学开始了真正的“去教育化”。作者并不是俯下身子虚伪俯瞰,而是把故事交给成人与孩子这双重主人公,既不做所谓快乐文学那童言稚语的“搔痒”,也不板起面孔来“训教”,能够让故事是故事,让情节说话,其要点就在于对儿童那份天真智性的客观书写。
秋游顺理成章地进行,将小说的主人公统摄于另一重偶发事件中。过桥时孩子们的天性与亚亭自己的胆怯构成了对她的双重考验,她必须适应好师长的角色,同时找寻到自己的“涉渡之法”。显然,那漂亮的月亮桥象征着必须面对的挑战;而接下来那两棵长在一起的树在吸引孩子们的惊呼的同时也象征起了人与人,乡村与城镇,历史与当下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关系;当孩子们去争辩那个被凿出的石门究竟是出自谁的爷爷之手时,小说进入了意义上的“曲径通幽”,无名的开辟者,愚公般的祖辈,不断找寻出路的家园建设者,就在这样的偶发事件中被潜形于寥寥数笔间。这是独属于儿童文学的表意方法,那种跨代际的简单对话,完成着另一重理解之门的构筑,而留待的却是少年读者多年后的恍然而悟。所谓短小精悍易,太极无形难。
不妨让我们在看故事的结尾时,回看小说的开头。那个焦虑的新手教师,显然有着她的焦虑“前史”,“来到青木塔后,睡眠越来越好,‘小妖精很少出来捣乱了……”“小妖精”的所指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当秋游过后,亚亭说出:“其实是你们带我玩,你们给了我一次完美的秋游”时,我们已经看到了偶发事件背后的心理攻坚,是儿童疗愈了成人。当儿童为成人焦虑之时,小说就已经完成了教育双方的对位与置换,这无疑也是一种叛逆,而在这种显而易见的“叛逆”深处,却暗含着小说家对于文学之外更为深刻的思考。
《秋游》是一个关于教育的故事,同时也饱含着对社会中的人的悲悯。事实上,小说借助“梦与现实”“面的多与少”“危险与安全”“开辟与践行”等问题性情节的驱动,写出了人之难,写生活中的人之难。相较于借助天马行空的幻想来达到深刻的表意,这种寓深于浅,从生活肌理出发的书写更考验作家的功底与态度,在这个追求“效率”的时代,小说家写的是在生活之难的基础上,向难而生的重要性,这也是在幻想与宏大主题流行之下的“反向书写”。当然,当我们聚焦情节反观现实之后,会发现作者所指之处正是现实的症结所在——教师与学生之间还有足够的信任以完成一次“秋游”吗?师生间的教学相长是否还存在于生活现场?心理上的问题何以有效解决?
以常规的书写,只进行生活的描摹,去重申儿童文学在文学场乃至于社会学意义上的重要作用,《秋游》完全是一次“温柔的叛逆”,而这种“叛逆”的根源则在于作家对成长中的人的悲悯与不可或缺的社会责任。
二、《我的外公是一只飞鸟》:永远有多远
毋庸置疑,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几乎各行各业都在享受着人工智能的福利,也同时恐惧着大数据时代下人工智能对自身的取代危机。在几乎一切都可以通过算法来进行预判与对应的局面中,人心、情感、想象,因其具备着理性之外的特征而无法被“测绘”,而这三点又恰恰是整个人类社会能够运转并向前发展的内驱之所在。它们无疑也有力地诠释着文学世界的永恒性与存在的必要。换言之,捍卫想象,呵护人心,敬畏情感,在很大程度上即是尊重人类文明甚至是人的存在意义的最后防线。
当我们试图为优秀的儿童文学进行价值判断时,想象力往往成为一个重中之重的考量。幻想,这个被标记在童真上的属性,让儿童文学更为明显地区别于其他文学类型,尽管众所周知,想象应该是全部人文成果的主要构成要素。这种充满了偏见的定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儿童文学作家的自我判断,甚至产生了一种打着“捍卫想象力”大旗的“文体自觉”,进一步造成了儿童文学独立闭环的形成。当我们满怀敬意地重温《小王子》《安徒生童话》《海底两万里》《没头脑和不高兴》《非法智慧》这些闪光的名著时,是否会意识到,它们首先是优秀的人文成果,重要的文学成就,然后才是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
幻想并不完全等同于天马行空和令人惊讶或捧腹,这只是其表,而其内里则是严密的逻辑,严肃的指涉,发人深省的追问。所以,优秀的儿童文学当然可以是充满了烂漫幻想的故事,我们永远要发扬想象在儿童文学中的功用,但永远究竟有多远?这应是放在案头的一大命题。
廖小琴的《我的外公是一只飞鸟》就是一篇充满了想象力的幻想小说,“有节制”的想象让故事张弛有度,借助想象的波澜,完成丰富的现实指涉。
虽是幻想,却有着严密的逻辑,这是这篇小说最大的特点。生病的外公自述自己是一只飞鸟,以此为逻辑的起点,将一切情节统摄于“病中回忆”,幻想构建的基础虽平平无奇,却让小说在理性的始发点起航。外公的陶匠父亲娶了流民鸟姑,生下外公,鸟姑去世后续娶大脚女,生下了舅爷,外公则子承父业在山老头的帮助下成了一个货郎,一干就是一辈子。这就是故事的全部,而小说家却借助幻想,让旧故事生长出了新枝丫。是的,有了幻想一切便开始不同。
让我们尝试着用幻想去重述整个故事。为了救出那只珍贵的鸟,小陶匠用祖传的那个可以使旧物换新颜的陶罐进行了交换,那只鸟留下一团温暖的火焰之后离去,直到幻化为鸟姑嫁给陶匠,在牧鸟人的帮助下,鸟姑终于生下了外公。一家人幸福地生活直到一只神奇的鸟带走了鸟姑的灵魂,陶匠开始担着扁担讨生活,开始和植物说话,获得了倾听自然的能力,之后又娶了风幻化成的大脚女,生下了小儿子。外公则成功地获得了山老头的认可,开始了自己的卖货郎生涯,直到晚年病中才坦言自己是鸟姑的孩子,也是一只鸟,只是飞得太久太久了。
穿梭于旧故事的幻想元素,开始了对小说巧妙指涉的悄然重构,读者在潜意识里已经开始渐渐明白意象的符号学意味。向往着自由又不断面临落网之危的鸟;能够在旧中更新的,带有土地疗愈功能的陶罐;与“疯”谐音的风,代表着力量的大脚;还有充满了智慧,调皮的山……这些“符号”巧妙地构建起了一个故事之外的斜出旁逸,其中寄寓着时代与生活的变迁,个人生活与公共空间的矛盾,复杂而磅礴的情感,以及,“谁是疯子”这道永恒的难题。真实与虚妄交缠在故事的深层表意空间之内,在节制的想象中,编织成真正具有变换维度的理解之网,供人攀援与联想,粘连着更为广阔的现实命题与生命疑难。显然,因为幻想,小说具备了儿童文学宝贵的可读性,同样是因为幻想,让小说超越了人们对儿童文学狭隘的理解,无声地讲述着更为深刻的故事。
当我们重申永远要发扬想象在儿童文学中的功用时,应该明白的是,永远可以无限远,但必须以逻辑为舟楫,以现实的指涉为彼岸。就像纳博科夫在《文学讲稿》中所说的“读书人的最佳气质在于既富有艺术味,又注重科学性”【1】,而一名好的儿童文学作家他的创作也必须既富有艺术性或趣味性,又注重科学性或合理性,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充满了幻想色彩的讲述,带有警世危言的意味,这也是对优秀儿童文学的最高要求。
三、私人讲述或记忆同构
《秋游》与《我的外公是一只飞鸟》,一篇是现实主义题材儿童小说,一篇是幻想类儿童小说,在鲜明的文体特征下,却表现出了相同的气质,即对于讲述记忆的痴迷。
《秋游》讲述的是乡村故事,但无论是环境背景抑或是叙述腔调,都充满了怀旧的意味,我们无法定论那个初来乍到的年轻老师是否有着作者本人的影子,但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怀旧感让文章带有了明显的“私人讲述”的魅力。每一部经典的小说都应该是一部心灵秘史,作者显然深谙其道,小说以主人公之口阐明了人心抚慰的重要性,并将乡村与土地构筑到人与自然的关系网中,由此完成一次“隐秘的自省”。当下的我们,是否在过度强调主体性的同时,失去了获得主体性的能力?作者以一群孩子和乡村为疗愈之法,告诉我们没有人可以孤立地存在,问题永远在产生,但你并非“独上层楼”。这或许是这部小说真正的创作缘起。
而《我的外公是一只飞鸟》则更为明显,小说以“挖掘”外公记忆的方式展开叙述,叙述者与主人公的视角不断调整,相辅相成。这是一段明显的带有追溯腔调的讲述,一个遥远的时代以幻想的形式完美地对接了当下人们的理解通路。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家族的秘史,但关于家族往事的追忆往往带有时代和历史的印记。我们在外公的记忆中读到了困顿、选择,读到了自由、失去,同时也读到了生命的无常与人世间的无奈,在泥沙俱下的丰沛幻想之下,是作者着意要潜藏的叙述空间,是留给成长中的儿童在某年某月回忆时的恍然大悟。外公的个人讲述,我们完全可以看作是一代人的记忆同构,那个兼具自由与拘束,坚强与脆弱的飞鸟,是他们对自己的外化确认。
饶有意味的是,当我们尝试着将两篇文章进行对接,会发现外公完全可以看成是亚亭带着的那群孩子们的祖辈,是“开辟石门”的爷爷们,而他们秋游的山村,则可以看成是有着无数宝藏的山老头的属地,而作为“外乡人”的亚亭的到来,正可对应鸟姑的到来。
当两篇完全不同的文章开始对接,当两种不同的题材开始交融,私人讲述就开始有了记忆同构的另一重可能。这或许是因为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幻想题材,小说的讲述中都“隐伏着内在的契机,使得客观的小说叙述变成了寓意的结构”【2】。《秋游》通过对石门究竟开自何人,《外公是一只飞鸟》通过那个可以“由旧而新”的陶罐为何有此能力又何以失去这种能力等潜在的拷问,完成的是对历史何以被讲述、集体记忆中私人记忆与个人史如何被提及的追探。而不能忽略的是,无论历史被如何讲述,现实都已经到来,鸟姑与亚亭一样都是带着个人的“故事”来到山村,并在被疗愈的过程中为乡村带来变化的契机,孩子们与“我”一样,在长辈们的讲述中对家族乃至民族的往事充满了疑惑与敬畏,在这个过程中,小说借助私人讲述完成了记忆同构之外的精神传续,那是比故事更加宏阔而绵远的意义。
两篇调性各异的儿童小说,却为我们提供了同一种思考的方向——儿童文学如何在成人叙述者和儿童主人公之间做好叙述学与心理上的平衡,作为文学门类的一种,儿童文学又如何在“小”中呈“大”,承载起文艺之道,如何把“叛逆”理解为创作的诗学,又如何将想象力控制在永恒的中道之上。创作本身也是“私人讲述”之外的一种“记忆的同构”。
注释:
[1]纳博科夫:《文学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91年10月,第24页。
[2]汪晖:《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第8页。
陈曦,天津市作家协会文学院签约作家,青年评论家,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员。出版有《梅兰芳京剧大师》《蝴蝶知道一切》等图书多部,在《山东文学》《文艺报》《光明日报》《新京报》等报刊发表文章三百余篇,曾在《儿童文学》《儿童文学选刊》等杂志开设专栏。
责任编辑:崔健
——两岸儿童文学之春天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