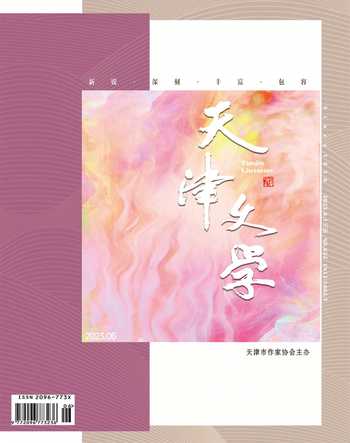是后河沿的鱼吗
从林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天吧。
后半夜下起了雨,很大,电闪雷鸣的,像七八月的天儿。已经初秋了,这样的景象有点儿不同寻常。幸亏我们回到了所里,不然一个个全浇成落汤鸡了。
与我们一起回到所里的,还有七个人,六男一女,破衣烂衫、脏兮兮的。他们是在工地的一个还未启用的污水井里发现的,大半夜的,窝着这么多人,肯定要带回所里审一下。一回到派出所,所长老程就让我把那几个人带到前院值班室对面的空屋子里,锁上,由平时只上半天班的老钱看管。老钱是老病号。那晚全市统一行动,清查,全所停休,人手还紧张,连老钱都得加班了。我刚当警察,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行动,很是兴奋,颠儿颠儿地跑前跑后,像个多动症的孩子,一会儿都不识闲儿。老程正在办公室喝水抽烟,我敲门进去,问他那几个人怎么处理。老程看着我,笑笑,没说话。那意思是,这事儿好像不该你请示我吧,但又有肯定我工作积极性的意思。老程放下茶杯,猛地抽了口烟,说,先歇会儿,不急。我从老程办公室出来,回到宿舍躺到床上,闭目养神。
雨似乎小了点儿,但“哗哗”的雨声仍充斥双耳,脑袋“嗡嗡”的好像灌满了水。我钓上了一条鱼,鱼应该不小,突然拉黑漂,差点儿把鱼竿拖走,我使劲儿拽住鱼竿,鱼在水中拼命挣扎,“哗哗”地翻着水花,鱼竿像拉满弦的弓箭,弯成了半圆。我双手攥住鱼竿,紧张地遛着鱼。我不会钓鱼,平时看到别人钓上大鱼时这样做,我也模仿着这样做。但人家很老练,一点儿不紧张,就着鱼的力顺势遛,不硬来,硬来一来费力,人很累;二来鱼很可能挣脱开鱼钩逃脱。不急不慌地遛着,慢慢消耗鱼的体力,一会儿鱼就累了,水花渐渐小了,等水花基本消失,鱼就精疲力尽了,用一个抄子,轻而易举就把鱼捕获了。我笨拙地遛着鱼。我急得满头大汗。四下张望,竟空无一人。我更慌张了。突然下起了暴雨,雨大得像天上裂了大口子,水直接漏下来,倾在脸上睁不开眼,喘气也费劲。我一只手攥着鱼竿,一只手俯身从包里掏雨衣,撕扯半天也没掏出来,帆布包还被大水冲走了。一着急,两只手抓帆布包,鱼竿脱手,瞬间没影儿了。鱼把鱼竿拽跑了。
老程在院里嚷嚷。老程大嗓门,平时说话声音就大,“哇啦哇啦”,像个破锣,大家都习惯了,没人觉得不正常。这次好像不一样,声音也大,却透出不一样的气氛。平时都是嘻嘻哈哈、满不在乎,现在明显觉出了紧张和急促。
我睁开眼。我刚才竟迷迷糊糊睡着了。
天已微明,雨停歇了。空气濡湿,隐隐飘荡着一股咸腥的味道。
老程站在自己办公室外面的屋檐下,冲李姐喊道,马上报分局刑警,让小宋他们赶紧把手里的活放下,跟着我出现场,快!
李姐小跑着回前院值班室去了。李姐是所里的内勤,平时的工作就是在值班室办理户口和值班。老程回屋迅速穿上白制服,出门看到我,说,哎,你和老钱把小宋他们手里的活接过来,仔细点儿。我问,都干什么啊?老程急急火火地往外走,回头甩了一句,问老钱。老程带着小宋他们,骑着自行车一溜烟没影儿了。派出所一共九个人,老程几乎带走了所有的人,除了老钱、李姐和我。肯定发生了大事,不然不会这么兴师动众的。所长老程一贯沉稳老练,突然就紧张起来了。
我往前院走,经过过道厨房,见老谢在里面“叮叮当当”忙着什么,随便问了一句,老谢,忙什么呢?老谢头也不抬地说,杀鱼。雨大,上游放水,冲下来不少鱼,早晨在后河沿捞的。我探头看了一下,老谢的围裙上,横一道子竖一道子,有鲜红的血迹,地上“尸横遍野”,横七竖八,躺着七八条大鱼,都是五六斤左右的鲤鱼和草鱼。有的已经开膛破肚,翻着肚皮,纯粹就是死鱼了,有的还没死,在地上捯气乱蹦,老谢就用一根手腕粗的擀面杖,用力敲它们的脑袋,只一下鱼就不动了,翻白眼了。老谢边敲边说,中午就可以吃了,我先炖一锅。
到了前院,见老钱坐在东屋里,靠在椅背上打盹。东屋是户籍档案室,平时哪个单位需要调阅户籍档案,老钱就凭介绍信接待一下。一般没什么事,挺清闲。我没打搅老钱,进值班室问李姐发生了什么事?李姐说,一大早有人报案,说后河沿发现了一具男尸。我吃惊地问,是吗?怎么死的?谁杀的?李姐一笑,说谁知道啊,那得查。老程他们已经去现场了,分局刑警马上技术勘查。我急不可耐地说,我也去。李姐说,你还是老实待着吧。老程临走时给你布置什么活了?我说,让我和老钱把小宋他们的活接过来干完。李姐冲值班室对面的南屋一努嘴,嗯,抓紧把那几个打发走吧。我又到东屋,老钱还在打盹,我故意吓唬他,哎,人跑了。老钱眼都不睁,跑不了,我耳朵比眼睛还灵。我来所里时间不长,感觉老钱总是这样“无精打采”的,话不多,也不太主动做什么,但他的“感觉”很好,别人没看明白的事,老钱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往往很准,所长老程很信任他,两个人的关系很近。据说老钱住家很远,上下班很不方便,刚到派出所不久,提出调动工作,调到住家附近的派出所,已经联系好了,就等这边放人。当时的领导不同意,领导说,哪儿有刚来就要调走的,没调成。过了好多年,后来同意了,那边接收单位换领导了,新领导说我不知道这事儿,不同意接收。老钱一急就病了,在家歇了半年。半年后上班了,每天只能上半天班。这时的所长换成了老程,老程和老钱是公安学校的同学,看在同学的份上,老程把老钱安排到户籍档案室,工作压力不大,没硬指标,挺清闲,一晃也十几年了,快熬到退休了。退休就解脱了,自由了。
我问老钱怎么干?老钱说,简单,问话,问清楚情况,必要时与原籍联系,核实清楚身份后,没什么问题请示放人,有问题的留下,送分局。我到后院办公室取问话笔录纸和笔,回来经过过道厨房,老谢那边已经消停了,一点儿动静没有,无声无息,死寂一般。鱼是泡在水池里,还是已经剁成了段,一会儿上锅炖呢?我拿着纸和笔问老钱,在哪儿问啊?老钱想了一下,说到后院吧。我转身刚要去叫人,老钱又叫住我,算了吧,就在这屋问吧。按规定问话必须是两个人在场,可能老钱觉得两个人都到后院去,前面就李姐一个人不妥,就让我把人带到户籍档案室问话。其实也没多少活了,小宋他们已经问完了五个,还剩两个,一男一女。男的年龄最大,看着有六十多岁了,女的年龄最小,看着也就十四五岁。户籍档案室不大,大概十五六个平方,摆上几排档案资料,一个三屉桌,一把椅子,基本就没站脚的地方了。我从值班室搬了一把椅子,坐在老钱旁边,斜着身体,跨着桌子一个角做记录。那一男一女只能坐到门槛上了。我问话,兼做记录,老钱不说话,仍闭着眼打盹。老钱说,你问吧,我在旁边听着,这是个练手的机会。先问的女的,说是不愿意上学,家长每天给她“护送”到学校,她就从家里跑了出来,坚决脱离开家长和老师的管束。后来跟学校和家长取得了联系,核实清楚情况后,让家长领回。最后一个是那个老头儿。我进南屋叫他的时候,他蜷缩在屋角,乱蓬蓬的长发枯草般盖在头上,遮住了多半个脸。一件肥大的半袖背心,松松垮垮地贴在瘦骨嶙峋的身上,脏兮兮,湿漉漉。他听见动静,抬头看了我一眼,又垂下头。那一刻,我看见他的嘴唇青紫,还打着冷颤。我冲他说,起来,跟我走。他双手撑地,一点儿一点儿往起站,显得非常吃力,一条腿已经撑住地,眼看就站起来了,“哐当”一下又跌坐在地上,伴随一声痛苦的呻吟。我冷冷地说,快,别装蒜啦,抓紧时间,完了,还有重要的事要做呢。我的脚崴了。他用双手捂住右脚,痛苦地看着我。我上前查看,他的右脚肿得像个酱熟的猪肘子,紧绷绷地把懒汉鞋上的松紧带都撑开了。伤着骨头了?我俯身查看他脚伤时,感觉有一股隐隐的热浪,撩了我一下。你发烧了?他“嗯”了一声。我用手背碰了一下他的额头,滚烫。他的脸蜡黄,没有一丝血色,身体缩成一团,筛糠般抖动。这样一个人,有严重的脚伤,发高烧,年龄不小了,随时会有危险的。
我赶快向老钱报告了这个情况。老钱说,这事应该请示一下老程。我说,所长在后河沿勘查现场,没在所里啊,怎么请示啊。老钱说,是啊。我急切地说,您倒快点儿拿个主意啊,这事等不得。刚参加工作,到一个新单位,就和老同志说话这么冲,连我自己也没想到。老钱笑了一下,还是没表态。我在院里来回疾走,从兜里掏出自行车钥匙,走向自行车,但又一想,从所里到后河沿现场,来回怎么也得两个多小时,两个多小时中间很可能发生意外。我又返回南屋,蹲在那人跟前,问,你感觉怎么样?他连抬眼皮的力气都很吝啬了,一个含混的呻吟在喉咙里咕哝了一下。不能再耽搁了。这时,老钱从户籍档案室出来,把我叫出来,拍着我肩膀说,先这样,你到附近医院先请一个大夫来,初步检查一下,如果病情严重再送医院,所里不能就李姐一个人。我骑自行车,飞奔到派出所附近的一个医院,说服了一个医生,跟我到派出所来了。医生给那人用听诊器听了听,说,像是肺炎,得马上送医院。说完就走了。那人肯定坐不了自行车,身体已经虚弱得没有一点儿力气。派出所旁边是针织厂,门口有一辆拉货的三轮车,我和看门的师傅打了个招呼,把三轮车骑到派出所前院。那人还是个大个子,死沉死沉的,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把他拖出南屋。我和他都出了一身汗。老钱和李姐也一块儿用力,一个病号,一个女同志,不管用,一个到所里办事的小伙子见状跑过来帮忙,才一起把那人抬到三轮车上。
医生说,再晚点儿,就有危险了。他的脚拍了片子,粉碎性骨折;关键是肺炎,引起高烧,已经昏迷休克。我一直陪在他身边。这是我的职责。无论什么人,哪怕他是杀人犯,在派出所接受处理期间,都不能出现任何问题,特别是人身安全问题。他基本处于昏迷状态,有时惊厥突然睁开眼,有时断断续续说胡话,听不清他说什么。
他到底是哪里人?干什么的?
昨晚,前半夜过去了,没发现任何异常,整个辖区每个角落都转了,啥情况都没有。大家就议论说,派出所平时跟早市似的,报案的一拨跟着一拨,很少有闲着的时候,怎么一离开派出所这么安静,真是河里没鱼市上找。老程说,没发现什么情况是好事,说明我们平时的工作到位。老程带着我们到了一个早点铺。昏黄的灯光下,一个师傅正在一口大锅里熬豆浆,满屋弥漫着醇厚的豆香味。豆浆黏糊滑腻,白如凝脂。我喝了有生以来最好喝的豆浆。我这才意识到,我们每天早晨在外面喝的豆浆有多么不真实,经过勾兑和处理的豆浆已经不是它的本来面貌了。老程还让师傅炸油饼。我们每人又吃了好几个油饼,有糖油饼,有白油饼。吃完了,大家的嘴都油亮油亮的,像抹了猪油。老程问,都吃够了吗?我们说,吃够了。老程就说,收队。一行人浩浩荡荡骑自行车回所。就这么走了?我不解,扭头问小宋,没见谁付钱啊?小宋就笑。后面跟上来的老程问,笑什么呢?小宋说,你怎么吃完油饼喝完豆浆不给钱啊?老程惊讶地说,呦,还真是的,忘了给钱了。那怎么办啊?我说,那我回去给钱吧。掉转自行车要回去给钱。老程拽住我,行了。我不明就里,愣怔着。大家都笑。我又问了小宋一句话,我们喝了那么多豆浆,只剩半锅了,明早他们会不会兑水啊?大家笑得更厉害了。小宋和我并排骑着自行车,告诉我派出所记着账呢,一个月结一次账。
过了小桥,后河沿渐渐在我们身后远去了,正在建设中的居民小区,离我们越来越近。一条小路蜿蜒曲折,两旁野草丛生,荒芜杂乱。回所里这是必经之路。我们刚才已经来过这里,仔细检查了每一个地方,没发现任何异常。忽然,蒙蒙夜色中,大约五十米处,有个黑影闪了一下。我激灵一下,飞快骑过去,却什么都没发现。看花眼了?老程也过来了,问我发现了什么。我没答话,继续在四周搜索。手电筒光柱里,一个黑洞洞的洞口掩藏在杂草中,旁边有个差不多洞口大小的石板。记得我们先前检查这个地方的时候,石板是在洞口上面的,现在明显有人挪动。应该就是这儿。我把手指向洞口,对老程说。我把手电筒照向洞内,就要往里跳。老程一把拉住我,又叫了两个人跟我一起下。
老程嘱咐我们,都机灵点儿。这是个污水井,还没有启用,是个遮风挡雨的好去处。那六男一女就是在里面发现的。当时,那人蜷缩在离洞口不远的一个角落,身上盖着一块工地上随处可见的破苫布。他走路不利索,一瘸一拐,拄一根木棍。我着急,想快点儿回所,看他岁数又比较大,就用自行车把他驮回所里。还真巧,离所里还有几步远了,雨突然下起来了。我们紧走几步,才没被浇成落汤鸡,但身上还是湿了。
快中午的时候,老程来到医院。我一直守在那人床边,医生一直给他输液。老程向医生询问这个人的情况,得知已无危险,表情放松了些。刚进医院时,表情还很紧张。老程是听回所里取饭的同志说的这个人的情况,立刻赶到医院的。我向老程打听后河沿男尸的事,老程说,刑警正在勘查现场。说完就急匆匆走了。我在心里埋怨,也不找个人替换一下我。
中午我回所里吃饭。老谢已经炖好了一大锅鱼,红烧的,看着闻着都很诱人。可所里冷冷清清,只有老钱、李姐,还有她的两个女儿。李姐的两个女儿,在派出所附近的一个小学上学,早晨李姐上班,把她们送到学校,中午在派出所吃饭,晚上下班一块儿回家,自行车驮着,前面一个,后面一个。两不误。我到厨房打饭,问老谢勘查现场的回来了几个?老谢说,两个,吃完了又走了,我给他们盛了一盆鱼,一袋子馒头,拿现场吃。老谢的手艺真不错,鱼的味道很香。早饭没吃,饿极了,一口恨不得吃下半个馒头。我拿着饭盆边吃边往前院走,想看看关在南屋的那几个人怎么样了。一进门,见屋内有两个饭盆,一个盆里全是吃剩下的鱼刺,另一个盆里还剩少半个馒头。他们吃饱喝足,靠在墙边打盹。我笑了。和警察一个生活标准,你们有功!李姐和孩子吃完了,正在辅导她们写作业,周末,下午不用上课了,下了班李姐直接带她们回家。李姐告诉我,老程让回来吃饭的传话,说别让带回来的那几个人饿着,发生了大案,千万别再后院起火,出别的事。老谢没做别的,只有鱼,就给他们端来一盆鱼,反正鱼多得是。我从东屋门前过去,老钱靠在椅子上打盹,有轻微的鼾声。桌上一堆鱼刺,吃得干干净净。
那几个人得抓紧时间处理了。昨夜,小宋他们差不多把该做的都做了,做问话笔录,与原籍电话联系,核实身份,没发现什么问题。吃完饭,我问老钱,那几个人怎么办?老钱说,老程去现场前交代过了,没啥问题就放人。我进南屋跟那几个人说,以后别瞎跑,该回家回家。就放他们走了。站在院子里,心里轻松不少,总算了了一档子事。我恨不得立刻飞向后河沿男尸现场。
现在就只剩医院的那个人了。
下午,小宋回来了,自行车还没停稳,我就跟了过去,李姐和老钱也出来了,把小宋围在中间。小宋从后河沿男尸现场带来了一些消息,综合如下:一、分局刑警刚勘查完现场。二、人是从后面遭到袭击,窒息性死亡,肯定是他杀。三、暴雨对杀人现场造成了严重破坏,基本没有获取到有重要价值的物证和线索。四、案发时间:昨晚大约11时至12时之间。
小宋的脚也崴了,站着聊天没在意,支上自行车往后院走,发现一瘸一拐的。我问他脚怎么啦?他说在后河沿摔了一跤,天黑路滑,差点儿掉进河里。我说到医院看看吧。他说老程也让他去医院,太麻烦,没大事儿,回来找老谢要点儿酒搓搓就好了。小宋往后院走,刚进过道就喊,老谢!老谢!
傍晚前,我回到医院,那人的烧退了一些,人看着精神点儿了。他见我进来,要坐起来,我说你躺着吧。他面露歉意,表示感谢。我面无表情,例行公事地说,这是我的职责。医生说,病人的病情基本稳定了,但还得再观察几天。医生尽到了医生的职责。我很感谢这个医生。我刚把那人送进医院急诊室时,医生让我去交费,然后才能治疗。这没有错,他是按规定办事。我向医生说明情况。医生说,什么情况看病也得付费啊。但他的手并没有停,用血压仪和听诊器给他检查,吩咐护士验血输液。忙活完,对我说,你到楼上找我们院长说一下吧,他同意了,我这儿就好办了。我到楼上找院长,院长没在,找了几次都没在。我不知道,即使院长在他会同意吗?过后我才知道,所长老程找了院长,老程和院长很熟,院长同意先救人后把钱补上。
我从所里带了些吃的,馒头和鱼,放在病床旁边的桌子上,让他饿了吃。他看了一眼,没吃。我跟医生、护士交代了一下,又回到所里。所里突然热闹起来,出现场的都回来了,老程的大破锣嗓子在前后院回荡。我也兴奋起来了。老程招呼大家到会议室开会。老程看见我,让我把手里的事处理完,不用参加会了。他还嘱咐我把医院的发票保存好,回头给民政局写个报告,让民政局出看病的钱。我答应着,想说我也想参加会,老程已经拐过弯儿到后院去了。会议室的门关上了,哄笑声也锁在里面。
院子安静极了,空气中仍弥漫着咸腥的潮气。
我无事可做,又回到医院。那人安静地躺在病床上,旁边桌子上的馒头和鱼少了一些。我试图了解些情况。
你叫什么名字?
邝世平。
出生年月日?
1923年4月8日。
籍贯?
xx省xx县。
什么职业?
小学教师。
出来干什么来了?
那人猛烈咳嗽起来,用被子捂住嘴,十分痛苦的样子。
我只好停止询问。
我出了病房,坐在楼道的椅子上。护士站的值班护士低头写着什么,一个患者家属提着尿壶,从厕所出来。坐了一会儿,我觉得有些闷,下楼在医院的院子里溜达。医院不大,是一栋三层小楼,那人在二层的一个病房。我抬头望了一眼,病房的窗户半开着,窗外有一棵树,好像是桃树,我说不好。
我感到无聊得很,上楼,在楼道里继续溜达,经过病房门口,无意间瞥见那人病床旁桌子上的鱼没了,馒头只剩下半个。我走进去,站到他床前。他双眼紧闭,嘴唇挂着油腥,亮晶晶的。我问,你还饿吗?他不答话。我认为他的身体没多大问题了,很快就会康复。我实在不愿再在他身上费更多的精力。我的心里长着草。我骑自行车又跑回所里。
派出所又静了。我以为开完会,派出所还会热闹起来,打打闹闹的,气氛活跃。我还想跟谁再聊聊后河沿杀人案的情况,整天让我在所里干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心里实在不踏实,像长了草似的。我跟邝世平谈完话,把他往前院带的时候,发现会议室已经空了,会开完了。不但会开完了,人也都走了。怎么一点儿动静都没有,真神速。越重要的事,动静越小。我想起一句话:开水不响,响水不开。
实际上,我在医院那会儿工夫,老程在会议室紧急布置了任务,并且马上进行落实。老程通报了后河沿杀人案当前的情况:技术人员在现场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经过仔细甄别,一双解放胶鞋的鞋印,很有可能是作案人留下的。从鞋印的深浅程度判断,作案人大约五十多岁,男性,身高一米八左右,体重七十五公斤左右。老程布置任务说,按照上级要求,从现在开始,要在全市各交通要道、港口、码头、车站、机场设卡,进行严格检查、盘查。案子发生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不用我说,我想大家应该知道怎么做……
老钱参加了会议,把老程布置的任务向我传达了一遍。
我支上自行车,向过道的厨房走去。年轻,火化石,跑了一趟,又饿了。老谢在厨房“叮叮当当”忙着,老程让他把晚饭送到执勤点儿。我到厨房跟老谢说,我跟你一块送饭去吧?老谢说,那怎么行啊,家里都没人了。其实,我也就是说说,手里的事还没干完,怎么能脱身,真要是去了,老程非一脚把我踹河里不可。老谢晚饭蒸的包子,猪肉白菜馅,小米粥。老谢跟我打了个招呼,蹬三轮车送饭去了。我拿起一个包子,两口就塞进嘴里,盛了一碗粥,吸溜吸溜喝着,没喝完,又抄起一个包子。
那人的情况怎么样?
老钱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身后,我毫无察觉。
我吓了一跳,一口粥差点呛到气管里。
哎哟,老钱,你怎么跟猫似的,一点声音都没有。
那人后背有一处伤,刀伤,脚上的鞋不是他自己的,不合脚,小很多,撑裂了……老钱说。
我问老钱,你不吃包子吗?
放走的一个小个子男人穿着解放胶鞋。
放心吧,那人不会有什么大问题,顶多再在医院待两天,就可以出院了。派出所成救济所了,净忙这些乱七八糟的碎事儿。
你没觉得那人有什么异常吗?
嘿,还有鱼呢,老谢这手艺真不错。不知道今天后河沿还有没有鱼,让老谢再给咱们炖一锅。
我用手夹起一大块鱼整个吞了进去。
你该在医院看着他。
老钱,我这就算完成任务了吧?人没出事,及时送到了医院,烧退了,没危险了,很快就出院。我是不是可以找老程他们去……啊……我大叫,“噗”的一声,一根坚硬的鱼刺,深深扎进喉咙。
我捂住嘴,跳了起来,险些滑倒,一屁股坐在已经凉透的鱼锅上。我拼命向外跑,边跑边咧着嘴,痛苦地喊道,我去医院,我去医院!
老钱在后面高声回应,我去找老程。
邝世平没在病床上。病床上空荡荡的。桌子上的半个馒头也没了。医院的楼上楼下都找遍了。
第二天,邝世平在派出所交代了整个作案过程。
邝世平还是在那个未启用的污水井里抓获的。他说,没想到你们还来这儿找我。
责任编辑:王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