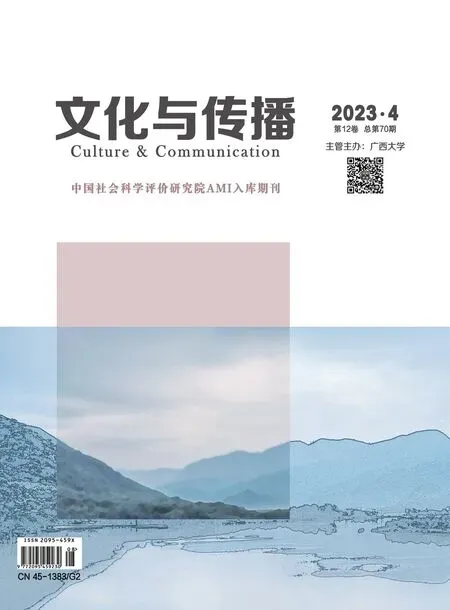高尔斯华绥戏剧《银盒》的社会阶级与伦理书写
金敏娜,刘茂生
英国小说家、剧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1867—1933)是英国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人物,被誉为20 世纪最优秀的剧作家之一,1932年以“描述的卓越艺术”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高尔斯华绥是一位跨世纪的文坛巨匠,出生于维多利亚时期的中后期,又经历了爱德华七世和乔治五世时期,与韦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阿诺德·贝内特(Enoch Arnold Bennett)—起被称为爱德华时代文学“三巨头”。他们继承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传统,在情节发展、人物塑造、细节描写等方面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以细腻的笔法反映英国社会从维多利亚时期向现代英国转变过程中的种种社会现实。[1]38高尔斯华绥的戏剧创作,多以19世纪末和20 世纪初的英国社会为背景,通过描绘资产阶级社会中道德、家庭和婚姻等方面的矛盾纠葛,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罪恶和资产阶级的虚伪和腐朽。从艺术角度来看,高尔斯华绥的戏剧题材丰富广泛,结构严谨统一,人物逼真细腻,语言简练准确。他常常通过合理运用偶然性来构建事件的开端,并以高超的叙事技巧和冷静客观的笔触不断推动剧情的发展,将不同人物的道德风貌一一展现在观众面前,同时也巧妙地表达出剧本的主题思想,[2]因此他的作品有着无穷的艺术魅力。
自1906 年首部戏剧作品《银盒》面世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八年时间里,高尔斯华绥共创作了十几部戏剧作品。这些剧作大多反映社会现实问题,聚焦劳资冲突、阶级对立、法律不公、非人的监狱生活、殖民战争等,也有触及婚姻、家庭生活、社会公德等问题的伦理道德剧。高尔斯华绥以疏远静观的冷静笔法,[3]创立了与易卜生、萧伯纳风格迥异的社会问题剧,为现实主义戏剧开辟了新的表现形式,具有强烈的时代性、批判性和艺术感染力。1906 年,高尔斯华绥在评论家加纳特的建议下,在伦敦创作完成TheCigaretteBox(《香烟盒》),后更名为TheSilverBox(以下简称为《银盒》)。①The Silver Box 有多种中译本,如陈大悲1921 年译本《银盒:三幕喜剧》,郭沫若1927 年译本《银匣》,安其1935 年译本《银烟盒》,裘因1991 年译本《银烟盒案件》。下文所引译文皆选自裘因版译文。同年9 月,该剧在伦敦皇家宫廷剧院上演,高尔斯华绥成为年度最有争议的剧作家(该剧同年被译为德语、俄语)。《银盒》的创作旨在反映19 世纪末和20 世纪初英国当代社会资产阶级的伪善和法律制度不公所造成的苦难。该剧强调客观和理性,真实地再现“人”的生活和心理,从而给观众带来内心的震撼。借助对比和讽刺,高尔斯华绥大胆针砭时弊,振聋发聩,将法律在面对贫富不同阶层时的扒高踩低、资产阶级的虚伪做作和自私自利、底层小人物的悲惨结局描绘得淋漓尽致。作者揭露和批评滋生这种现象的社会土壤,突出了该剧强大的道德力量。
一、阶层对立下的伦理冲突
作为维护社会关系和社会稳定的工具,法律本应平等对待不同阶层、身份、地位的人。然而,法律又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实际司法常常是最大限度地服务于他们的利益,所以在阶级社会里,司法不公往往体现了不同阶层的利益对立和伦理冲突。《银盒》围绕议员巴斯威克家一个银烟盒的丢失而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该剧讲述了发生在贫富两个不同阶层人物身上、性质一样结局却截然不同的事件——议员巴斯威克之子杰克和底层小人物琼斯都无心偷窃了物品,同样的偷窃行为所致后果却大相径庭:巴斯威克用钱财替子消灾,在法律从业人员的“帮助”下,杰克的偷窃行为直接被忽视而他得以逍遥法外;而琼斯即便归还了偷窃物品银烟盒仍被判罚做苦役。
和高尔斯华绥的很多剧作例如《正义》一样,《银盒》的背景也是司法行业,这和高尔斯华绥的家庭背景及学习经历密不可分。他出身于律师家庭,曾在牛津大学攻读法律,如此背景让高尔斯华绥描绘起司法行业的种种不公、下层人民的艰难困苦时轻车熟路,使他“比其他剧作家更能真实和深刻地揭露司法制度的阴暗面,引导人们深入地思考法律的真正意义”[1]48,即法律面前如何实现人人平等。高尔斯华绥借该剧揭露了资产阶级的黑暗面,但是他始终认为人类社会并没有纯粹的恶人,因此,在《银盒》和他的其他很多剧本中,作者并非以一种科学家般的全然客观冷静的态度来塑造剧中角色,无论是琼斯还是杰克或巴斯威克,他们既非十恶不赦,也非毫无瑕疵。《银盒》中,两组主人公来自截然不同的社会阶层:一组是上流社会富有的议员巴斯威克夫妇及其一无是处的儿子杰克,一家人坚信其信誉和社会地位坚不可摧;一组是贫困潦倒、地位卑微的琼斯夫妇,被生活逼得毫无还手之力。同样的偷窃行为,杰克和琼斯不同的结局让观众认识到,当时的法律对社会的不同阶层执行截然不同的评判标准。第一幕开始,杰克在醉酒状态下就道明了该剧的主题之一:“我们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这是胡说八道,愚蠢透顶。”[4]6换言之,杰克心如明镜,对于像琼斯之类的穷人而言,“平等”二字虚无缥缈,远不可及。
在剧中,高尔斯华绥着力描绘了议员巴斯威克家的奢华:“场上是巴斯威克家布置豪华新式的餐厅,窗帘已经拉上,电灯亮着。一张宽大的圆餐桌上摆着一个托盘,盒中放有一瓶威士忌,一瓶苏打水和一只银烟盒。时间已过午夜,已是复活节后的星期二。”[4]5主人公之一的杰克华丽登场:“他穿着一身晚礼服,戴着一顶歌剧帽,手里拿着一只蓝色丝绒女士提兜。”[4]7寥寥数笔,一个富家公子的形象便跃然纸上。杰克一回到舒适的家便迫不及待地继续享用苏打水,同时极力邀请送他回家的琼斯喝一杯威士忌。穷如琼斯也注意到这个家的奢华:“他们这儿的东西可真不少。”[4]7戏剧还展现了巴斯威克夫妇享用早餐时的情形:巴斯威克安详、庄重,戴着眼镜阅读《泰晤士报》——这是他热衷政治,保持和当权的托利党步调一致的象征之一。作者还特意设计了早餐桌上的一封信——这也是当时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重要象征。室内装饰的华丽和生活的舒适无一不衬托出巴斯威克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剧中对琼斯家的细致描写呈现了截然不同的一幅画面:“室内陈设简陋,地上铺着一张破碎的油布,潮湿的墙壁涂上了一层胶画颜料,给人一种贫穷但整洁的印象。”[4]31在巴斯威克一家享用早餐、甜品、一九六三年的葡萄好酒、胡桃时,琼斯则用《泰晤士报》包着一家人所要吃的半个面包、两个洋葱、三只土豆和一小块熏肉。在这个家里,连最基本的必需品都成问题,琼斯夫人以周全的心思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这个家的生计。高尔斯华绥用现实主义的基调为观众呈现出不同阶层的生活差异。
高尔斯华绥的戏剧生动地刻画了资本主义社会贫富悬殊的现实,敏锐地揭示了其最尖锐和黑暗的问题,把资产阶级虚伪自私的丑恶嘴脸暴露在公众面前,正如译者裘因在译序中指出,“高尔斯华绥揭露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面前并非人人平等,它的职能是实际上是专门为了对付穷人,保护有产阶级”。[4]2无论是《银盒》中的法律制度不公问题,还是《正义》中的监狱制度对人性的摧残,抑或是《争斗》中的阶级对立和斗争,高尔斯华绥以另类视角注视维多利亚时期的种种社会问题和现象,既勾勒出上层社会的飞扬跋扈、虚伪肤浅,又入木三分刻画了下层民众的艰辛坎坷、倒悬之危。
二、下层阶级的伦理困境
通过盗窃事件,《银盒》除了揭露司法不公,还折射了下层人民的伦理困境,展现了故事的人物关系。戏剧开头,杰克醉酒并拿走女伴的手提包,回家路上遇到同样醉酒的琼斯并被其送回家;琼斯在杰克家顺手拿走银烟盒,琼斯太太刚好是杰克家的女佣,人物关系在这一系列的事件逐渐明晰。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的心理机制与思想意识有其特殊性与丰富性,[5]这个时期经济的高度发展使英国社会积累了更多的财富,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中产阶级、上流社会对金钱、财富的极度追求几乎达到贪婪的程度。同时,人们的道德意识极强,道德观念深入人心,其影响力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到处都是道德准则(moral law)。琼斯的酗酒、偷窃等行为毫无疑问有悖于时代的道德标准,但都源于他陷于失业的经济压力所造成的伦理困境中。据琼斯及其妻子所言,他并非不想工作,反而是“卖命”地想干活,但在此过程中,他四处碰壁,遭人白眼。琼斯迷茫又痛苦,只能通过酗酒排解心中苦闷。此种情形不单发生在琼斯身上,在第三幕法官审理的第一个案子中,莱文斯先生也提及“我是很结实的,阁下,我非常愿意干活,但是拼了性命也找不到任何工作”“我什么都尝试过,阁下——我尽了一切努力”“好像无论我怎样奔走,也找不到工作”。[4]58-59“伦理环境就是文学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文学必须回到历史现场,即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批评文学。”[6]《银盒》中琼斯和莱文斯之遭遇并非简单的个体失业现象,若将其放置在当时的社会伦理环境中,挖掘现象产生的根源,就能更好地对琼斯和莱文斯的失业问题作出解释。
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资本主义呈上升趋势,工业革命极大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早期的资本扩张致使贫富两极分化,阶级矛盾业已酝酿,执法不公等成为普遍现实,而后工业衰退,大量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劳工纠纷愈演愈烈。资产阶级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快速壮大,然而这大都是建立在统治阶级对底层劳动人民的无情压迫和残酷剥削的基础上的。因为缺乏专业技能,大多数底层劳动人民只能充当廉价劳动力,饱受欺压。以琼斯为例,起初他只能以当马夫为生,而随着交通工具的发展,类似马夫之类的职业也逐渐消失。即便是这样的廉价工作,琼斯几个月下来也找不到了。在琼斯太太眼里,丈夫的确在尽力找工作,甚至于“回来时都快累倒了”“但现在市面上很不景气”。[4]11可以说,黑暗的社会现实是诸如琼斯和莱文斯这样的男性失业和莱文斯太太选择做妓女的根本原因,首恶者不是个人而是当时的社会。和同时期的其他剧作家例如萧伯纳不同的是,高尔斯华绥的戏剧总是客观冷静地描绘各种现象,尽量避免任何感性诉求。但观众透过现象,很容易读出这些社会问题的真正根源。高尔斯华绥借助这些现象,深刻揭露了维多利亚时代底层人民贫困无助且无力改变的社会境遇,表达了对琼斯夫妇和莱文斯夫妇深刻的伦理关怀。
琼斯是一个集多重矛盾于一体的典型代表。维多利亚时期,中下层民众脚踏实地,关注自身利益,崇尚用自己的双手来过上梦想的生活。勤劳与节俭是衡量人的品格的重要标准,当上层阶级有懒惰、不劳而获等违背“道义”之举时,劳动群众会感觉愤怒。因此,一方面,琼斯对巴斯威克这样的富人疾恶如仇,“我看见你们的那个巴斯威克每天舒舒服服、惬惬意意到议会去吹牛……他们干了些什么,他们哪一点比我强”。[4]33出于内心一时的愤懑,他偷走杰克的东西。另一方面,琼斯身上也呈现出了不少宝贵品质,例如热爱孩子、保护家庭等。当琼斯太太抱怨他从不考虑自己的孩子时,他“沮丧地从房间这头走到那头”,“你要是以为我想抛弃那些小要饭的,你就他妈的错了”,[4]35他甚至认为让孩子们过着饱一顿饥一顿的日子是一种犯罪。他也打算用“捡”来的几英镑去加拿大谋生来改变命运。当琼斯太太说若她失去孩子时会想坏他们的,琼斯也闷闷不乐地承认“不光你一个人是这样”。[4]36毋庸置疑,琼斯此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获得工作机会,省吃俭用,安居乐业,而非粗衣粝食,愧对妻儿。虽然酗酒后会殴打妻子,但清醒时他也会意识到妻子和他过的日子很不轻松,也会柔情地对待妻子。在妻子被冤枉偷了银烟盒时他会挺身而出,竭力甚至不惜以暴力殴打警察来保护妻子。琼斯所在的维多利亚时代,随着当时女性觉悟和女权意识的兴起,女性在家庭、爱情中的地位日趋上升。当琼斯察觉到私人侦探斯诺冤枉妻子偷取烟盒时,他先礼后兵,先尽量与斯诺沟通,替妻子辩解,说她是个“正派的妇女”[4]39等来保护自己的妻子不受伤害。沟通无果后,他无可奈何,挥拳以待警察,导致夫妻双方被警察抓走。在法庭上,他大声疾呼:“那么,我的妻子又怎么样呢,谁来赔偿她的损失?谁来恢复她的名誉?”[4]71不言而喻,琼斯身上集中呈现了维多利亚时期极其重视的阳刚男性气概:一方面,他们渴求一份能养活妻儿的体面工作;另一方面,保护妻儿的责任被时代不断正当化、崇高化为男性的道德义务。
在古希腊悲剧中,主人公往往是和天命或不可抗拒的命运在抗争,而《银盒》中的主人公则是和法律或社会系统中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抗争。琼斯从一开始无心“偷走”银盒,到剧终时在法庭上的义正词严、据理力争,这一过程凸显了社会底层无名小卒对时代和社会的不自量力的反抗,即个体同社会体系的抗争,其结局自然不言而喻:主人公只能陷于一种讽刺的绝望中。在第三幕庭审中,由于巴斯威克授意罗珀(巴斯威克家的律师)阻止杰克讲出其偷窃真相,在社会和法律制度的共谋下,琼斯一家陷入无助之中。宣判过后,琼斯一出去,那些没精打采的男男女女发出一阵嘶哑而轻微的嗡嗡声,[4]73但是琼斯在离开之前扭过身来大声疾呼:“这公正吗?对他怎么样?他也喝醉了!还拿了别人的钱包……他拿了钱包,可是,是金钱救了他……什么正义……”尽管他的疾呼被这些嗡嗡声给掩盖住了,但他还是喊出了心底所想。巴斯维克手握大权,积聚了大量财富,这使得法官和律师因此在审判时倾斜天平。显然,这是琼斯愤懑不平的源头,琼斯在剧终时对法律不公的控诉是对自由的呼唤和渴望。借琼斯之口,通过对真相的尊重和具体细节准确而又真实的描述,高尔斯华绥意欲探究黑暗中的真实人性所在,表达了对社会现实的关切和无奈。作为个体,琼斯是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曼彻斯特学派“放任和自由”概念的牺牲品,他试图以一己之力找寻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却以屡屡失败告终,他一念之差犯下偷窃之罪,终难逃法律惩罚。高尔斯华绥通过琼斯的遭遇,揭露了资产阶级主导的社会中的邪恶之源。琼斯身上集中体现了当时底层民众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困境。高尔斯华绥在剧中将生活无望的小人物的沮丧、绝望和痛苦刻画得淋漓尽致。
三、上层阶级的虚伪道德
“在某种意义上,文学的产生最初完全是为了伦理和道德的目的的。”[7]5高尔斯华绥在《银盒》中用生动的笔触尖锐地指出,温文尔雅的上流社会议员巴斯威克在面临自己利益可能受到损害时,会撕碎其亲民的面具,他和律师、法官沆瀣一气,做出人们所不齿的勾当。《银盒》真实地揭露了资产阶级伪善的本质和当时社会道德的堕落,传递出剧作家对底层人民深切的伦理关怀。自由党议员巴斯威克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善资产阶级的代表。作为一个议员,巴斯威克热衷于政治,“严肃”对待种种事件。其道貌岸然的严肃表面掩盖了他以双重标准对待政治、伦理问题的丑恶嘴脸。道德权威往往掌握在上层人士手里,他们动辄将问题上升到道德高度,而这些道德准则对社会上流人士根本毫无约束之力,实际受到侵害的正是诸如琼斯这样的下层人士。巴斯威克自诩相信人民及其行为的种种动机,对“能导致事物激怒的任何变化都持欢迎态度”。作为自由党人士,他不排斥其他党派,且认为“任何真正的改革,恰当的社会政策,必须有各党派人士参加”。[4]13-14事实上,这时本该为民众服务的政治变成了政客们玩弄权术的主要工具,作为反映民众呼声主要阵地的议会成为各派斗智的重要场所,议员们热衷于参与社会政治,其所作所为却和政治道德背道而驰。表面上冠冕堂皇、背地里虚伪是维多利亚时期政客表现出的伦理意识。在尔虞我诈、人心叵测的伦理环境中,唯有精心钻营才有立足之地。
在剧中,巴斯威克反复强调“原则”二字。他自认为讲原则,但当身处有违原则的伦理困境中时,他总会打破其原则,身上的人性因子随之让位于兽性因子。在杰克无法偿还妓女的八英镑而可能面临被起诉时,他迫不得已替子还钱,其后仍不忘强调这是个“原则问题”。在银烟盒被发现丢失之后,他依然坚持“从原则上说,我一定要弄清楚是谁的责任,这是涉及基本的安全原则”。[4]25但讽刺的是,在得知烟盒的丢失和杰克脱不了干系之时,巴斯维克竭尽全力避免杰克接受法庭的审讯,不追究琼斯偷窃银烟盒的行为并再三要求撤回对琼斯的起诉。这时的他并非大发慈悲,而是为了阻止他人了解杰克的偷窃丑闻,为了维护名声——儿子上庭作证势必会给家族名誉抹黑。当杰克不得不出庭时,他迅速地找到律师罗珀,二者商议出“撒谎”这一挽救之法。通过这一系列事件,巴斯威克典型的资产阶级本性,即追求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这一特征暴露无遗。某种程度上,巴斯威克议员是感性的。他反复强调“原则”二字,但其行事准则中却很难体现出他是否真正为其道德行为设置了相应的准则,因此,他只能是一个纯粹的机会主义分子,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乔治·勃兰兑斯曾指出,英国人的那种正义,并不是一种深藏在内心的、事先设想的观念,而是一种功利的产物。[8]巴斯威克的正义正是建立在利己的基础上的。然而,其伪善的面具随着剧情的发展慢慢被撕开。他只想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名声,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更不顾承受多少不公。巴斯威克的伪善和自私在剧末表露无遗:失去工作后,当清白的琼斯太太卑恭地向他投去恳求的眼光,他“迟疑了一会儿,然后尴尬地做了一个羞愧的拒绝的手势,匆匆走出法庭”。[4]73巴斯维克是自由党人,在剧中他曾多次表达了他对穷人命运的关心和同情,反复强调“如果我们不能为穷人干多少好事,那至少也要对他们抱有极大的同情”。[4]26但当个人利益受到威胁时,巴斯威克所谓的同情心被证明是虚假的。通过对比、讽刺等手法的运用,高尔斯华绥入木三分地揭露了资产阶级伪善、自私和冷漠的真实面目。
剧中杰克是一个自私的年轻男性,缺乏责任感,撒谎成性。溺爱儿子的巴斯威克夫妇不愿承认儿子的懦弱和无能,即便是家里的下人都清醒地看清了儿子的真实面目。女仆之一慧勒曾说,“他[杰克]是个小捣蛋鬼,真的。我看他昨天夜里是喝醉了,跟你丈夫一样。他酗酒也是因为整天没事儿,只是性质不同”。[4]9当酗酒醒来后,杰克毫无愧色地要求琼斯太太帮他隐瞒睡在沙发的真实情况,“这完全是偶然的,我不知道怎么会躺在这儿,我一定是忘了上床了”。[4]10随着剧情的发展,撒谎成性的杰克在外面到处借钱、乱开支票,甚至偷拿妓女的提兜。当无名女士(妓女)上门讨要钱包时,地位显赫的巴斯威克先生不敢相信这样的丑闻会发生在自己儿子身上,他大为震惊,“怎么搞的,在哪儿”。当杰克一看到无名女士时,他又开始撒谎,“提兜?我什么也不知道呀!”。[4]19无能且懦弱的杰克东张西望,只想找个机会溜走。在巴斯威克先生和无名女士的双重逼问下,他不得不承认拿了人家的提兜。杰克此时身无分文,只能空口承诺开个支票,但当无名女士恶狠狠地警告杰克如果拿不回钱,她就会去告他这种偷窃行为。此时,万能的议员父亲不得不放低身段,掏出八英镑替儿子摆平此桩闹心事。尽管事后巴斯威克狠狠批评杰克,说他是“社会的累赘”“危险分子”甚至是“犯罪”。可即便如此,他仍认为杰克只值得一次“好好的教训”而已,浑然不知是他们夫妇的溺爱才造就了杰克花天酒地、没有担当的性格。而杰克也毫不留情地指出,“我知道,这次要不是你怕事情会登报,你也不会帮助我的”。[4]23当巴斯威克太太说“我最讨厌不说真话的人”[4]41时,父子俩用酒杯挡住,交换了一下眼色——他俩对巴斯威克太太隐瞒了一些事情。在这个缺乏信任的家庭里,家庭成员之间相互隐瞒、互相欺骗,资产阶级上欺下骗的本性在杰克和巴斯威克身上表露无遗。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斯芬克斯因子在人身上分别以自然意志、自由意志以及理性意志等形式体现出来,由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组成。人性因子即伦理意识,其表现形式为理性意志。人性因子可以使人产生伦理意识,获得人性,能够分辨善恶,以此区别于兽;兽性因子则是人的原欲驱动,其外在表现形式为自然意志和自由意志。[7]39在杰克身上,观众看到了兽性因子的过度膨胀,他撒谎成性,虚伪欺骗,毫无担当。在第三幕中,他走上证人之位时向上帝宣誓所说皆为真实,然而一转身他就大声宣告他不认识那个男的(琼斯)。此时,他尚心存良知,偶尔内心还会感到惭愧,体现了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的较量。但在审讯中,杰克在撒谎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自私和虚伪战胜了仅存的一丝良知,最后失去对自由意志的控制,突破了伦理禁忌,作出了非理性的伦理选择。在法官揭穿他谎言时,他“惭愧地”微笑了一下,继而“不顾一切地”承认他那天晚上“大概”是香槟酒喝得太多了。当琼斯提问杰克时,他再次撒谎,“坚决”否认:“不,我不记得,我不记得有这种事。”[4]69尽管面对着法律与神灵的双重监督,杰克的证词却几乎全是谎言。令人感到讽刺的是,琼斯和他妻子这些被巴斯威克一家称作下层阶级的人,所给出的证据却全部是事实。懦弱如杰克,自然不敢为其行为承担后果。在法官宣判琼斯就是“社会的累赘”时,杰克在他父亲耳边说,“你不就是这样说我嘛”。待审判结束后,杰克“昂首阔步朝走廊走去”。这正如琼斯在结尾大喊“是金钱救了他……什么正义”。[4]73琼斯的激动和不正义的审判正好映衬了杰克的铁石心情和毫无同情心。因杰克不负责任的行为,琼斯家庭遭受了灭顶之灾,而一切事端的始作俑者的他却免遭法律的制裁。他在陈述真相时“低声地”“极轻微地”说话,在撒谎时则用“大声”“自信而干脆的语调”的表达,通过反复刻画杰克的神情和语调,作者入木三分地描绘了一位在父母的纵容和庇护下变得毫无责任感、自私冷酷的儿子形象。
结 语
《银盒》是高尔斯华绥首次以戏剧的方式关注社会与伦理道德。尽管出身于富贵之家,高尔斯华绥心系贫苦大众,作为剧作家的高尔斯华绥既不像萧伯纳那样为社会主义代言,也不简单地用“善”“恶”两分法的道德框架来建构戏剧,凸显了一位正值盛年时期的剧作家对社会问题的忧虑与民众疾苦的关怀。[1]39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伦理道德、伦理困境和伦理意识等概念有助于观众进一步理解《银盒》中,既有对底层人民法律不公的控诉,也有对维多利亚时代资产阶级伪善和自私的揭露,高尔斯华绥在剧中对琼斯和莱文斯失业的反复刻画,其目的不仅是凸显失业给社会和普通家庭带来的灭顶之灾,更在于揭露和批评滋生这种现象的社会土壤和社会制度,突出了该剧强大的道德力量。通过运用对比、讽刺等手法,高尔斯华绥将阶级对立、司法不公等社会现象描写得淋漓尽致,在后来的创作中,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持续关注成为高尔斯华绥戏剧创作的一种重要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