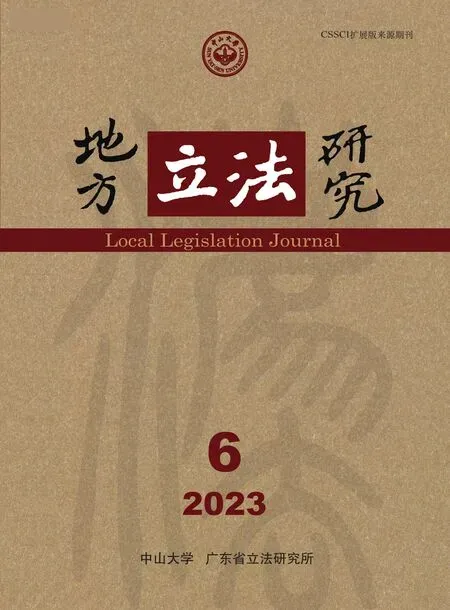如何理解网络规制中的“代码”?
——兼评莱斯格《代码2.0》
沈伟伟
岁月如梭,哈佛大学劳伦斯·莱斯格教授的《代码》一书,自第一版问世至今,已过去25年。按互联网时代的时间尺度,此书堪称“古籍”。25年间,互联网潮起潮落,《代码》及其网络规制理论却长盛不衰。那么,《代码》为何会有如此影响?其对网络规制的理论分析是否过时?作为正在亲历互联网技术革命的中国学者,我们又该如何理解网络规制中的“代码”?这是本文着重探讨的几个问题。
一、什么是《代码》的贡献
如果非要用一个最精简的、近似微博标签的词组来概括《代码》一书,那就非“code is law”(代码即法律)莫属。(1)这一说法比较早的表述,参见Larry Lessig,“Reading the Constitution in Cyberspace”,45 Emory L.J. 869 (1996),pp.896-897;Joel R. Reidenberg,“Lex Informatica”,76 Texas Law Review 553 (1998),pp.572-573。莱斯格因提炼出这一说法而声名鹊起,但在这一说法本身留存的同时,莱斯格的相关论述却被有意无意地疏远,以至于今天有些讨论常常曲解这句话的原旨。(2)[美]劳伦斯·莱斯格:《代码 2.0》,李旭、沈伟伟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2页。下文中对此书的引用不再一一注明,只给出中译本相应页码。
事实上,英文单词“code”一语双关,既指律令法典,又指电脑代码。这样一来,“code is law”便具备了双重意涵:美国东海岸国会山议员编纂的律令法典(code),规制着互联网;西海岸硅谷程序员编写的电脑代码(code),同样规制着互联网。当然,与律令法典不同,电脑代码规制互联网,不是通过官僚制度,而是通过架构(architecture)。(3)规制嵌入架构这一视角,在James Boyle看来,这是福柯社会规制理论的互联网延伸。参见James Boyle,“Foucault in Cyberspace:Surveillance,Sovereignty,and Hardwired Censors”,66 U. Cin. L. Rev. 177 (1997),pp.177-179。
如何通过架构来规制呢?莱斯格举了一个极其接地气的例子。在现实空间,为防止校园道路上机动车超速,传统法律规制的处理方式是道路交通法规、立警示牌、派驻巡警、行政或刑事处罚等。但法律规制成本较高,效果却未必很好。于是,实践中出现了一种法律之外的规制方式:加装减速带。如果司机超速穿越减速带,颠人肉疼,颠车心疼。人们正是通过在机动车道路上加装减速带这一物理设计上的改变,来限制司机的超速行为。这便是莱斯格所说的架构规制。在超速管制这个例子中,架构规制比法律规制成本更低、效果更好。
现实道路可以如此,那么,在网络空间的信息高速公路上,我们能不能采取架构规制的方式呢?莱斯格的回答是肯定的。互联网信息交互,本质上是信道中的数据包交换(packet switch)。在互联网信道上设置减速带,比在现实空间中更容易实现。比如,若要保证电信流量套餐超过20G流量后限速,运营商所需要做的,仅仅是在服务器程序中,加上一小段代码[类似“if (data usage >= 20gb),then (bandwidth<=X kb/s)”]。与之类似,不少学校或公司通过服务器端的代码设置,禁协议,堵端口,限制挤占带宽的应用程序。
除了速度限制之外,由于网络空间的可塑性,架构规制有着更宽泛的应用空间。举一个更日常的架构规制实例——网约车的虚拟号码。起初,网约车平台为方便乘客司机联系,双方号码在彼此客户端明文呈现。这类设计存在隐患:司机或乘客有可能滥用对方手机号,进行引发一系列骚扰报复等司乘纠纷。事后法律规制成本过高,对平台影响也不好。于是,平台动起了架构规制的脑筋——虚拟号码技术。司乘通过平台随机生成的虚拟号码彼此联络。虚拟号码的最大亮点,便是“阅后即焚”。通话结束之后,任何一方便无法通过同一号码再次联系对方,从而保护彼此隐私安宁,避免事后产生司乘纠纷。在上述几个例子中,架构规制比法律规制更奏效。
正因为代码在网络规制中的重要性,网络法研究才需要技术的视角。
网络法研究者不懂技术,无异于盲人谈书法、聋人论音乐。一则广为流传的轶事,讲的是莱斯格早年在美国最高法院实习时,曾嫌弃当时最高法院所采用的文字处理软件,并在斯卡利亚、奥康纳和苏特面前现场演示,说服这三位大法官采用他亲手编程的新软件。(4)Aaron Zitner,Internet-savvy Legal Scholar Foretells Government Control,Chicago Tribune (Mar. 26,2000):https://www.chicagotribune.com/news/ct-xpm-2000-03-26-0003260116-story.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3年10月1日。莱斯格之所以能够洞悉技术的规制意涵,并且在理论上重构网络空间治理的范式,都与他对技术的熟悉密切相关。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代码》一书所体现的研究视角及其对研究对象的把握,无不渗透着作者的技术洞见。莱斯格与当时大部分法学家的区别在于:后者仍是从法理分析出发来研究网络规制问题,因此技术问题要么居于研究视野之外,要么被搁置在一个从属位置;而莱斯格的一切思考出发点就是技术架构的可塑性。
也正因如此,《代码》对互联网技术演变和由此引发的规制回应,作出了更具理论颠覆性的解析,甚至初看起来没那么像法学理论。这对于置身数字时代、“身在庐山中”的读者而言,足以构成一种眼前一亮的阅读体验。这种眼前一亮的体验,并不意味着《代码》拥有着百科全书式的信息,也不意味着《代码》提供了严丝合缝的论证,而在于它指明了一条理解网络法甚至互联网社会的全新思考进路。这一思考进路,最直观、犀利的表达,便是“code is law”:技术规制网络空间,进而法律可以通过影响技术来规制网络空间。(5)有论者甚至指出,莱斯格对于技术的强调,本质上是“技术决定论”(Technology Determinism)。参见Viktor Mayer-Schönberger,“Demystifying Lessig”,2008 Wis. L. Rev. 713 (2008),pp.737-740。这一理论视角颠覆了传统法学的规制理论,强调互联网规制既需要法律意义上的code,也离不开代码意义上的code。尽管这无疑会增加网络规制研究的复杂性,但对于极大依托于技术代码的网络规制,这种复杂性不但是有益的,在绝大多数情形下,甚至是必需的。
举例来说,在《代码》第十章中,莱斯格对网络版权规制的分析,尤其是讨论P2P技术的章节,尤其具有启发性。的确,早年在互联网横行无忌的盗版音乐、影视作品,充斥着各大点播平台、P2P共享和云储存,在最近几年,共享盛宴(或者说“盗版盛宴”)的状况不复当年。按照莱斯格的视角,其原因并不在于版权立法的突飞猛进,或是版权执法的天降神兵。恰恰相反,文本上的法律,对付大规模网络版权侵权,尤其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P2P共享技术,无异于“高射炮打蚊子”,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到头来,还是得倚仗技术——数字版权管理技术、侵权监测技术、数字水印、数字指纹、IP地址监控、地理屏蔽等等。于是,“应版权方要求,文件无法下载”“任务包含违规内容,无法继续下载”“此链接分享内容可能因为涉及侵权、色情、反动、低俗等信息,无法访问”等为网民所熟知的版权警示,表面上法言法语,背后其实是代码的功劳。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莱斯格所强调的网络规制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以往分析中对互联网治理的狭隘理解,帮助我们以更宏大的视野来分析网络规制问题。他所提出的代码规制理念,现已成为当下主流观点。大家碰到棘手的网络规制问题,通常会先问,“这个问题,能不能用技术解决?”再问,“法律能不能通过影响技术来解决问题?”。其背后逻辑,莱斯格早在25年前便点破:code is law。虽然这句话放在当下只是陈腔滥调,但在25年前,便是石破天惊。
假如《代码》的理论建构,就到“code is law”为止,那么,本书也不失为一本佳作,本篇书评也可就此从容收尾。可是,莱斯格并没有满足于这一描述性结论,而是进一步在制度层面探索其互联网规制的理论,并在技术代码和法律之外,结合他以往对规制理论的思考,提出网络规制“四要素”理论,亦即网络空间的行为由四要素合力规制,它们分别是:法律、架构、市场和社会规范。(详见第七章)正是基于网络规制“四要素”理论,《代码》几乎以一己之力,界定了后世网络法的研究框架,佳作成为经典。
回顾之前的网络法著作和文章,无一具备《代码》的视野和深度。而之后的主流网络法学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代码》影响,带入技术、市场和社会规范的多元视角。这些讨论,在当下看来很自然,但实际上得益于此书。换句话说,当今网络法研究“主流”,是当年此书开出的“野路子”。其中,两处贡献尤其重要。一是“code is law”这一描述性论断。现在,学者们常常结合技术来研究网络规制,这个思路早期最透彻的论证源自《代码》。二是“四要素”理论这一分析性框架。这么多年来,“四要素”理论框架从未被超越。正是借助这一研究视野,当代学者们才能更系统地理解:谁在规制网络?怎么规制?规制背后受到哪些力量约束?(6)恰恰是对这些网络法根本问题的持续考察,才引出了更多试图阐释网络规制机理的理论,包括乔纳森·兹特芮恩(Jonathan Zittrain)的创生性网络和尤查·本科勒(Yochai Benkler)的网络信息生产理论、芭芭拉·范·舍维克(Barbara van Schewick)的互联网架构创新、吴修铭(Tim Wu)的互联网总开关等。《代码》的这两处贡献,开风气之先,奠后世格局。
总而言之,《代码》一书描述了人类社会进入网络时代的大转型,以及伴随着这个过程的规制范式的变化。这一转型进程至今远未结束,因此,我们时常能感觉到,《代码》的分析范式直指当下的网络规制问题。举例来说,虽然当下社交平台的网络内容已经与传统网络内容大相径庭,但“四要素”理论框架依然适用于平台内容管制分析。除了法律之外,社交平台采取大量技术手段、市场手段和社群规范手段来管理平台内容。并且,随着技术的发展,代码规制变得更加多样化,从以往简单的关键词过滤,到如今能够进行降低可见度、人工智能分级分类、账号限制等精细化技术限制。而这些新一代的网络法学者,都毫不意外地援引了《代码》,使用了“四要素”理论框架。(7)Tim Wu,“Wil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at the Law?The Rise of Hybrid Social Ordering Systems”,119 Colum. L. Rev. 2001 (2019),footnote 12;Eric Goldman,“Content Moderation Remedies”, 28 Mich. Tech. L. Rev. 1 (2021),footnote 36;Ari Ezra Waldman,“Disorderly Content”,97 Wash. L. Rev. 907 (2022),footnote 33.就此而言,当我们站在25年后的今天,审视《代码》这部“古籍”,我们可以断言:它仍未过时。
二、网络规制“四要素”的缘起与挑战
有关“code is law”,前文已作阐释。下面谈谈网络规制“四要素”理论。在此,我们有必要稍做迂回,考察“四要素”理论的缘起及其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法学研究谱系中的地位,这也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莱斯格的论证逻辑,进而提示似乎一直被中国网络法学界忽视的理论脉络。
从理论谱系上,网络规制“四要素”理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兴起的法律现实主义。当时,以霍姆斯为代表的法律现实主义,依托不断壮大的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在理论层面上强调社会规范、市场、文化、权力、意识形态等因素对法律实际运作(law in action)的影响。(8)从莱斯格的著述中,我们不难发现霍姆斯对他的影响,单单《代码》一书就曾三次引用霍姆斯的理论。有关霍姆斯和美国法律现实主义的兴起,参见 Thomas C. Grey,“Holmes and Legal Pragmatism”,41 Stan. L. Rev. 787 (1989),pp.805-861;Richard A. Posner,“What has Pragmatism to Offer Law?”,63 S. Cal. L. Rev. 1653 (1989),pp.1653-1655。20世纪90年代初,罗伯特·埃里克森(Robert Ellickson)发表《无需法律的秩序——相邻者如何解决纠纷》一书,是法律现实主义的集大成之作。该书通过考察美国西部夏斯塔县牧民们的纠纷解决机制,得出一个在法学界颇为激进的观点:在维持社会秩序过程中,社会规范与法律同等重要,甚至比法律更重要。(9)参见 [美]罗伯特·埃里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相邻者如何解决纠纷》,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
5年后,莱斯格发表《社会意义的规制》一文,从法律、社会规范和架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多元社会规制理论。(10)参见Lawrence Lessig,“The Regulation of Social Meaning”,62 U. Chi. L. Rev. 943 (1995)。该文认为,社会规范可以分为效率社会规范(efficiency norms)和分配社会规范(distributional norms)。截至2023年10月,已有600篇法律评论引注该文。这篇文章是时任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的莱斯格,讨论社会规制理论最深刻的一次努力。这一次努力中,莱斯格或多或少受到他在耶鲁大学的老师埃里克森的影响,沿袭法律现实主义,不拘泥于法律文本,而是将法律置身于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中考察。而在1998年的一篇文章中,莱斯格采用了一个开宗立派式的标题——“新芝加哥学派”(The New Chicago School),首次完整提出了社会规制“四要素”——法律、社会规范、市场和架构。(11)参见Lawrence Lessig,“The New Chicago School”,27 J. Legal Stud. 661 (1998),p.662。该文融合了多元视角并强调法律规制能动性的研究旋律,我们可以在他其后的网络法著述中不断听到回响。莱斯格的“新芝加哥学派”特色鲜明:与其他法律现实主义者一样,“新芝加哥学派”拒斥法律中心主义,将其他规制要素纳入研究范畴;同时,又有别于轻政府、重市场的“老”芝加哥学派,“新芝加哥学派”在规制理论建构上更接近政治自由主义,强调法律规制的能动性和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了解这一理论脉络,我们再来考察网络规制“四要素”理论。细心的读者稍作对比便不难发现,它是莱斯格的社会规制“四要素”理论在网络空间的变体,可以说是“旧瓶装新酒”。因此,与其说莱斯格的网络“四要素”理论反映了网络法理论的突破性进展,不如说是将他早年的社会规制“四要素”理论引入网络规制分析的一次尝试而已。尤其考虑到美国社会科学自身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和技术治理(technocracy)传统,(12)关于美国社会科学传统的论述,参见 [美]多萝西·萝丝:《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王楠、刘阳、吴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1-18页。把社会规制“四要素”理论放在互联网这一更为强调技术治理的现实情境中,也就更加顺理成章了。而美国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技术实践的突飞猛进,更是为这一理论打下了技术烙印。也让这类兼具实用主义传统和技术敏感导向的理论体系,很容易地在美国的土壤中扎根成长。当我们把目光投向美国之外的西方学术界时,将毫不意外地发现,在欧洲各国发展起来的网络法理论,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进路。(13)以网络隐私研究为例,欧美就存在理论研究范式上的巨大差异。参见James Q. Whitman,“The Two Western Cultures of Privacy:Dignity Versus Liberty”,113 Yale L.J. 1151 (2004),pp.1151-1222;Robert C. Post,“Data Privacy and Dignitary Privacy:Google Spain,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67 Duke L.J. 981 (2018),pp.981-1072。
这是“四要素”理论的缘起,下面我们再谈谈挑战。不可否认,莱斯格吸纳了法律之外的架构、市场和社会规范三个规制要素,比起法律单打独斗,“四要素”理论在回应网络规制问题时,具有更大的解释力。当然,代价就是更复杂的理论争议和实践挑战。
首先,我们回到“code is law”。这一表述恰恰折射出莱斯格将早期社会规制“四要素”理论嫁接至网络规制所带来的错位。原先社会规制“四要素”使用的概念是架构,而《代码》一书中,代码一词作为标题,是全书真正具有理论活力和分析意涵的核心概念。《代码》一书表达的是“code is law”,而非“architecture is law”。由于莱斯格将现实空间的架构规制与网络空间的代码规制对照使用,在修辞上,《代码》有意无意地给读者造成了一种错觉:代码等同于架构。(第122-125页)(14)因中译本再版页码变动,本文所引《代码》原书内容均为英文版原书页码,对应中译本页边码。下同。
然而,“代码”与“架构”毕竟不一样。“架构”内涵更宽泛,它既包含编程算法,也包含互联网的物理架构。换言之,代码所指的架构仅仅属于前者,然而,互联网从诞生开始就不只是纯粹的0和1的代码世界,撑起代码世界的还有现实空间的物理基础设施,而针对后者,代码规制这一说法很难称得上严谨自洽。这一概念辨析并非吹毛求疵,它对我们思考网络规制的意义重大。《代码》所强调的代码规制的特征分析,并不完全适用于互联网物理架构。(15)胡凌:《超越代码:从赛博空间到物理世界的控制/生产机制》,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第7页。莱斯格在概念上的模糊处理,如今更值得重视。这是因为近年来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加速交融,以往那些只需借助代码即可实现规制的问题,现在不得不与物理架构(尤其是数字基础设施)结合起来考量,而当下热度颇高的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也只会让这一挑战变得更加值得重视。或许也正因为这一概念上的错位,有些学者索性抛弃“代码”和“架构”这两个被过度符号化的概念,而直接代之以“软件”(software)或“算法”(algorithm)。(16)比如James Grimmelmann,“Regulation by Software”,114 Yale L.J. 1719 (2005),p.1719;R. Polk Wagner,“On Software Regulation”,78 S. Cal. L. Rev. 457 (2005),p.457。
此外,莱斯格是在人工智能被大规模应用之前写的《代码》,因此,“code is law”的前提是:代码能为规制者所用,能用作规制网络空间的工具。如今,哪怕是对人工智能技术最乐观的学者,恐怕也不会完全认同这一前提。这是因为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尤其是强化学习、神经网络、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挑战了这一前提:代码有可能脱离规制者的控制——它可能挣脱、可能反叛、可能对抗。也恰恰在此意义上,莱斯格在耶鲁大学的另一位老师杰克·巴尔金(Jack Balkin)用他惯常的戏谑口吻调侃道:code is lawless(“代码就是无法无天”)。(17)Jack M. Balkin,The Path of Robotics Law,6 Cal. L. Rev. Circuit 45,52 (2015),pp.51-55.毕竟,人工智能时代,代码不但可以作为工具,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甚至代码也可以是本体,是世界本身,一旦失控,秩序何以实现,这是个技术实践给理论创造的新难题。
其次,四要素的互相转化和流变,是该理论需要面对的另一挑战。广义上的规范包括法律、习俗、社会规范等,而它们之间的界限是变动的,可能并存共振,我们很难严格辩认是它们中的哪一种在发挥作用。(18)韦伯专门讨论了法律与习律(konvention)、习俗(sitte)之间的流动与相互影响。参见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31-342页。在网络法情境下,《代码》所论及的法律和社会规范,随着网络的复杂化和多样化,也不断发生碰撞和交融,边界趋于模糊。甚至,四要素之间也可能互相转化。尤其是社会规范这一要素,几乎照亮了所有规制问题的死角,因为文化、宗教、意识形态甚至法律、市场、技术等要素,都可能被纳入“社会规范”。(19)有关网络规制中社会规范的讨论,参见戴昕:《重新发现社会规范:中国网络法的经济社会学视角》,载《学术月刊》2019 年第2 期,第114-123页。例如,如今耳熟能详的通知删除制度、反通知制度,可以被看作BBS(网络论坛)、网络聊天室等在早期“提醒版主删帖”和“用户投诉建议”这类社会规范上的制度化。(20)罗玲:《水木清华BBS 纠纷解决机制的变迁》,载苏力编:《法律和社会科学》第2 卷,法律出版社2007 年版,第 188-214 页。而这些具体法律规定,在互联网出现之前的传统法中,无论是侵权法的过失责任,还是财产法的知识产权保护,要么是未曾出现,要么是没有足够的条件施行。这是社会规范向法律的渗透和转化。它是法律,还是社会规范?很难说。反过来,互联网法律实践、技术设计的操守、商业习惯和礼仪,也无时无刻不在重塑网络社区的社会规范。在动态流变之中,它们到底是属于社会规范,还是属于其他要素?也很难说。这不禁让人想起马克·图施奈(Mark Tushnet)的批评:在经典社会学理论面前,所谓“新芝加哥学派”的社会规制,一是没那么“新”,二是经不起仔细推敲。(21)Mark Tushnet,“‘Everything Old Is New Again’:Early Reflections on the ‘New Chicago School’”,1998 Wis. L. Rev. 579 (1998),p.580.
莱斯格不可能不清楚四要素转化与流变的问题所在,但《代码》第一版并未做过多的阐释。当然,这一点并没有躲过批评家的眼睛,于是,在第二版增补的附录中,针对“四要素”理论的这一软肋,莱斯格引入了主客观视角加以回应与澄清。但莱斯格在这方面的论述也只是寥寥几笔,点到即止。这与其说是本书的一个遗憾,不如说是其社会规制理论本身的困境。
三、25年的变迁
《代码》的现实素材集中在世纪之交,这正好为站在25年后的我们,创造了一个绝佳的观察互联网变迁的机会。取25年前后两个时间节点进行对照,我们可以看出一条脉络:互联网由“低法治”向“法治化”的转变。
正如莱斯格在《代码》第二版前言中所提到的:
第一版诞生于一个与如今大相径庭的时代,而且,在许多方面上,它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格格不入。
莱斯格在这里想表达的是,今时不同往日,第一版成书之际,谷歌的佩齐和布林尚未从斯坦福大学退学,脸书的扎克伯格还在守候他的犹太成年礼,互联网方兴未艾,网络空间处于典型的“低法治”状态。(22)恰恰得益于低法治状态,互联网行业野蛮生长,“非法兴起”。参见胡凌:《非法兴起:理解中国互联网演进的一个视角》,载《文化纵横》2016年第5期,第120-125页。就像埃里克森描述的美国农村一样,互联网有着自身独特的社会规范体系,即便这些规范体系确有法律的一席之地,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法律与社会规范经常纠缠不清,甚至处于事实上的边缘地位。(23)Robert C. Post,“The Social Foundations of Privacy:Community and Self in the Common Law Tort”,77 Cal. L. Rev. 957,(1989),pp.974-978.
正因此,当早期互联网先驱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吹响网络无政府主义号角的时候,当时的人们丝毫不会像后人一样感到诧异:
工业世界的政府,你们这些肉体和钢铁的巨人,令人厌倦,我来自网络空间,思维的新家园。以未来的名义,我要求属于过去的你们,不要干涉我们的自由。我们不欢迎你们,我们聚集的地方,你们不享有主权。(24)参见 [美]约翰·佩里·巴洛:“网络独立宣言”,1996年,李旭、李小武译,高鸿钧校,载高鸿钧编:《清华法治论衡》(第4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09页。表达类似想法的还有另一句名言,出自与约翰·佩里·巴洛联合创办电子前线基金会的约翰·吉尔莫(John Gilmore),即“互联网将政府监控视为破坏,并绕道而行”。有关网络无政府主义的兴衰,参见Will Rodger,R.I.P Crypherpunks,Security Focus (Nov. 29,2011),https://www.securityfocus.com/news/294,最后访问时间:2023年10月1日。
当时的互联网好像武林江湖,“自己的圈子,自己人料理。江湖有江湖的正义和规矩,王法不王法,民国不民国,都无关紧要”(25)张北海:《侠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5页。。
更为重要的是,儒学在东晋的流行与复兴,绝对离不开其文化载体——儒家经传传播者与接受者对其道德伦理的发自内心的、真诚而非功利的日常切实践行,因为从某种程度上,儒学本身就是关于道德伦理的践履、一种实践的学问,否则,儒学便不可能根植于现实社会并真正使之生活化;自两汉以来,儒学尤其是儒家经传中的儒家道德伦理,一直在影响着古代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在生活日用层面上,其甚至在以某种方式参与着东晋时期人们的生存。如儒家道德伦理观念“忠”与“孝”、“友”与“悌”等,在东晋确然基于一种思想信仰或者亲情的身心需要,而内在为、践履成东晋士大夫与儒家学者的价值生命。
的确,在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加密与破解、漏洞与补丁、赏金与复仇、暴力侵入与逆向工程,全都游走在法律边缘。最典型的例证,当属早期十分流行、至今仍有影响的“黑客赏金”制度。黑客凭借技艺,发现漏洞,破解软件,侵入系统。互联网的江湖规矩是:软件开发者甘拜下风之余,对于此类“违法”行为,非但不诉诸法律,财力雄厚者甚至会重金犒赏黑客。(26)最大方的金主莫过于微软。每逢发行新系统或新软件,微软都会悬赏那些破解系统漏洞的黑客。2015年Windows 10发行之时,单单破解一个系统漏洞,赏金就高达10万美元。参见https://www.microsoft.com/en-us/msrc/bounty,最后访问时间:2023年10月1日。此外,计算机领域还有不少专门的黑客赏金平台,比如HackerOne、BugCrowd、OpenBugBounty、SynAck、YesWeHack等等。
也正是在这个江湖中,诞生出许多“惩恶扬善”的英雄骇客。亚伦·斯沃茨(Aaron Swartz)便是如此。事情的起因是学术论文网站JSTOR垄断论文版权,并高价出售。这位知识共享运动先锋少年看不惯,决意用他的黑客天才,扮一回侠盗罗宾汉。于是,斯沃茨编了一个程序,利用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园网,抓取JSTOR服务器上的海量学术论文,打算事后免费提供给广大互联网用户,造福公众。可惜,斯沃茨生不逢时。放在以往,这种破解共享行为比比皆是,网管斗不过黑客,只能认栽,极少会求助官方。可偏偏此事发生在2004年的美国,先有版权工业推动的《千禧年数字版权法案》(DMCA)力保数字版权,再有“9·11”事件发生后突击颁布的《美国爱国者法案》(USAPATRIOTAct)赋权美国特勤局调查网络犯罪。特勤局手眼通天,论文数据下载到一半,斯沃茨就被当场抓获。最终逼得斯沃茨畏罪自杀,以悲剧收场。(27)参考纪录片《互联网之子:亚伦·斯沃茨的故事》(2014)。作为斯沃茨的忘年之交,莱斯格本人亦有出镜,并在镜头前悲愤落泪。
斯沃茨的死,从侧面印证了《代码》对互联网无政府主义消亡的判断,(28)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知识界涌现出大量互联网无政府主义论断,参见 David R. Johnson &David Post,“Law and Borders-The Rise of Law in Cyberspace”,48 Stan. L. Rev. 1367 (1996),pp.1387-1391;David G. Post,“Governing Cyberspace”,43 Wayne L Rev 155 (1996),p.155;John T. Delacourt,“The International Impact of Internet Regulation”,38 Harv. Intl. L J 207 (1997),pp.207-209;Dan L. Burk,“Federalism in Cyberspace”,28 Conn. L Rev 1095 (1996),pp.1095-1097;Joel R. Reidenberg,“Governing Networks and Rule-making in Cyberspace”,45 Emory L J 911 (1996),pp.919-921。《代码》一书对互联网无政府主义作出了多处回应。是网络江湖撞到“网络法治化”这堵墙的一个注脚。当然,这并不是说莱斯格认为法治化的互联网,就一定比江湖时代的互联网更优越。作为一个背负技术浪漫情怀的老网民,莱斯格在书中体现的立场,或许更接近贵族出身的托克维尔看待美国民主的立场:既然网络法治化已无可避免,回到江湖时代已无可能,我们也只能因势利导、趋利避害。他既希望那些拥抱互联网法治的人不要把法治想得那么美好,也希望那些缅怀早期互联网无政府主义的人不要把法治想得那么糟糕。(29)Lawrence Lessig,“The Zones of Cyberspace”,48 Stan. L. Rev. 1403 (1996),p.1406.
的确,25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商业化和大众化以及网络社会多元化,线上线下的分野也更加模糊,互联网自治无以为继,国家权力应时介入。(30)Jack L. Goldsmith,“Against Cyberanarchy”,65 U. Chi. L. Rev. 1199 (1998),pp.1132-1138.议会立法、法院司法、行政执法,互联网逐步法治化。(31)吊诡的是,网络空间(cyberspace)一词本身,就源自控制论(cybernetics),似乎从诞生的那一刻开始,网络空间就带着“控制”,而非“自由”的烙印。法治化的互联网,不再是法外之地,反而成为强化控制的土壤。
在我国,第一部互联网规制专门法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颁布于1996年。其后,立法进程逐步加速,我国25年间先后出台了超过50部涉及互联网的法律和行政规章,而这还不包括地方性法规、司法解释、指导案例以及包含网络规制条款的其他部门法。互联网规制的行政和司法机关同样不断壮大,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互联网法院、国家数据局等职能部门相继设立。与此同时,互联网规制范围也急剧扩张,涵盖内容管控、消费者保护、电子商务、网络版权、平台垄断、不正当竞争等诸多问题。而这样针对某一领域,如此密集扩张的法律规制趋势,翻遍中国近现代法制史,如果称不上绝无仅有,至少也是极为罕见的。在这25年间,互联网治理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粗放到精细的过程。曾经的武林江湖、共享天堂、法外之地,几乎不复存在。如今我们所面对的,是数字监督,是智慧司法。
针对“低法治”社会,曾经我们“送法下乡”,如今我们“送法上网”。不同的是,送法下乡,从上到下,时常会有层层阻力。送法上网,则顺畅很多。新中国成立以来,电子产业高速发展,并有军民融合的客观需求,但总体而言,民用技术发展并不是时代主旋律。改革开放后,理工科背景的知识分子干部逐渐走上政治舞台,他们更熟悉技术,更拥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伴随着新自由主义推动的科技资本化、资本全球化的浪潮,信息化在神州大地铺开,在这期间,出现了互联网。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决策层的重视,以及互联网主流用户群体对法治话语的熟悉甚至迷恋,送法上网的各类条件齐备。也正因此,我国互联网法律制度的迅速崛起,甚至在个别领域(比如互联网法院、生成式人工智能规制)实现了对西方法治国家的“弯道超车”。
四、“巨吉斯之戒”的启示
莱斯格到底是一位宪法学者,权利与权力问题,是宪法学者的天然关切。
《代码》的核心问题之一是:代码究竟是赋予了个体更多自由权利,还是助长了国家或者技术巨头的权力控制?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莱斯格借用了《理想国》的一则故事——“巨吉斯之戒”。在故事里,这枚神奇的戒指赋予了牧羊人巨吉斯隐身能力,任其肆意任为,而不被人察觉。于是,借助它,一个普普通通的牧羊人,得以弑杀国王,霸占王后,篡夺王位。(第59页)《理想国》的“巨吉斯之戒”还有这么一层隐喻:拿到它,可行正义,也可行不义。柏拉图借此点明:最高明的守卫,也是最厉害的窃贼,因为两者使用同一套技艺。
莱斯格提醒那些把代码理想化的无政府主义者,代码就是网络空间的“巨吉斯之戒”,它可行正义,也可行不义。比如,代码可以化身全面监控的“黑镜”,(32)“在墙上挂着的电视,在桌面摆着的电脑,在手掌把玩的手机,这些屏幕散发着冷酷的光亮,它们就是黑镜。”参见“Charlie Brooker:the Dark Side of Our Gadget Addiction”,The Guardian,1 December 2011.成为边沁福柯式“圆形监狱”(panopticon)。这些都已不再是科幻电影的桥段,而已成为人们逐渐见怪不怪的日常,并为研究者们所关注。(33)Shoshana Zuboff,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Profile Books,2019,pp.1-5;Matthew Hindman,The Internet Trap,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8,p.176;Andrew Keane Woods,“Public Law,Private Platforms”,107 Minn. L. Rev. 1249 (2023),pp.1256-1259.而近年来,在看似风平浪静的舞台上,斯沃茨、斯诺登、阿桑奇等事件一次次揭开幕布,幕布之下,那只被曾被互联网自由卫士们寄予厚望的“巨吉斯之戒”,却屡屡化身刺破互联网自由泡沫的利器。
因此,以莱斯格为代表的第一代网络法学者,尽管有着各自的研究侧重,但他们的问题意识却集中到一点: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互联网“巨吉斯之戒”的控制权到底掌握在谁手中?(34)Jack Goldsmith and Tim Wu,Who Controls the Internet?Illusions of a Borderless Worl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Tim Wu,“When Code Isn’t Law”,89 Va. L. Rev. 679 (2003),pp.679-751.在他们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将直接决定互联网是变成自由空间,还是控制领地。
于是,一个贯穿《代码》全书担忧是:在网络空间,技术巨头对代码的控制程度更高,在某些情境下“私权力”(private power)甚至凌驾于国家的公权力。(35)Kate Klonick,“The New Governors:The People,Rules,and Processes Governing Online Speech”,131 Harv. L. Rev. 1598 (2018),pp.1662-1669.正出于这一担忧,后来莱斯格数次联合多位自由派学者发声,强调民主政府应通过法律规制技术巨头,其近年来演变出的新形态便是平台反垄断。(36)沈伟伟:《迈入“新镀金时代”:美国反垄断的三次浪潮及对中国的启示》,载《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9期,第70-73页。
《代码》的另一个关切,便是国家和技术巨头联合起来,威胁互联网自由。(第4页)具体而言,国家作为法律的控制者,技术巨头作为代码的控制者,两者合力控制网络。弗兰克·帕斯奎尔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政府和技术巨头之间,不是单纯的商业交易关系,而是存在“隐婚”(secret marriage)关系。(37)Frank Pasquale,The Black Box Societ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5,pp.49-50;Gillian E. Metzger,“Privatization As Delegation”,103 Colum. L. Rev. 1367 (2003),pp.1377-1380.抛去其中戏谑的成分,这一表述牢牢抓住二者关系的两大特点:亲密和隐蔽。恰恰是借助这种“隐婚”关系,国家得以利用技术巨头,实现网络行为监控、审查惩罚规训等常规行政执法手段难以实现的管控。而技术巨头也有机会利用旋转门、监管俘获等手段,将私人利益渗透到本应关注公共福祉、公民权益的规制政策中。这在美国,不乏先例。“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就加强了与诸多技术巨头的合作,利用彼此的数据和资源。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时,政府和技术巨头里应外合,严密监控,抵制镇压。公众一开始被蒙在鼓里,直至维基解密(WikiLeaks)爆料,方才昭示天下。(38)Partnership for Civil Justice Fund,“FBI Documents Reveal Secret Nationwide Occupy Monitoring,” (December 22,2012):http://www.justiceonline.org /commentary/fbi-files-ow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3年10月1日。 当然,维基解密也由于这类反抗给自己招来麻烦,比如美国政府就下令亚马逊切断服务器供应,并要求维萨和万事达查封其捐款通道。参见Derek E. Bambauer,“Orwell’s Armchair”,7 9 U. Chi. L. Rev. 863 (2012),pp.891-893;Yochai Benkler,“A Free Irresponsible Press:Wikileaks and the Battle over the Soul of the Networked Fourth Estate”,46 Harv. C.R.-C.L. L. Rev. 311 (2011),pp.330-351.
人们应该怎么应对?25年前成书的《代码》,给出了一个似乎自相矛盾的答案。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莱斯格对技术巨头的批判和对政府规制的期待。具体而言,莱斯格认为,美国西海岸的“code”(代码)已逐渐落入资本的控制,面对由私权力主导、不受民主制度约束的代码规制,政府应当扮演“技术哲人王”,(39)这是迪克莱恩对莱斯格所阐释的理想政府网络规制的表述,并借此回应莱斯格在《代码》最后一章“迪克莱恩没有意识到什么”的批评。参见Declan McCullagh,What Larry Didn’t Get,in Ten Years of Code,Cato Institute (May 4,2009):https://www.cato-unbound.org/2009/05/04/declan-mccullagh/what-larry-didnt-get,最后访问时间:2023年10月1日。利用东海岸的“code”(法律),捍卫网络开放和个体自由。然而,莱斯格不会否认的是,美国东海岸的“code”(法律)同样面临着资本的威胁,寻找“技术哲人王”的过程并非坦途。而莱斯格近年的研究,恰恰集中在资本对政府和国会的腐蚀中,这一研究转向,在一些人看来,已经偏离了《代码》和相关网络法议题。但换个角度看,莱斯格关注的焦点,只不过从资本对于美国西海岸的“code”(代码)控制,转向资本对东海岸的“code”(法律)腐蚀。(40)参见戴昕:《犀利还是无力?——重读〈代码2.0〉及其法律理论》,载《师大法学》2018年第1辑(总第3辑),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267页。不幸的是,莱斯格本人公共事业上的两次挫折都与此相关:一次是在著名的Eldred v. Ashcroft案中败走麦城;(41)该案中,莱斯格作为控方代理律师,力图挑战版权工业推动的1998年《索尼-柏诺版权期限延长法案》,最终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败诉。参见Eldred v. Ashcroft,537 U.S. 186 (2003)。另一次则是2016年竞选美国总统,遭到民主党内部的扼杀。莱斯格的这些颇具悲剧色彩的个人经历,在让人对其屡败屡战的精神产生敬佩之余,也不禁让人对《代码》所开出的应对之策产生怀疑:无论面对被控制的代码,还是面对(用莱斯格自己的话来说)“被腐蚀的政府”,以莱斯格为代表的自由派学者所构想的这套应对之策,是不是能既治标、又治本?这是个问题。
结 语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无法贸然断定,代码反抗权力所控制的最初梦想已成泡影,但至少,在互联网规制越来越普遍的时代,我们没有理由对此抱太高期待。莱斯格在《代码》中拉响的警报,在25年后,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更响亮。
在网络空间中,某只看不见的手,正在打造一个与网络空间诞生时完全相反的架构,这只看不见的手,由政府和商业机构共同推动!正在打造一个能够实现最佳控制、高效规制的架构。(第4页)
这是一个鸵鸟时代!我们因未知而兴奋,我们自豪地把事情交给看不见的手来处理,这只手之所以看不见,只因我们选择视而不见!(第339页)
鸵鸟时代似乎还未结束,多数人还一直把头深埋沙中;但总有人想把头抬起——在一切都太迟之前。在这个意义上,25年后的网络法学者,可以、也应当比《代码》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