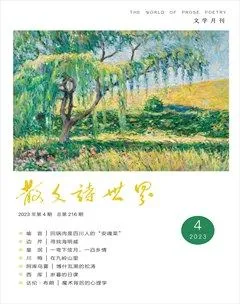永久的记忆
徐连梅
小时候,我的家乡沿南镇康庄村大多数村民房屋是土墙麦秸顶。仅有少数村民朝南的土墙外面,再砌一层青砖以防风吹日晒和雨淋。
在悠悠的岁月里,这些老屋被风雨侵蚀,变得灰黄暗淡,斑驳的土墙面密布着洞眼。低处有的砖块已松动,蚂蚁就在里面安了家,从砖缝里进进出出。油菜花开的季节里,漫天飞舞的野蜜蜂采蜜累了就飞进去小憩。这也为我和几个孩子增添了一种娱乐方式:拿个空火柴盒、一根火柴棒寻土墙洞眼掏野蜜蜂玩。
那时,不管是大路还是小道都是坑坑洼洼、曲曲弯弯的。雨过天晴的时候,鸡群从上面走过就有了一些杂乱无章的“个”字。下雨时,屋檐上晶莹的大水珠硬生生地砸下来。时间久了,下面的地面就有了一排整齐的窝窝。水滴声滴滴答答,仿佛要耐心地说服人们相信“滴水穿石”的奇迹。
大人们每天要参加集体劳动。我和几个差不多大的小孩,都被家长们带到队部大场玩耍。边上都是附近人家堆放的草垛,这几个草垛里有时也荡漾着我们的欢笑声。
有时,我们也跑到附近人家里捉迷藏。见着没关门的院落就跑进去,藏在犄角旮旯里或箩筐之中。找人的伙伴用手捂住双眼大声问:你们躲好了没有?我和几个伙伴,傻乎乎脆亮亮地回答:躲好了,你来找。
结果,马上就被找人的找着了。然后,我们再“石头、剪子、布”地比划一番,谁输了谁找人。
有时是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起先是在队部场上玩,但“小鸡”们总是往附近人家里跑,因为跑进人家里,“老鹰”无法分身,很难捉着谁。当“老鹰”久久地捉不着“小鸡”的时候,就大声抗议:应该修改游戏规则,“小鸡”不能跑进附近人家里。
儿时的桂林学校,西边两个通向操场的门洞都没按上大门。双休日,学校里不上课,我们便跑去玩打野仗。两队人马拿着铁丝做的手枪和弹弓,装上纸做的“子弹”,各占“阵地”互相射击。射中谁,谁就得躺倒装死。
有时两队相持不下,就有人绕过那些自然生长的树林,试图从后面包抄。结果对方早有人躲在必经之路,中了人家埋伏“壮烈牺牲”。有时玩得好好的,突然有人跳出来气呼呼地叫嚷:刚才,小飞被我射中了胸口,咋不“死”呢?不玩了,耍赖皮,没意思。
桂林学校院墙西边的“大操场”,大约有十亩田的范围。一年召开两次“开学典礼”和“体育运动竞赛会”。挨着院墙的中央,垒有一个宽四米、长八米的长方形“土台”,请泥匠师傅砌了三面砖墙。留作每天做早间操时,体育老师上去“领操”;一年两度的颁奖会,颁发“三好学生”。
夏夜,家里闷热难耐。孩子们都是一手摇着废纸折成的扇子一手拿筷夹菜吃饭。被骄阳晒了一天的大人们吃完晚饭,都拿一块塑料纸领着孩子来“大操场”纳凉。
立时,“大操场”犹如烧开锅的热水沸腾。人们在一起聊地里的庄稼,聊沿南镇代销店的物价,聊村子里的新鲜事,也聊道听途说的国家新闻、政策……
明亮的月光下,瞅见几位端着碗吃饭的人。碗里的饭菜冒着尖,手里像托着座小山。一边吧嗒着嘴吞咽饭菜,一边见缝插针地搭腔。饭吃完了也不回去,仿佛怕错过了精彩的情节。
有时做错事或者犯了错,妈妈就会横眉冷目地大叫要打我。趁着她四处寻棉棒时,我就转身溜出去跑到队部大场钻进麦秸草垛里。夜幕降临,我听见妈妈的呼唤声。但是,我却不答应她。听着妈妈的嗓音越来高亢和焦急,我心里还感到挺开心的。
家家戶户庭院里的瓜藤,攀着土围墙执拗地往上爬,终于和墙头上的狗尾巴草会合了,一起在风中招摇,或者窃窃私语地话家常。
它们看见过很多苍老的父母站在路口,目送拎着蛇皮袋的儿女去远方求学,或者外出打工。后来,又看见他们光光鲜鲜地回来了。它们带着上百年的记忆沉默着,见证着乡亲们的喜怒哀乐。
它们无数次听见过婴儿清脆的啼哭声,知道又一个新生命降生在带血的床头;它们也无数次看见过送葬的队伍哭哭啼啼吹吹打打非走过,知道村里又少了一个蹒跚的身影……
康庄村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景象、那些建筑物,伴随着我长大,浸染着我童年的欢乐。在无数个谋生的日子里,我不管多么忙碌都会时时想起它们。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居住条件的改善,土墙麦秸房早已不见影踪。如今,沿南镇、康庄村、桂林学校都已消失,但是却在我心里留下永久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