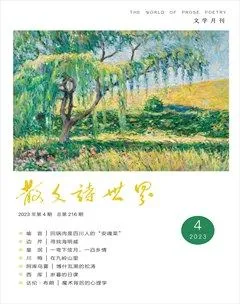绝色
2023-04-23 11:24:17金晓慧
散文诗世界 2023年4期
金晓慧
“在雪色与月色之间,你是第三种绝色。”而我认为,天地间的雪色、月色、霜色都堪称绝色。
雪色是尤其属于冬天的。在枯索难耐的凛冬,雪的降落如同时差,短暂地,让人们遗忘了寒意、委顿、黯淡,投入到盛大的洁白、简单、至纯。在所有的雪色中,我独爱西湖雪色。远处的山峦、眼前的湖水、疏朗的树枝、飘摇的孤舟,都变成了一种意境,仿佛我们都可以是张岱,看懂这世间的绝色。
秋天的月色最是皎洁,“明如镜,清如水”,可不应该是快乐的。风里,陶醉地嗅一番,稻花香翻腾,如浪,丹桂飘香,久远。远处,秋虫嘶鸣。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这样的月夜,或独酌,或漫步,或起舞弄清影,或此时此刻难为情。凝望着,直至那片柔和的光,落入眼中成为水汪汪的清泉。
月色,疑是地上霜。霜色,在冬天的清晨常见,稻草垛,菜叶子,薄薄的一层。还没枯萎的花朵,白蒙蒙的,糖霜一般包裹。與零下的空气一样,清冷,遥远,肃杀,却又带着一种转瞬的美。霜色,让人想起昨夜的月光,想起腊月已经不远。窗边结着晶莹剔透的窗花,那独有的冰晶,脆弱、易逝、朦胧,像是夜色消退的一种神迹。
猜你喜欢
江苏广播电视报·少儿文学(2024年12期)2024-06-12 01:34:59
意林(2024年6期)2024-05-11 05:07:39
ELLE世界时装之苑(2023年4期)2023-03-31 10:14:33
北广人物(2020年44期)2020-11-17 09:01:36
阅读与作文(英语高中版)(2019年10期)2019-11-28 02:35:04
艺术设计研究(2018年4期)2019-01-08 02:13:14
新闻传播(2018年4期)2018-12-07 01:09:58
散文选刊·下半月(2018年7期)2018-09-26 11:39:18
黄河之声(2016年24期)2016-04-22 02:39:47
户外探险(2014年1期)2014-02-14 09:07:38